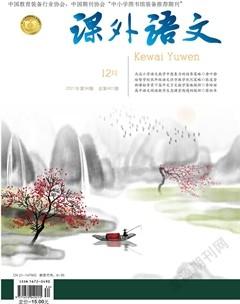論李白的干謁詩文
【摘要】唐代干謁之風盛行,干謁詩文應運而生。許多大詩人如李白、杜甫、高適都寫過干謁詩或干謁文,通過與杜甫、高適干謁詩的對比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李白干謁詩文的特點。同時,通過對李白干謁詩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唐代文人在干謁過程的復雜心態以及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的依附性。
【關鍵詞】李白;干謁詩文;心態;依附性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文章編號】1672-0490(2021)34-014-03
【本文著錄格式】張海蘊.論李白的干謁詩文——兼與杜甫、高適干謁詩之比較[J].課外語文,2021,20(34):14-16.
所謂“干謁”就是文人士子向當朝達官貴人或文壇知名人士進獻詩文,以求得他們的賞識舉薦,進而取得入仕門徑的一種手段。干謁的風氣早在漢代就出現了,一直到了唐代尤其是盛唐時期蔚為大觀。大唐王朝國力強盛,政治清明,深受儒家積極入仕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具有強烈的使命感,他們渴望從政,對生活在封建時代的讀書人來說,從政是他們實現治國平天下理想的不二途徑。唐代文人入仕的途徑很多,除科舉和入幕外,還有薦舉,一種是在參加科舉的過程中,舉子向當朝權貴或者文壇知名人士進獻詩文,求其為自己延譽,使自己名聲大振而科舉中第。趙彥衛《云麓漫鈔》卷八載:“唐之舉人,先借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后以所業投獻。……至進士則多以詩為贊,今有唐詩數百種行于世者,是也。”另一種就是在達官貴人或文壇名士的推薦下,朝廷不經常規科舉考試而直接錄用人才。于是,對仕進具有空前熱情的盛唐士人積極奔走行干謁投獻之事,干謁成為時代的風尚。如詩圣杜甫,他的家族自晉代起就世代為官,為了振興其“奉儒守官”的家世,也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得不放下讀書人的清高與傲氣,寫出許多詩文去干謁權貴。以“務功名”而著稱的詩人高適也在干謁權貴的道路上奔波忙碌。
“初盛唐文人無論是貢舉還是釋褐,調選還是隱居,只要不放棄仕進,就離不開干謁,干謁之風的盛行也就勢在必然了。”同樣,詩仙李白為實現其“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的政治理想,也是煞費心機四處干謁權貴,進而謀求仕進的通道。
李白將干謁作為入仕的捷徑,從他留下的詩文中可以明確地看到他一生中干謁過很多顯貴官僚,如益州長史蘇颋、渝州長史李邕、安州都督馬正會、長史李京之、裴長史、荊州韓長史,干謁過玉真公主和秘書監賀知章等,真正如他自己所說是“遍干諸侯”“歷抵卿相”。細讀李白的干謁詩文,通過與杜甫和高適干謁詩的對比分析,可以發現其干謁詩文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對自己的才能過分自信。李白自詡甚高,抱負極大,企圖通過干謁得到權貴的援引,由布衣而一下子位極人臣,做管仲、晏嬰一類“輔弼”大臣,從而實現自己使國家安定、使百姓各得其所的政治理想。李白對自己的才能也十分自信。首先,他經常在詩文中夸耀自己的文學才能,如在《與韓荊州書》中寫道:“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以下所引李白詩文均出自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又如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寫道:“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 又通過和馬公之語夸耀自己的文采。其次,對自己的品行也頗自負,對自己的俠義行為津津樂道。比如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一文中以散金濟人來證明自己的輕財好施,在該文中又舉了自己為友人吳指南殮葬的具體事跡,進一步證明自己的俠義之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但是,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在這些詩文里,除看到李白對自己文才德行的夸耀卻看不出李白對治國安邦的任何政治主張,也看不出他有任何施政的才能。在這些干謁詩文中,李白還以極其夸張的口吻對自己的政治理想大肆宣揚,但都顯得十分空洞。這充分說明李白是一位只有詩才而無政治素質和政治才能的文人。也正是李白的這種政治上的無知和幼稚,使他看不清當時的政治局面,進而失去了許多進身的良機。研讀李白的生平資料,我們會發現李白的干謁行為曾經取得過一定的成效。天寶元年,李白在權貴的推舉下終于得償所愿被征召入朝,供奉翰林。作為皇帝的近臣,李白以翰林為基礎一步步謀求將相高位,并非沒有可能,但李白對皇帝的征聘抱著過高的期望,認為高位不難取得,遺憾的是在唐玄宗的眼中,他只是個寫寫詩詞的御用閑人,而不是定國安邦所需要的“廊廟之器”,再加上本身性格的狂放不羈使他不能適應宮廷閑臣的生活。所以,李白在長安一年多后,便被“賜金放還”。
在這一點上,杜甫的干謁詩與李白的詩文有許多相通之處,杜甫的《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也是對自己的文才十分自負的同時,對自己的從政愿景也期望過高。但與李杜類似的詩文相比,在表現自己的才能方面,同時代的高適卻現實得多,對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負,在干謁詩中有不肯輕言的特點。但在現實中,高適的政治才能和政治識見比李白、杜甫要高明得多。安史之亂時,玄宗和肅宗對高適青眼有加,哥舒翰兵敗后,高適急忙奔赴玄宗行在,謁見玄宗,陳述潼關敗亡之勢,受到玄宗的賞識,遷官為監察御史。后永王謀反,高適向肅宗陳述永王必敗的形勢,受到肅宗的器重,被任命為淮南節度使,并參與平定永王之亂。而政治上天真的李白卻在這場斗爭中站錯了隊,竟然加入了永王的幕府,在永王兵敗被殺后,李白被流放夜郎。安史之亂讓高適平步青云,杜甫也當上了左拾遺,成為肅宗皇帝的近臣。李白卻成了階下囚,也許這是當年三人同在肅宗時料想不到的吧。對于高適,正如鄭振鐸先生說的:“他不使酒座罵,不故為隱遁自放之言,不說什么天上地下、不落邊際的話,他是一位‘人世間’的詩人。”大概就是在具備了這種才能的條件下,才使得高適被稱為有唐以來詩人中仕途通達的典型。
第二,雖然在干謁過程中,干謁者免不了請求援引的話語,但在李白的干謁詩文中,卻沒有那種近乎搖尾乞憐的句子。無論是對自己斐然文才的自信、自己俠義行為的夸耀、對被干謁者陳述自己的宏偉抱負,還是請求被干謁者予以援引,字里行間流露出作者傲人的才情和狂放的浪漫氣質,充溢著一種睥睨萬物、傲岸不羈的精神和力量,沒有搖尾乞憐之態。如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李白表明自己的心跡說:“愿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鵠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品讀詩句,令人啞然失笑,明明是自己求人援引,但語氣豪邁仿佛不是在求人,而是人在求己。結尾以馮諼自比,毫無軟語求人的模樣。又如在蜀中時,李白干謁渝州長史李邕時,由于李邕不以平等的禮節相待,甚至看不起他。為此,李白拂袖即去,臨別呈送一首《上李邕》的詩,詩中這樣寫道:“時人見我恒殊調,見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輕年少。”本來就對李邕怠慢、輕視自己的言行不滿,于是,趁“干謁”機會寫詩委婉地進行指責。
在杜甫與高適的干謁詩中卻可以看到這樣的句子。杜甫在《贈韋左丞丈濟》中向韋濟陳其仕進無門、風塵奔走的坎坷和艱辛:“江湖漂短褐,霜雪滿飛蓬。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在《奉寄河南韋尹大人》中明確地期盼韋濟的舉薦:“老驥思千里,饑鷹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在《贈翰林張四學士垍》中向這位張公子哭窮途不遇之悲:“無復隨高風,空余泣聚螢。此生任春草,垂老獨漂萍。”甚至還病急亂投醫去干謁專權亂政臭名昭著的楊國忠。高適《真定即事奉贈韋使君二十八韻》稱贊韋的政績,最后寫自己的貧困失志,并表達了希望韋濟能夠給予援引的意圖。《信安王幕府詩》最后六句訴說自己寄食權門的艱辛,請求援引。
這一點不同,是由于李白雖出身庶人,但家中資產不菲,才高而又富有,足以增其豪縱放浪。這些不是家境貧寒的杜甫和高適所能夠望其項背的,對杜甫和高適來說,入仕的艱難,生活的困頓,使他們不得不放下知識分子的尊嚴去奉承被干謁的權貴,訴說自己的艱辛以博得被干謁者的同情和援引。
從李白、杜甫、高適的干謁詩中,可以看出,有著深厚的入仕情結的盛唐文人,在投獻干謁的過程中表現出的普遍心態:
第一,志在必得的心態。盛唐的知識分子大都對自己有較高的期許,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稱“以為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 少年時期曾經苦讀詩書,有著遠大的政治抱負,早年曾經想能夠受到天子的召見和賞識,不多時即獲取公卿的高位,一飛沖天。
高適也曾經和李白一樣,不屑走考進士、明經的常道,夢想著一飛沖天。但是這個理想很快就破滅了。后去應制舉,一直到了46歲高適才艱難地登上仕途。對以才華自負的詩人來說,長期的不遇導致生活的困頓窘迫,炎涼世態帶來的情感上的抑郁,在這些干謁詩中都有所反映。《真定即事奉贈韋使君二十八韻》中把自己比作還沒有發跡時的蘇秦,在求仕的路途上奔波徘徊。后句把自己比作途窮的阮籍。《信安王幕府詩》:“曳裾誠已矣,投筆尚凄然。”訴說自己寄食權門的酸辛。
第二,逢迎吹捧的無奈。既然是求人自然免不了低三下四,從古至今沒有哪個文人是通過辱罵顯貴而取得功名的。為能夠得到對方的賞識和同情,他們通常把對方吹捧得很高。如李白在《上韓荊州書》中就借別人之口吹捧韓荊州。李白一向自詡甚高,但為了入仕,以躋身官場,不得不對那些才學一般的官僚大肆吹捧。杜甫在《奉贈太常張卿二十韻(均)》中稱贊張均的出身高貴,學問博深。高適在《留上李右相》一詩中,將以口蜜腹劍著稱的奸相李林甫吹捧得無與倫比,從中都可以看出其無可奈何的一面。
同時,在謀求入仕的過程中,知識分子對權勢的依附性充分暴露出來,“中國的知識分子似乎不是為自己而活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才是人生歸宿。只有以社會為本位,通過從政,憑借皇帝或統治階級的支持,才能實現人生理想,盡到自己的社會責任,‘達則兼濟天下’,明白地告訴士人要做官才能有所作為”。狂放一如李白,在唐代諸多詩人中,恐怕沒有誰能夠比李白更加標榜自己獨立的人格,但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負,也不得不放下清高的架子,取悅于權貴,吹捧韓荊州說“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中正一如杜甫,也不得不四處獻詩,尤其他在長安期間,寫了很多懇求權貴援引的干謁詩篇,甚至在《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中稱:“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平津這里借指楊國忠,有借助楊國忠的意思。杜甫對哥舒翰的窮兵黷武曾經大加筆伐:“慎勿學哥舒。”但他于仕進無門的窘迫困境中,已顧不得這些賢愚之辨了,在《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中,又對哥舒翰大肆吹捧:“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 同時,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士人無不視本朝為有道之邦,因而,無論是爭取金榜題名,還是探尋終南捷徑,人們對這個富有魅力的時代充滿希望,從政也成為知識分子熱烈追逐的目標。
再者,從最基本的生計上講,也注定了這種依附性。尤其是對于像杜甫和高適這種家境并不富足的士人。以高適為例,史書說他家道中落自己也不事生業,這種家貧落魄的境況在他的詩歌中也多有反映,如“兔苑為農歲不登,雁池垂釣心長苦”(《別韋參軍》)。開元十一年,他到長安初探仕途失敗而歸,客居宋州,以耕釣維持生計。“許國不成名,歸家有慚色,托身從畎畝,浪跡初自得,雨澤感天時,耕耘忘帝力”(《酬龐事十兵曹》),也是講自己親自參加農業生產勞動。
這種依附性導致了知識分子不得不放下清高的架子,取悅于權貴,從而為自己的政治理想尋找實現的道路。
參考文獻
[1]趙彥衛.云麓漫鈔[M].北京:中華書局,1985.
[2]葛曉音.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3]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 北京:中華書局,1977.
[4]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5]劉明華.杜甫研究論集[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
作者簡介:張海蘊,1983年生,河南濮陽人,碩士研究生,中教一級,研究方向為高中語文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