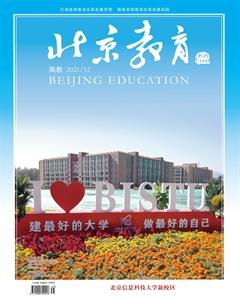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的共同體邏輯
李梟鷹
摘 要:大學與城市作為關系共同體、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而存在,此乃兩者互動發展的根本動因,也是解讀兩者互動發展的認識論邏輯。作為一個關系共同體,大學與城市互塑共長;作為一個利益共同體,大學與城市共生共贏;作為一個責任共同體,大學與城市共建共擔;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大學與城市休戚與共。
關鍵詞:大學;城市;共同體;互動發展
大學與城市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產物,是社會現代化最為重要的力量和標志。城市早生于大學,兩者在歲月的推移中奇跡般地相互走向和走進了對方,彼此不離不棄、互動發展,當中充滿了人與人之間那種“聯姻”的浪漫和神奇。這不禁引起無數人的好奇和遐想—到底是什么力量驅動大學與城市走到了一起,又是什么力量維系和增強著大學與城市之間密不可分的聯系?歷史與現實昭示:大學與城市作為一個特殊的共同體而存在,實為兩者互動發展的根本動因,也是解讀兩者互動發展的認識論邏輯。
互塑共長:大學與城市是一個關系共同體
互動發展不是無根之木或無源之水,沒有任何關聯的不同主體是不可能形成互動發展關系的。當然,這也并不意味著存在關系就一定會存在互動發展,因為還得看彼此之間存在什么性質的關系和什么程度的關系。在現實中,我們經常用“共同體”來描繪不同個體之間的密切關系。
關系共同體是最普遍和最基本的共同體,是一切共同體樣態的前提,即一切共同體首先必須是關系共同體。廣義地說,整個宇宙世界是一個關系共同體,而且是最大的關系共同體,當中又存在或圈套難以數計的子關系共同體。宇宙世界的不同主體或事物之間存在這樣或那樣的關系,這種關系的存在將整個宇宙世界聯成了一個有機整體,其中包括人類社會的各種共同體。人類社會的共同體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人們圍繞不同的對象、需要、利益、目標、愿景等形成不同的共同體,如政治共同體、經濟共同體、文化共同體、科技共同體、軍事共同體、教育共同體、衛生共同體、交通共同體、安全共同體、生命共同體等。大學與城市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特殊共同體,而大學或城市本身又是作為“共同體中的共同體”而存在,即大學或城市本身又是一個共同體。作為人類社會的兩大不同主體,大學與城市在社會發展進程中因存在共同訴求,逐步結成了與眾不同的關系共同體,即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共同體,一種“互塑共長、榮辱與共”的關系共同體,一種“超越了一般聯系意義”的關系共同體。
1.大學與城市共棲共榮。大學與城市有著特殊的地緣關系,這種關系主要表征為城市包圍著大學,而大學身處城市的“內城地帶”。當然,也有另外的情形,而且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以及不同的歷史時期還有所差異。例如:一些大學沒有圍墻,大學與城市幾乎沒有邊界、渾然一體,大學在城市中,城市在大學中,不存在所謂的中心或邊緣;一些大學一開始就建在城市周邊或遠離城市的小鎮上,然后小鎮以大學為中心逐步拓展開來,大學的發展過程伴隨著小鎮的城鎮化過程;一些大學一開始建在城市,后來為了躲避城市的喧囂,搬出大城市,來到城市的郊區或周邊的小鎮,表征為一種“反城市傾向”。歷史告訴我們,無論今天的大學身處何處,隨著時間的推移,遲早會被城市包圍,或大學本身變成“大學城”。這種特殊的地緣關系,讓大學與城市的互動發展和協同合作具有了“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地緣優勢,同時也讓大學與城市的互動發展和協同合作容易形成“向陽花木易為春”的雙贏格局。大學逃匿不了城市,城市也拒斥不了大學,大學與城市之間的“聚力”遠遠大于兩者之間的“張力”,大學與城市遲早要走到一起。
2.大學與城市互為輻射源。大學與城市是人類社會的兩座高地,系統性地匯聚了人類社會的優質資源,具有強勁的輻射勢能,因而作為一種特殊的輻射源而存在。一方面,大學因自身知識的、科技的、文化的資源優勢而成為城市的輻射源,大學的能量以大學為中心向周邊輻射,對所在城市及其區域產生有形或無形的影響。大學所在的城市是“近場”,大學的人才、科技、文化的輸出,首先惠及的是所在的城市,然后逐步拓展到城市之外的更廣大的“遠場”。另一方面,城市因自身政治的、經濟的、交通的、能源的、醫療的、衛生的資源優勢而成為大學的輻射源,城市向大學輸出物質、信息和能量,支撐和維系大學的生存與發展。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大學與城市互為動力站和供給站,大學與城市又同為人類社會的中觀“地域單元”和一個國家或區域的創新活動的孵化器,雙雙成為社會的輻射源,兩者協同合作還會產生“共振性輻射”或“輻射的共振”。
3.大學與城市互為名片和磁石。大學是城市的名片和磁石,城市也是大學的名片和磁石。擁有一流大學的城市,或坐落于著名城市的大學,都會提升各自的知名度和社會影響力,都會增強各自吸引社會資源的磁力。大學與城市要各自發揮自身的“磁場效應”,服務于彼此,為對方加持、賦值和增值。事實的確如此,一流大學容易吸引品學兼優的學生和高水平的教師,一流城市容易受到國家關注并吸引優質投資,一流大學和一流城市合體更容易使雙方成為人們朝圣的目標。中國的大學普遍依城市而立,城市常因大學而興,城市的品位和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所在城市之大學的影響,尤其是在今天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背景下,創辦和建設一流大學也已經成為我國城市的未來抉擇。
4.大學與城市是高科技與先進文化的生產者與消費者。大學與城市是當今社會的“自動化天堂”,是科技化和現代化的重鎮和中心。大學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站,大學科技成果的轉化促進社會發展。越是一流的大學科技成果轉化率越高,越是現代化的城市自動化程度越高,大學與城市的這種耦合會助推科技化和現代化。大學是創新創造的“現代工廠”,是高科技與先進文化的“代名詞”。城市是人類社會創新創造的先鋒,同時也是高科技和先進文化的主要消費者。大學與城市之間的生產與消費的矛盾運動,構成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的不竭動力。
5.大學與城市互為對方的重要器官,又同為社會有機體的重要器官。大學猶如城市的大腦,大學為城市提供意識與思想;城市猶如大學的心臟,城市為大學提供血液;城市又是人類社會的大腦和中樞神經系統,指揮著社會有機體的運行發展。大學是城市乃至社會的智庫,大學改變著城市的思維方式和神經網絡,同時通過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推動著社會的發展。腦死亡是判斷人死亡的最終標準,只要大學永葆青春,那么城市或社會的生命力就會健旺。英國牛津大學校長約翰·胡德認為,城市是全球創新網絡的中心,大學是城市的中心,創造和傳播知識、培養人才,大學被鼓勵與城市同心協力,共同致力于知識和技術轉移,以及促進城市經濟發展。[1]
共生共贏:大學與城市是一個利益共同體
任何共同體在根本上都是存在某種利益的共同體,而且互利互惠是維系共同體可持續穩定發展的最根本動因。作為一個關系共同體,大學與城市之間的關系是多元的和網絡態的,各種關系的生成、維持和廢除的背后是各種利益的博弈—各種利益的生成、維持和廢除。關系是生成的和發展的,沒有一成不變的關系,大學與城市之間的關系一直在變,因為兩者之間的利益和需要在變,利益互動是大學與城市互動的內在驅動力。利益不僅決定著大學與城市互動的方向,而且也決定著大學與城市互動的過程,還決定著大學與城市互動的結果。
1.大學與城市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兩者之間存在多種共同的利益訴求,各自又能以自身獨有的方式滿足對方的利益訴求。大學與城市之間的利益互動不是一次性博弈或一次性買賣,而是多次博弈和循環性買賣。如果只是一次博弈,出于自身利益的權衡和考慮,大學與城市皆有可能選取直接對抗或傷害對方的方式,爭取各自的最大利益,由于多次博弈的存在,合作最終會成為大學與城市實現利益最大化的共同選擇。這也解釋了為何中世紀大學在產生之初,大學與城市的關系主要是競爭性的,而隨著大學與城市的多次博弈,大學與城市越來越體現出合作為主的特征,即合作而非沖突成為主流。站在歷史的長河中看,大學與城市的利益博弈不是零和博弈,而是非零和博弈;大學與城市之間的合作是主流的,對抗是非主流的。大學與城市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也已經意識到,零和博弈只能帶來大學與城市的“共同創傷”,不利于大學與城市的長遠發展,大學與城市完全可以在不損害對方利益的基礎上,實現利益共享、精誠合作、共同發展。
大學與城市在互動發展中雙贏。當前,大學與城市在經濟、文化、科技、國際化、城市規劃等方面實現了全面合作。一方面,大學因城市提供的土地、人口、經費等得以生存和發展;另一方面,大學是創新文化的聚集地和創新人才的匯聚地,大學的創新優勢和人才優勢使大學在城市建設中至關重要,城市將因大學提供的智力、人才、科技、文化創新而快速有效地發展。大學與城市通過強強聯合、優勢互補、取長補短、特色互補等形式的互動,達成了彼此的利益訴求,滿足了彼此的現實需要。城市對大學的影響是可感的和可見的,大學對城市的貢獻也是昭然若揭的,像“信息的爆炸,通訊革命、電子全球村莊、自動化生產、電腦化管理……的存在,都是在過去一百年中發源于大學和研究所之中的”[2]。
2.大學與城市并非總是一團和氣,兩者也因利益訴求的不同而發生矛盾和沖突,但最終會在矛盾和沖突中走向合作。互動是雙向的,有互動就必然會產生這樣或那樣的沖突,這是人類社會的常態。大學與城市也存在沖突,但沖突不等于對立。沖突也不存在解不開的“死結”,沖突也不必然引起“對抗”。沖突能否形成對抗,與特定的時空條件有關,避免沖突從隱性走向顯性、從舒緩走向緊張的必要手段就是建立有效的“安全閥”制度,使對抗或對立的態度與情緒通過排解或替代等方式安全釋放出去。大學與城市的沖突是必然的,即便大學與城市之間看似的和平,或許只是沖突極其微小的極端表現而已。“在某種意義上,沖突是社會的生命之所在,進步產生于個人、階級或群體為尋求實現自己的美好理想而進行的斗爭之中。”[3]大學與城市的沖突調節著大學與城市之間的關系,有助于建立和維持雙方的身份特征和職責邊界,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大學與城市之間的矛盾運動,促使兩者走向深度互動與合作。
3.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帶來的利益,既有顯性的有形利益,也有隱性的無形利益,而前者相對后者僅是“冰山一角”。各種有形的利益是可見的、可感的,如大學與企業共辦工廠 、大學與政府共同開發項目等。同時,大學作為城市的一種文化符號,本身就代表著城市精神和文化發展的高度、品位和境界,長遠地和永恒地影響著城市的規格、檔次和質量。大學智力集中、人才薈萃、設備和科研條件優越,這些為城市文化的豐富活躍、引導提高、變革更新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大學可以提升城市的硬實力和軟實力,而在城市科技、文化、生態等軟實力方面,尤其需要大學支持。大學之于城市發展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我們不知道一個沒有大學的城市會更富有還是更貧窮,因為誰也無法預知一個沒有像大學這樣的大機構存在的社區會是怎樣的一種情況。但是,我們相信,相對來說,很少有其他方式可以像大學那樣給一個城市帶來如此大的經濟效益。”[4]事實上,大學帶給城市的絕不僅僅只是經濟效應,而且還有深遠的社會效應。
共建共擔:大學與城市是一個責任共同體
利益共享與責任共擔是一體的,這是共同體的內在邏輯。共同生活需要一種共同的秩序和擔當,這對于家庭、單位、城市和社會的成員,莫不如此。大學與城市既然是利益共同體,那么也自然是責任共同體。責任不共擔的共同體,一定不是長久的利益共同體。大學與城市利益共同體的建立和延續,必須以大學與城市作為責任共同體為前提。大學與城市既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人類文明持續發展和進步的動力,兩者在與時推移中共同承擔的社會責任也在遞增。現代大學已走出象牙塔而步入經濟社會,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英國學者埃里克·阿什比指出,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美國的貢獻就是“拆除了大學校園的圍墻”,直接讓社會服務成為大學的第三大職能。時至今日,大學擔當的社會責任還在增加,游離于城市之外、我行我素的大學極其稀少,不承擔任何社會責任的大學也極為罕見。尤其是知識經濟時代,“大學作為知識的生產者、批發商和零售商,不可避免地要向社會提供服務”[5]。
人類進化以拓展生存空間、提高生活品質、滿足發展需要為動力,只要人類還有自我進化的需求,那么建設和發展大學與城市的行動就不會停駐,大學與城市的利益互動就不會終止,大學與城市構筑的責任共同體就不會解體。大學與城市承載著人類的美好愿景,如政治的穩固、經濟的繁榮、文化的昌盛、科技的創新、教育的公平、生態的和諧等,是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的責任與使命。縱觀人類社會發展史不難發現,人類社會最優秀的思想、文化和科技等基本是在城市或大學的土壤中孕生的;甚至大學與城市的周期性興衰,與國家民族的周期性興衰存在某種歷史的一致性或相似性。譬如:歐洲的工業革命創造了一大批新型的城市和大學,而當時的歐洲正是世界經濟、文化的繁榮與富庶之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經歷了數次“城市革新運動”,大學與城市的關系得以重塑并得到快速發展,而這一時期美國作為世界霸主的地位也在不斷地得到強化和促進。
1.大學與城市是一個責任共同體,大學與城市理應對彼此負責,同時也要對人類社會的健康、持久和長遠發展擔負某種應有的使命和職責。大學是社會發展的頭腦,城市是社會發展的開路先鋒,當政府、企業、社團等機構探索人類社會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時,大學應擔當起引領者和思考者的角色。大學作為知識創新創造的主體和高層次專門人才培養的陣地,面對不確定性日益增強的社會環境,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定位,權衡自身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大學擔負著特殊的社會責任,各種社會機構的存在“有賴于那些有專門知識和特殊技能的人的存在……隨著長期貿易擴大而發展起來的商業與銀行機構都要求有一批具備新知識的人才”[6]。當今社會,大學與創新型城市要互動發展,大學推進城市的技術創新、知識創新、制度創新、服務創新、文化創新、創新環境等,與企業、科研機構、創新服務機構和政府等創新主體,形成集聚和擴散知識、技術的網絡系統,同時也從中獲得一系列有助于大學自身發展的優質資源。
2.大學與城市是人類的偉大杰作,它們因人類的需要而誕生、存在和發展。大學的發展或城市的發展,最終是為了人的發展,這是大學與城市共同的責任和使命。大學是以高深知識為基本的加工材料,以高深知識的傳播、保存、創新和理解為基本活動方式,以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為根本目的的社會機構。大學首先是人的大學,人構成大學的主體,更是受教育的對象,大學的發展歸根結底都是為了人的發展。城市也是如此,人是城市的主人,城市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發展無非是為了人發展得更好。一言以蔽之,大學與城市的聯合、互動和發展,在根本上不是為了大學或城市自身,而是為了人的發展,兩者在這一點上具有內在的一致性,這正是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的內在動因和終極目標。
休戚與共:大學與城市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宇宙是一個有機整體,“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都是互相關聯的。每一件事物影響另一件事物。不管差別多么大,不管距離多么遙遠,我們都是相互關聯這個整體的一部分……事實上,在我們中間,在其他人群和我們周圍的世界找不到真正的分隔—除非在我們的思想里制造這種分隔。”[7]廣義地看,宇宙萬物是一個相互聯系的命運共同體,有些事物之間相距遙遠,看似無關,實乃命運與共。
1.作為共棲共榮的兩大社會主體或人工生態系統,大學與城市之間存在一種協同進化和耦合并進的關系。大學或城市既在關聯中“自成系統”,又關聯中“互成系統”;大學與城市在共同體中存在、演化和發展,又在共同體中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各自作為一種“自組織”的生態系統在進化,也作為一種“他組織”的生態系統在進化,并且一方的進化部分地“依賴又促進”另一方的進化。城市的進化越完善,城市對大學的哺育能力就越強,大學的生存條件和發展平臺就越好,大學從城市中汲取的生長元素、養料養分和物質能量就越多。大學的進化越充分,大學對城市的反哺能力就越強,就越能為城市整體功能的釋放提供支撐。大學與城市相互影響的渠道是多元的,城市主要以資源與政策為核心影響大學的發展速度或規模,大學主要以人才和智力為核心影響城市的發展步伐和方向。
大學與城市作為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而存在。最初的大學盡管不是城市的“有意設計”和“刻意安排”,誕生后的大學,它的生存和發展,與城市發生著這樣或那樣的關系。大學的誕生、存在、發展、壯大和繁榮,總是關聯著特定的一所或幾座城市。大學誕生之后,城市的命運也在被不斷改寫,大學通過向城市提供源源不斷的人才和技術,增強了城市的軟實力,內在地推動了城市的發展步伐,改變了城市的發展軌道,提升了城市的發展效能。尤其是現代社會,“大學教育成為專業精英的標志。這些精英從事法律實踐、政府管理、醫療和教育,他們通常是城市各部門的行政等官員,如市長、法官,以及律師、公證人、醫生等。”[8]大學與城市在互動中不斷滿足各自的種種需要,充分彰顯了兩者時空共在性、文化共生性和資源共享性的獨特優勢。城市辦大學、新大學運動、大學城建設、地方與城市共建大學、城市與大學共建科技園區等客觀事實的存在,理性而雄辯地表明大學與城市協同發展具有特殊的意義和價值。
2.城市是大學生發和進化的土壤,大學發展強勢,很快超出了城市最初的預估和設想,若干大學不僅分享了城市,甚至占有和生成了新的城市。中世紀大學昭示:“起初,大學的教師社群是與其他行業的社團共享牛津城,但后來大學竟然逐漸獨占了這座英格蘭的重要城市”。[9]大學與城市從疏遠到親近,最后越來越難以分割,大學與城市的命運緊密地聯系到了一起。大學與城市的關系在與時俱進中改變著對方,即大學改變著城市,城市也改變著大學,而且這種改變不是一種被動的適應性改變,亦即就算是大學身處城市,但大學也不是附庸于城市的,更不是城市的“寄生蟲”,駐扎于城市的大學不是“寄人籬下”。當然,大學也不是凌駕于城市之上的,即便歷史上曾經有過大學主宰城市或控制城市的先例,像牛津大學之于牛津城等。作為大學的生存與發展的環境,城市也不是專門服務于大學的,更不是作為大學獨家的環境而存在,城市還是政府、企業、軍隊等的環境。不管怎么說,大學與城市猶如河流之兩岸,是一種對生性的存在,此岸和彼岸不能有短板,否則,洪水來臨其后果不堪設想。
城市孕生在前,大學孕生在后,而且晚生了數千年,盡管如此,這并沒有影響兩者之間的“聯姻”,而且由于命運相連、興衰與共,大學與城市之間的關系隨著歲月的推移而愈加密切甚至不可分割。今天,我們應該理性地認識到:大學或城市不是“孤生”的而是“整生”的,兩者在系統關聯中存在著、發展著和消逝著。一言以蔽之,大學與城市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兩者在互動發展中從過去走來,匯聚于現在,又奔向未來。大學在路上,城市在路上,大學與城市的互動發展也永遠在路上。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的印痕,是非線性的和螺旋式遞進的,在哺育與反哺耦合對應的螺旋發展中、在大學發展與城市發展所形成的對生互化中,呈現出復雜的超循環生發態勢。
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圍繞發展目標長遠規劃和統籌考慮。確立互動發展目標,形成互動發展理想,標識互動發展軌跡,是一種戰略性的互動發展運籌。互動發展目標可以生發互動發展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進而形成與增加互動發展的推動力和牽引力。這既可提高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的系統性,又能增強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的自覺性,還會生發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的持續性與整一性,成就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的整體生發。誠如此,大學與城市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就有了系統性的、可持續的互動發展,而不是心血來潮“唱一曲是一曲”,抑或是“腳踩西瓜皮,踩到哪滑到哪”。
結語
大學與城市的互動發展具有典型的“國別特征”,即在不同國家的大學與城市具有不同的關系或不同的互動發展模式。譬如說,美國大學與城市的互動發展具有“自生自發性”,而中國大學與城市的互動發展則帶有鮮明的“政府主導性”。當今中國,城市發展迅猛,大學發展快速,可謂是“城市越來越大,大學越來越集中”。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大學與城市的互動發展,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現代大學和現代城市之間呈現出一種“誰也難以獨處”的共生關系。事實昭示:城市是大學的基本生存環境,沒有城市的土地、人口和經費,大學難以獲得存在的資本和生長的營養;大學是鑲嵌在城市中的璀璨明珠,沒有大學的引領、謀劃和助力,城市難以彰顯其獨特的文化品位和青春活力。大學與城市的這種關系,無需我們去找尋它,只需要去揭示和發展它。
參考文獻:
[1]約翰·胡德,邵常盈.大學對城市的影響[J].復旦教育論壇,2005(6):15-16.
[2]徐輝.高等教育發展的新階段:論大學與工業的關系[M].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1.
[3]L·科賽.社會沖突的功能[M].孫立平,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6.
[4]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現代大學的社會責任[M].徐小洲,陳軍,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52.
[5]克拉克·克爾.大學的功用[M].陳學飛,等,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80.
[6]Edited by Warren Treadgold. Renaissances before the Renaissance: Cultural Revivals of Late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130.
[7]邁克爾·富蘭.變革的力量—透視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5:118.
[8]張育林.歐洲中世紀大學與城市關系研究[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6.
[9]海斯汀·拉斯達爾.中世紀的歐洲大學—博雅教育的興起(第三卷)[M].鄧磊,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1:48.
(作者單位:大連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
[責任編輯: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