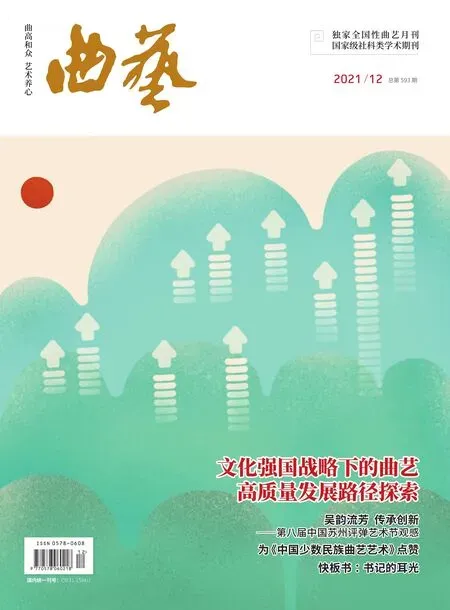推動各國民族間的說唱藝術交流
高博
《東北亞說唱藝術散論》(以下簡稱《散論》)集多位青年曲藝學者智慧于一體,活用科研領域中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實證性方法,對中、韓、日三國的說唱藝術進行了實地考察、歷史考證和深入探討,并在此基礎上加以比較,不僅能使讀者增加對不同國家說唱藝術的了解,更能讓從業者和研究者觸類旁通,為豐富自身表演形式,拓展藝術理論研究的視野和深度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正如序言所說,“科學和藝術屬于全世界,通過對東北亞說唱藝術的調研和比較,我們可以解除的不是我一個人的一些迷惑。撥開眼前的云霧看到一個真實的對方。藝術的交往、借鑒、相互學習,對于任何國家的藝術發展無疑是最具價值的。”
《散論》主要由三章組成,分別是“中國說唱藝術散論”“韓國說唱藝術散論”和“日本說唱藝術散論”。
在“中國說唱藝術散論”一章,作者首先闡述了“曲藝”一詞的由來,寫明“‘曲藝’一詞作為各種說唱藝術形式的總稱,始于1949年7月。在北京召開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期間······最后決定以‘曲’代表說唱藝術,以‘藝’代表雜技,合稱‘曲藝’,并成立了‘中華全國曲藝改進協會籌備委員會’”。接著又分析了說唱藝術區別于其他藝術形式的主要特征,即“說唱藝術的主要特征是演員以第三人稱,即‘說書人’的身份用‘說’或‘唱’等手段來向觀眾敘述故事,其中同時擁有代言的部分,以說書人與角色的轉換即跳出跳入的技法增強敘述故事的效果。”然后,作者將中國說唱藝術的表現形式具體劃分為“說的藝術”“唱的藝術”“有說有唱的藝術”“似說似唱的藝術”“邊舞邊唱的藝術”和蒙古族、朝鮮族等的“少數民族的藝術”,并對其進行了細致描述。其中,“說的藝術”包括評書、評話、相聲、故事等;“唱的藝術”有鼓書、牌子曲、琴書、時調小曲、漁鼓道情等;“有說有唱的藝術”有彈詞、西河大鼓、墜子書等,這類演出多以說為主,以唱為輔;“似說似唱的藝術”如山東快書、快板書、數來寶等;“邊舞邊唱的藝術”如二人轉、二人臺、采茶、花鼓、花燈等。而少數民族的曲種也可依據以上種類,做大致分類。但同時,作者也認為,“而選擇‘說’還是選擇‘唱’,是由受眾所決定的。說唱藝術的藝人們一直視觀眾群體為‘衣食父母’,觀眾群體的好惡不僅僅決定著藝人的選擇,更重要的是決定著藝術形式發展的方向。”這也意味著,作者認為,曲藝作為一種說唱藝術,“說”與“唱”的“成分”對比不可能始終如一。類型劃分是一種框架性描述,可便于讀者對曲藝建立更直觀的印象。
第二章“韓國說唱藝術散論”重點論說了“漫談”“才談”和“盤索里”三種說唱藝術形式及其表演特征。該章首先從介紹韓國的“傳奇手”入手,揭示了韓國說唱藝術的起源。“韓國的傳奇手又被稱作買賣講讀人、講讀師、精讀師,指那些一邊四處轉悠,一邊說書,并多少獲得一些報酬的人。”傳奇手講讀時并沒有特別的肢體動作,主要是以語言感染人,他們所用的講本被文學研究者稱為“畫本”,而藝人們自己卻稱之為“故事集”。傳奇手與故事集為韓國后世的說唱藝術奠定了基礎,之后興起的“漫談”和“才談”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深受其影響。
提起漫談,作者首先指出,“漫談是一種幽默諷刺的語言藝術”“主要反映的是現代生活和現代人的情感心理。”具體來說,漫談必須以“有趣”為前提,不僅要有美妙的詞語,也要有抓住現代人心的魅力。漫談往往以詼諧的手法諷刺社會不良現象,彰顯真善美,反映當代人的生活和心理。接著,作者又談及了報紙、唱片與廣播等媒體的出現為漫談發展所帶來的變革性影響。
才談是韓國的傳統說唱形式,類似于中國的對口相聲。在該節中,作者先是追溯了才談的起源,然后通過與其他藝術形式對比的方法,探討了才談的藝術特征,認為才談通常以巧妙的方式引人發笑,同時很重視諷刺性,但從藝術風格上講,“才談多帶些土俗純樸的味兒,而漫談則稍有些現代味兒。”
盤索里是韓國最具代表性的說唱藝術,與我國朝鮮族的盤索里系出同源。因為在“中國說唱藝術散論”中,作者對盤索里的藝術特征已經有了較為明晰的闡釋,所以在論述韓國的盤索里時,作者著重討論了它的傳承發展、音樂特征和部分著名曲目。
《散論》第三章聚焦日本說唱藝術,主要探究了落語、漫才、講談和曲唱等多種日本傳統藝能表演方式。在開篇,作者先就諸如“寄席”“釋場”“小劇場”等傳統藝能的演出場所進行了詳細介紹,而后又梳理了日本“笑的歷史”,并在此基礎上對最具日本民族特色的說唱藝術“落語”進行介紹。所謂落語,頗似我國的單口相聲。這里的“落”就是指抖包袱,落語最精彩之處即在于段子最后的“落”。表演落語節目的藝人被稱為“落語師”。演出時,落語師往往跪坐在軟墊上,依靠詼諧幽默的笑話和惟妙惟肖的表演制造笑料。在當今多元化的日本社會,落語依然保持著原汁原味且不斷發展。
與落語藝術相近的說唱表演即為“漫才”,只不過漫才通常由兩人組合演出,“一人負責擔任較嚴肅的找碴角色,也就是從對方的行為和語言中找到切入點,發出感慨或疑問,不配合對方,為上手;另一人則負責滑稽的裝傻角色,為下手。”漫才里運用的笑話大都圍繞兩人間的誤會、雙關語和諧音字展開。
“講談”是日本傳統的說唱藝術形式之一,類似于中國的評書、說書,原稱“講釋”,表演者稱為“講談師”,男女不限。講談的內容基本都是以歷史事件為主,演員需要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對復雜的內容加以解說,從而使觀眾易于接受且有深刻印象。
“曲唱”屬于含有說唱技藝的敘詠類傳統藝能,其源頭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紀的“語部”。目前,比較流行的曲唱形式包括:平曲、凈琉璃以及浪曲。平曲是日本古老的傳統藝能,始于12世紀末,以說唱《平家物語》中的辭章而得名,因使用琵琶作為樂器,所以又名平家琵琶曲。表演者身著傳統服裝,集說唱與伴奏于一身。凈琉璃形成于17世紀后半葉,是以三味線為主奏樂器的一種藝能形式。表演中,朗誦、對白與吟唱三部分穿插進行。浪曲形成于19世紀后半葉,它是由日本傳統的說經、祭文演變而來,是一種結合了說與唱的藝術,分為和著三味線伴奏的歌唱部分和道白部分。
通讀《東北亞說唱藝術散論》,筆者認為,本書具有3個突出特點。
一是放眼國際,深入比較。《散論》立足中國,放眼國際,不是只就事論事地闡述3個國家的說唱藝術,而是以文化與歷史的大視野,在找到3個國家說唱藝術異同的同時,更在探索相互學習、借鑒、吸收,最終共同發展的可能性。“日本的漫才是不是就是中國相聲?中國的曲藝和日本的一些藝能是同一藝術形式嗎?日本的漫才和韓國的漫談是否有關系?日本藝人說,我們的漫才是從中國學的,有歷史根據嗎?東北亞地區民族傳統藝術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還能生存多久?”這一系列問題,都是本書作者想要解決的。這其實是在啟示廣大曲藝工作者,討論曲藝“從何處來,現在發展如何,要往何處去”時,不應該只局限于藝術本體,而要在此基礎上結合社會學和文化學等的研究成果,做更有深度的解答。
二是主線清晰,論證充分。筆者認為,主線清晰是《散論》最值得稱道的特點。3個章節條塊清晰,之下又詳細介紹了不同時期流行于各國主要說唱曲種的起源、流布、特征和現狀等基本情況,層次清晰,內容豐富。而為了保證材料的客觀以及論據的翔實,年輕的曲藝學者“客座日本的明治大學、韓國的首爾大學;造訪蒙古國的烏蘭巴托藝術學院;走訪這幾個國家的藝人、演出場所并觀摩演出。在日本學者加藤徹夫婦,韓國首爾大學志愿者協會主席、中國留學生楊衛磊先生,蒙古族學者恩科巴雅爾、布仁白乙和蒙古國藝術家協會的藝術家們的幫助下”,歷時4年,才編成了這本書。不難看出,《散論》在組織學術材料,考究學術觀點上所下功夫之深。舉例來說,為了研究盤索里中著名曲目《沈清歌》,《散論》不但廣證博收,將該曲在不同國家由不同演唱者演唱的不同版本加以對比研究,通過比較其中的差異及其音樂的變異過程,更加全面、客觀地挖掘出盤索里的藝術特征。
三是史論結合,有敘有議。就筆者了解的情況而言,在《散論》出版之前,雖然也有部分曲藝理論界前輩學者就東亞各國的說唱藝術做過探討,出版過一些學術論著,但他們的著作傾向于對各國說唱藝術的歷史及其形式進行描寫輯錄,較少對相關文獻資料的系統整理和理論升華。《散論》則把對各國曲種的歷史考證作為依據,輔之以實地考察,然后加以深化討論,最終升華為系統理論,可謂“史論結合,有敘有議”的典范之作。
《東北亞說唱藝術散論》是在中國文學藝術基金會資助的“東北亞說唱藝術探源”課題下所完成的重要科研成果。筆者希望,未來能夠有越來越多這樣的研究課題,生發出越來越豐富的學術成果,以此促進世界各國說唱藝術的交流與發展,使說唱藝術成為不同國家、不同民族間心靈溝通的橋梁。
(責任編輯/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