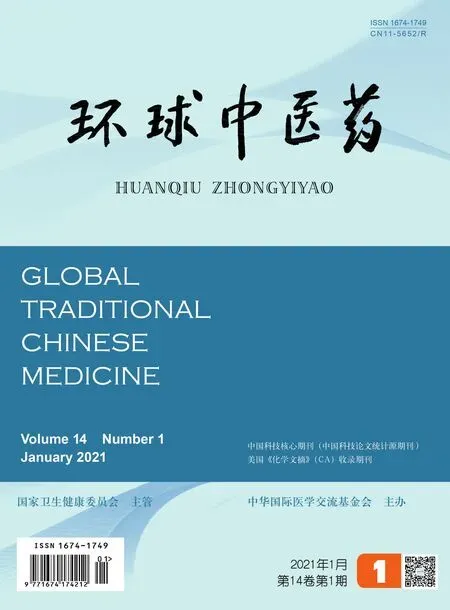中醫防疫思想之思考
王蘭 張藝璇 康雷 丁霞 姜良鐸
2019年12月以來,湖北省武漢市陸續出現了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隨著疫情的蔓延,中國其他地區及境外多個國家也相繼出現了此類病例。世界衛生組織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為“COVID-19”。中醫認為此病屬于“疫病”范疇,濕毒之疫自口鼻而入,導致肺失宣肅,阻滯氣機,從而出現發熱、咳嗽、氣促等癥狀,甚至危及生命。中醫中藥的介入使輕癥轉重癥、重癥轉危重癥的比率明顯降低[1-2]。
中華文明傳承千年,經歷過無數的災難洗禮,“瘟疫”一詞令人談之色變。瘟疫也稱疫病,最初名“役病”,傳染病在軍隊中出現并得到重視而得名,后改“疫”并沿用至今。《說文解字》解釋“疫”[3]:“疫,民皆疾也”。它本身就表現了瘟疫的特點:傳播范圍廣,傳染性強,人人易感。歷史上的每一次疫病爆發,都是一次艱苦卓絕的人類與天災人禍斗爭的紀錄片,疫病的發生與許多因素相關,政治、貿易、戰爭、環境、氣候、人口流動、饑荒等等都有可能導致一次瘟疫的流行。幾千年來的中國歷史上,經歷了幾百次大型的疫情。有研究者統計,在1911年以前,中國的瘟疫有352次之多[4-5]。在西醫傳入中國之前,全部是中醫藥防治的。中醫藥為歷次瘟疫的防控和治療發揮過重要的作用,推動了中醫學的發展,也成就了多位中醫歷史上有名的醫家。中醫藥在瘟疫的防治過程中,形成了許多有價值的防控思想與實踐方法,在現代依然有參考意義。
1 古代中醫對瘟疫防控的認識
1.1 巫術與醫術分離階段
殷商甲骨文中就出現對流行性疫病的描述,稱之為“疾年”,是對疫病的最早描述。那時的人們認為疫病是天命或者是鬼神作怪,所以人們采用祈禱、祭祀等方式應對疫病[6]。《周禮·秋官·司寇》中記述:“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凡驅蠱,則令之,比之”。這時的人們對疫病的傳染性有了一定了解,用熏法殺滅蠹蟲,控制傳染。隨著中醫學理論的逐漸完善,在現存最早的中醫理論專著《黃帝內經》中對“疫”論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的病情描述及“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的預防觀點。中醫藥素有“上醫治未病”的觀念,《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曰“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 。預防疫病就是一種“治未病”思想。春秋時期《左傳》出現“癘疾”“瘈狗”,人們通過驅逐瘋狗來預防狂犬病。至此,在防疫方面,巫術與醫術產生分歧,中醫理論逐漸成熟,中國古人對疫病的認識逐步深入,防控手段逐漸科學。
1.2 中醫對瘟疫防控的認識逐漸完善
晉朝葛洪《肘后備急方》治療狂犬病“仍殺所咬犬,取腦敷之”。這是第一個傳染病專方。唐代孫思邈將疫病患者的膿汁、血清等用于防治疣、疵,在其所著《備急千金要方》中“天地有斯瘴癘,還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備之”,書中描述了痢疾、狂犬病、麻風病、肺結核、血吸蟲病等多種傳染病[6],并提出了20余首辟疫方,藥物使用方法多樣,除佩戴香囊外,還有口服、煙熏、粉身、身掛、納鼻、浴體等,藥物劑型除蜜丸外,還有散劑、湯劑、酒劑、膏劑等。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常食大蒜預防霍亂、疫痢等傳染病,胡正心《萬病驗方》的蒸汽消毒法,張景岳《景岳全書》“福建茶餅”進行口腔消毒[7]。這一階段的中醫人,已經有了預防傳染病的多種方法,手段多樣,藥物、劑型皆多變化。
明末著名醫學家吳又可,創立“戾氣”說,著成我國第一部治療急性傳染病的專著《溫疫論》。在預防方面,他重視機體胃氣,治療方面,提出透達膜原、攻下疫邪、滋養陰液的三個重要治則,并創立治療瘟疫的重要方劑達原飲,對后世影響深遠。陳修園之辟疫之法,強調節欲、節勞、飲食有度,壯其膽氣并擬方神圣避瘟丹。清朝熊立品著《治疫全書》,提出瘟疫流行期間“四不要”:“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穢污;毋憑死者尸棺,觸其臭惡;毋食病家時菜,毋拾死人衣物” 來防止疫病傳染。
中國古人對疫病的認識由淺入深,防控方法從繁雜變得科學可取,已經初步有了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的防控思路雛形。隨著現代科技發展,醫學的進步,人們得以看到致病微生物,基因工程技術幫助人類更細致的認識病原體。
2 中醫瘟疫防控思想與方法
《黃帝內經》中就存在“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的防控思想,把握好“正”與“邪”,就把握好了疫病的防控。在疫病這個特殊疾病類別中,“避其毒氣”是十分重要的一環,能夠減少疾病的傳播范圍,有效控制疫病蔓延。另外一項重要工作是提升人體正氣,使其有能力抵御外來邪氣。所以中醫治病防病,內求正氣固攝,外求抵御邪氣。內外同防同治,達到最佳防治效果。
2.1 正氣存內
中醫學“正氣”指的是人體抵御病邪的能力,所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一個人的正氣強弱取決于許多因素,包括年齡、生活習慣、飲食、情志、房事等。《素問·上古天真論篇》中描述的“上古之人”,年可度百歲且動作不衰,究其原因是“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 。正氣的強弱在疾病的發生、發展、轉歸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傳染性疾病當中尤其如此,傳染病來勢兇猛,起病急促,歷代許多醫家認為,增強自身正氣,可以抵御疫病,不使感染,也能在患病之后更快康復,避免病情惡化,病愈后不使反復。
2.1.1 起居有常 “起居有常”指根據外界變化和自身來安排起居,符合自然規律。隨著太陽東升西落的時間規律和一年四季氣候變化來調整自己的作息,不過于放松,不過于勞累,維持一個相對平衡的狀態,這樣就能保持精神清凈,肉體充實。這種機體的平衡狀態,使得臟腑之氣充實,正氣充足。
2.1.2 食飲有節 《溫疫論》[8]中言:“昔有三人,冒霧早行,空腹者死,飲酒者病,飽腹者不病” 。在相同的致病條件下,飲食得當者,正氣充足,病邪不侵。陳修園在治療瘧疾時提出“消息飲食之法為治久瘧之正法” 。說明調整飲食不僅僅能夠抵御邪氣入侵,在已經受邪的狀態下,還可以起到治療疾病的作用。“食飲有節”包括了食和飲兩部分內容,都是維持生命不可缺少的,食飲要有節制,避免暴飲暴食、不按時就餐,食飲做到定時、定量[9];食飲節制的同時也要食飲清潔,不食用不干凈不衛生的食物。飲食入于胃,其精微之氣、濁氣都有其歸處,充實臟腑。合理的飲食使得臟腑之氣充實,精神清明,正氣充足。
2.1.3 情志舒暢 《靈樞·口問》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敗……乃失其常”。因此,保持情志清靜是保證陰陽平和的重要內在條件之一。古人們采用打坐冥想的方式來清心養神[10],避免強烈的情緒變化和長久的負面情緒對人體產生影響。調節自己的情緒就是調節陰陽平衡,用積極平和的心態面對疾病,不論是在預防還是抵御疾病都顯得至關重要。
2.2 避其毒氣
2.2.1 藥物防控 《山海經》中“其中多箴魚……食之無疫疾”的帶有一定神話色彩的說法就是一種藥物預防方法。葛洪在《肘后備急方》中提出內服、鼻吸、外敷、佩戴、熏等藥物使用方法,組成數個預防方藥。宋·龐安時《傷寒總病論·辟溫疫論》中記載的屠蘇酒,口服或倒入水中消毒皆可;辟溫粉可用于擦涂身體防疫;殺鬼丸可以點燃熏香,也可佩戴身上,必要時還可以內服[11],這些方藥用途不同,劑型多樣。《松峰說疫》為清代著名醫家劉松峰的代表作之一,書中所列的針刮、罨熨、除穢、點眼、塞鼻、涂敷、取嚏、吹藥、藥浴等外治法,在疫病預防和治療中有其特色,應用廣泛[12]。口服防疫方藥是古文獻中記錄最多的,《千金要方》避瘟方25個,《太平圣惠方》26方,其中部分方劑不僅可以用于口服,還可以燒熏、佩戴來避免邪毒入侵。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宋朝逢疫病流行、季節交換之時,由太醫局統一定方,配制成藥,分發百姓,開倉賑濟來預防疫病發生和防止疫病大范圍擴散。這樣政府支持、百姓配合的防疫方式無疑值得學習借鑒。除此之外,歷代醫家根據經驗將有效的方藥配伍修書印刷,甚至將部分方藥刻在石碑上供百姓參考;醫家們總結經驗,將有效的藥物作為君藥更大范圍的使用,使得控制效果更好。
2.2.2 隔離避邪 熊立品《治疫全書》中“四不要”很好的概括了中國古人對于隔離的措施:隔離病人,遠離其病榻;隔離污染物,不食患者家食物,遠離死人衣物;隔離死者,不碰死者棺槨。事實上,中國歷史上記載過許多疫情期間朝廷介入,強制隔離的措施:《漢書·平帝記》中記載“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晉書·王彪之傳》要求疫病傳染之時,朝臣家中有三人以上染病者,禁止上朝入宮;王士雄《霍亂論》“人煙稠密之區,疫癘流行”來告訴百姓疫癘流行時應該避免前往人群密集處,減少人員聚集。
2.2.3 消毒殺蟲 胡正心《簡易備驗方》記載蒸汽消毒法用于處理患者衣物;《肘后備急方》首先提出了空氣消毒法,將預防方劑在房屋中燒熏進行空氣消毒,也有隨身攜帶或者懸掛屋中的用法,這些空氣消毒法多用燒熏的方式來達到防疫的目的。也有藥浴消毒的方法,《本草綱目》記載“白茅香、茅香蘭草并煮湯浴,辟邪氣”。為了防止病從口入,中國古人保持井水潔凈或者在井中投放藥物來保證健康。
2.2.4 預防接種,人工免疫 唐代孫思邈做過疫病患者的膿汁、血清等用于防治疣、疵的嘗試,這有現代接種疫苗的影子。據清朝《痘科金鏡賦集解》記載,明代民間醫生將輕癥患者的痘疹接種于健康人的鼻內來獲得免疫力,名為“鼻苗”,這是最早的民間人痘接種術。這些新的治療方式的嘗試得益于中醫“以毒攻毒”的思想,這為人類免疫學的進展邁出了第一步。
3 中醫防控瘟疫思想與方法的優勢
中醫預防疫病,既包括特異性的預防,也包括非特異性的預防,同時提倡未病先防,已病防變,病后防復。
3.1 特異性預防
即針對致病因素“雜氣”的預防。如前所述,藥物防控,隔離避邪,消毒殺蟲,預防接種、人工免疫等都屬于特異性預防。此次新冠疫情防控強調避免前往人群密集處、減少人員聚集、隔離、管控、限制人口流動、戴口罩、勤洗手等,都屬于特異性預防,都來自于“避”字,即“避其毒氣”。
3.2 非特異性預防
即針對可能受感染的人群進行預防。通過提升人體抵御外邪能力預防疫病,稱之為“非特異性預防”。如前所述,“起居有常,食飲有節,情志舒暢”等,都屬于非特異性預防。另外治療基礎疾病,在辨證思想的指導下,結合發病的時節、發病的地點、癥狀的統一表現,結合患者本身特點,因人、因時、因地,進行辨體施防,辨證施防,辨病施防,也是中醫防治疫病的重要組成部分。
3.2.1 治療基礎疾病 有慢性基礎疾病的人群,由于身體機能下降和免疫力低下,導致他們面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時更為脆弱,病情進展相對更快,嚴重程度更高。所以在防控疫病時,更需注重基礎病的治療和調整,使患者屏障功能正常,內環境穩定,防止病毒的侵入。如糖尿病病人,需要嚴密監測血糖,使得血糖盡量在正常范圍,減少感染的發生,可以適當補氣養陰。慢性腎病的病人,注意維持正常腎功能狀態,避免外感,可以適當補氣固表。有慢性呼吸系統疾病的病人,在積極適應氣溫變化的同時,可以適當補肺健脾,化痰理氣。
3.2.2 辨病施防 新冠肺炎患者臨床表現濕毒明顯,如發熱,乏力,咳嗽,頭身重痛,氣短,脘痞,或有便溏,舌紅,苔白膩或黃膩,脈滑數。病性為濕毒,病位在肺在脾,易快速化熱耗氣傷陰。根據病因病機特點,預防及治療時均需體現出針對證候特點的法則和方藥。所以,在預防用藥時,會加入蒼術、藿香、等藥物化濕,雙花、連翹等清熱,黃芪或人參補氣。
3.2.3 辨證施防 中醫在治療疾病的過程中,遵從辨證論治思想。在預防疫病的過程中,也同樣重視辨證思想。綜合考慮病情本身特點,并結合發病時節、發病地點、具特征性的臨床表現來確定病因病機,針對病因病機施以預防方案。
3.2.4 辨體施防 中醫學一貫重視體質與患病的關系。如朱丹溪《格致余論》說:“況肥人多濕,瘦人多火,白者肺氣虛,黑者腎不足。形色既殊,臟腑亦異,外證雖同,治法迥別也”。葉天士在《外感濕熱篇》中說:“吾吳濕邪害人最廣,如面色白者,須到顧其陽氣……面色蒼者,須要顧其津液……”,強調了重視體質在治療中的重要性。
體質平和的人群,陰陽平和,氣血調暢。表現為平時精力充沛,面色紅潤,舌淡紅,苔薄白,脈和緩有力。此體質人群自我調節能力強,適應氣候變化能力強,臟器代償能力強。可感邪而不發病,或發病而癥狀較輕。
體質虛弱人群, 如高齡、有慢性基礎疾病、 素體虛弱者, 易感外邪,易成為重癥患者,易出現臟器衰竭。在預防疫病時,需補其不足,使陰陽平衡。
易上火體質人群,平時多表現為面紅、手足熱、 口干咽干、易便秘、小便黃、舌紅、苔黃,脈滑等。多為內有郁熱,致氣機升降失常,也易患病。在預防疫病時,可適當清其內熱,使其陰陽平和。
3.3 未病先防,已病防變,病后防復
中醫治病追求“上醫治未病,中醫治欲病,下醫治已病”,這種思維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中醫人,這是我們數千年積累的智慧。在季節交換、氣候異常、疫病流行之時,提前采取預防措施,防止疫情發生及大范圍播散;在已染時,要盡早介入,控制病情,防止惡化。在患者病情好轉之后,要轉換治療思路,關注患者本身,平衡調理患者整體狀況,防止病情反復。
4 中醫防控瘟疫思想與方法的不足
4.1 理論思想并非適用所有傳染病
吳又可將溫病與瘟疫結合,形成熱病獨特的論治體系,后世醫家們多在此基礎上發揮。但現代傳染病不僅局限于熱病,肝炎、腸道傳染病和結核性疾病等高發性傳染病尚沒有完整的理論體系,對于這類疾病,缺乏治療經驗,臨床還在積累、摸索中。
4.2 防控效果缺乏直接證據
中國文獻中所記載抗疫成功案例多為間接證據,部分防疫措施效果明顯,但缺少數據支持,也缺少中西醫對照治療結果。中國古人缺少科學技術、方法學的支持,具體藥物作用不清,藥物作用環節不明確,其藥理作用機理缺乏研究支持。這也是中醫防疫抗疫為人所詬病的地方,同時也使得中醫防疫抗疫思想傳播和實施難。
4.3 藥物使用不規范
中國古人們在入夏以后,蚊蟲繁殖致疫病四起,故端陽節用艾葉、蒼術、白芷、雄黃焚燒于室內辟疫驅邪,殺滅蛇蟲[13]。不僅民間采取有毒藥物消毒,官方醫書中也不乏運用“毒藥”的辟瘟方,如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載有赤小豆丸方(赤小豆、鬼臼、鬼箭、丹砂、雄黃)、雄黃散等方劑也用到雄黃這一味“毒藥”。考慮到雄黃含硫與砷,對人體神經、血管,肝、腎等內臟有損傷和致癌作用,現在一般并不使用。
4.4 科技限制,方法欠缺
古人常用酒消毒,但濃度不夠,多用自家釀的低濃度的米酒和果酒,這種酒在用于疫病防控中就顯得力量微弱,古人沒有意識到濃度為75%的酒精才能達到更好的消毒作用。中國古人受科技發展限制,許多防疫方法有探索,但在臨床應用效果欠明確。
5 小結
關于中醫藥預防瘟疫流行,在學術界一直存有爭議。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某個中藥針對某種病毒有抑制或殺滅作用的證據,無論是新型冠狀病毒還SARS冠狀病毒。而事實上,中醫有沒有精確打擊病毒的能力,還待進一步研究,但整體觀是中醫的長處。目前,預防瘟疫有效無效的研究著眼點多在能否抑制殺滅病毒,這當然是正確的,但并非唯一途徑。預防的目的是病毒所引起的疾病, “得病”包括了人與病毒兩方面。所以臨床上能不能防止“病”的發生應該是研究的著眼點。從這個角度看,中醫防治疫病還有許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