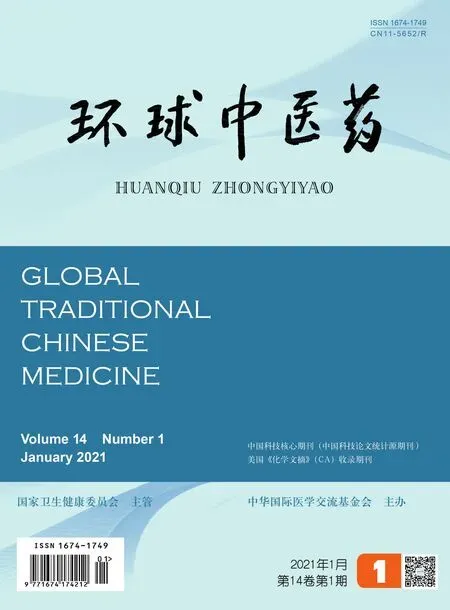淺析謝煒教授“從肝論治”癲癇經驗
劉桂余 梁小珊 楊路 王靜 伍志勇 鐘正 丁月文
癲癇是一種由多種病因引起的慢性腦部疾病,以腦神經元過度放電導致反復性、發作性和短暫性的中樞神經系統功能失常為特征[1]。癲癇屬于中醫學中“癇病”的范疇,又稱“癲癇” “癇證” “羊癇風”等,以突然意識喪失,發則仆倒,不醒人事,兩目上視,口吐涎沫,四肢抽搐,或口中怪叫,移時蘇醒,一如常人為主要臨床表現[1]。歷代醫家治療癲癇有“從痰論治” “從熱論治”等觀點,如 《丹溪心法·癇》曰:“癇證……無非痰涎壅塞, 迷閉孔竅”, “大率行痰為主火……尋痰尋火,分多分少,治之無不愈者”,《醫學正傳》曰:“癇病主乎痰, 因火動之作也。”
謝煒,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省名中醫,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中醫科主任,從事中醫醫療、教學、科研工作三十余年,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對于癲癇的治療,謝煒教授有著獨到見解,認為癲癇發生發作的關鍵因素在于肝臟生理功能失常,從肝郁、肝血、肝風及肝陽等方面立論,主張“從肝論治”癲癇,以疏肝理氣、柔肝養血、平肝安神等為基本治療大法,并創制“柴胡疏肝湯”,臨床療效顯著。現將其對“從肝論治”癲癇的經驗淺析如下。
1 從肝論治的理論依據
癲癇的發生與多種因素有關,其病因可分為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兩大類。先天因素主要為先天稟賦不足或稟賦異常,《素問·奇病論篇》曰:“人生而有病癲疾者……病名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并居,故令子發為癲疾也。”后天因素包括情志失調、飲食不節、外邪侵擾、跌仆外傷或患他病致腦竅損傷等。
在病機方面,無論是先天還是后天因素均可造成臟腑功能失調,風、火、痰、瘀閉塞清竅,積痰內伏,偶遇誘因觸動,則臟氣不平,陰陽失衡而致氣機逆亂,清竅蒙蔽,元神失控而致癲癇發作。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篇》曰:“木郁之發,太虛埃昏,云物以擾,大風乃至,屋發折木,木有變。故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脅,鬲咽不通,食飲不下,甚則耳鳴眩轉,目不識人,善暴僵仆。”這既說明了癲癇的主要癥狀,又明確指出了癲癇的病因病機在于木郁——肝之疏泄失常。肝藏魂,開竅于目,肝木郁而有變,疏泄失常,氣機逆亂,魂不附體,則出現神志喪失,包括昏迷、失神,即短暫意識喪失、無自主運動或自動癥。此段經文是“從肝論治”癲癇的重要理論依據,具有臨床治療指導意義,故謝煒教授認為,風、火、痰、瘀諸邪雖然作為癲癇發作的關鍵病理產物,但其產生引動皆本于臟腑功能失調,而肝氣失于疏泄乃是臟腑功能失調的始動因素,正如《四圣心源》曰:“風木者,五臟之賊,百病之長。”
2 謝煒教授“從肝論治”癲癇的治法精要
2.1 疏肝理氣以化痰
肝主疏泄而藏血,體陰而用陽,調和氣血,剛柔相濟。肝氣疏通,則全身氣機暢達,臟腑經絡之氣的運行通暢無阻,氣機升降出入運動協調平衡,從而使調暢精神情志、協調脾胃升降、維持血液循行及津液輸布正常等功能正常發揮。《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指出:“癲癇病,皆由驚動,使臟氣不平,而生涎,閉塞諸經, 厥而乃成。”謝煒教授認為,癲癇發作的關鍵病理產物——痰的產生與引動均主責之于肝氣疏通。
一方面,肝之疏泄功能正常,全身氣機暢達,則水液輸布氣機運行正常,則水濕無以留滯,痰飲無以凝聚;另一方面,肝氣條達,協調脾胃升降,脾胃健運,運化水濕功能正常,痰飲自除。若肝氣郁結,則水液停聚,化濕生痰,或肝氣乘脾,脾虛生痰。正如《壽世保元·癇癥》曰:“蓋癇疾之原,得之驚……則肝脾獨虛,肝虛則生風,脾虛則生痰。蓄極而通,其發也暴,故令風痰上涌而癇作矣。”痰濁上逆,閉阻腦竅,魂不附體,則發為癲癇。
《雜病源流犀燭》曰:“痰之為物,流動不測、故其為害、上至巔頂、下至涌泉,隨氣升降、周身內外皆到、五臟六腑具有。”癲癇病久不愈,必致臟腑愈虛,痰濁愈結愈深,單純地化痰不能從實質上解決問題。《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木郁達之。” 故在治法上需兩者結合,從疏肝出發進而化痰,肝氣疏通,全身氣機暢達,痰濁既無以化生,又可隨氣機運動消散。故從肝論治是治療癲癇的關鍵所在,治肝為本,治痰為標,疏肝理氣則痰化氣清。
2.2 柔肝養血以化瘀
肝主藏血,在體合筋,其華在爪。肝血除濡養肝臟本身外,還輸布至周身形體官竅,濡養四肢、筋、爪、目等,維持其正常的功能。正常生理狀態下,“氣為血之帥,血為氣之母”,血與氣,一陰一陽,相互維系,氣血平和,人體生命活動的正常進行則能得到保證。“氣有一息之不行,則血有一息之不運”,若肝氣郁結,氣不行而血不運,血不運則瘀;瘀血留滯于肝,又致肝失疏泄,肝脈阻滯,氣血運行障礙,而加重血瘀。
一方面,瘀血使得局部或全身的血液運行不暢,臟腑功能失調,氣血逆亂,或瘀阻腦竅,均可發為癲癇,正如朱丹溪曰:“氣血沖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諸病生焉。”另一方面,瘀血致肝血濡養功能減退,筋脈失養,則致肢體麻木、手足震顫、肌肉顫動、筋脈拘攣、手足瘛疭,甚至角弓反張等癲癇表現,故《素問·至真要大論篇》曰:“諸風掉眩,皆屬于肝。”
“瘀血不去,新血不生”,瘀血阻滯體內,日久不散,就會嚴重影響氣血運行,導致臟腑失于濡養,功能失常,勢必影響新血生成。肝血虧虛,血虛生風,風動痰升,又成為癲癇發作必要的環節之一。正如王清任曰:“氣有虛實,實者邪氣實,血有虧瘀,血虧必有虧血之因。” 虛實夾雜,使癲癇病情愈加復雜。《素問·至真要大論篇》曰:“疏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故治療需補血養血,又要兼以活血化瘀,調節氣血,肝中氣血陰陽平衡,剛柔相濟,則肝風無所化生,痰邪無所引動。
2.3 平肝安神以息風
肝主情志,為“風木之臟”, 風木多震動,若肝之疏泄失常,則易受驚恐所傷。肝又為剛臟,主升發,若肝之升發太過或不及,均可導致陽升風動,風動痰升或虛風內動,風動痰升,繼而痰邪壅滯經絡,閉塞清竅,氣機逆亂,元神失控,從而出現抽搐、神昏、口吐涎抹等癲癇常見癥狀。
《古今醫鑒·五癇》:“原其所由,或因七情之氣郁結,或為六淫之邪所干,或因受大驚恐,神氣不守,或自幼受驚,感觸而成,皆由痰迷心竅,如癡如愚。”《證治匯補·癇病》:“或因卒然聞驚而得,驚則神出舍空,痰涎乘間而歸之。”《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指出:“癲癇病,皆由驚動,使臟氣不平, 郁而生涎, 閉塞諸經, 厥而乃成。”由于突受驚恐,肝之疏泄失常,致臟腑氣機逆亂,痰濁隨氣上逆,蒙蔽清竅;或五志過極化火生風,或肝郁日久化熱生風,風火夾痰上犯清竅,元神失控,均可發為癲癇。小兒元氣未充,臟腑嬌嫩,神氣怯弱,更易受驚恐而發生本病。
《素問·至真要大論篇》曰:“驚者平之。” 癲癇發病多為氣血上逆且有余,其驚悸多為實,治以重鎮安神為主,養心安神為輔。而肝風內動為驚嚇誘發肝臟疏泄失常所致,神志安定,則肝風無以引動。故治療在疏肝理氣的基礎上,加以定驚安神,平肝息風。
3 謝煒教授“從肝論治”癲癇用藥特色
3.1 柴胡桂枝湯為底
在“從肝論治”癲癇的中醫理論的指導下,謝煒教授臨床擅長運用自擬方“柴胡疏肝湯”加減治療癲癇,其方合用柴胡桂枝湯、四物湯等經方,藥物組成主要包括柴胡、黃芩、半夏、桂枝、白芍、鉤藤、生龍骨、生牡蠣、黨參、炙甘草、大棗等,功擅疏肝理氣、柔肝養血、平肝息風。臨床實踐證實,本方在臨床癲癇的預防和治療中取得客觀療效[2],同時,謝煒教授也通過實驗研究得出本方能夠降低戊四氮點燃模型大鼠的癇性發作潛伏期及發作級別[3],減輕鋰—匹羅卡品誘發的難治性癲癇模型大鼠的癲癇發作[4]。
故方中以柴胡桂枝湯為底方,取其疏肝理氣之用。柴胡桂枝湯由小柴胡湯和桂枝湯各半量相合而成,兼具小柴胡湯及桂枝湯之功。《醫貫·主客辨疑》曰“小柴胡木郁達之也”,小柴胡湯和解少陽,調暢樞機,以達疏肝之功用。其主藥柴胡、黃芩均重在疏肝瀉熱。柴胡辛苦微寒,入肝膽經,芳香疏泄,其性升散輕清,正合乎肝木條達之性,善開木郁。黃芩味苦性寒,善于清泄少陽膽腑火熱。《本草綱目》曰:“柴胡行手足少陽,以黃芩為佐。” 柴、芩相配,經腑同治,一升一降,能使少陽之氣郁得達,火郁得發,郁開氣活,則樞機自利。桂枝湯乃群方之冠,后世將桂枝湯的功用總結為“外證得之,解肌和營衛,內證得之,化氣調陰陽”。方中桂枝辛溫通陽,可疏肝膽氣機,《本草綱目》曰其:“能治驚癇。” 白芍味酸,入肝經,養血柔肝,以平息肝風,且與柴胡配伍,使柴胡得芍藥而又不至升散太過而傷陰。
3.2 四物湯為輔
方中配以四物湯,取其柔肝養血,調血化瘀之功。熟地甘溫味厚,入肝腎,質潤滋膩,為滋陰補血之要藥;當歸補血和血,與熟地相伍,既增補血之力,又行營血之滯;白芍養血斂陰,柔肝緩急,與熟地、當歸相協則滋陰補血之力更著;川芎活血行氣,與當歸相協則行血之力益彰,又使諸藥補血而不滯血。
3.3 重用鉤藤、龍骨、牡蠣、
方中重用鉤藤、龍骨、牡蠣三味藥,取其平肝息風以安神之功。鉤藤質輕氣薄,味甘性涼,入肝經,有息風止痙之用,為治肝風內動,驚癇抽搐之要藥。龍骨、牡蠣均為鎮驚安神,平肝潛陽之要藥,正如陳修園曰:“龍骨能斂火安神,逐痰降逆,故為驚癇顛痙之圣藥……若與牡蠣同用,為治痰之神品。”兩者均質地重墜,二藥相合,引陽破陰,使陰陽得以相交,氣機得以暢通,從而鎮驚安神;二藥又可平肝潛陽,兼具化痰之功,使得肝陽得抑,痰邪得消。
3.4 隨證加減
癲癇的發病機制和臨床表現復雜,故謝煒教授多根據患者臨床表現在“柴胡疏肝湯”基礎上隨證加減。若患者表現脾虛濕盛,加白術、山藥等健脾益氣之品,以助化痰祛濕;若患者氣郁較重,情緒抑郁,加枳殼、香附等行氣解郁之品;若患者心神不寧、失眠多夢,則加酸棗仁等養心安神之品;若患者痰濕之邪尤甚,則加石菖蒲等開竅豁痰、醒神益智之品。
4 驗案舉隅
患者,男,26歲。2019年11月9日初診,主訴:發作性神昏、四肢抽搐20余年,加重1年。現病史:患者2歲時出現意識不清,雙目上視,牙關緊閉,四肢抽搐,持續10分鐘后自行緩解,醒后疲乏,無大小便失禁,于當地醫院就診治療,服用苯妥英鈉、丙戊酸鈉等后病情好轉,此后9年未見發作。于2004年1月上述癥狀再發持續5~10分鐘,此后偶有發作,伴有意識障礙、雙目凝視等癥狀出現,近1年發作3次,病情加重,時有情緒低落,心情抑郁,11月3日發作1次,刻診見舌質暗紅,苔薄黃,脈弦細。輔助檢查:2004年6月9日腦電圖示:小兒不正常腦電圖:(1)背景腦波較同齡組稍慢;(2)睡眠狀態偶見發作波;(3)支持癲癇診斷。2010年6月6日腦電圖示:正常腦電圖。中醫診斷:癲癇;證候診斷:肝郁化熱夾瘀型;西醫診斷:特發性全面癲癇。治法:疏肝理氣,活血化瘀。處方:柴胡疏肝湯加減,組成:柴胡 25 g、黃芩10 g、法半夏 10 g、黨參 10 g、甘草 10 g、生姜 3 片、大棗 7枚、桂枝 10 g、白芍 15 g、生龍骨先煎30 g、生牡蠣先煎30 g、鉤藤30 g、當歸10 g、酒川芎10 g、丹參20 g、石菖蒲30 g、遠志10 g,7劑,水煎服,日1劑。
2019年11月16日二診,本周未發作,服藥后無明顯不適,偶爾排便次數稍多,或稀軟。舌暗,苔薄稍黃,脈弦細。守方再服用14劑。
2019年11月30日三診,癲癇未發作,無其它不適,繼續守方再服用14劑。隨后一直隨診至今,處方隨證略作加減,病情穩定,半年以來癲癇未再發作。
按 患者發病較早,因胎元不實,元陰不足,胎中受驚,致氣血逆亂,發為癲癇。癲癇日久,情志內傷,肝郁化熱,木旺乘土,脾虛痰盛,痰熱擾神明,故反復發作。肝郁氣滯,氣血運行不暢,故見舌質暗紅。癲癇的治療宜從肝論治,治法以疏肝為主,其次以化痰、活血、清熱、息風等。疏肝以柴胡桂枝湯;因郁生瘀,加四物湯、丹參;因郁可引動肝風,肝為風木之臟,故宜投鉤藤,以鎮肝息風;因郁可出現氣上逆,夾痰上沖,宜用生龍骨、生牡蠣,鎮氣上沖;肝郁化火生痰,加石菖蒲、遠志以化痰開竅。另外,要注意患者精神方面的疏導,樹立信心,堅持長期、規律服藥,以圖根治。
5 結語
癲癇病因病機的復雜性決定了其治法的多樣性,中醫治療本病的方法眾多,謝煒教授的臨床實踐及實驗研究均證實了 “從肝論治”癲癇的獨特療效。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癲癇患者社會功能及社會適應性降低,以及患者本人對于癲癇發作的恐懼感、羞恥感等,常使其憂愁郁結、情懷怫郁,久之肝氣郁結、情志不舒,發為郁病。故癲癇治療中重視疏肝解郁的同時,從社會心理方面解決病因同樣重要。重視心理干預,加強與患者溝通,增強患者對疾病的適應性,幫助患者樹立治療信心,在癲癇治療中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