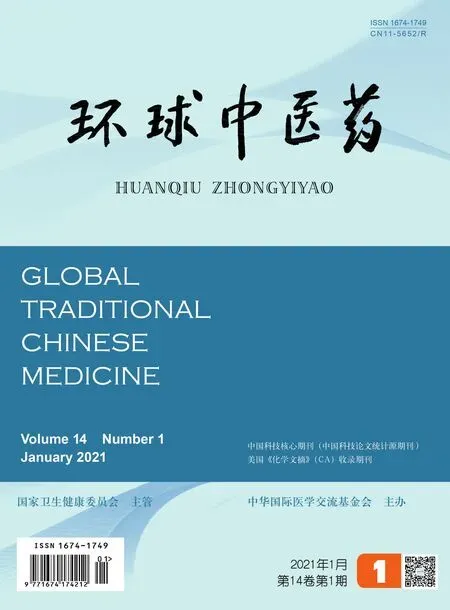郭維琴教授巧用對藥角藥辨治心系疾病
李倩倩 樊曉丹 趙一霖 胡超群 梁晉普
心系疾病是包括胸痹、心悸、心衰病等的一組疾病,與現(xiàn)代心血管疾病關系密切。現(xiàn)代醫(yī)學在心血管疾病中發(fā)揮的作用毋庸置疑,但臨床觀察發(fā)現(xiàn)冠心病支架術后、擴張型心肌病、慢性心力衰竭等部分患者在現(xiàn)代醫(yī)學基礎治療下,生活質量仍不高,常因體力耐力下降及精神壓力大而影響日常生活工作,而近年來中醫(yī)藥在此發(fā)揮的作用日益凸顯,越來越多的心血管患者尋求中醫(yī)藥的幫助。筆者查閱相關文獻,大多數(shù)現(xiàn)代醫(yī)家對心系疾病的辨治為氣血陰陽辨證結合臟腑辨證,大多強調益氣活血法在胸痹、心悸等心系疾病中應用的重要性,同中存異,不同的醫(yī)家辨治的側重有所不同,如嚴世蕓教授重視調理氣血,治心應兼調中,重視調理脾胃,調必有法[1]。張琪教授更加突出以脾胃為基礎去調節(jié)五臟,確保機體健康[2]。張永康教授認為氣虛血瘀貫穿整個病程,以益氣活血為根本[3]。而郭維琴教授強調病證結合,以益氣活血安神為治療大法,在此基礎上辨證加減,尤其重視調理脾胃而調動人體的正氣以達到扶正祛邪。
郭維琴教授為首都國醫(yī)名師,著名中醫(yī)心血管專家,從事中西醫(yī)心血管臨床工作50余年,在治療心血管疾病方面已形成自己完整而獨特的辨證治療體系,其巧用對藥、角藥治療心系疾病,療效顯著。筆者有幸跟師侍診,收獲頗多,現(xiàn)簡要總結郭教授在“益氣活血安神”及“重視脾胃”的思想指導下,治療胸痹、心悸等心系疾病的常用對藥角藥的經(jīng)驗,以饗同道。
1 益氣活血安神為治療大法
《素問·調經(jīng)論篇》言“人身所有者,氣與血爾”,《丹溪心法·六郁》云:“氣血沖和, 萬病不生, 一有拂郁, 諸病生焉。”《醫(yī)林改錯》中提出了“治病當以氣血為先”,氣血調暢對人體至關重要。《靈樞·平人絕谷》中所言“血脈和利,精神乃居”。反之若氣血失和,則神無所依附,如《素問·湯液醪醴篇》中提到的“形弊血盡”會導致“神不使”[4]。氣血是神的物質基礎,神可統(tǒng)攝氣血,形神一體,二者相輔相成。而心主血脈,心主藏神,故心與氣血神關系尤為密切,心的功能失常則易相繼引起氣血神的失調。“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郭維琴教授強調心氣的充沛,是心系所有正常生理活動的基礎,心氣虛為心系疾病發(fā)病之本[5],氣旺則血行,血瘀為心系疾病的中心病理環(huán)節(jié),氣血失調進一步會導致“神不使”表現(xiàn)為心悸、失眠、焦慮等等,神不使亦會加重氣血失調,最終致使氣血神失調。故在治療上強調益氣活血安神為治療大法。
1.1 益氣以固本
1.1.1 黨參—黃芪 黨參和黃芪皆為補氣之要藥。黨參性味甘平,專入脾肺,可健脾補肺,益氣生津。黃芪被稱為“補藥之長”,《湯液本草》中記載:“黃芪實衛(wèi)氣,是表藥;益脾胃,是中州藥;治傷寒遲脈不至,補腎元,是里藥”,其通達表里上下三焦,一藥三用,補肺氣以固肌表,健脾胃以生氣血,益腎元以壯元氣。二藥相伍,其功有四:一者,補益脾肺,脾氣旺則氣血生化得源,氣血充沛,心神得養(yǎng);二者,肺氣足則治節(jié)有權,氣血得生,宗氣得旺,胸中大氣不虛而貫心脈行血氣;三者,脾肺健則水液代謝正常,外達皮膚,下輸膀胱,不致凌心射肺;四者,黨參、黃芪甘溫益氣,氣屬陽,益氣亦可助陽,達“少火生氣”之意。現(xiàn)代藥理研究示:黨參具有強心、抗心肌缺血和抑制血小板聚集作用[6],黃芪可保護受損心肌細胞,并有強心、抑制心室重構、抑制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tǒng)激活等多種作用[7]。此藥對是郭教授最為推崇的補益心氣的藥對[5],她認為胸痹、心衰病等心系疾病多為慢病,病程較長,黨參和黃芪藥性平和,亦有“慢病緩治”之意,在用量上,黨參多在10 g ~ 30 g,黃芪多在15 g ~ 45 g,根據(jù)患者氣虛輕重而定,在改善患者疲倦乏力等癥狀方面,療效顯著。
1.1.2 太子參—黃精 《藥性切用》言太子參:“退虛火,止煩渴,所謂甘溫能除大熱也”,其藥性平和,為清補之品,益氣養(yǎng)陰兼顧。《本草備藥》記載黃精平補而潤:“甘,平。補中益氣,安五臟,益脾胃,潤心肺,填精髓,助筋骨。”甘平質潤的黃精平補肺脾腎三經(jīng)之氣。二者相須為用,長于平補氣陰,而無助熱之虞。在臨床治療中,若患者兼具烘然發(fā)熱,手足心熱,舌紅無苔或少苔,脈細數(shù)等,陰虛內熱之象明顯,屬氣陰兩虛者,郭教授通常選用太子參、黃精,并作為君藥使用,扶助正氣的同時,又可達益氣活血之效。太子參多糖具有心肌保護、降低血脂、免疫調節(jié)、保護胃腸道等作用[8]。黃精多糖具有抑制肝臟脂質氧化,調節(jié)與脂類代謝相關基因和蛋白表達的作用,進而起到防治高脂血癥的功效,還具有抗動脈粥樣硬化的作用[8-9]。
1.2 “靈活”活血以治標
1.2.1 丹參—紅花/鬼箭羽 郭士魁先生是現(xiàn)代活血化瘀學術思想的奠基人之一,善用活血化瘀法,活血化瘀治法靈活多樣,治療病證廣泛,除了前人常用之治療的癥瘕積聚、疼痛、婦科病等病癥,也常用于治療各種心病、腎病、血液病等等,“分層用藥,祛邪而不傷正”是郭老應用活血化瘀法的一個重要特點[10]。郭維琴教授繼承了其父郭士魁先生運用活血化瘀法的經(jīng)驗,根據(jù)血瘀輕重而選擇不同的藥物,丹參和紅花是其最為常用的活血藥對。李時珍言:“丹參能破宿血,補新血……其功大類當歸、地黃、芎、芍藥。”故有“丹參一味,功同四物”之說。紅花苦寒,活血化瘀兼能涼血。二者配伍相須為用,活血化瘀之力尤佳,且活血而不傷正。現(xiàn)代研究亦發(fā)現(xiàn)丹參和紅花水溶性組分配伍較單獨使用丹參或紅花更能有效發(fā)揮心肌和腦保護作用[11]。以二者為基礎制成的丹紅注射液目前亦廣泛應用于冠心病。郭教授在治療胸痹、心悸等血瘀輕癥時,常選用此兩味藥。若血瘀較重時常加用鬼箭羽組成角藥。《本經(jīng)逢原》言:“鬼箭,專散惡血。”《藥性論》又言其有“破陳血”之功,鬼箭羽的散惡血、破陳血可進一步加強丹參、紅花的活血通絡作用[12]。若血瘀重癥,則常在此三藥基礎上,加用三棱、莪術、桃仁等破血藥,短期應用、中病即止,同時佐制以扶正藥物如黨參、黃芪等。
1.2.2 莪術—昆布—浙貝母 莪術,辛散苦泄溫通,能破血祛瘀兼可行氣,為化瘀血之要藥。昆布,氣味咸寒,可軟堅散結、消痰利水。浙貝母味苦可泄,性寒清熱,清熱化痰散結。三藥相伍共奏破血消癥化痰,軟堅散結之效。蓋脈道之狹窄為痰瘀積久所致,非數(shù)日能消,必以補藥佐之,方能久服無弊,如《醫(yī)學衷中參西錄》所言:“若治瘀血積久過堅硬者,原非數(shù)劑所能愈,必以補藥佐之,方能久服無弊,或用黃芪六錢,三棱、莪術各三錢,或減黃芪三錢,加野臺參三錢,其補破之力皆可相敵,不但氣血不受傷損,瘀血之化亦較速,蓋人之氣血壯旺,愈能駕馭藥力以勝病也。” 故郭教授在臨床治療時,若痰瘀互結膠著于脈壁,阻滯脈道,形成經(jīng)現(xiàn)代檢查所能發(fā)現(xiàn)的頸動脈狹窄、冠狀動脈狹窄,常在益氣活血、行氣活血藥物的基礎上加用莪術、昆布、浙貝母以破血消痰、軟堅散結。
1.2.3 郁金—枳殼—片姜黃 推氣散出自《重訂嚴氏濟生方》,由枳殼、片姜黃、甘草、桂心四味藥組成,原方主治右脅疼痛,脹滿不食。郭教授取此方理氣活血止痛配伍之精華,將片姜黃、枳殼與郁金組成角藥,應用于心悸、胸痹等胸部悶痛明顯者,取其行氣活血止痛之意。郁金為氣中血藥,既可理氣,又可活血;片姜黃可活血化瘀;枳殼理氣寬胸,更增強其化瘀行血,通絡止痛的作用。此三味藥為郭教授運用行氣活血之法的典型角藥。郭教授認為在治療心系疾病時,除重視益氣固本、益氣活血外,亦要重視行氣活血,單純補氣藥容易導致氣機的壅滯,而加用寒溫適當?shù)男袣馑幰酝苿託庑校墒箽庾愣校袣舛粋齕10]。
1.2.4 當歸—赤芍—白芍 當歸和赤白芍皆為和血類藥物,是郭教授常用的養(yǎng)血和血的角藥。當歸和芍藥均為四物湯的主要組成藥物。后世以“血家百病此方通”評價此方,其通過地黃、芍藥的選擇及用量和配伍的變化,適用于各種血分病變。郭教授認為心系疾病為血脈之病,故此方亦適合于心系疾病。郭教授考慮到活血化瘀為祛邪之法,過度則會耗傷正氣,而心系疾病又常須長期服藥以維持病情,故對血瘀之象不明顯者,常選用兼顧養(yǎng)血、和血的藥物,此三味藥配伍,動靜相伍、補調結合,而當血瘀之象明顯時,又常與丹參、紅花、郁金等活血化瘀藥物同用,以期補血不滯血,行血不傷正。
1.2.5 丹參—赤芍—丹皮 丹參、赤芍、丹皮為清熱活血的常用角藥。三藥皆為苦微寒之品,同時兼顧活血、涼血、清熱之效,組成角藥,可協(xié)同增效,清熱涼血活血之力尤佳,且丹參、赤芍兼具養(yǎng)血之功,故三者配伍涼血無滯血之弊,活血無傷血之端。此角藥,郭教授常用于冠心病支架術后。郭教授認為氣虛血瘀、熱毒內結是冠心病支架術后再狹窄的重要病機,為預防再狹窄應盡早使用清熱涼血、解毒散結的藥物[13],常在此角藥清熱涼血活血基礎上,加用黃芪、金銀花、連翹、山慈菇、莪術等藥,益氣活血、解毒散結。
1.3 安神以助行血脈
1.3.1 靈磁石/龍眼肉/合歡皮—炒遠志—炒酸棗仁 炒酸棗仁、炒遠志、靈磁石是郭教授善用的安神的角藥。炒酸棗仁是養(yǎng)血安神藥,炒遠志是滌痰開竅、寧心安神藥,靈磁石是重鎮(zhèn)安神藥,該藥物組合分別從養(yǎng)血榮脈、祛邪寧心、潛陽安神多角度共同達到安神定悸的效果[5],神明得安則血脈和利。若心血不足之象明顯,郭教授仿歸脾湯之義,常以龍眼肉替換靈磁石旨在養(yǎng)心血安心神,多用于心律失常,無論有無失眠,取其安神定悸、助行血脈之效,亦辨證用于胸痹等心神不安者。若肝郁明顯,郭教授多以合歡皮替換靈磁石,恐質重之品折肝木條達之性。《雷公炮制藥性解》中記載合歡皮“味甘,性平,無毒,入心經(jīng)。主安五臟,利心志……令人歡樂無怒”,其善于舒肝解郁、悅心安神,可使五臟安和,心志歡悅,此三藥配伍側重于解郁安神。
1.3.2 當歸—芍藥—首烏藤 在心系疾病中眠差較為常見,不同的情形證治機理亦不同,郭教授認為睡眠早醒,關鍵在于陰血虧虛,蓋因陰血不足,陰不涵陽所致,故用藥應以養(yǎng)血安神為主,常選用當歸、芍藥、首烏藤。當歸補血活血,芍藥通常赤白芍同用,“白補赤瀉”,養(yǎng)血活血兼涼血清心。《飲片新參》言首烏藤:“苦澀微甘。養(yǎng)肝腎,止虛汗,安神催眠。”首烏藤可補養(yǎng)陰血、養(yǎng)心安神,三藥相須為用,標本兼顧,養(yǎng)血之力尤顯,陰血充沛,涵陽于內,陰陽平和,心神得安,血脈和暢。一項關于養(yǎng)心安神藥對改善冠心病穩(wěn)定型心絞痛心肌缺血的療效的臨床試驗結果表明:養(yǎng)心安神藥可有效緩解冠心病穩(wěn)定型心絞痛心肌缺血的患者心絞痛發(fā)作的癥狀,緩解情緒,提高生活質量,有助于患者康復[14]。
1.3.3 生龍骨—生牡蠣 生龍骨和生牡蠣為典型的重鎮(zhèn)安神藥對,為近現(xiàn)代醫(yī)家所常用。施今墨先生將此藥對用于失眠兼有血壓高、工作壓力大等患者, 有降血壓、治頭暈之效[15]。張錫純言:“人身陽之精為魂, 陰之精為魄。龍骨能安魂, 牡蠣能強魄。魂魄安強, 精神自足, 虛弱自愈也。是龍骨、牡蠣, 固為補魂魄精神妙藥也。龍骨入肝以安魂, 牡蠣入肺以定魄。魂魄者心神之左輔右弼也。”二者安定魂魄而安心神。郭教授認為心系疾病凡肝陽、肝火上擾心神者皆可使用,尤其對心律失常患者可安神定悸,與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之意相同。用于老年高血壓病時,遵循“介以潛之,酸以收之,厚味以填之”的原則,常配伍補益肝腎藥物如山萸肉、枸杞子,改善頭暈、失眠等癥狀療效明顯。當肝火偏旺時可配伍夏枯草、梔子等清肝瀉火藥物。
2 重視調理脾胃
“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居中央灌四傍,為氣血生化之源、氣機升降之樞,脾胃運化失職,則水濕飲痰內生,水濕飲痰是心系疾病的重要病理因素;心脾五行上為母子關系,若功能失常,或子盜母氣、或母病及子而致使心脾同病;“土生萬物”,脾胃為后天之本,一身之氣血充盛的關鍵,調理脾胃即調理氣血、調理五臟。《景岳全書·脾胃》云:“善治脾者,能調五臟,即所以治脾胃也;能治脾胃而使食進胃強,即所以安五臟也。”故郭教授辨治心系疾病在益氣活血安神為大法的基礎上,尤其重視調理脾胃而調動人體正氣以達到扶正祛邪。現(xiàn)代研究也表明,調理脾胃的相關藥物能通過促進胃腸消化吸收功能,改善能量物質代謝,通過調節(jié)脂質代謝以減輕血管壓力,通過改善脂質過氧化損傷以減輕內膜損傷、脂質沉積,從而阻止動脈粥樣硬化的產(chǎn)生[16]。
郭教授認為調理脾胃除補脾元以扶助正氣、養(yǎng)心氣外,祛濕濁以醒脾氣、通腑氣以降胃氣也很重要。在臨床中從患者的舌象、大便情況可發(fā)現(xiàn)內濕尤其多見,這與脾的生理特性相關,故有“治濕不理脾,非其治也;治脾不理濕,非其治也”之說。六腑以通為用,以降為順,《靈樞.平人絕谷》:“胃滿則腸虛,腸虛則胃滿,更虛更滿,故氣得上下,五臟安定,血脈和利,精神乃居。”故胃氣降則和,不降則滯而表現(xiàn)為腹脹滿、噯氣、便秘等。而便秘是心血管疾病的常見伴隨癥狀,當發(fā)生排便困難時,心血管病患者因腹內壓急劇增加,極易給患者的冠狀動脈血流量、心率帶來反射性影響,進而使其病情進一步惡化,更有甚者導致患者死亡。因此,預防及治療便秘對于心血管疾病患者具有重要意義[17],對于此類患者通降腑氣尤為重要(補脾元常以黨參、黃芪相伍,前已論述,不再詳述)。
2.1 祛濕濁以醒脾氣
2.1.1 藿香—佩蘭—砂仁 藿香、佩蘭伍用,出自《時病論》芳香化濁法。施今墨先生認為其芳香化濁作用強,凡濕濁困脾,脘腹脹滿,惡心嘔吐等癥皆可選用[18]。郭教授常將兩味藥與砂仁組成角藥,用于舌苔厚膩,脘腹痞悶,口中黏膩等濕濁中阻之象明顯者。《本草正義》:“藿香,清芳微溫,善理中州濕濁痰涎,為醒脾快胃,振動清陽之妙品。”其可芳香化濕,醒脾快胃。《素問·奇病論篇》:“治之以蘭,除陳氣也。”佩蘭氣味芳香可化濕辟濁醒脾,用治口甘、口中黏膩。砂仁可化濕開胃,溫脾止瀉,理氣安胎,《玉楸藥解》:“和中之品,莫妙如砂仁,沖和條達,不傷正氣,調理脾胃之上品也。”三藥均為氣味芳香之品,焦香入脾,可化濕濁、醒脾氣。一般用量為藿香、佩蘭各10 g、砂仁后下6 g。現(xiàn)代研究亦發(fā)現(xiàn)芳香化濕藥的揮發(fā)油,均具有胃腸道作用[19]。
2.1.2 郁金—石菖蒲—砂仁 郁金和石菖蒲是常用的化痰開竅的藥對,是菖蒲郁金湯的主要藥物,多用于神識昏蒙的病證,現(xiàn)代亦多用于腦血管疾病、抑郁癥、癡呆等病,主要側重于其化痰開竅醒神之用。郭教授認為郁金和石菖蒲具有芳香通竅,化痰解郁的作用,亦可開心竅,可與活血化瘀藥、化濕藥配伍,用于痰瘀互阻之冠心病、心衰病等。她常將此兩藥和砂仁組成角藥應用,三藥相伍,郁金解郁開竅,石菖蒲化痰開竅,砂仁芳香化濕,使得濕濁散、脾氣醒而清陽升、濁陰降,則神清氣明。對兼有濁陰上擾清竅而癥見頭昏沉、困倦者,療效顯著。
2.1.3 炒白術—蒼術—茯苓 炒白術、蒼術、茯苓是郭教授常用的健脾祛濕的角藥,多用于舌胖大齒痕明顯,大便溏薄等脾虛濕盛者。《本草正義》記載:“白術氣味芳香,苦甘而溫,稟坤土中和之性,故專主脾胃,以補土勝濕見長。”炒白術味甘能補,長于補氣健脾,祛濕利水。《本草備藥》言蒼術:“甘,溫,辛烈。燥胃強脾,發(fā)汗除濕,能升發(fā)胃中陽氣。”其可燥濕健脾,升發(fā)清陽。《玉楸藥解》:“白術守而不走,蒼術走而不守,故白術善補,蒼術善行……白術偏入戊土,則納粟之功多,蒼術偏入己土,則消谷之力旺,己土健則清升而濁降,戊土健則濁降而清亦升……若是脾胃雙醫(yī),則宜蒼術、白術并用。”二者相伍清升濁降,配合茯苓甘淡滲利,使?jié)裥皬男”愣狻H幫茫a脾、燥濕、滲濕,標本兼顧。郭教授在脾虛濕盛者寒熱征象不明顯時,多選用此角藥,若舌苔白膩,胃脘部怕冷等寒象明顯多加干姜、畢澄茄等溫中散寒,健運脾陽。若舌苔黃膩,大便黏膩不爽等熱象明顯多加薏苡仁、黃柏等清熱燥濕。
2.2 通腑氣以和胃氣:生白術—全瓜蔞/黨參/熟大黃/火麻仁
生白術和全瓜蔞是郭教授治療心系疾病時最常用的通降腑氣的藥對,多應用于大便干燥,排便困難者,取其潤腸通便之效。白術為甘苦溫之品,通過補氣健脾可增強胃腸道推動力。全瓜蔞甘寒質潤,可開宣肺氣,長于潤燥滑腸通便,又可化痰寬胸散結。郭教授認為二者相伍,一溫一寒,一推動一潤降,既相反相成又相輔相成,潤腸通便而無損傷脾胃之弊。臨床應用時白術常生用至30 g,全瓜蔞為15 g~30 g,全瓜蔞的用量因人而異。現(xiàn)代藥理研究表明:白術具有雙向調節(jié)胃腸道作用,可調整腸道微生物[20],可能與其通便作用相關。若排便乏力,自汗出等氣虛明顯者,多加黨參補氣通便。若內熱明顯,多加熟大黃瀉熱通便。若津液不足明顯,大便干燥尤著,多加火麻仁以增強潤腸之力。
3 小結
胸痹、心悸、心衰病等心系疾病是目前較為常見的疾病,現(xiàn)代醫(yī)家對心系疾病的治療見解各有側重不同。郭維琴教授繼承了其先父郭士魁先生的經(jīng)驗,同時結合古籍文獻及自身臨證經(jīng)驗,形成了自己辨治心系疾病的學術特點,并在此指導下將不同的藥物配伍使用,形成了諸多的對藥、角藥,臨床療效顯著。對藥、角藥往往可以取長補短、相互制約、協(xié)同增效,同時更便于后輩學習繼承經(jīng)驗及臨床使用,但需注意在辨證論治的基礎上隨證用之,以達到藥證相應、藥簡功專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