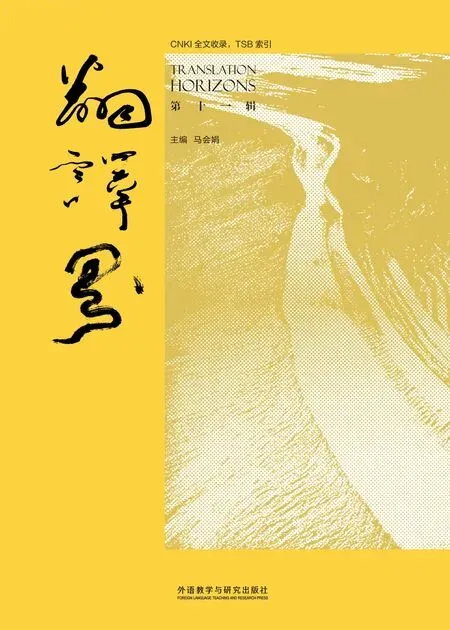霍布斯鮑姆的史學思想在中國的譯介、傳播與接受
白 倩 劉曉峰
西安外國語大學
1 引言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簡稱“霍氏”)是英國新左派的代表,被譽為“近代史大師”。《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著名編輯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稱他是一位“兼具了理性的現實感和感性的同情心”①語出《資本的年代》一書副文本,原書無頁碼。下文米利班德對霍氏的贊譽與此同理,不再重復注明。的共產主義者。霍氏出生于1917年,中學時期便開始信仰馬克思主義,并在日后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堅定擁護者。1956年后,許多與霍氏一同組成馬克思主義小組的歷史學家紛紛退出了英國共產黨,唯有他堅持馬克思主義信仰,并始終認為“馬克思的研究方法依舊是唯一能夠使我們解釋人類歷史整個過程的理論,并且為近代學術研究開創了最有成就的起點”(霍布斯鮑姆,2002:178-179)。霍氏曾親歷很多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歷史事件,因此對世界歷史有著獨到的見解,其世界史學思想也對后世有極大的借鑒意義。于他而言,“歷史學是一門以過去為基礎追求現實意義的學科,歷史研究就是力圖發現和理解過去的人類活動何以發生,它與現在有何聯系的問題”(梁民愫,2003:82)。霍氏對歷史的研究對當代社會的發展同樣具有現實意義。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他主張“自下而上”地觀察歷史,突出了人民群眾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有鑒于此,他的史學著作的目標群體也就是人民大眾。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贊譽他為“一位把歷史研究帶出象牙之塔,帶給普羅大眾的偉大學者”。這些作品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漫長的19 世紀”三部曲——《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和《帝國的年代》。1944年發表的《極端的年代》,則講述的是“短促的20 世紀”歷史,與上述三部作品合稱為“年代四部曲”。結合其他著作,霍氏為大眾講述了時間跨度達三個世紀的世界歷史。
到目前為止,國內只有2009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霍布斯鮑姆的史學研究》是唯一一部系統研究霍布斯鮑姆史學思想的著作。作者梁民愫對霍布斯鮑姆的研究較為深入,發表了多篇研究霍布斯鮑姆史學思想的學術論文。他的博士后論文《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及在中國的反響——以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史學研究為中心》集中梳理了國內外對霍氏的研究現狀,并深入分析了霍布斯鮑姆思想對中國史學的影響(梁民愫,2006)。他在《堅持唯物史觀與霍布斯鮑姆史學思想的理論反思》一文中,探討了霍布斯鮑姆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繼承與發展問題,昭示了其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地位(梁民愫,2009)。張亮(2017)對霍氏在勞工運動方面的研究進行了客觀的評價。對霍氏思想研究頗有建樹的還包括易克信、喬瑞金和姜芃等。易克信(1994)闡釋了霍布斯鮑姆對于馬克思的理解,霍氏認為不應該教條地應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喬瑞金、曹偉偉(2012)梳理了霍氏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發展所留下的寶貴財富;姜芃(2001)則探討了后現代思潮在霍氏歷史觀念上的反映。總體而言,他們的研究多集中于霍布斯鮑姆的馬克思唯物史觀、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史觀、整體主義的哲學立場、整體史觀、社會史觀、民族主義等思想。
在知網、讀秀等知識庫中輸入關鍵詞“霍布斯鮑姆”,搜索結果有近兩百條,細讀后可以發現這些研究都是關于其思想的,沒有對霍氏著作的譯介進行研究的文獻。可見學術界對霍氏思想在中國的譯介、傳播和接受研究闕如。可是,在閱讀的過程中,不難發現引用霍布斯鮑姆著作譯本的研究數目眾多,說明霍氏的思想對學術界的史學思想具有很大的建構意義。因此,研究其作品譯本及其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很有必要。
本文將從以下三個方面對霍布斯鮑姆作品在中國的譯介與傳播進行研究分析:(1)霍布斯鮑姆思想在我國的譯介概覽;(2)文本變形情況以及譯者采取的翻譯策略;(3)譯本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情況及其對國人思想的塑造。希望借此研究,可以引起中國學術界對霍布斯鮑姆史學思想在中國的譯介和影響的關注。
2 譯介概覽
霍布斯鮑姆史學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主要是通過著作翻譯來實現的。國內對于霍布斯鮑姆史學思想的譯介情況與國內翻譯環境有很大關系。受我國社會歷史文化影響,霍氏史學思想的傳播經歷了20 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前十年和2010年至今三個階段。
2.1 20 世紀90年代末
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建設成為國家發展的重心,并形成了一切服務于經濟發展的思想,這使得我國當代翻譯活動不再單純集中于文學作品的譯介上,實用文本也開始成為重要的翻譯對象。20 世紀80年代,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國民思想亟需更多的養分,促成了翻譯西方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翻譯熱”。90年代,實用類文本的翻譯更是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值此,國內出版社集中翻譯出版了霍氏的多部作品,為普通讀者提供了觸摸歷史的機會。
1997年,臺灣的麥田出版社集中出版了霍氏的“年代四部曲”,霍氏的史學思想首次出現在國人的視野中。這一時期的主要譯作有:(1)《革命的年代》麥田出版社1997 版,譯者王章輝、趙文洪①王章輝,畢業于蘇聯彼得格勒大學歷史系,現為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英國史研究會名譽會長;趙文洪,歷史系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2)《資本的年代》麥田出版社1997 版,譯者張曉華;(3)《帝國的年代》麥田出版社1997版,譯者賈士蘅②賈士蘅,中國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考古人類學碩士,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班肄業,美國威斯康星州東亞語文學博士肄業。;(4)《極端的年代》麥田出版社1997 版,譯者鄭明萱③鄭明萱,中國臺灣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廣告碩士、北伊利諾伊大學電腦碩士,業余從事翻譯,返中國臺灣后專門從事文學和文史翻譯。;(5)《民族與民族主義》麥田出版社1997 版,譯者李金梅。1999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霍氏最為著名的“年代四部曲”,自此大陸出版社開始譯介霍氏著作。同年,麥田出版社出版了《原始的叛亂》,譯者楊德睿④楊德睿,中國臺灣大學政治學碩士,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社會人類學碩士,1999年翻譯此書時博士尚未畢業,2003年獲倫敦政經學院人類學博士,2004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現任中國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這一階段,霍氏思想譯介的贊助者主要是麥田出版社和江蘇人民出版社。麥田出版社是臺灣城邦集團旗下著名的出版社,主要出版文學、歷史、人文、軍事類書籍。臺灣書市充斥著大眾文學和翻譯文學書籍,而文史哲類書籍的市場很小,這類書籍的出版往往得不到讀者的青睞。于是,麥田出版社集中翻譯霍氏著作旨在通過選擇好書以及高質量的譯文來抓住讀者的眼球,吸引讀者選讀,從而打開臺灣文史哲類書籍的市場。江蘇人民出版社為國家一級出版社,以出版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學術著作、心理學著作、歷史、人物類圖書為重點。它所推出的“鳳凰文庫”更是以出版暢銷書立足,其出版宗旨是:忠實記載當代國內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學術、思想和理論成果,促進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為推動我國先進文化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有益的學術參考和創新的思想理論資源(霍布斯鮑姆,2010)。
2.2 21 世紀前十年
21 世紀前十年,我國對霍氏著作的譯介進入發展階段,并呈逐漸繁榮之勢。中國學界通過閱讀大量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吸收和借鑒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中的觀點,拓展自己的史學視野以及研究方法,從而促使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斷創新。
2001年,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了李立瑋和谷曉靜聯合翻譯的《匪徒》。2002年麥田出版社推出了由臺大歷史所碩士黃煜文翻譯的《論歷史》。同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馬俊亞、郭英劍漢譯的大陸版《史學家:歷史神話的終結者》。2005年麥田出版社對霍氏“年代四部曲”進行再版。2006年,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及《帝國的年代》三部著作。2008年,麥田出版社又出版了周全①周全,畢業于中國臺灣大學歷史系,德國哥丁根大學西洋史碩士及博士候選人,精通六國語言,曾旅居歐美二十年,現從事寫作及歷史書籍的翻譯。譯介的《趣味橫生的時光》。同年,又推出了《霍布斯鮑姆看21 世紀》,譯者為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系畢業生吳莉君。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0、2004 以及2006年三次出版《民族與民族主義》。
這個階段的主要贊助者有中國友誼出版公司、麥田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中國友誼出版公司是專門為海外僑胞、臺灣同胞、港澳同胞提供出版服務的出版機構;上海人民出版社屬于綜合性圖書出版機構,主要出版各學科的學術專著和通俗讀物;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是一家以出版哲學、經濟、政治、歷史等社會科學領域著作的中央級出版機構,旨在出版中外學術著作和通俗讀物。
2.3 2010年至今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批判借鑒國外有益的理論,促進我國的現代化。作為英國新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霍氏的著作中有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精辟見解。因此,這一階段霍氏的史學思想在中國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傳播。
2010年,馬凡等重新翻譯了《極端的年代》一書,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年,畢業于臺灣中原大學電機系以及臺灣“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蔡宜剛首次將《非凡小人物》譯介到中國,并由麥田出版社出版。2014年,在中信出版社的贊助下,譯者林華將《斷裂的年代》翻譯為中文。林華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以及聯合國北京譯員訓練班,在聯合國總部擔任同聲傳譯譯員30 余年。在這一階段,中信出版社在傳播霍氏史學思想上功不可沒。中信出版社是中國中信集團公司旗下的出版機構,主要出版財經、人文社科、時尚、生活等領域的圖書。它分別于2014年和2017年再版了“年代四部曲”,并對《趣味橫生的時光》和《霍布斯鮑姆看21 世紀》也進行了再版。
綜上所述,除了林華,霍氏著作的譯者大都畢業于歷史系,是歷史系的專家學者。王佐良(1989:73)認為,“一個譯者只應該譯與他自己的風格相近的作品。沒有人能掌握所有的風格。通常一個譯者只適宜于譯某一類作品”。譯者有所譯,有所不譯。非文學書籍中存在大量的專業術語,這要求譯者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如果譯者為非專業人士,就很難正確理解原文,也就無法產出好的譯文。以上譯者基本上皆為專業學者型,這從源頭上保證了霍布斯鮑姆思想譯介的忠實性追求。除此之外,譯者的翻譯觀點不同,產出的譯文風格也會有所不同。在翻譯觀點上,歷來有科學與藝術之分。這幾部書譯者的身份都是歷史學者,這使得他們的翻譯觀點更側重于科學翻譯。不同于語言學習者的創造性翻譯,他們更注重對原文的忠實,追求翻譯的形似和真實。這也是由于歷史類書籍講究的便是尊重歷史事實,要避免錯譯和漏譯。加之霍氏著作譯介的贊助者偏向學術性和通俗性,他們的出版要求與譯者自身意識形態影響下的翻譯選擇恰恰相似,即既要忠實于原文所描述的歷史事實,保留霍氏思想內涵以及文化信息,又要使譯文語言符合暢銷書的定位,能吸引大眾讀者的興趣,簡明流暢,通俗易懂。譯者與出版社有著相似的“意識形態”,譯文文風自然是樸實無華、不加修飾。
3 翻譯策略
對比原文與譯文可發現,譯者在翻譯正文與副文本時采取了不同的翻譯策略。原文的副文本均被刪減,正文本則得到完整的保留。
3.1 副文本翻譯策略
《革命的年代》漢譯本刪減了原書的附錄部分,其中包括歐洲地圖、引用文獻和注釋,以及扉頁的圖例說明,并將腳注嵌入正文內。《資本的年代》漢譯本刪減了原書的圖例說明,以及附錄部分,包括地圖、引用文獻、推薦書目和注釋,也將腳注直接放到正文部分。《帝國的年代》與以上兩本相同。《極端的年代》刪掉了圖例說明、引用文獻、推薦書目和注釋,這種處理方式增強了譯文的流暢性和可讀性,充分地考慮了讀者。除此之外,江蘇出版社出版的譯本增加了作者簡介,并為《極端的年代》附上了出版說明。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革命的年代》添加了題為《和解的年代》的推薦序,中信出版社在此基礎上又為圖書增添了贊譽推薦。《趣味橫生的時光》增加了中文版序以及對此書的評介。書后附上了譯者的譯后記,正文部分附有譯注。本文提及的其余書目的漢譯本較之于原文都刪減了引用文獻和注釋,增加了作者簡介和譯注。
由此可以看出,譯著對原著正文部分的還原度較高,副文則本發生了很大變化。原著中的副文本過于繁雜,會給國內讀者造成閱讀障礙,為了減輕讀者的閱讀負擔,出版社對其進行了刪減。譯文中增加的譯注,則是以漢語為母語的譯者為了迎合漢語讀者的預設和期待而做出的改變,客觀上方便了讀者對正文的理解。贊譽推薦則是出版社將譯作定位為暢銷書而增加的內容,目的是吸引讀者的目光,屬于市場營銷手段。
3.2 正文本翻譯策略
“霍布斯鮑姆年代四部曲”是公認的“現代世界史的最佳入門讀物”,是霍布斯鮑姆耗時三十余年而作的史學巨著。考慮到篇幅長度及可操作性,本文選擇霍氏“年代四部曲”中最為著名的一部——《極端的年代》,討論其正文的翻譯策略。《極端的年代》探討了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至1991年蘇聯解體這段時期的世界歷史。作者從獨特的觀察視角講述了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對封建主義的取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一分為二的狀態以及后現代主義的發展。作者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并非完全處于相互對立的狀態,世界是一個有機而完整的整體,是社會主義促使資本主義擺脫危機,走上繁榮發展的道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都是對現代化的探索。此書在國內有兩個不同的譯本,分別由鄭明萱和馬凡等翻譯。本文根據以上三個文本建立英漢平行語料庫,對比原文和譯文的主要差異,探討譯文相對于原文的對應和對等情況,并進一步分析譯者所采用的翻譯策略和方法,總結翻譯規律。文章首先通過Tmxmall 在線對齊網站以及人工調整對語料庫進行了句子層面對齊。然后通過中國科學院ICTCLAS軟件對中文譯本進行分詞與詞性標注。最后使用了WordSmith Tools 6.0 和ROST CM6 對語料庫中的術語、詞頻、平均句長等進行檢索和統計分析。
3.2.1 詞匯層面
詞長是決定文本難易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來講,當單詞的字母超過六個,便屬于較為復雜的詞匯。詞長越長,文本難度越高,反之難度則越低。圖1 是通過WordSmith Tool 6.0 軟件統計的原文單詞長度。

圖1 《極端的年代》原文單詞長度
從圖1 可以看出,文本中2—5 個字母的單詞數量占比例最大,其中三個字母的單詞數量最多,達到1,593,十六個字母的數量最少,只有一個。并且軟件檢索結果顯示文本平均詞長為4.9。這說明文本難易適中,適合普通人閱讀。這也符合霍氏寫書的初衷,即讓普通人也有機會了解歷史。
本文通過軟件WordSmith Tool 6.0 統計出原文的關鍵詞,用軟件ROST CM6 分別統計出兩個譯本中的關鍵詞,并列出了排名前十五的高頻詞(見表1),再對比分析兩個譯文與原文的對等情況。

表1 《極端的年代》兩譯本關鍵詞統計
從表1 可以看出三個文本中“世紀”一詞的頻次最高。三者的關鍵詞都很相似,只是順序有所不同。原文中“world”一詞出現了65 次,但是兩個譯文中出現的次數卻較少。通過對比原文和譯文,可以發現兩位譯者將其中一部分譯為“國際”“各國”或省略。例如,“How did the world of the 1990s compare with the world of 1914?”(Hobsbawm,1995:12),譯者譯為“20 世紀90年代的世界,與1914年相比如何?”(霍布斯鮑姆,1999:18),省略了第二個“world”,避免了拖沓和冗余。
另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術語兩位譯者有不同的譯法。原文中“Short Twentieth Century”一詞出現12 次,鄭明萱將其譯為“短促的20 世紀”,馬凡等譯為“掐頭去尾的二十世紀”。通過閱讀原文可以清楚地發現,作者之所以將20 世紀形容為“短促的”20 世紀,是因為他將20 世紀認定為從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到1991年蘇聯解體的這段時間,短于其他史學家所認定的。與之相對應,鄭明萱將“long nineteenth century”譯為“漫長的十九世紀”,馬凡等將其譯為“連頭帶尾的十九世紀”。作者筆下的“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指的是蘇聯實行的中央指令性計劃社會主義,鄭譯為“現實中的社會主義”,馬譯為“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除此之外,鄭將“Crisis Decades”譯為“危機20年期”,將“laissez faire”譯為“自由放任”,將“megadeaths”譯為“以百萬為死亡單位計”。馬則分別譯為“危機時期”“放任政策”和“百萬人死亡”。由于歷史觀存在差異,兩位譯者有著不同的語言表達和概念選擇,但兩者都沒有損失原文的信息,對原文內容進行了較為忠實的傳達。
3.2.2 句子層面
平均句長是衡量文本難易程度的另一指標。一般來講,句子越短越容易理解,反之則越難理解。通過運行軟件,本文得到了這三個文本的平均句長。原文為29.09;鄭譯本為41.66;馬譯本為45.78。漢譯本句長高于原文句長的主要原因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采用了顯化的翻譯方法,通過增詞的方法將原文中隱含的內容明晰化或者對原文中表達不清晰的信息進行刪減。例如,“The argument of this book is organized accordingly”(Hobsbawm,1995:6)的鄭譯為“本書的論點就是基于這項原則組織而成”(霍布斯鮑姆,1999:9),將原文的“accordingly”處理為“基于這項原則”,使信息更明確;馬譯本的句長長度大于鄭譯本的句長長度,表明馬譯本的難度要略高于鄭譯本。
翻譯研究中的及物性分析有助于考察譯文忠實于原文的情況,如果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能盡量保持原文動詞的及物性過程,那么所產生的譯文就更忠實于原文。因此本文借助軟件工具統計出原文出現頻率較高的動詞(見表2),分析譯文對于這些動詞的及物性過程的處理。

表2 《極端的年代》原文高頻動詞統計
從表2 可以看出,譯文中be 動詞(is,are,was,were,been)使用頻次較高,屬于包孕型關系過程。本文選取了部分例句用以分析。
原文:[I]t is not easy to grasp the extent of the, unfortunately accelerating. (Hobsbawm, 1995:13)
譯文:我們很難領會自己這種每況愈下的嚴重程度。(霍布斯鮑姆,1999:20)
原文:Humanity was far better educated than in 1914. (Hobsbawm, 1995:12)
譯文:至于新時代人類的教育程度,顯然也比1914年時高出許多。(霍布斯鮑姆,1999:18)
以上關系過程表現的形式主要是be+形容詞,表示的是某物具有某性質,漢譯一般譯為“……是……”。譯者在翻譯時都采用了意譯的方法省略了“是”,但是沒有改變屬有某性質的關系過程。
本文選取了體現屬有型關系過程的動詞(have,has,had)在譯文的譯法。
原文:[O]nly governments and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s still have, or pretend to have, much confidence in it. (Hobsbawm, 1995: 5-6)
譯文:只剩下政府及經濟研究機構還對它們存有幾分信心——也許。(霍布斯鮑姆,1999:8)
原文:But not only one old historian has the past as part of his permanent present. (Hobsbawm, 1995: 4)
譯文:可是擁有這一段成為今生永不可分離的過去的人們,并不僅限于這位執筆作書的老邁史者。(霍布斯鮑姆,1999:6)
屬有型關系過程主要形式是“名詞+have+名詞”,漢譯時一般譯為“……有……”,譯者將“have confidence”譯為“存有信心”,將“has the past”譯為“擁有這段過去”,原文過程類型在譯文中都沒有發生變化。
動詞“made”出現了17 次,體現的是物質過程。
原文:President Mitterrand of France... made a sudden appearance in Sarajevo. (Hobsbawm, 1995:2)
譯文:法國總統密特朗……突然造訪戰火中的薩拉熱窩。(霍布斯鮑姆,1999:3)
原文:It was the Great Slump of the 1930s that made it look as though it was so,…which made the USSR into the indispensable instrument of Hitler’s defeat. (Hobsbawm, 1995:8)
譯文:然而,發生于30年代的大蕭條,……使得它看起來似乎確有取而代之的可能,……也令蘇聯成為擊敗希特勒不可或缺的一環。(霍布斯鮑姆,1999:12)
從以上句子中可以看出,原文中made 的用法主要有兩種,一是“made+名詞”,譯者將“made a sudden appearance”譯為“突然造訪”,這里“造訪”依然是動詞加名詞的形式,保留了原文的物質過程。二是“made+形容詞性短語/復合賓語”,表示“使……某物……;使……成為……”,“made it(possible)”譯者譯為“使它……可能”,對“made the USSR”譯者譯為“令蘇聯成為……”,翻譯時沒有進行詞性的變化,保留了原文的過程類型。
可見,在意識形態的影響下,兩個譯本在詞匯與句子層面均存在差異,但兩者都對原文信息還原度較高,忠實地傳達了原文作者的史學思想,追求忠實是這些學者型譯者的主要翻譯策略。忠實的譯文有助于國內學者借鑒霍氏的社會史學思想,豐富了國內學界對社會史的概念與范疇以及理論與方法等基本問題的討論,也讓讀者了解了作者關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如何相互聯系的觀點。另外,與馬譯相比,鄭譯出版的時間更早,難度也較小。在知網上搜索關鍵詞“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可發現學界研究此書時參考的譯本均為鄭譯,這表明鄭譯比馬譯更為經典,在國內的接受度也更高。
4 傳播與接受
要考察霍氏著作在我國知識界的接受程度,對其譯著的館藏、引用及評價情況的分析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環節。本節將收集并分析以上數據,據此考量霍氏思想對國人史學思想的建構程度,并指出在傳播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4.1 學界接受情況
本文通過在讀秀知識庫里輸入書名,搜索每部著作的館藏情況和被引次數,搜索結果于下文表格中列出(見表3)。

表3 霍氏著作譯本在國內的館藏情況及被引次數

續表
通過分析以上數據,可以看出霍氏的史學著作在國內的館藏數量很大,但引用率相對還較低。這些譯著為國內學者研究霍氏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提供了重要的中文材料。
此外,國內重要期刊上發表了大量關于霍布斯鮑姆史學思想的研究成果。在讀秀上搜索“霍布斯鮑姆”,發現與之相關的知識共有5,192 條、相關期刊357 篇、出版在報紙上的文章97 篇、學位論文34 篇、會議論文8篇以及書籍2 本。然后再搜索國內研究霍氏思想的兩本書籍,得到如下結果:梁民愫所寫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霍布斯鮑姆的史學研究》一書收藏館有307 個,被引用6 次;曹偉偉所作的《霍布斯鮑姆的整體性哲學思想》一書收藏館有11 個,被引用次數為0。
在CNKI 上輸入關鍵詞“霍布斯鮑姆”,搜索結果為163 條。搜索指數顯示,1986年國內學界開始出現研究霍布斯鮑姆的文章,共有2 篇;2015年相關文獻量最多,達到13 篇。研究內容多集中在史學理論、政治學、馬克思主義等方面;“民族主義”出現次數最多,為7 次;發表文章數量最多的機構是江西師范大學和南京大學,發文數量分別為13 篇和8 篇。將搜索到的結果按照引用次數排序,排名前10 的論文見圖2。

圖2 CNKI 研究霍布斯鮑姆的論文按引用次數排序截圖
再將結果按照下載次數排序,發現最高下載次數為4,144。由于篇幅有限,截圖不在此展示。從圖2 中可以看到論文的最高引用次數為63 次。所引用的霍氏思想內容主要是民族理論、整體社會史觀、“自下而上”史學觀念、歷史唯物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史學。發表論文數目最多的學者是梁民愫與姜芃。前者是江西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后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研究員。作為教育工作者,他們對霍布斯鮑姆的史學思想研究成果可直接影響其學生的研究方向,這對國內未來對霍氏思想的研究大有裨益。另外,霍氏作為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代表人物,其思想被編入了普通中學與高校歷史課堂教材中,也散見于各類研究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專著中,本文則不一一列舉。
20 世紀20年代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進入中國后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隨著馬克思主義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一同沉浮,發展歷程相當復雜。霍氏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強調歷史唯物主義對史學研究的重大意義。認為歷史可以從經濟史、政治史以及社會史這三個方面著手進行研究,并指出社會史研究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將底層人民的歷史納入了研究范圍,從而形成了新社會史學派。在勞工史研究領域,霍氏注重對底層勞工群體歷史的研究,關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與發展,并探討了勞工史上的重大問題。霍氏對社會史的論述直接啟發了國內歷史學界從80年代初開始的對社會史問題的研究,他的整體社會史觀念拓展了國內學者的視野,成為他們研究世界歷史的理論基礎。中國史學界的“民間史學”概念就源自他主張的“自下而上”的研究社會史的視角,即“一般的社會現象、普通的歷史人物、下層社會民眾的歷史”(吳漢全,2006:10)。總而言之,霍氏關于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的論述在很大程度上為國內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增添了活力。
4.2 大眾接受情況
通過分析圖書的評價信息,可以探析大眾讀者對霍氏史學思想的接受情況。豆瓣圖書在國內屬于信息較全、用戶量最大的閱讀平臺,書評數量眾多且不乏優質的評論。將霍氏著作譯本在豆瓣上的評分和各星級占比數據加以整理,可得表4。

表4 霍氏著作譯本豆瓣評分情況

續表

表5 《極端的年代》情感評價詞
從表4 數據可以看出,霍氏著作的漢譯本在豆瓣圖書上的最高評分為8.7 分,最低為7.3。星級占比較大的集中在3、4、5 星級,這說明讀者對霍氏思想的認可和接受程度較高,但略低評分的出現說明其譯文還是存在一定問題。至于出現問題的原因,將會在下文做詳細的分析和解釋。
本文選用了評分較高的《極端的年代》和評分最低的《斷裂的年代》,對其進行書評分析。因為《極端的年代》是霍氏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和其他三部“年代”相比有更豐富的書評來源。《斷裂的年代》評分最低,對比分析這兩本書的評價有可能找到霍氏著作在傳播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從而解釋出現低評分的原因。從豆瓣圖書上摘取主要的評論并整理成txt格式,再利用軟件ROST CM6 對其進行情感分析,便可以得到情感評價詞及其頻次(見表5、表6)。

續表

表6 《斷裂的年代》情感評價詞
從表5 可以看出,《極端的年代》的情感評價詞排名前11 的均為正面詞,出現次數最多的是“深刻”“宏觀”和“經典”。出現的正面詞共有32個,負面詞僅有3 個,并且出現次數都為1 次,中性詞1 個。正面評價遠超于負面詞。從表6 可以看出,《斷裂的年代》情感評價詞出現次數最多的有5 個,分別是“深刻”“失望”“客觀”“零散”和“重復”。其中有3 個是負面評價。總體而言,正面詞共有17 個,負面詞18 個,中性詞1 個。負面詞超過正面詞。結果顯示,讀者對《極端的年代》接受度和認可度遠超過《斷裂的年代》。
對《極端的年代》的負面評價共有3 個,其中有兩個是與譯文的翻譯質量相關的,分別為“生硬”和“不通”。對《斷裂的年代》的負面評價多為“零散”“分散”“散漫”和“松散”。這是由于此書是霍氏的演講和短篇文章合集,每篇之間缺少直接的邏輯聯系而導致。但也有和譯文的可讀性相關,例如:“晦澀”“費解”和“艱澀”。除此之外,在統計詞頻的過程中,可以發現與譯文質量相關的詞,如“翻譯”出現10 次;“可讀性”出現5 次;“繞口令”出現2 次;“直譯”出現1 次。由于這些詞并不屬于情感詞,因此沒有列在表格內。使用Word 查找功能,分別對這三個詞語定位,通過共現詞語分析其情感色彩,發現這些詞表達的都是翻譯中出現的問題,認為譯文過于直譯,導致晦澀難懂,還有翻譯中出現的少量失誤。例如:
原文:Today there are already only two parts of the world where the majority of people are illiterate: southern Asia (India, Pakistan and the surrounding regions) and Africa. (Hobsbawm, 2013:13)
譯文:今天,世界上只剩下兩個地區不識字的人還占大多數:南亞(印度、巴基斯坦和周邊地區)和非洲。(霍布斯鮑姆,2014:20)
作者將地區的定語放在其后面,過于直譯,不太符合中文的表達習慣,譯為“不識字的人還占大多數的地區”更好。譯文中還出現了定語過長的句子,沒有巧妙地轉換句式,導致理解困難。這是由學者型譯者的語言能力不足造成的。
綜上所述,雖然在翻譯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翻譯質量的問題,但是譯作在中國較高的接受度說明了霍布斯鮑姆著作在中國的譯介和傳播是成功的。霍氏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為普通讀者了解世界歷史打開了一個窗口,讓他們得以了解其思想體系,并獲得了較高的評價。但要想深入探索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的全貌,還有待于史學家等歷史專業人士對其進行分析研究,產出更符合大眾歷史認知水平的文章,從而推動其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
5 結語
本文對霍氏思想在中國的譯介、傳播和接受做了較為詳細的描述和分析。研究發現:霍氏著作的譯者主要為學者型譯者,他們大多主張直譯,爭取忠實,加之出版機構的忠實和通俗性追求與學者型翻譯恰好契合,所以產出的譯文較之于原文文本變形幅度較小,基本保持一致,原文中的史學概念與思想在譯文中也得到了完整的再現;但學者型譯者的語言能力不足,致使部分譯文晦澀難懂,并出現了質量問題;就譯本的接受度而言,其館藏量較大,并被諸多歷史學者引用,普通讀者也對其有很高的評價。這使得霍氏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在中國得到了極大的傳播,為中國學界研究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新的視角與方法。
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漢譯外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這無可厚非。但是“譯出”和“譯入”研究可相互借鑒經驗,兩者都應該受到重視。研究霍布斯鮑姆新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在中國的譯介,可以提升學術界對哲學社會科學(非文學)譯介的重視程度,既能推動翻譯學科的發展,也能挖掘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史料和傳播效果,在當下皆具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