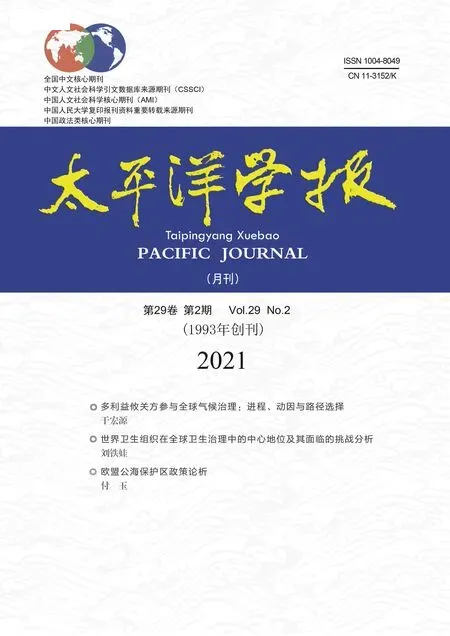我國學界關于越南所謂“黃沙”“長沙”問題的研究綜述
于向東 徐成志
(1.鄭州大學,河南鄭州450001)
位于南海中的西沙群島、南沙群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我國對這些島嶼享有無可爭辯的主權。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越南官方與學術界相互配合,公開挑戰中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千方百計搜集一些歷史記載和各種文獻,對有關文獻資料內容特別是越南文獻中非常有限的關于“黃沙”“長沙”記載進行選擇性使用和片面解讀,制造出所謂“黃沙”“長沙”問題,并采用張冠李戴、指鹿為馬的手法,將“黃沙”“長沙”與我國的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相混淆。我國學術界對越南所依據的“歷史典據”和各種資料,從歷史學、地理學、文獻學等多角度進行深入研究,考證出越南“黃沙”“長沙”是指越南沿岸近海海域的一些島嶼和沙洲,有力駁斥了越南關于“黃沙”“長沙”問題的謬誤之說,為捍衛我國南海島礁主權和海洋權益作出了積極貢獻。
我國學者早已有關注、記錄、研究南海和南海諸島的學術傳統。新中國成立后,這一傳統得到賡續傳承和發揚光大。早在20世紀前半期,我國學界就已形成多次南海和南海諸島研究的高潮,一是1928年前后日本商人非法開發東沙群島、西沙群島后,有陳天錫編《西沙島東沙島成案匯編》、沈鵬飛《調查西沙群島報告書》、朱庭祜《西沙群島的鳥糞》等;二是1930年代法國侵占南海我國的一些島礁后,有凌純聲編《今日中國之海疆問題》等大量著述;三是二戰結束后,中國接收西沙、南沙兩群島,有杜定友編《東西南沙群島資料目錄》、鄭資約編《南海諸島地理志略》、楊秀清編《海軍進駐后之南海諸島》等;四是針對20世紀50年代南越和菲律賓對我國南海提出主權訴求,有李長傅《帝國主義侵略我國南海諸島簡史》、邵循正《我國南沙群島的主權不容侵犯》《西沙群島是中國之領土》、陳棟康編《我國的南海諸島》、鞠繼武《祖國的南海諸島》等。①張明亮:“早期的南中國海研究”,《東南亞研究》,2007年第3期,第44-47頁。我國學者關于南海問題的早期研究,還可參見袁航:“史學視域下的國內南海主權問題研究綜述”,《民國研究》,2018年春季號,第254-255頁;曾勇:“國內南海問題研究綜述”,《現代國際關系》,2012年第8期,第58頁;王曉鵬:“國內學術界南海問題研究:回顧與思考”,《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第20頁;郭淵:“從南九小島事件看民國學者對南沙主權之論證”,《北方法學》,2016年第1期,第95-106頁;張建媛、王琦、吉家凡:“民國報刊中南海文獻分類與整理研究”,《瓊州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第11-17頁。我國著名學者如馮承鈞、向達等在研究南海史地、中外交通史的過程中,也十分關注南海和南海諸島,作出了重要貢獻。馮承鈞譯有《昆侖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交廣印度兩道考》等,并著有《中國南洋交通史》。向達主持《中外交通史籍叢刊》,發現并整理、校注《西洋番國志》《鄭和航海圖》《兩種海道針經》等重要史料。正是許多學者扎實的調查和研究成果,使我國學界對南海和南海諸島的認識不斷深化,為我國學者回應批駁越南拋出的所謂“黃沙”“長沙”問題打下了堅實基礎。
一、對越南官方文件主張所謂“歷史依據”的批駁
1975年初,行將就木的南越偽政權外交部發布《關于黃沙(帕拉塞爾)群島和長沙(斯普拉特利)群島的白皮書》,列舉越南聲稱擁有西沙、南沙兩群島主權的“歷史依據”“法律依據”,提出了所謂“黃沙”“長沙”問題,并在附件中收錄了1974年2月《越南共和國政府聲明》及《關于帕特爾島肥料的開發與運輸合同》等資料。70年代末,剛完成南北統一后不久的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外交部,一改過去承認中國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擁有主權的外交立場,先后發布了《越南對于黃沙和長沙兩群島的主權》白皮書(1979年9月)、《黃沙群島和長沙群島——越南領土》白皮書(1982年1月)、《黃沙群島和長沙群島與國際法》外交文件(1988年4月),拋出南海中的西沙、南沙兩群島就是越南所謂“黃沙”“長沙”群島的謬論。這些文件包含了越南對我國西沙群島、南沙群島提出主權聲索的主要理論依據:一是黎貴惇(Lê Quy?n)《撫邊雜錄》的相關記載,并輔以《纂集天南四至路圖》《大南實錄》《大南一統志》等文獻資料的部分內容;二是西方相關地圖及傳教士的筆記與專著;三是曲解1943年12月1日《開羅宣言》及1951年9月8日《舊金山和約》相關規定;四是將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規定進行曲解。根據這些內容,越南宣稱自17世紀以來已對“黃沙”和“長沙”群島進行開發和管理,并稱這兩個群島就是今天南海中的西沙群島與南沙群島。
越南的無理和非法主張提出后,我國外交部隨即對其白皮書及外交文件進行了及時的回擊和系統有力地駁斥。1980年1月30日,我國外交部發布《中國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主權無可爭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文件》②“中國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主權無可爭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80年第 1 號,第 19-28 頁,http://www.gov.cn/gongbao/shuju/1980/gwyb198001.pdf;該文件又載《人民日報》,1980年1月31日;《中國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主權無可爭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文件·評越南外交部關于越中關系的白皮書》,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9頁;《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4頁。。該文件介紹了中國對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的發現、開發和經營的歷史以及20世紀以來中國捍衛兩群島主權的斗爭,指出中國對西沙、南沙兩群島的主權得到國際上的廣泛承認,揭露了越南官方此前正式承認、現又提出主權聲索的出爾反爾表現,是違反國際法“禁止反言原則”的非理和非法行徑,明確闡述了我國對于南海諸島擁有不可置疑的主權的原則立場。1988年5月12日,我國外交部又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關于西沙群島、南沙群島問題的備忘錄》①“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關于西沙群島、南沙群島問題的備忘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88年第12號,第396—398 頁,http://www.gov.cn/gongbao/shuju/1988/gwyb198812.pdf。,以歷史事實和國際法為根據,再次梳理我國對西沙、南沙兩群島有效管轄的悠久歷史,列舉越南1975年以前所發表的政府聲明、正式照會和公開出版的地圖和教科書中承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是中國領土的證據,有力地駁斥了越南外交部1988年4月外交文件提出的謬誤觀點,重申了中國對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的主權。
我國學者也注意到越南官方立場和觀點的變化,對越南的無理和非法主張通過各種形式進行批駁。我國學者所做的大量工作,主要集中在20世紀80、90年代和進入21世紀兩個時期。一方面是發表大量研究論文,對越南具體的論據和觀點進行批駁(有關論文發表情況除此部分的敘述外,也見于本文其他部分);另一方面是翻譯出版相關資料文集,為更多學者系統了解、深入批駁越南的觀點提供便利。各種資料文集的翻譯與整理工作既體現出系統的學術研究,也為我國學者了解越南官方的觀點提供了基礎性材料,為批駁其謬論提供了便利。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戴可來、于向東等人將越南包括南越偽政權外交部1975年5月白皮書(包含1974年2月14日聲明、關于帕特爾島肥料的開發與運輸合同、《開羅宣言》三個附件)、越南外交部1979年9月28日、1982年1月18日兩個白皮書、1988年4月的外交文件和越南學者署名的其他一些相關資料進行翻譯整理,出版《越南關于西南沙群島主權歸屬問題文件資料匯編》②戴可來、童力編譯:《越南關于西南沙群島主權歸屬問題文件資料匯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該資料匯編前載“編者的話”中,他們從法理和史地兩方面對越南的論據和觀點進行剖析,尤其是基于對越南歷史和古代文獻的研究,揭露了越南在利用《纂集天南四至路圖》《撫邊雜錄》等資料時,采用的指鹿為馬的手法及其拋出“黃沙”“長沙”問題的虛偽性。
在此時期前后,還有一些涉及海洋問題的相關資料特別是越南官方文件為我國學者所關注。曾繼福、謝兆余等編譯《越南與海洋》③曾繼福、謝兆余等編譯:《越南與海洋》,印行年份未注明。,翻譯收錄了《越南關于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及大陸架的聲明》(1977年5月12日)、《越南政府關于外國漁船在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海域進行漁業活動規定的決定》(1980年1月29日)、《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關于確定領海寬度基線的聲明》(1982年11月12日)、《黃沙群島和長沙群島與國際法》(1988年4月)等官方文件資料。廣西東南亞經濟與政治研究中心編譯《越南關于我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歸屬問題的若干資料匯編》④廣西東南亞經濟與政治研究中心編譯:《越南關于我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歸屬問題的若干資料匯編》,廣西東南亞經濟與政治研究中心,1990年版,第84-105頁。,也翻譯收錄了越南政府公布的有關領海、領空、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的聲明,以及《越南的陸地邊沿基線》(1982年11月12日)、《關于越南領空的規定》(1984年6月5日)等文件資料。進入21世紀,吳士存主編《南海問題文獻匯編》⑤吳士存主編:《南海問題文獻匯編》,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 211、212、227 頁。,進一步搜集有關資料,又收錄了《越南對黃沙群島和長沙群島的聲明》(1979年8月7日)、《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關于長沙群島的節略》(1987年2月12日)等官方文件資料。
對于越南試圖攫取我國南海島礁主權權益的非法主張,我國學術界一些學者如韓振華、戴可來、林金枝、吳鳳斌等一批學者針對越南外交文件中的論據和觀點,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進行反駁。如韓振華、吳鳳斌明確指出:1.關于杜伯(Bá)《纂集天南四至路圖》相關圖說,從地形上看,“長沙”“葛鐄”南北長、東西短,但西沙群島東西長、南北短,南沙群島又較之寬二十多倍;從地理位置上看,以17世紀越南帆船航海技術,不足以從越南大占門、沙淇門到達我國西沙群島、南沙群島;2.關于黎貴惇《撫邊雜錄》,越南白皮書將該書所載110多個島嶼改為130多個,但我國西沙及南沙群島的數量與之不符,更無“長約三十里”“平坦廣大”的“黃沙島”,珊瑚島礁也不能作為“諸蕃舶”的避風之所;3.法國主教路易·塔伯爾(Jean-Louis Taberd)《交趾支那地理札記》所載越南阮朝嘉隆皇帝阮福映(Gia Long, Nguy n Phúc ánh)在“黃沙群島”插旗所在經緯度亦與我國西沙群島不同;4.據清代盛慶紱纂、呂調陽重訂《越南地輿圖說》,“黃沙渚”指越南沿海的哩島,而從其在各古籍中的名稱和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及黃沙隊海上交通工具與活動范圍考察,黃沙群島即今理山島群島和占婆島群島。5.所謂“長沙群島”在《大南一統全圖》中的位置距離越南中部海岸不遠,且“黃沙”“萬里長沙”緊挨一起,因而是指越南中部沿海的一些島嶼和沙洲①韓振華、吳鳳斌:“駁越南當局所謂黃沙、長沙即我國西沙、南沙群島的謬論”,《人民日報》,1980年8月1日;又載韓振華著:《韓振華選集之四·南海諸島史地論證》,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3年版,第19—27頁。。
吳鳳斌從歷史地理和法律兩方面駁斥了南越阮文紹(Nguy n Vǎn Thi u)政權外交部發布的白皮書。他認為:1.據三幅越南古地圖、越南古代船只航程距離、“葛鐄”地名學的歷史記載和占婆島、廣東群島的歷史情況,“葛鐄”或“葛鐄”指越南廣義、廣南沿海一帶從占婆島至廣東群島一帶的沙灘和島嶼;2.據越南援引古籍中“黃沙島”的島嶼數量、面積、物產及商船足以避風,與西沙群島不符,而據中越古地圖資料及《撫邊雜錄》相關內容,“黃沙島”應為廣義省平山縣海外廣東群島及其附近一帶的島嶼,但越南阮朝受法國殖民者影響,故意將其范圍擴大至西沙群島;3.關于《白皮書》所引外國有關“帕拉塞爾”的歷史資料,通過分析當時西人專著、傳教士筆記、西方航海圖等內容,指明“帕拉塞爾”最初明確區分于西沙群島;4.關于“大長沙島”,通過分析中越史料及地圖,尤其是《撫邊雜錄》《大南一統全圖》涉及“大長沙島”“萬里長沙”的部分,指出它并非我國南沙群島,而是指越南廣平、廣治和承天三省沿海岸的沙灘和島嶼①吳鳳斌:“駁南越阮偽政權《白皮書》所謂擁有我國西、南沙群島主權的論據”,《南洋問題》,1979年第4期,第83-105頁。。
戴可來發表長篇文章②戴可來:“漏洞百出、欲蓋彌彰——評越南有關西沙、南沙群島歸屬問題的兩個白皮書的異同”,《光明日報》,1980年6月9日。該文也收錄于《西沙群島、南沙群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73頁。分析越南1975年5月南越阮文紹政權白皮書與1979年9月越南外交部白皮書的異同,指出其諸多漏洞,批駁越南對我國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主權的無理聲索,在中國和越南學界產生較大影響。他將兩個白皮書所羅列的史料依據進行了細致地比較,從歷史與地理方面分析指出后一個白皮書只是前者的改寫本,只不過就前者明顯的錯漏之處進行了修補。他指出越南將“黃沙”群島視為中國西沙群島完全沒有道理,可從八個方面進行批駁:一是越南海岸至“黃沙”群島里程;二是《撫邊雜錄》所載“群山零星一百三十余嵿”,而西沙群島所有島嶼、沙洲、暗礁、暗灘相加只有35個;三是《撫邊雜錄》的記載多有不準確之處;四是《撫邊雜錄》載越南人在洋中“時遇”中國漁舟,又“常見”瓊州文昌縣正堂官巡視,反而證明中國政府早已在此行使管轄權;五是嘉隆王在“帕拉塞爾”插旗一說不符合東方儀式,而是西方禮儀習慣;六是1816年嘉隆王對“帕拉塞爾”群島的所謂“御駕親征”,《大南實錄》等越南阮朝史籍均無記載;七是其所稱“帕拉塞爾”群島位于自北緯11°至17°,東經109°至110°,與我國西沙群島無關;八是河內白皮書也未敢使用塔伯爾主教1837年關于嘉隆王插旗的材料。關于將我國南沙群島稱為“長沙群島”,其所依據的是《大南一統全圖》,但此圖來歷不明,制作年代不詳,不足為信。
此外,郭明主編《中越關系演變四十年》③郭明主編:《中越關系演變四十年》,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46-159、204-208頁。也對越南官方文件作出分析與評述,詳細列舉1974年以前越南承認中國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主權的證據,系統梳理我國發現、開發、經營及有效管轄南海的歷史,對越南所稱“黃沙”“長沙”,則主要援引韓振華、戴可來教授等學者的研究成果,批判越南侵占我國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的企圖。
二、對越南學者研究動態的追蹤與研究觀點的批駁
在越南官方提出對我國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的主權聲索的過程中,越南學術界也在極力尋找各種論據,發表論著,渲染所謂的“黃沙”“長沙”問題。1975年西貢《史地》季刊與南越偽政權的白皮書相配合,把學者阮雅(Nguy n Nh?)、黃春翰(Hoàng Xuan H?n)等人的 16 篇文章,編輯為《黃沙和長沙特考》。《黃沙和長沙特考》的內容較早集中體現了越南學界追隨西貢偽政權所拋出的關于“黃沙”“長沙”問題的論點和論據,在“黃沙”“長沙”問題的形成過程中頗具影響,不少觀點為后來的越南學者所沿用。
20世紀70年代后期,戴可來將《黃沙和長沙特考》全書迻譯為中文出版④[越]阮雅等著,戴可來譯,白東岳校:《黃沙和長沙特考》,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并對其主要觀點進行了初步介紹和批駁,揭露《黃沙和長沙特考》在企圖證明所謂“黃沙”“長沙”群島就是中國的西沙群島、南沙群島時采用的卑劣手法,如故意混淆古今概念,聲稱“現在的越南版圖應該從百越時代算起”,還把清代陳倫炯《海國聞見錄》中的“粵洋”曲解為“越洋”等。后來,戴可來又與于向東、余富兆等學者合作,及時將越南學者劉文利()的《越中關于黃沙和長沙兩群島的爭端》⑤[越]劉文利著,戴可來、于向東、余富兆等譯,戴可來校:《越中關于黃沙和長沙兩群島的爭端》,1996年印行。該書系1995年由越南人民公安出版社出版,作者劉文利曾任越南部長會議邊界委員會(越南國家邊界委員會)主任。整理翻譯,廣西東南亞經濟與政治研究中心也將越南《海軍》雜志1986年第2期和《軍事歷史》雜志特刊1988年第6期刊載的相關文章翻譯,收入《越南關于我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歸屬問題的若干資料匯編》⑥廣西東南亞經濟與政治研究中心編譯:《越南關于我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歸屬問題的若干資料匯編》,廣西東南亞經濟與政治研究中心,1990年版,第4-75頁。。這些工作都為我國學者跟蹤了解、回應批駁越南學界的觀點提供了便利。
針對越南外交文件和學術界特別是其史學界提出的各種謬誤之說,中國學者發掘中國史料,并利用越南文獻記載,結合越南歷史發展背景,詳細考證越南所謂“黃沙”“長沙”問題的文獻出處、作者背景、史料價值、地貌特征、地理位置等,發表的研究成果既有針對越南學者具體文章觀點的批駁,也有對越南關于“黃沙”“長沙”研究狀況的評介與剖析。
1979年10月,越南《人民報》連載了越南學者武海鷗(Vu~?u)《越南對黃沙和長沙兩群島的主權非常明確,不容爭辯》①[越]武海鷗:“越南對黃沙和長沙兩群島的主權非常明確,不容爭辯”,載戴可來、童力合編:《越南關于西南沙群島主權歸屬問題文件資料匯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133頁;該文原連載于越南《人民報》,1979年10月10日至13日。一文,從《撫邊雜錄》《大南實錄》《大南一統志》等越南史料相關記載、西方地圖及西方傳教士的信件與著作、越南阮朝與法國殖民政權、南越偽政權對兩群島的占領和“行使主權”的歷史等三方面進行論述,宣稱“黃沙”“長沙”就是我國的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對其謬誤之說,吳鳳斌發表文章②吳鳳斌:“關于越南‘黃沙’和‘長沙’的問題——駁武海鷗《越南對黃沙和長沙兩群島的主權非常明確,不容爭辯》一文的謬論”,《南洋問題》,1981年第3期,第88-100頁。逐項進行批駁。他指出該文中提及的越南銅鼓船形不足以稱為大型越海船只,無任何具體信息的15世紀末地圖集不足采信。他根據《順化廣南地圖日程》《黎代過廣南路圖》等史料指出,阮朝建廟、立碑和植樹之所是廣義“黃沙”,即廣南、廣義省沿海的沙灘和島嶼,而非我國西沙群島;《大南實錄(前編)》《大南一統志》將清朝公文中的“萬里長沙”擅改為“黃沙島”,把《撫邊雜錄》“黃沙渚”作為“黃沙島”的注析遷移過來,造成“黃沙”問題的混亂;對于西方地圖及傳教士信件及著述資料,武海鷗錯誤引用了古茲拉夫《交趾支那王國地理》原文,并進一步考證古帕拉塞爾(葛磺)的具體方位與自然環境,指出其并非我國西沙群島,更無包含我國的南沙群島;認為法國殖民政權及西貢偽政權對兩群島所謂“行使主權”,系違反國際法的侵略行為,不能作為主權主張的依據。
黃國安發表文章③黃國安:“越南所說的‘長沙’并非中國的南沙群島——兼評越南某些學者所謂對南沙擁有主權的言論”,《印度支那》,1988年第2期,第19-21頁。認為,黎貴惇《撫邊雜錄》和潘清簡(Phan Thanh)《越史通鑒綱目》所記載的大小長沙是越南廣平省和廣治省海中的島嶼;劬勞哩又稱理山島,即越南廣義省東北部沿海的廣東群島;18世紀越南帆船航海技術也不足以到達我國南沙群島;南沙群島多為珊瑚島,并非越南史籍所載船舶航行之處。該文還結合《越南輿地圖說》《大南一統志》等中越史籍記載,考證《大南一統全圖》所繪“萬里長沙”,位于與越南中部海岸相平行位置,在平治天省東部沿海,距我南沙群島不下五百海里。
進入21世紀,中國學者不斷跟蹤越南學界關于“黃沙”“長沙”問題的研究動態,而且隨著中越關系正常化后兩國學術交流環境的改善,不少學者還有在越南進行實地調查研究的經歷,與越南學界有較多學術交流,在此基礎上不斷發表研究成果,及時分析越南學界觀點主張的變化、使用的論據資料和對我國學者研究觀點的回應。
戴可來《越南方面的論點及我國學界的批駁》④戴可來:“越南方面的論點及我國學界的批駁”,載李國強著:《南中國海研究:歷史與現狀》,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208頁。一文圍繞越南學術界關于“黃沙”“長沙”問題的主要論點,列舉了越南援引的《纂集天南四至路圖》《大南一統全圖》《撫邊雜錄》等主要“歷史典籍”,梳理了越南提出的法國以越南國家名義及越南歷屆政府對兩群島“行使主權”的會議及事件,從多方面剖析了越南學界的觀點和對中國學者主要觀點的回應意見,進一步辨析《纂集天南四至路圖》《撫邊雜錄》《大南一統全圖》的相關記載,考證越南古籍中“黃沙”和“長沙”的地名只是越南近海的島嶼和沙洲,并非我國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
于向東對21世紀初越南實施全面海洋戰略背景下其學者關于南海爭端的研究觀點進行梳理⑤于向東、郝曉靜:“關于南海爭端越南學者的若干觀點評析”,《和平與發展》,2012年第 3期,第 48-52、71頁。,認為其學者多就南海爭端的歷史、地緣政治、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展開,并有從強調歷史依據研究向強調國際法研究轉變的趨向。
李國強發表文章①李國強:“南海歷史研究中的若干問題——對越南學術觀點的分析與回應”,《齊魯學刊》,2015年第2期,第34-39頁。認為,越南的南海歷史研究呈現出“歷史依據研究與法理依據研究的整體化”“官學互為支撐的一體化”“文獻資料搜集的全球化”等特點,指出越南阮朝嘉隆皇帝所謂插旗之“帕拉塞爾”是越南中部沿海一些島嶼、沙洲,并非我國西沙群島;他強調越南連“黃沙”“長沙”等地名的由來和所指區域位置都無法明確說明的情況下,即以“黃沙隊”“長沙隊”的活動作為其政府管轄的依據,不具有任何說服力。
秦愛玲撰文②秦愛玲:“對越南‘黃沙、長沙’主權要求及歷史依據的評析”,《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第9-18頁。介紹了越南有關“黃沙”“長沙”的研究成果,指出越南南海研究具有“學為官用”“借學術之名將南海問題國際化”“國外越僑異常活躍”等特點,認為越南學術界的歷史依據和主要觀點含糊不清,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經不起推敲和論證。
張明亮發表文章③張明亮:“越南對南(中國)海島礁與海域的權利要求及其依據”,《中國海洋法學評論》,2013年第1期,第59-104頁。分析了越南對“黃沙群島和長沙群島”的權利要求及其依據:越南企圖繼承法國殖民者及南越偽政權的“權利依據”,1979年、1982年的白皮書和1988年的外交部文件是其集中體現;20世紀90年代以來越南則著力宣傳這三份外交文件中的核心觀點,并詳細介紹了劉文利()《越中關于黃沙和長沙兩群島的爭端》與陳公軸()《東海上的越南烙印》兩部代表性著作。文章指出所謂“黃沙”“長沙”群島與我國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的經緯度差別,從地理位置上否定了越南的主張。
趙衛華在其著作④趙衛華著:《權力擴散視角下的中越南海爭端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19年版,第14-18頁。中列舉了近年來越南相關研究的代表性專著與學術論文。他指出,越南的研究多為對策性研究,鮮有理論性成果,但較多涉及了歷史、國際法、安全因素、大國因素、東盟因素、多邊機制和中國國情等各方面因素。他批評越南學者在歷史方面的研究中忽略或淡化、隱去不利于其主張的資料,有諸多漏洞,但其卻善于利用中文文獻或西方文獻批駁中方研究,并利用國際輿論宣傳其成果和觀點。
徐曉東的研究⑤徐曉東:“南海問題所涉歷史依據英文研究述評”,《太平洋學報》,2020年第10期,第73-75頁。則對21世紀以來越南學者關于“黃沙”“長沙”問題的英文研究成果進行了述評。他分析了阮洪濤()、阮雅、阮友肅()、范翠莊(Thúy Trang)等越南學者的著作及主要觀點,認為越南學者一方面從對越南史籍、中西方史料相關記載的歷史地理考證、“有效占領”證據強調其主權要求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誣稱中國用以支撐對南海進行發現、命名以及管轄的史料存在問題。他指出越南學者所援引的歷史依據說服力不足,“學術政治化”現象嚴重,但其帶來的負面效果不容小覷。
我國學術界一貫重視對越南所謂“黃沙”“長沙”問題的研究,對越南學者不斷尋找證據體系,企圖證明其“黃沙”“長沙”即我國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的謬誤觀點和官方主張進行深入批駁,對越南學界尋求“歷史依據”的一些研究動向及時進行跟蹤和研究。在此過程中,一批具有語言條件和研究基礎的青年學者加入研究隊伍,對越南官方和學界的謬論進行深入批駁,也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三、對越南所謂“重要典據”的專題性分析
我國學者對越南所援引的典籍史料進行梳理、考證與分析,并發表專門文章予以駁斥。他們使用大量中國、越南及西方的史料進行分析比對,包括從文獻學角度運用版本、校勘、考證、辨偽等方法考證分析,對越南典籍所載相關內容進行仔細辯駁,從而證明越南所謂“重要典據”不能佐證越南所謂“黃沙”“長沙”的主權主張。
郭永芳發表文章①郭永芳:“西沙不是‘黃沙’——越南的史書揭露了越南當局”,《世界知識》,1980年第14期,第 16-17頁;又載《西沙群島、南沙群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84頁。考證杜伯《洪德版圖·纂集天南四至路圖》中《圖說》所載從大占門、沙琪門至“黃沙”的時間,認為越南帆船不足以到達我國西沙群島,并指出《撫邊雜錄》《歷朝憲章類志·輿地志》《皇越地輿志》所載“黃沙”不同于我國西沙群島的地貌特征。他依據《越南地輿圖說》《越南地圖》《越南輯略·越南全圖》指出,“黃沙”只是越南中部近海廣東群島一帶的島嶼。他還有文章②郭永芳:“越南史籍記載的‘黃沙’、‘長沙’決非我西沙、南沙群島”,載廣東地名委員會編:《南海諸島地名資料匯編》,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87年版,第405-412頁。具體考證出“黃沙”島實際是廣東群島北面的“椰子塘”,并援引越南及中國的史料,指出“大長沙”并非我國南沙群島,而在越南思賢海口即峴港附近。他認為,依據越南《大南一統志》、明代黃衷《海語》、暹羅貢使《廣東紀行詩》、清初大汕廠翁《海外紀事》的記載,占婆島、外羅山一線是中越兩國海洋的分界線,“黃沙”“長沙”均在該分界線上及其以西范圍內,而我國南沙群島遠在該分界線以東數百海里。
戴可來撰文③戴可來:“越南古籍中的‘黃沙’、‘長沙’不是我國的西沙和南沙群島——駁越南關于西、南沙群島主權歸屬問題的‘歷史地理論據’”,載呂一燃主編:《中國邊疆史地論集(1990年)》,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9-423頁;呂一燃主編:《南海諸島:地理·歷史·主權》,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207頁。就越南所謂歷史地理依據進行深入剖析,通過對《纂集天南四至路圖》杜伯所繪廣義地區圖、《交州志·廣南處三府》、迪穆蒂埃重繪《黎朝過廣南路圖》、1741年重繪《天南路圖》的分析,認為“長沙”即“葛鐄”,都是北起大占門南至沙榮門的近海島嶼和沙洲,即今占婆島至廣東列島一帶的島嶼沙洲。他認為《撫邊雜錄》以抄本傳世,多有不一致及后人篡改之處,且當時越南帆船航程時間不足以到達我國西沙、南沙兩群島;“劬勞薙”與“黃沙渚”“大長沙島”均指理山島;黃沙渚島嶼數量與物產不同于我國西沙群島、南沙群島;該書“遇北國漁舟……常見瓊州文昌縣正堂官”等記載也體現出中國對這些島嶼的開發與管轄,并進一步指出越南所謂《大南一統全圖》為偽圖,不能作為法理依據。
于向東于20世紀80年代依據韓振華先生贈予的《撫邊雜錄》縮微膠片資料,完成了6萬多字的碩士學位論文《黎貴惇及其〈撫邊雜錄〉研究》④于向東:《黎貴惇及其〈撫邊雜錄〉研究》,鄭州大學碩士論文,1988年。,在國內較早對該書及其作者進行系統研究。越南后黎朝士大夫黎貴惇于18世紀后
期編纂的《撫邊雜錄》,經常為越南官方及學術界提及,稱之為“重要歷史典據”之一,對19世紀越南關于“黃沙”的一些記載也產生了較大影響。于向東研究此書的成書過程、體例內容、抄本流布、史料因襲和價值等,在中國和越南學術刊物發表系列研究論文。尤其是他針對越南學界歪曲利用《撫邊雜錄》的情況,撰寫剖析論文,與戴可來合作在《國際問題研究》發表⑤戴可來、于向東:“《撫邊雜錄》與所謂‘黃沙’‘長沙’問題”,《國際問題研究》,1989年第3期,第24-28、38頁。該文也收錄于呂一燃主編:《南海諸島:地理·歷史·主權》,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217頁;戴可來、于向東著:《越南歷史與現狀研究》,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400-409頁。,對該書中關于“黃沙”“長沙”的零星記載進行考證,認為《撫邊雜錄》卷二中的記載或根據楊文安()《烏州近錄》的記載轉述,或根據傳聞記錄,黎貴惇并未進行海上實地踏勘,其關于海洋的一些記載,并非可信史料。他們從該書具體內容分析指出,一是“黃沙隊”所駕“私小釣船”難以正常到達中國的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二是書中雖然偶爾提及“黃沙渚”“大長沙島”,但并未使用專用的“黃沙”群島的名稱,到阮朝后期“黃沙”和“長沙”才被用來指越南中部沿海南北分布的島嶼和沙洲;三是根據其相同的航程、海物舶貨及同為黃沙隊作業主要地點判斷,“黃沙渚”和“大長沙島”實為一地,根據方位與面積看“黃沙渚”與“劬勞薙”同指一處,均指理島;四是“長沙”首先是指沿海沙岸,其次是指沿海沙洲,再次是越南近海島嶼。他們明確指出,《撫邊雜錄》的記載清楚地證明了“黃沙”“長沙”不是中國的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
李金明發表的論文①李金明:“越南黃沙、長沙非中國西沙南沙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第71-79頁。及其著作《中國南海疆域研究》第五章“越南黃沙、長沙非中國西沙、南沙考”②李金明著:《中國南海疆域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8-86頁。,從《纂集天南四至路圖》《撫邊雜錄》《大南一統全圖》三種越南史籍及帕拉塞爾的位置著手論證越南“黃沙”“長沙”與我國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無涉。他考證《纂集天南四至路圖》中所志四道路程,探究越南船只航行距離、各國商船漂泊地點及大汕廠翁的相關記載,認為“廣義地區圖”注釋的“長沙”實際是越南外羅海中的一些小島、沙洲;《撫邊雜錄》卷二所載安永社指永安、安海二坊,130余嶺指外羅山,即今理山島,其中有黃沙渚,注為椰子塘,即理山島北部小島通草嶼,而劬勞哩所指是理山島附近的小島;越南外交部拋出的《大南一統全圖》何時何人所作尚有爭論,且該圖 “黃沙”“萬里長沙”與英國船長約翰·沙利(John Saris)1613年《航海志》中所繪腳狀的“舊帕拉塞爾”相似,其形狀與經緯度均區別于我國西沙群島;關于越南大量引用19世紀20年代以前西方史籍所載“帕拉塞爾”,考證法國傳教士塔伯爾1837年《交趾支那地理考釋》、1838年《拉丁文—安南文詞典》所附《安南大國畫圖》及18世紀10年代英國船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相關記載,指出其所載“帕拉塞爾”并非我國西沙群島,而是沿著與越南中部海岸平行、分布在外羅海中,由一些小島和沙洲組成的“長條地帶”。
劉文宗撰文③劉文宗:“越南的偽證與中國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主權的歷史和法理依據”,載中國國際法學會主編:《中國國際法年刊(1989)》,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336-359頁。除了回顧中國發現、開發和經營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的歷史外,還從國際法“禁止反言”“關鍵日期”等角度論證我國對這兩個群島的主權,也從“越南地圖中的廣義地區圖”和《撫邊雜錄》及《交趾支那地理札記》等記載展開論述。他認為越南所說“黃沙灘”“黃沙渚”無論從地理位置、長度面積或地形地貌都與我國西沙群島毫不相似;“嘉隆升旗”之所亦非我國西沙群島;將《撫邊雜錄》和《越南地輿圖說》兩相驗證,越南“黃沙”“黃沙渚”指的是越南中部近海廣東群島劬勞哩和磐灘石一帶;《大南一統全圖》所載“萬里長沙”與越南中部海岸平行,并據《海語》“分水”條認為“長沙”指大占海門至沙榮,“大長沙”指從“長沙”至草鞋石。
于向東的博士學位論文④于向東:《古代越南的海洋意識》,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吸收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進一步從海洋史的視角分析研究越南古代的海洋環境、海洋活動、海洋著述、海洋神祗崇拜與信仰,對越南古代的海洋意識進行了系統的分析總結。他較早指出,直到20世紀前期越南并不具備近代海洋意識和海洋國土觀念,越南古代所認識的“東海”()海洋范圍非常有限,僅限于其東部沿海幾十公里的近海海域,20世紀70年代隨著現代海洋意識成長,越南才把“東海”范圍大為擴展,用以指稱南海,以支持其對“黃沙”“長沙”的主權聲索。阮廌()、黎貴惇和其他一些參與海洋活動的封建士大夫以及封建帝王大多僅意識到越南沿海海岸和近海海域的存在;他們所記載的從越南中部到南方沿近海分布的眾多島嶼、沙洲,都是位于越南近海航行的航線附近;黎貴惇所提及的“黃沙”“長沙”并非越南當代所謂的“黃沙”“長沙”群島,更與我國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無涉。
孫志文和王楠文章⑤孫志文、王楠:“越南‘東海’考辨”,《東南亞研究》,2019年第5期,第 72-85、155-156頁。具體考察歷史上越南對南中國海的稱謂變化和東海的詞源和詞義演變,指出19世紀以前的漢喃古籍并無對南中國海的專屬稱謂,淪為法國殖民地后,越南還借用法文中的“中國海”“南中國海”“南海”指稱南中國海。20世紀20—30年代,法國殖民者侵占我國南海諸島,才開始從越南古籍中尋找歷史證據,將漢喃古籍中的“東海”與南中國海相混淆,其范圍也不斷擴展,成為越南對南中國海的專屬稱謂之一。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為謀求我國南海主權,越南將東海完全作為對南中國海的官方稱謂,編造所謂歷史證據,誤導國際輿論,掩蓋其侵略行徑。
王志強的文章①王志強:“從《撫邊雜錄》版本的比對看南海爭議島嶼的歸屬問題”,《中國邊疆學(第十輯)》,2018年第2期,第205-228頁。比對研究了《撫邊雜錄》5種抄本中涉及“黃沙”的內容,認為至少有11處文字意思上有巨大差異,降低了該書的記載作為歷史文獻的史料價值。他認為“大長沙島”和“黃沙渚”不是我國南沙群島,因為它們在廣義府東北,而南沙群島在東南,且越南釣船航速三日夜不能到達南沙;從《撫邊雜錄》所記載的島嶼數量、地形面積、自然環境、物產及當時越南航海技術等方面考察,也不可能是我國的西沙群島。此外,該文章還就“海南廉州府”與“海南廣州府”、“常”與“嘗”等文字的校勘辨偽進行了分析,否定了越南這一“歷史典據”的價值。
宗亮針對越南學界找出19件有“黃沙”字眼的硃本檔案資料作為所謂“新證據”進行了研究②宗亮:“試論越南關于南海問題的硃本‘新證據’”,《南海學刊》,2015年第1期,第89-95頁。,通過對這些材料具體內容的分析,認為其記事價值有限,同時也是越南阮朝國史館史官早已棄用的材料。這些硃本記事內容與越南其他典籍記載相沖突,也與國際法原則相違,并不能成為越南關于南海“主權”聲索的“新證據”。
四、對西方文獻中“帕拉塞爾”及“嘉隆皇帝插旗說”的辯駁
越南官方文件及越南學者援引西方史籍中的“帕拉塞爾”(Paracel)為自己佐證,將其“黃沙群島”、19世紀之前西方人所稱“帕拉塞爾”與如今專指我國西沙群島的“帕拉塞爾”相混淆,并提出嘉隆十五年(1816年)阮朝嘉隆皇帝阮福映曾登上“帕拉塞爾”插旗,宣示主權。對這些問題,我國學者在運用歷史學、文獻學方法進行批駁的同時,也從地理學與地理測繪、檔案學等角度進行專題研究。
韓振華當年搜集大量歷史資料,以深厚功力加以細致考證,先后發表了關于“帕拉塞爾”的系列研究成果③韓振華:“古‘帕拉賽爾’考(其一)——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外國記載上的帕拉賽爾不是我國的西沙群島”、“古‘帕拉賽爾’考(其二)——十六、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外國地圖上的“帕拉塞爾”不是我國西沙群島”,《南洋問題》,1979年第5期,第1-47頁;又載韓振華編:《南海諸島史地考證論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73-207頁;韓振華著:《韓振華選集之四·南海諸島史地論證》,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3年版,第375-438頁。,認為16至19世紀中葉外國地圖上的“帕拉塞爾”不是我國西沙群島,并較早發表相關著述④韓振華:“西方史籍上的帕拉塞爾不是我國西沙群島——揭穿越南當局張冠李戴魚目混珠的手法”,《光明日報》,1980年4月5日;《西沙群島、南沙群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79頁;韓振華著:《韓振華選集之四·南海諸島史地論證》,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3年版,第369-374頁。,揭露越南當局張冠李戴、魚目混珠的手法,提出必須將古“帕拉塞爾”與19世紀后期以來的“帕拉塞爾”相區別的主張。在對西方人士的專著、傳教士筆記、航海圖等資料詳細考察的基礎上,他認為19世紀中葉以前,西方記載的“帕拉塞爾”,為古“帕拉塞爾”,并非我國西沙群島,而是指靠近越南中部海岸并與該海岸相平行的、傳說相當危險的一群島嶼和巖石。19世紀后期,“帕拉塞爾”的名字才逐漸被用來指稱西人稱為“眼鏡”的我國西沙群島。
近年來,有學者進一步從地圖學及地圖測繪的角度探究“帕拉塞爾”問題,取得新的成果。如許盤清、曹樹基發表文章⑤許盤清、曹樹基:“西沙群島主權:圍繞帕拉塞爾(Paracel)的爭論——基于16—19世紀西文地圖的分析”,《南京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第19-34、157頁。,從16—19世紀西文地圖的分析入手,探討圍繞“帕拉塞爾”的爭論。王濤發表文章⑥王濤:“從‘牛角 Paracel’轉為‘西沙群島 Paracel’——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西人的南海測繪”,《南京大學學報》,2014年第 5期,第 35-47、158頁。從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西人進行的南海測繪,探討從“牛角Paracel”轉為“西沙群島Paracel”的歷史演變。前者著重分析西方地圖,后者側重研究西方對南海測繪與調查的歷史。他們認為Paracel最初指越南海岸線外一南北走向呈“牛角”狀的沙礁群,在丹尼爾·羅斯(Daniel Ross)與詹姆斯·豪斯伯格(James Horsburgh)推廣下,將之轉移到西沙群島,才造成兩個地理形態的重名與混淆。1830年以后,“牛角Paracel”從西文文獻中消失。越南所謂“黃沙”只能是“牛角Paracel”,塔伯爾特主教所記嘉隆皇帝插旗之處亦指“牛角Paracel”,而非豪斯伯格經過測繪的“西沙群島Paracel”。
張磊的研究①張磊:“關鍵日期視野下地圖為中心的越南南海主張非法性問題”,《河北法學》,2018年第8期,第85—100頁。則將地圖學與國際法上的關鍵日期概念相結合,指出越南對我國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主權聲索的非法性。他認為1975年5月15日是中越南海島礁爭端的重要時間節點,越南官方媒體發布越南全國地圖,將我國西沙、南沙兩群島劃入,稱為“黃沙群島”“長沙群島”,挑起了中越南海爭端。不同時期中國官方繪制的一系列南海地圖表明了其對南海諸島和海域主權訴求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但越南在關鍵日期前后的官方觀點和地圖卻存在巨大反差。他援引韓振華、戴可來等前輩學者的觀點,批判了越南作為主權依據的歷史地圖,并列舉法屬時期、五六十年代越南官方及西貢政權的一系列地圖,指明這些地圖或承認中國對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的主權,或未將其包含在越南版圖之內。他通過對比關鍵日期前后越南的官方主張和地圖上的這些反差,駁斥了越南的非法主張。
丁雁南的研究認為古地圖上的“帕拉塞爾”具有唯一性,但否定了嘉隆王在此插旗宣示主權的依據。其文章②丁雁南:“地圖學史視角下的古地圖錯訛問題”,《安徽史學》,2018年第3期,第20-26頁。通過比較分析,試圖復原有關帕拉塞爾的地理知識的產生、流傳、校正的過程,認為西方文獻和古地圖中不存在從古“帕拉塞爾”到“新帕拉塞爾”的急劇轉變。他又有文章③丁雁南:“兩個‘帕拉塞爾’之謎:地圖史變遷與西沙群島地理位置認知的演化”,《南海學刊》,2020年第3期,第77-87頁。運用“拼圖游戲”理論模型,梳理16—19世紀中、西方關于西沙群島的古地圖及其所含地理信息的傳承脈絡,指出17世紀中期荷蘭東印度船只在南海航行中發現西沙群島,所繪三角狀“普魯伊斯淺灘”(Pruijs Drooghten)是地圖史上對早期西沙群島局部的正確描繪,但并未勘正此前葡萄牙人錯繪的長條狀“帕拉塞爾”,只是將二者繪于一圖。對于越南聲稱的阮朝嘉隆皇帝曾于1816年登上“帕拉塞爾”插旗、宣示“主權”的問題,他的文章④丁雁南:“史實與想象:‘嘉隆王插旗’說質疑”,《南京大學學報》,2015年第 4期,第 88-101、158-159頁。認為《大南實錄》中并無直接的史料記載或佐證;塔伯爾特1816年尚未到達交趾支那,更不能接觸和參與阮朝朝廷活動,而是通過夸張的想象,把從別人那里獲知的阮朝“黃沙隊”的活動虛構成了一場威嚴雄壯的占領行為;19世紀早期的越南不具備科學測繪的物質條件和技術,也不具備產生現代意義上的領土主權思想的意識基礎。因而,越南提出“嘉隆王插旗”說是虛幻之說,缺少歷史依據,根本站不住腳。
谷名飛的文章⑤谷名飛:“再談‘嘉隆皇帝插旗’說的真實性——基于法國檔案的研究”,《南京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第69-78、159頁。依據20世紀30年代法國外交檔案材料,指出“嘉隆皇帝插旗”說是在法國外交部、殖民地部和印支殖民政府的指導參與下炮制出來的虛假說法。其主要依據是塔伯爾特對嘉隆皇帝在帕拉塞爾插旗的記載,而其“真實性”一開始就被負責資料搜集和研究的法國及安南官員所質疑。法國外交部在研究相關材料后也認為,以“嘉隆皇帝插旗”說無法主張法國對西沙群島的主權。
五、關于越南所謂“黃沙”“長沙”問題研究的若干認識
越南所謂的“黃沙”“長沙”問題原本是不存在的,有關歷史文獻的記載也非常有限。20世紀70年代,越南官方和學界出于攫取海洋島嶼主權與海洋權益的目的,制造了所謂的“黃沙”“長沙”問題,挑起了中越之間的海洋島嶼主權爭端。考察中越關系的歷史可以看到,在古代長時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中越兩國保持有密切聯系,以宗藩形式維系兩國關系。從古代到近代、現代的發展變化過程中,兩國關系逐步從傳統宗藩結構走向現代國家關系,但歷史上并無兩國間的南海爭端和所謂“黃沙”“長沙”問題。只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隨著現代海洋意識的成長,越南當局才以官方外交文件的形式制造了“黃沙”“長沙”問題,把“黃沙”“長沙”硬說成是南海中中國的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從我國學者關于越南所謂“黃沙”“長沙”問題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從越南所謂的“歷史依據”分析,越南文獻特別是海洋著述中關于“黃沙”“長沙”的記載,關于“東海”的記載非常有限。歷史上越南文獻中關于其東部海域認知非常有限,有多種名稱,僅將其近海海域稱為“東海”,文獻中偶有提及的“黃沙”“長沙”并不是有特定所指的地名,其具體含義需要具體分析;更不是兩組特定的、有具體方位的群島名稱,而是一種沿海岸和近海海域地理地貌的泛稱。當年,越南著名史學家陶維英在《越南歷代疆域》中曾認為,“黃沙群島”是還需討論的“特殊問題”之一。①[越]陶維英著,鐘民巖(戴可來)譯,岳勝校:《越南歷代疆域》,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第2頁。越南一些學者出于政治需要,對有關“黃沙”“長沙”記載進行擴大化、實用化和系統化的解釋,為官方挑起“黃沙”“長沙”問題提供學理支撐。
第二,中國學者對越南挑起的所謂“黃沙”“長沙”問題進行了多學科、多角度的深入剖析。經過我國學者從歷史學、地理學、文獻學、檔案學、測繪學和航海史等多方面的研究,證明“黃沙”“長沙”只是泛指越南東部沿海近海海域的島嶼與沙洲,與中國的西沙群島、南沙群島并無關系。西方文獻記載的古“帕拉塞爾”指越南近海島嶼和沙洲,到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帕拉塞爾”才指稱西沙群島。中國學者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各有不同,但基本觀點和研究結論都強調,不能把“黃沙”“長沙”、西方“帕拉塞爾”與我國南海中的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相混淆。
第三,從中國學者有代表性的觀點看,韓振華、戴可來、吳鳳斌、李金明、于向東、李國強等學者的研究共同點在于剖析越南官方和學界所依據的所謂“歷史典據”記載中的真正含義和自相矛盾之處,更從中國、越南和西方的史料以及古代越南航海技術、航海道里等方面進行深入的考證,辨明越南史籍所載“黃沙”“長沙”與我國西沙群島、南沙群島在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等方面存在的差異和不同,指出“黃沙”“長沙”并非我國的西沙群島、南沙群島,而是越南中部沿海的一些沙洲和島嶼。這些研究有力駁斥了越南混淆視聽的謊言,證明了中國對西沙群島、南沙群島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第四,中國學者目前的研究工作也有需要進一步加強的方面。一是近年來越南仍在全球范圍內廣泛搜集各種未曾使用過的資料,試圖建立和發展其“歷史依據”的證據鏈體系,而我國學者目前對新史料的追蹤、分析和研究尚有所薄弱。二是越南近年來爭取美國、日本、俄羅斯、印度等域外勢力介入南海爭端,尋求國際輿論支持,將歷史研究與國際法研究密切結合,試圖將南海問題訴諸國際司法或仲裁程序向我國施壓。如何利用歷史研究服務于國際法理斗爭,也是我國學界需要更加重視的。
第五,今后較長時期越南還會繼續堅持其所謂“黃沙”“長沙”問題上的立場,進一步加大其研究和宣傳力度。中國學術界對于此問題的研究還需要繼續深化,尤其是需要注重擴大研究成果的影響力,注重輿論話語傳播。在學術研究層面,既要堅持韓振華、戴可來等前輩學者奠定的基本學術觀點,又要結合中國在南海的航海史、貿易史和海洋史等多角度、多學科方向進行更深入研究,發掘更多越南自身材料反駁其非理非法主張。同時,還應進一步重視對越南現代海洋意識的發展和挑起南海諸島主權爭端過程的研究,揭示越南制造所謂“東海”“黃沙”“長沙”諸問題的方式與手段,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以正視聽,為維護南海主權和主權權益作出貢獻。
縱觀我國學界關于越南所謂的“黃沙”“長沙”問題的研究,可以看到非常可喜的是近年來一批年輕有為的學者正在成長起來,他們擁有較為扎實的學術研究基礎,能夠將歷史與法理研究很好結合,具有國際視野和運用現代化信息技術的能力,將會為我國南海諸島主權研究做出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