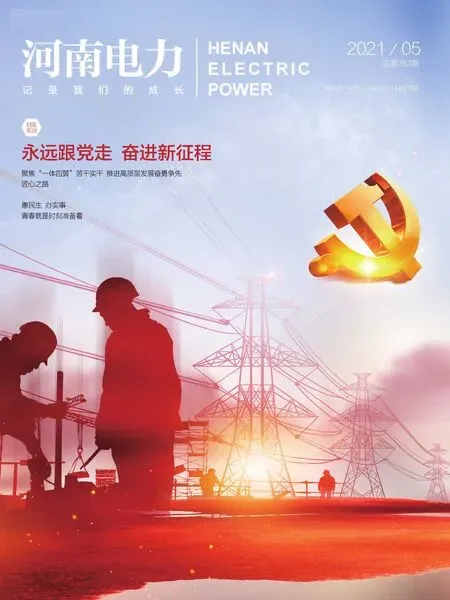與青年說
楊沁園
有時候我會問自己,到底什么是青年?
我曾經堅定地以為青年就是20歲無所顧忌的肆意,對所有一切都保有的好奇,是揮霍不盡的精力,是懵懂,是沖動,是仍然嶄新的夢想和對未來最初的渴望。
我曾經不愿意成為青年。因為在我看來,那些尚未被世俗磨平的棱角、那些仍未被生活澆滅的不甘、那些一次次不后退的嘗試都是不成熟的莽撞,所以我漸漸收起棱角,變得圓滑、世故;我一一藏起不甘,變得沉默、平靜。我不再沖動,我懼怕嘗試,在機會面前我總是怯于伸手,我總以時間、精力、記憶等各種各樣的理由把自己困在舒適區,我總是說機會都是留給年輕人的,我不后退,但我也不再前進。
可事實上,生活并不會因為年歲的增長而剝奪你的機會,它只會看你有沒有做好準備;命運也絕不因面容的改變就熄滅你希望的火焰,它只會評價你的渴望夠不夠深切。我停留在原地只因為我丟了那顆青年的心。
我有一位同事,他叫邢闖,一個20多歲的男孩子。他擁有著永動機一樣的熱情,臉上永遠帶著笑容。他喜歡鉆研業務,也樂于參加各種活動,對待每件工作、每次表演都給予發自內心的熱愛和毫無保留的付出。
他第一次讓我印象深刻是在某次紅色家書誦讀活動中,臨時救場的他,為了有最好的演出效果,晚上11點還在與我討論PPT的圖片選擇和時間設置,斟酌書稿的速度編排和情感表達。我跟他開玩笑說:“又不是比賽,那么認真干嘛?”他卻說:“在舞臺上展現的是我自己,和其他任何人無關。我習慣做最充足的準備,因為我要在每一次機會面前表現出最好的自己。”演出的那天,他的誦讀贏得了全場聽眾發自內心的掌聲,也讓更多的人深深地記住了他。
去年春天,國網遂平縣供電公司的駐村扶貧隊隊員進行到期輪換,得知消息的他第一時間就報了名。我們很驚訝他的選擇,也曾問他為什么要到鄉村去,面對扶貧路上的種種人和事,會不會曾感到一瞬間的疲憊和無力。之后,我們得到了一段出乎意料的回答:“可能很多人都會有一個改變世界的夢想,我也一樣。我出生成長于城市,可我的根扎在農村,我未曾經歷感受過貧窮,但貧窮曾映在我的眼中。我想改變這些。我希望貧困家庭能夠脫離貧困,我希望鄉村能夠建設得更美。可如果我只是坐在辦公室,那我能為他們做的是有限的,甚至有時是力所不及的。所以,當這樣實現夢想的機會來到我的眼前,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抓住它!我要到脫貧攻堅的一線去,我要到建設美麗鄉村的一線去,我要將電力產業的優勢更多更好地發揮出來,實打實地去幫助他們。我不曾感覺疲憊和無力,因為在追夢的路上,我有的是熱情。”
在那一刻,我看到他的眼里有光。我知道,這是一句很俗套的形容,可在那一刻,這虛無的形容在我這里有了具象。在那一刻,家國的未來愿景、企業的社會擔當和個人的抱負理想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在那一刻,我發現我所遺失的是屬于青年的力量。
那是尚未被社會打磨的棱角,卻可以沖破一切阻礙;那是未曾被生活澆滅的不甘,卻足以踏碎任何泥潭;那是不周全,是不經思索的沖動,卻拋灑出一往無前的堅定和永不回頭的執拗。
1919年,魯迅先生在《新青年》上曾發表過一篇文章,他說:“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時代不同,但青年卻始終在浪潮之巔,我們是創新者,我們是拼搏者,我們是塑造者,那些你認為應當改變的傳統,不要只是冷眼相對,用我們的發聲去改變它;那些你認為不合時宜的規矩,不要只是暗中鄙薄,用我們的力量去打破它;那些你所希望的更加美好的明天,不要只是隨口一說,用我們的崛起去創造它。一個人的光芒也許渺小,但當千萬人舉手,螢火也成星河,一個人的力量或許微弱,但若你足夠優秀,積沙可起高樓。尚且年輕的我們,不應當畏懼耗費時光的積累,而應當畏懼沒有時光;尚且年輕的我們,不應當畏懼機遇背后的困難,而應當畏懼沒有機遇。當舞臺帷幕就此拉開,我們要做的只有邁步,上臺。
民族復興百年,這腳下的熱土已開啟新的征程,時代長河奔涌,你我的拼搏亦有了新的方向。東風已至,何不乘風啟航,你若心有理想,自當展翅翱翔。成功將由你書寫,因為你生來優秀,未來會因你改變,因為你就是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