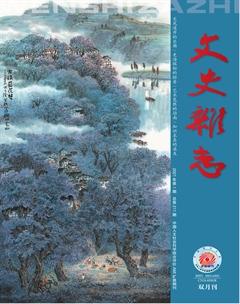好吧,我們回家
孟光全



2019年12月,中國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李建友老師的《內江舊聞錄》一書。這是一本對內江歷史文化“富礦”深入挖掘、真切記錄點滴記憶的文集。全書圖文并茂,由漢安流徽、文教熏染、革命浪潮、丹青遺墨、鄉土記憶、物華包容六部分組成,收文130篇,共66萬余字。
東漢順帝時,在內江設漢安縣,李老師對“內江·漢安”這方水土、鄉民一往情深,懷著對桑梓的愛、對文化的敬重,幾十年默默耕耘,孜孜矻矻:一則實地勘察、尋訪,包括文字筆錄、尋訪當事人、測量、攝影等,求真務實,做到言之有物;又博覽群書,廣泛查閱史書、方志、族譜家譜、地方契約、碑刻文獻、文集、筆記、專著專論、回憶錄等,做到了言之有據。這就使得其《內江舊聞錄》充實可信,足以傳世。
《內江舊聞錄》是在內江歷史文化這棵參天大樹上結出的一枚碩果,沉甸甸的。它的出版是內江文史界的一件勝事,可大大深化對內江歷史文化的認識,讓人對這方水土、鄉人頓生愛意,堪稱內江的《清明上河圖》。
縱向看,該書從內江出土的漢畫像磚石入手,梳理了隋唐、宋元明清、民國到現當代的內江舊人、舊事、舊物(文化遺址、遺物),畫就了一幅波瀾壯闊、璀璨輝煌的內江歷史文化長卷。其中寫明代、民國最詳,這是內江經濟、社會、文化最活躍、名人輩出、建樹最豐時期,堪稱內江史雙璧、兩個黃金期。
橫向看,全書內容豐富,經濟、社會、文化三位一體,實業與文化是全書兩軸:實業關乎國計民生,又與晚清、民國抗戰“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契合。作者如數家珍式地說了實業眾領域:農業、工業(糖、酒精、蜜餞、夏布與紡織等)、交通、金融、民間郵驛、倉儲、商業、餐飲、旅館等,敘寫平實簡明。內江古稱科舉之鄉、文獻名邦,今獲文化之鄉、教育之鄉、書畫之鄉、石牌坊之鄉等美譽。李老師富于人文關懷,悉心挖掘內江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內江詩詞文賦、著述、書畫雕刻、科舉、教育、出版與書畫裝裱等。
《內江舊聞錄》還點、線、面結合,立體寫內江曾有的輝煌——
“點”指一個個歷史文化名人,可分“走出去的內江人”“走入內江的外鄉人”,前者如王褒、趙貞吉、丈雪通醉、張善孖、張大千、范長江等,后者如黃云鵠、林同炎、魏巖壽、范旭東、李約瑟(英籍中國科技史研究者)、馮玉祥、黃炎培、老舍、豐子愷、沈從文等,出入交相輝映,共同譜寫了文化交流的雄偉樂章。內江自古“因航而興、因驛而興”,因此不保守僵化,勇于闖蕩大千世界,吸納外來文化。
“線”指一個個內江文化世家——劉家、高家、楊家、陰家、馬家、何家、梅家、趙家、張家等。這些家族瓜瓞綿綿,在公益慈善、教育、文化建樹、詩文書畫等領域都造福鄉民,反哺一方,成為內江文化星空里一顆顆璀璨之星,照耀這方水土。
“面”指內江舊日,尤其是明代、民國曾有的百業興旺局面——經濟繁榮、社會和諧、文化昌盛。
《內江舊聞錄》還動情地寫了內江豐富的文化遺址、遺物:古鎮古街、佛寺道觀、義渡、書院、牌坊、會館等。古鎮如椑木、白馬、東興、龍門、高梁、雙才等;街巷如民族路、桂湖街、蛋市巷、河壩街等;眾多以“義”字冠首的田、學、醫、橋、井、渡等,其中義渡最著名,素有“行遍州縣路,內江好過渡”的俗語。
佛寺如圣水寺。《內江舊聞錄》之《內江圣水寺及其名人緣》一篇就梳理了從宋到近代眾多高僧大德、文人墨客、書畫家、政治家、社會名流、學者、實業家等的圣水緣。一寺竟牽連出琳瑯滿目的有趣事兒、林林總總的卓有建樹的人物,有如《世說新語》“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頗讓人驚詫感懷。其實,從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可知,南北朝時佛寺作為全民共建、共享的文化空間(宗教的、文化交流的、政治的、集畫雕樂舞建筑園林于一體的藝術的、教育的、公益慈善的)就已發育健全了。佛寺在佛教中國化歷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社會文化功能十分重要而多元,與民眾有著密切關聯。
書中生動細膩描述了內江鄉土景觀之美,如言鷺瀾洞現有唐顏真卿,宋黃庭堅,明劉承祐,清胡微元、龔晴皋、黃云鵠、張船山、羅賜卿諸名家詩文、對聯、榜題等;又及堪稱詩書畫坊的“云霞古剎牌坊”——上刻釋本聰、王果、李春暄、劉稚、謝廷榮、張云衢、毛俊章、陳毓品、尤勤光、潘裕本、劉天衢、潘登瀛、陳文藻等諸家記、賦、詩、聯等及戲曲人物、花卉等,成為古典文學、書法、雕刻“三合一”的綜合性田野石質文獻。
隆昌石牌坊群數量多,門類齊,其歷史、社會、文化意蘊最是豐富。牌坊群位于成渝驛道上,借驛道將坊主事跡功德等口頭傳播開來,是富于表彰激勵性的公共紀念性建筑、敞開的公共文化空間。牌坊能體現古代良好的官民互動關系。其建立與維護,能體現民間社會組織機能、民間經濟實力,能培育共同的思想情感、文化心理,引導公眾一心向善。牌坊作為綜合藝術,聚建筑、詩文辭賦戲曲、雕刻書畫于一體,最能展現地方文化實力,見證書畫之鄉的文化璀璨。
美國約翰·布林霍夫·杰克遜在《發現鄉土景觀》一書中說,“景觀之美源于人類文明。我們看到的鄉土景觀的形象是普通的人的形象:艱苦、渴望、互讓、互愛。只有體現這些品質的景觀,才是真正的美的景觀。景觀不僅強調了我們的存在和個性,還揭示了我們的歷史。識別一處棲息景觀,棲居者都是憑感覺:公認的當地美酒佳肴的地道口味,特定季節的芳香,還有民歌的唱腔。”總之,內江鄉土景觀是美的,讓人流連忘返。
李老師較早關注沈從文在內江土改一事,他的《文學大師筆下的內江——讀〈沈從文家書〉》一文比較全面地梳理了沈從文家書的豐富內容與重要價值,稱其“除談及家事以外,筆墨多用于記錄、描寫內江所見鄉土民風民俗、蔗鄉的人文精神、舊時糖房的生產情況及資金,對表現和反思鄉村世界的文學的思考”;“正是這位蜚聲中外的藝術家留給內江人民,可惠傳百代的寶貴地方文獻”。應該說,“沈從文與內江”這一課題非常重要,沈從文的內江之行,是“內江一座城與沈從文一個人”的“共贏”。《沈從文全集》第十九卷收有沈從文于1951年11月8日到次年2月9日從內江雙才鄉(今鎮)寄妻、子家書36封,寄友人金野、楊振聲書信各一。沈從文曾自稱“鄉下人”。他關注內江“鄉巴佬”的勞動、生活,對內江農村民俗文物描述簡明生動,有時隨文線描,寥寥幾筆卻形神俱備,如那加鐵釘以防雨天路滑的釘鞋、“這里竹椅子都是宋代款式”、烘籠、大木甑、雙才老戲臺、神龕雕花長案、陶盆陶壇……沈從文在家書里寫道:“本地極好的紅陶質器,卻很少有本地人提起。本地的舊式木浮雕,到處都有極有價值的東西,在國內都可展覽,即以鄉村窗欞而言,也可以收集成一大觀”。沈從文的考古被尊為“抒情考古”,其背后是鄉民的勞動生活,是沈翁的溫情與體悟。從書信內容看,目前所見應該還不是沈從文內江書信的全璧,以后可能會有新發現。不過,這批書信是迄今為止內江外來者寫內江最詳、內容最豐富的歷史文獻,也是描寫生動細膩、淡淡抒情的最優美的白話文學。復旦大學張新穎在《沈從文九講》里說:“書信所包含的信息涉及諸多方面,豐富復雜,不可簡慢對待”。誠哉斯言!
稍加爬梳,歷史塵埃就會拂去,老舊的人、事、物就會鮮活起來,就會有血肉、有情意。也許,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幸福就在此吧!舊日中國,為迎接春節,很多地方都有“打陽塵”習俗,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天職也許就是“打陽塵”吧!
總之,《內江舊聞錄》內容豐富,文獻查閱、實地考察都詳實可靠,敘述簡明。由此我們不難看出:1.經濟繁榮、社會和諧、文化昌盛往往一體,陳垣說:“一個國家是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民族是長時期積累起來的”,多方面發展與長期積累缺一不可。2.民間有力量,民眾有活力、創造力。3.人才要有出有入,要有交流。經作者的苦心翻閱文獻、勘訪實地,那些時光中已漸漸模糊的先賢身影變得清晰,沉于塵埃中的舊事重又活現,那些牌坊、民間契約、摩崖題刻等的文化意蘊得以生動細致地揭示。
地方文史,應走兩條路:一是充分汲取中國傳統學術資源。古典中國,地方文史的著述、研究傳統很久遠,學術資源甚豐富,歷代史書、方志、譜牒、都市賦、筆記、竹枝詞等,都足資借鑒取用,依舊有學術活力,此舉一例: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專記洛陽佛寺,兩宋繼以《東京夢華錄》《夢粱錄》《武林舊志》《南宋臨安兩志》《剡錄》等,形成一文脈不斷的都市著述譜系。它們直接推動朱自清寫成《歐游雜記》《倫敦雜記》,并直接催生法國漢學大師謝和耐之漢學巨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的誕生。二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歐美已有的西方新文化史學派、年鑒學派(可參考辜振豐《布爾喬亞:欲望與消費的古典記憶》),關注社會與文化、勞動與生活的“全部”;中國都市史研究方面,美國施堅雅和日本的一些漢學家都已著先鞭,成果不俗。我們很可以借用這些“利器”,使地方文史關注的空間更大,更具國際視野;讓地方文史更有滋味,從而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
“漢安·內江”有美食可咀嚼,有先賢可景仰,有溫婉可人的民俗可依戀,有蘊含無限情味的舊址可流連,有“老物件兒”可撫摩——上面隱隱還有祖輩的手澤與溫情、勞動生活的智慧情思……
這就是我們的“家”。
好吧,我們回家。
(題圖為內江隆昌牌坊之一)
作者:內江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四川張大千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