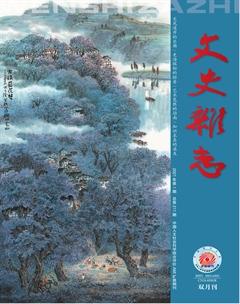關于“烏臺詩案”
陳星蒙 錢玉趾


北宋元豐二年(1079年),發生了一起后人稱為“烏臺詩案”的文字獄。事件的主角是北宋著名文學家、學者、書畫家蘇軾(1037—1101)。英宗時,他以進士出身入判登聞鼓院,后入史館修起居注。王安石擬行變法時,蘇軾向神宗上書陳說新法之弊。神宗便單獨召見他,想聽聽他的具體意見。《宋史·蘇軾列傳》記載了他對神宗的直言:“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愿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后應之。”《宋史》本傳講,神宗聽到這毫不遮掩的話,“悚然”,就是恐懼害怕。蘇軾隨后在開封府代理推官任上又聽說宮內為上元節置燈,指名要最好的浙燈,卻要燈商折價。蘇軾又上書神宗認為“此事至小,體則甚大”,神宗只好下詔不買了。《宋史》有意無意間記的這兩件事,其實為“烏臺詩案”的發生埋下了伏筆。蘇軾之所以從神宗身邊被趕到開封府(處同一座城市),雖說是王安石忌憚他而使的壞,但沒有神宗的批準是不行的。看來神宗對他是敬而遠之。王安石的新法正式推行后,蘇軾再次向神宗上書論新法之“不便”,卻又暗含批評說神宗不顧人心向背。《宋史》本傳說,他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自知不見容于當軸者,遂自請外放,先后赴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職。雖說一路能聲不斷,但他卻閑不住思想,總愛用筆和墨去議論朝政。不過,所用乃是《詩》的比興手法與《春秋》筆法。盡管如此,也還是令朝廷頗難受。
元豐二年,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等將搜集到的蘇軾在地方上所作詩文、包括給皇帝的上書制作成厚厚的四大冊,再加上他們的分析報告,上奏神宗。神宗遂以“謗訕朝廷”罪在湖州逮捕了他,投入汴京(今河南開封)御史臺監獄受審。由于御史臺吏舍的柏樹叢中常有數千烏鴉棲息,故而御史臺又稱為“烏臺”或“烏府”,因此,蘇軾此案遂以“烏臺”得名。蘇軾系獄四個月,自己也承認“作詩賦等文字譏諷朝政闕失”等。友人在他死后的墓志銘上載明:“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托事以諷,庶幾有補于國。”[1]《宋史·蘇軾列傳》說,后來“神宗獨憐之”,實際這是神宗一手炮制的詔獄,目的是給蘇軾一個教訓,讓他從此停住思想,少管政事、國事。蘇軾出獄后,被安置到黃州做團練副使,但“不得簽書公事”。此案受牽連的25人(接受過蘇軾詩文者),王詵、蘇轍、王鞏3人謫降,自張方平以下22人罰銅。這25人被視為與蘇軾同聲相應者。神宗讓他們也從中受到“教育”,從此噤聲。
到了當代,余秋雨先生卻在《黃州突圍》這篇文化散文里將“烏臺詩案”中蘇軾的不幸,輕率地指為系小人所害,是遭小人嫉妒的結果:“批評蘇東坡的言論為什么會不約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簡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蘇轍說的那句話:‘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響亮,能把四周的筆墨比得十分寒磣,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點狼狽,于是引起一部分人酸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腳地糟踐。……在這場可恥的圍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當了急先鋒。”[2]蘇軾的原話,見于南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十·東坡五《元城先生語錄》云:“元豐二年,秋冬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子由曰:‘……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爾;今安道之疏乃云:其文學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這里的關鍵詞語不在于“名太高”,而在于“與朝廷爭勝爾”(余秋雨先生未全引,有斷章取義之嫌),這才會“激人主之怒”;而他人的攛掇,只不過是外力助推罷了。
蘇軾自幼飽讀詩書,忠公體國,具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他自認“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沁園春·孤館燈青》)。“胸中萬卷”指他的學識才情,是他報國的憑依,亦是他能夠清高豪邁的資本。但是,他“致君堯舜”的滿腔熱情以及與之相應的一肚子不合時宜的思想使他在新舊兩黨當權時都遭到打擊。明末毛晉所輯《東坡筆記》載有一則故事:“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蘧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為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為當。至朝云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入時宜。坡捧腹大笑。”朝云“敏而好義”,在蘇軾遭貶,他的幾個小妾相繼離去的情況下一直追隨其南遷,義無反顧。這位紅顏知己頗識愛人志趣,故能深得蘇軾歡心。當她說出“學士一肚皮不合入時宜”之語時,蘇軾甚為自得,言:“知我者,唯有朝云也。”可見蘇軾的性情,實在太耿直;思想實在太自由,又加上胸懷報國之志,這才會不知進退,率性而為,以至口無遮攔,想啥說啥,想啥寫啥,給世人造成“與朝廷爭勝”(連其弟蘇轍也這么認為)的印象。如此,他要遭到朝廷打擊,也便是早晚的事。誠如蘇軾后來在《杭州召還乞郡狀》(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的檢討所說:“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和,進用可必。”(《蘇軾文集》卷三十二《奏議》)顯然,如果蘇軾雖不贊成變法,但倘能采取沉默是金的態度,不公開評論、反對,也不會被彈劾、入獄,遭貶謫。
《宋史·蘇軾列傳》講蘇軾激烈反對王安石新法,令后者大為不快,但未講王安石是否參與了李定、舒亶對蘇軾的構陷。按照王安石的人品,想必不會去落井下石的;否則,蘇軾不會在元豐七年(1084年)七月,由黃移汝(由黃州團練副使遷汝州團練副使)途中,路過金陵(今南京)時去拜訪已經失勢的王安石而推心置腹,相談甚歡。[3]相傳王安石聽說蘇軾下御史獄,曾發出話來:“豈有盛世而殺才士者?”“不知更幾百年,方有此人物!”其憐才惜才之情,溢于言表。而他的弟弟王安禮(時值舍人院、同修起居注)在蘇軾“勢危甚,無敢救者”之際挺身而出,向神宗直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宋史·王安禮列傳》)云云,恐怕也是受到王安石的鼓勵,甚或就是代王安石傳話吧?
蘇軾后來的獲釋,乃是王安禮、吳充、章惇(他也是蘇軾的政敵)、張方平、范鎮、蘇轍以及仁宗之后慈圣光獻曹氏等各方面多方奔走、大力營救的結果。這當然也說明其時文壇、政壇的整體氛圍不是妒才而是愛才;不是文人相妒、相輕,而是惺惺相惜;盡管也有李定、舒亶等小人興風作浪,但終未成大勢。
但話又說回來,中國封建社會原本就是皇權作主的社會——盡管其間不乏廣開言路、以兼聽相標榜的所謂政治清明的時段(典型者如貞觀之治),但總體而言,皇帝乾綱獨斷,是不容許旁人置喙的。“烏臺詩案”的實質,是在新舊黨爭的幌子下,封建統治者為維護皇權,掃除威脅皇家利益的障礙而用高壓手段來控制士民的思想,繼而操縱輿論、控制言路的政治迫害。統治者以天下為家天下,讓天下人只準對自家唱贊歌,不準提不同意見乃至反對意見,從而在宋代開了一個以言獲罪、以文字獲罪的很壞的頭,對后世造成極大的影響。誠如張方平《樂全集》所言:“自夫子刪《詩》,取諸諷刺,以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故詩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當世之事,話涉謗黷不恭,亦未聞見收而下獄也。”[4]
注釋:
[1][4]孔凡禮:《蘇軾年譜》上冊,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450頁,第464頁。
[2]余秋雨:《摩挲大地》,華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81頁。
[3]參見孔凡禮:《蘇軾年譜》中冊,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638頁—642頁。
作者 陳星蒙:四川省科普作家協會會員
錢玉趾:中國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