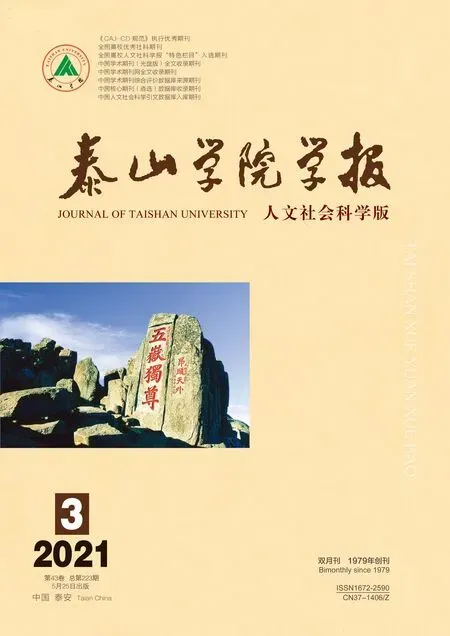唐《靈巖寺碑頌并序》碑考
楊 陽,王 晶
(1.濟南市考古研究所,山東 濟南 250000;2.山東女子學院,山東 濟南 250300)
長清靈巖寺有唐代書法家、文學家、北海太守李邕撰書的《靈巖寺碑頌并序》碑(以下簡稱《靈巖碑頌》)一通,自宋代趙明誠《金石錄》著錄后,為歷代文人史家所關注。如清代阮元《山左金石志》卷十二、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十七、吳榮光《石云山人文集》卷五、李葆恂《三邕翠墨簃題跋》卷一,近代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卷七七、方若《增補校碑隨筆》等均有考釋。當代溫玉成、馬叢叢也各有考論專文(1)溫玉成.李邕“靈巖寺頌碑”[A].中國佛教與考古[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512-522.。筆者對此碑內容擬作進一步研究,試揭析其中所蘊寺史滄桑,以就正讀者。
一、《靈巖碑頌》現狀與碑文校錄
《靈巖碑頌》今嵌魯班洞遺址內西墻壁,碑系青石質,碑面磨制拋光。原有蟠龍碑首及方形碑座,今僅殘剩碑首和身,且碑身斷為上下二石鑲嵌于石墻之上。碑首左側顯露的立面(碑身與嵌墻之間的縫隙觀之)雕有四條下垂的蟠龍,殘存的龍首長0.30米,下垂至碑面的上邊沿;靠近碑面的兩條蟠龍遭人為毀壞,留有痕跡。碑面的左上角留有一長0.50米、寬0.30米的長方形糙面(與垂龍水平雕飾),應是碑面碑首雕飾遭人為破壞而致。蟠龍碑首與碑身為一石體,碑首的雕飾布局呈拱券式結構。碑身左邊加工規制,抹角,為碑刻的原始之作;右邊呈人為錘砸痕跡,碑首缺少與糙面對應的碑體部分,去除了李邕頌文以外約1/3碑體。今碑殘高2.27米,寬1.06米,厚0.52米。碑文行書,凡刻21行,滿行43字,字縱3厘米,橫2.5厘米,行距1.5厘米,字距2厘米。今將原碑文字校錄如下:
靈巖寺碑頌并序
靈昌郡太守(以下殘)
邕以法有因,福有緣,故得真僧戾止,神人告祥,宜(以下缺24字)或真空以悟圣,或密教以接凡,謂之靈巖,允矣。真(以下缺24字)晉宋之際,有法定禪師者,景城郡人也。嘗行蘭若,(以下缺24字)若是者歷年,禪師以勞主人,逝將辭去,忽有二居士(以下缺23字)建立僧坊,弘宣佛法,識者以為山神耳。因(以下缺23字)夫山者,土之至厚;谷者,虛之至深;水者,因定而清。林(以下缺23字)貝葉之經衡,岳廓蓮花之會,獨人存法立事,著名揚(以下缺23字)空,矧乎辟支佛牙,灰骨起塔。海龍王意,貿金(以下缺11字)志尤□見□□□則有□□□仍舊。昔者州將厚具,邑吏孔威,廣□支供,多借器物,□義□□。解脫禪師以杖叩力士脛,曰:令爾守護而送之,仍施絹五十匹。□若武德阿閣,儀鳳堵波,□高祖削平之初,乃發□弘愿。高宗臨御之后,克永光堂,大悲之修,舍利之□,報身之造,禪祖之崇,山上燈□,□切宇內。舍那之構,六身鐵像,次者三軀,大號金剛。□□增袤。遠而望之,云霞炳煥于丹霄;即而察之,日月照明□□道耳。皆帝王之力,舍以國財,龍象之□□□□,二□□宕植之不生,汎于草間,穢于垅上。職由□□保眾,茂慮道摧。□清凈之田,解昏迷之縛。不然曷□律,住持入慧之境;恐繁文字,削筆杪于連章;思廣闕遺刻,陰圣于別傅。大德僧凈覺,敬惟諸佛□□。上座僧玄景、都維那僧克祥,寺主安禪,或上首解空,或出□□義。僧崇憲、僧羅喉、僧零范、僧月光、僧智海、僧□永言悟入,大啟津梁,咸高梯有憑,勝宅自照,仍依俗諦,典碑,宛委昭宣,弘長增益,桃源失路,迷秦漢而□□天長。其詞曰:
倬彼上人,巍乎曾嶺,冥立福地,神告□□。爰始幽居,逝言遐映,寂用內照,塵勞外屏。其一
□□□宮,歲時建置,今古齊同,磴道逶迤,霞閣玲瓏。其二
□□效靈,觸類元相。扶持凈域,警誡州將,延集□□。其三
□□岳寺,臺之國清,岱之北阜,蒲之西陘。是人依法,即事聯聲,宜□□二,誰云與京。其四
碩德勤修,真□□□,□哉轉覺,以極斯萬。其五
大唐天寶元年歲次壬午十一月壬寅朔十五日景辰建。
按作者李邕(678—747年),字泰和,廣陵江都(今江蘇揚州)人,祖籍江夏(今湖北武昌)。歷任戶部員外郎、括州(浙江麗水)刺史、靈昌郡(河南滑縣)太守、北海(渤海)太守等職,后人稱之謂“李北海”。該碑文即是在天寶元年(742)任靈昌郡太守時所作。李邕在文章、書法方面有著卓越的成就,博學多才,行書師從羲之王體,且不受限,將魏碑楷法融入,以楷書為體,行書為勢,創立了“行楷大字”書體。《宣和書譜》云:“邕初學,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即得其妙,復乃擺脫舊習,筆力一新。李陽冰謂之‘書中仙手’。裴休見其碑云:‘觀北海書,想見其風采。夫人之才多不兼稱,王羲之以書掩其文,李淳風以術映其學。文章書翰俱重于時,惟邕得之。’當時奉金帛而求邕書,前后所受鉅萬余,自古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觀邕之墨跡,其源流實出于羲之。議者以謂骨氣洞達,奕奕如有神力,斯亦名不浮于實也。”杜甫作歌以美之曰:“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制。”為世之仰慕,率皆如是。其文章、書法在歷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李邕書法以碑版為多,且書碑版皆是親自撰文,流傳至今有數種碑帖,影響最大者為《李思訓碑》《麓山寺碑》和《靈巖碑頌》碑,三者在書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靈寺碑頌》是現存記載靈巖寺歷史最久、內容最多、信息量最為豐富的碑刻史料,是填補盛唐以前記載的重要文獻。
二、法定來山與靈巖始創
碑文中載:“晉宋之際,有法定禪師者,景城郡人也。嘗行蘭若,(以下缺24字)若是者歷年,禪師以勞主人,逝將辭去,忽有二居士(以下缺24字)建立僧坊,弘宣佛法,識者以為山神耳。”說的是東晉末至劉宋初之際(約公元420年左右期間)法定禪師常云游各地的佛教寺院,如此經歷了若干年。法定云游到靈巖,當時的靈巖還不具備正式佛教道場的等級和規模,似是一個小型的傳教場所,應是朗公初創于“十八畝地遺址”的講經處(朗公石東南約百余米)。居住一段時間后,感覺到給主人添些麻煩,勞煩于人,決定離開。一夜醒來,出現兩位居士建造的僧坊,是為弘揚佛法而建。僧坊出現得很突然,人們認為是山神營造的。由此,把法定禪師挽留下來,開始了靈巖寺規模道場的正式創建。故此,史料通稱法定為開山祖師。
關于法定到來的細節,后人賦予神奇般的佛教色彩及傳說。金皇統七年(1147)陳壽愷撰書的《濟南府靈巖寺祖師觀音菩薩托相圣跡序》碑載:“夫靈巖大剎,昔自祖師觀音菩薩托相梵僧曰法定禪師,于后魏正光元年(按:年代有誤)始建道場,興梵宮,居天下四絕,境中稱最,而世鮮知其由。我祖師其始西來,欲興道場于茲也,前有二虎負經,青蛇引路,捫蘿策杖,穿絕壁而不可登,乃徘徊于南山之巔。面石之久,感日射巔峰成穴,透紅光于數里。師乃躅光而下,美其山林秀蔚,可居千眾。道遇村人,亦異人也,顧師而言曰:‘師豈有意于茲,患其無水耶?回指東向不數里可得之矣。’師既徐行,則有黃猴顧步,白兔前躍,俄驚雙鶴飛鳴,其下涓涓,果得二泉。又擊山泐,隨錫杖飛瀑并涌,遂興寺宇,逮今八百余年。”說法定來靈巖時,是觀音菩薩的法身托化成法定禪師的形象,并有雙鶴同飛、青蛇引路、白兔前導,側有黃猴隨步,后有二虎托經等動物的陪伴,有卓錫、白鶴、雙鶴泉的出現,打造出“五步三泉”的意境,其畫面氣勢浩蕩,前后映照,頗顯神秘,達到大力渲染佛教盛事來臨的效果,增強人們對佛教的崇敬感。金明昌七年(1196)黨懷英撰并書的《十方靈巖寺記》碑文又載:“四眾驚異,檀施云集,于是空崖絕谷化為寶坊。”驚動四方,引來大量的捐資信士,將絕崖幽谷營造成佛教的道場。
法定禪師創建的寺院,據清版《靈巖志》載:“至孝明帝正光初(按:年代有誤),法定禪師始建寺,為開山第一祖。原建之寺在今寺東、甘露泉正西。”調查所述遺址,果如志書所云。在現靈巖寺院落東端的上山出口,拾級登道北行約120米處,向北至絕景亭遺址的登山道處之間約為167米,有三道東西向的人工堰堤,其構成的塊石形體龐大,盡顯蒼老,石縫長出的柏樹幾近千年,形成了三級院落平臺。在第一、二級平臺院落的后部遺有疑似大殿的臺基,相貌極為滄桑。在該遺址的東側溝壑底部,發現一殘動物圓雕刻石,石質砂巖,顆粒略粗。殘長0.68米,殘寬0.68米,厚0.33米,為動物的下半身,通體刻有鱗甲,身軀直筒略顯扁平,有脊椎凸起,似蛇形態;右腿幾近殘缺;左腿猶如嬰兒腿狀,大腿、膝蓋、小腿俱全,全覆鱗片;足的形制前段殘缺,腳腕、腳面、腳掌、腳踝俱有,且不帶鱗片,為自然彎曲狀。腰身的兩側空間,鑿有菱形紋雕刻,凸顯蒼老,與靈巖寺倉庫里殘存的北齊晚期半截蟠龍圓形石柱上的幼龍下身極為相似,其風頗古,實屬難得,彌足珍貴。
三、高祖弘愿與閣塔肇建
碑文載:“……武德阿閣,儀鳳堵波,□高祖削平之初,乃發□弘愿……。”從文字記載中知道,唐朝建立初期,高祖李淵誓發弘愿,在靈巖寺要完成“阿閣”等宏大建置。武德(618—626)是唐朝建國高祖李淵的年號,查李淵與宗教的信息,主要對三教是采取以儒為主體,調和并用的政策,對佛教既不崇信也不排斥,充分利用儒釋道三教勢力,相互平衡,為其政權服務。
從碑文前的“阿閣”,到后面頌文的“霞閣”,非常清楚是指“證明功德龕”。“閣”,應是唐代人對石窟概念的稱謂,在這里指的是方山頂處的積翠證明功德龕。碑文后面的頌文贊曰:“歲時建置,今古齊同,磴道逶迤,霞閣玲瓏。”自始建道場踏著過去同樣彎彎曲曲的臺階山道到達太陽最早照到的“阿閣”,在這里就描寫成了“霞閣”,玲瓏俊美。按照頌文所指定的起點攀蹬,道路形制、方向、目標矢的、時間照耀的效果與碑文記載極為吻合,且史料記載造像初創的大體時間亦極為相近。明隆慶五年(1571)山東布政使王宗沐《東游記》稱:“登高閣以望群山,翠圍四合漱玉泉、轉輪藏、鐵袈裟。”山道的盡端即是證明龕造像處,也是最佳瞭望群山勢景的地點,這里的“高閣”勢必也是指證明功德龕。“閣”的建筑就單體而言,要比殿堂體量高,古人對高處的建筑工程通用“閣”來冠以稱謂,應是古人的慣用做法。由此,為實現某種意愿于武德年間開鑿石窟造像,是史料首次揭出高祖佛教活動的具體事件,應是可信的。
唐大中八年(854)鐫刻于其佛座下的題記中,講述唐初有一男孩善子為“求無上正真之理”而舍身的故事,“乃鑿此山成龕立像,旌之曰‘證明功德’”(大中八年題記),其造像即名謂“證明功德龕”。高祖造像的緣由借用于此,低調做出開鑿造像的佛事活動,潛意識地做出佛事功德,以撫慰多年戰爭后心靈上的某種安慰,應是受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隋文帝崇信佛教行為的影響。選擇泰山靈巖,距京城遙遠,避免發生宗教爭執。同時,靈巖位居泰山,歷史上的“行徒清肅”“勵節弘規”(2)[唐]釋道宣.續高僧傳[M] .北京:中國書店,2019:176-178.早已聞名,選擇靈巖為最佳處。
到了唐“會昌法難”時,“毀去佛□,天下大同……所奉驅除,略無遺孑。惟此龕佛像儼然,微有董殘。”(3)見該佛座唐大中八年題記。靈巖寺遭到空前毀滅,只有證明功德龕造像保留下來,此非一般功德主所能,定與高祖李淵這個大功德主有關。
唐朝皇帝的第二項弘愿是“儀鳳堵波”。儀鳳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九個年號。“堵波”是佛塔的梵音,碑文中記載儀鳳間(676—679)靈巖建造過佛塔,即碑文中所說的“矧乎辟支佛牙,灰骨起塔”,即營建的辟支佛牙舍利塔。所謂的辟支佛,即辟支迦佛陀的略稱,意即“緣覺”“獨覺”。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七《婆羅尼斯國·鹿野苑》中載阿育王塔“其旁窣堵波,是五百獨覺入涅槃處。”由此可知,歷史上有眾多的小乘佛。碑文繼續載道:“解脫禪師以杖叩力士脛,曰:令爾守護而送之,仍施絹五十匹。”解脫禪師用錫杖敲打護送舍利牙護法力士的小腿說:命令你們好好守護舍利,安全送達,還施于靈巖寺五十匹綾絹。由此說明,碑文記載“灰骨起塔”的辟支佛舍利牙是唐初的解脫和尚贈送給靈巖寺的。唐《續高僧傳》卷二六《代州照果寺釋解脫傳》有載,俗姓邢,臺山夾州人,年輕時“遠近訪法,無師不詣”。后居五臺山佛光寺數十年,專崇華嚴。永徽中(650—655)卒。由此推之,解脫應是隋代過渡到唐代初期的和尚。明代釋鎮澄纂《清涼山志》卷四《解脫和尚見圣傳》云:“解脫和尚……嘗于(五臺山)東臺麓,于三昧中,見諸佛現,佛并為之說偈。”說明解脫和尚是相信“諸佛”的。
般舟殿遺址上遺有斷為兩節的八棱石立柱,刻有功德銘殘記,摘取文字地名時代特征集中縮減為:“……施主鄆州(今山東東平)張元斌合家供養……施主兗州(今山東兗州)役韌節合家供養……舍利塔主長清(今山東長清)邑尼靜修合家供養……舍利塔主魏州(今河北邯鄲)游棘將軍張義方妻供養……舍利塔主博州(今山東聊城)前□兗州□□二縣尉宋貞國供養……舍利塔主濟州(今山東茌平)郭懷合家供養……。”無紀年。以上六處古地名同時稱謂于同一時間段的時間為唐武德五年(622)至調露二年(680)之間,時間上吻合對接解脫禪師贈送舍利起塔。各地施主捐資建造的舍利塔,即是碑文記載的“辟支佛牙,灰骨起塔”無疑,明確為儀鳳(676—679)年間建造。碑文又載:“昔者州將厚具,邑吏孔威,廣□支供,多借器物……。” 寺院建造佛牙舍利塔,是地方官府的一件大事,州府贈送眾多的法器,官吏也大力造勢,積極獻力,廣泛支持擁護靈巖寺舍利塔的營造。
唐代辟支佛塔的營建時間,早于天寶(742—756)年間始建的千佛殿。從魯班洞遺址下底的營建平面地形看,因創建千佛殿鑿崖挖壁,產生大量的渣石土方,直接推至南面的溝壑,山洪夾雜著泥沙不斷沖擊,加速魯班洞周圍的淤積,致使其深陷地勢。同時,墊基拓展出現今寺院的院落基礎,為宋代時期建造五花殿、獻殿等提供了可能。因此,當時的千佛殿以南是不可能建造舍利塔的。加之《舍利塔功德銘柱》發現于般舟殿遺址,且當時的地理環境沒有千佛殿的存在,般舟殿前相對開闊平坦,佛塔選址應于北齊時期始建的般舟殿設計相配置。依據唐代初期佛塔在寺院中的地位及其寺塔關系的設置規律,應與般舟殿同軸安置,營造于般舟殿軸線的正前方,大約現今大白果樹前一點的位置。
“儀鳳堵波”的舉動應是唐帝受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隋文帝頒賜舍利于各地建塔的影響,將五臺山解脫法師收藏的辟支佛牙舍利,于武德年間送達靈巖寺,后又瘞埋于儀鳳年間營建的辟支佛舍利塔地宮內。1995年般舟殿遺址發掘現場未發現該佛塔的建筑構件,推測該塔為全木結構構造,至唐會昌五年(845)滅佛運動被毀。此次發掘至般舟殿臺基地平,亦應是唐辟支塔營造的地平,塔下地宮一般約在地平下1—2米處起券砌室,因此,般舟殿遺址的發掘工程沒有觸及到佛塔地宮的結構,有待于今后的清理發掘,得以進一步證實。
佛塔的建造對其寺院的影響是深遠的。自宋代淳化五年(994)西移重建磚石結構的辟支佛塔,竣工于嘉祐二年(1057),前后營造六十余年,氣勢之浩大,結構之精巧,為國內佛教建筑之精品。值得注意的是,該塔基座周圍原雕刻有四十幅浮雕畫面,八角臺基每面五幅,現存三十七幅;各角蜀柱雕護法力士像。宋代的重建,是“儀鳳堵波”供奉影響的繼續,該塔阿育王故事內容的鐫刻,進一步體現出營造主效仿阿育王頒賜舍利于各地建塔的意圖。在宋代重建辟支塔體上似乎感覺到唐代始建辟支佛牙舍利塔的相關文化因素,原有的唐代佛塔極有可能載有阿育王的內容,才有宋代重建時的傳承繼續。建塔的功德主淋漓盡致地仿效阿育王的做法,低調地在靈巖寺營建辟支佛塔,并賦予阿育王相關的文化因素,以顯示自己是當朝的阿育王在世,此非李淵所不能也。
唐會昌五年(845)滅佛,乃是國家行為,毀塔是預知的。當事的寺僧很大可能將瘞埋于塔內地宮的辟支佛牙舍利提前取出,收藏于寺內保存下來,成為宋淳化年間(990-994)又重建辟支佛塔的因由。否則,宋代僧人可以建造其它大乘佛教的舍利佛塔。因此,瘞埋于現存辟支佛塔地宮內的法物舍利,極有可能就是山西五臺山佛光寺解脫法師遺贈的辟支佛牙舍利,有待于今后新發現資料的證實。
四、高宗臨御與靈巖繁興
《舊唐書》卷五《高宗本紀》載:“(麟德二年)十二月丙午,御齊州大廳……命有司祭泰山。丙辰,發靈巖頓。……麟德三年春正月戊辰朔,車駕至泰山頓……。”高宗與皇后武則天自麟德二年(665)初冬十月啟動封禪,從東都洛陽出發,至十二月來到齊州(濟南)官府大廳,前后逗留九天,于丙辰日臨御靈巖。自來到靈巖寺的丙辰日至麟德三年(666)春正月戊辰日到泰山,中間有二十四天的時間,是在靈巖駐蹕,從中可見帝后對靈巖的喜愛。另有高宗隨從大隊人馬的食宿接待,顯示出靈巖寺的房舍規模及接待能力。事后朝廷發出旨令,齊州免除一年半的賦稅,正與此駐寺之舉相關。
“高宗臨御”之后的靈巖寺進入高速發展期。該時期的遺物至今留存的有千佛殿、慧崇塔及塔林晚唐時期的墓塔基座一個。碑文載:“高宗臨御之后,克永光堂,大悲之修,舍利之□,報身之造,禪祖之崇,山上燈□□切宇內。舍那之構,六身鐵像。次者三軀,大□金剛,□□增袤。遠而望之,云霞炳煥于丹霄;即而察之,日月照明□□□道耳。皆帝王之力,舍以國財。”指出唐麟德二年“高宗臨御”之后,靈巖寺發生很大的變化,使寺廟建筑“克永光堂”。修造了大悲觀音菩薩閣(殿),營建了辟支佛牙舍利塔,建造了供奉報身盧舍那佛的大殿和祖師殿,山上的長明燈照耀的廟宇亮麗。寺院鑄造盧舍那佛像,另外還鑄造了六尊鐵像,又鑄造了三尊等級較低的護法金剛像。對應古文獻在現存實物中找到的有觀音殿、舍利塔、祖師殿、長明燈座、金剛像,下面依次對應敘之。
清康熙版《靈巖志·殿閣》載:“后土殿在御書閣東。”又載:“祖師殿亦名定公堂,在后土殿東,今廢。”“達摩殿即袈裟殿,在祖師殿東北崖上。”“觀音殿亦名五氣朝元殿,在達摩殿東。”按照《靈巖志》敘述的順序排列自西向東依次為:御書閣、后土殿、祖師殿、達摩殿、觀音殿,這是法定開山創建道場的原始道路,宋代以前進出寺院道場皆通過此路往返。1995年魯班洞遺址發掘,遺址北部石券拱橋對接處出現路面的文化地層,與橋等寬,說明當時進入寺院是從山門功能的魯班洞殿堂后門進入靈巖寺的,正北登道直行到般舟殿、御書閣,再東北向到后土殿,由所說的原始古道進入早期寺院。由此觀之,盡管現今的西院落在唐代以前就營建了魯班洞和般舟殿,但“高宗臨御”后的主要營建活動還是以早期的東寺院落為主要道場,并開始出現向西寺院落過渡發展的趨勢。
辟支塔營建于西寺院的般舟殿前;大悲菩薩觀音殿、報身盧舍那佛大殿始建于東寺院內,且盧舍那佛大殿應為主殿。“高宗臨御”靈巖時,皇后武則天隨至。河南龍門石窟奉先寺盧舍那佛“……皇后武氏助脂粉錢兩萬貫……至上元二年乙亥十二月三十日畢功。”(4)劉景龍.奉先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1.由此證明武則天是信奉盧舍那佛的。此次來靈巖,專門營造奉祀盧舍那佛的大殿及造像,是非常大的耗資工程,非一般人能為之。故而推測,此項工程極有可能承武后懿旨。盧舍那佛大殿及佛像被唐“會昌滅法”毀掉,不見遺跡。另據宋李公顏《金像記碑》記載,寺僧惠從于治平二年(1065)將在錢塘江(杭州)制作的盧舍那佛搭船運至靈巖寺。至明成化十三年(1477)信士孫海通發愿募施,用銅五千斤鑄造的佛像還是盧舍那佛,兩尊佛像至今仍供奉于千佛殿內。此乃武氏懿旨寺院奉祀盧舍那佛意圖的持續發效,其影響力是深遠的。
“禪祖之崇”供奉的是禪宗祖師達摩,結合碑文中的“六身鐵像”,應是禪宗祖師達摩開始至唐代的禪宗六祖,其順序是:初祖菩提達摩、二祖惠可、三祖僧燦、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神秀。“六身鐵像”的鑄造時間應在開元(713—741)以后完成。夜間照亮寺院的長明燈,在1995年發掘的魯班洞遺址附近,發現刻有紀年“大唐開元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歲次戊午乙亥朔比丘僧范敬造石燈臺一所。”石燈座三件,是兩個個體的石燈座。另據般舟殿遺址上刊有唐永徽元年(650)石柱功德題記載“……慧炬恒燃建長明燈鎮修供養□一光一起通明十方鐸一桷一嵬……乘長明燈長涉篤呼……慈燈慧明萬德□□十為虔主見聞。”三處提有長明燈,且有“一光一起通明,十方鐸一桷一嵬”的描述。如此形制的石燈臺,在唐代的靈巖寺應為數不少。遺存的石燈座形制滄桑,包漿猶存,觀之乃為盛唐之物,實屬難得,彌足珍貴。碑文中的三尊護法金剛,現今遺有一個鐵像的下體部分,即被后人謂之“鐵袈裟”。 “鐵袈裟”出自早期東寺院遺址,“高宗臨御”后的主要營造工程道場于“會昌法難”毀滅,再也沒有復興。從史料上觀之,鐵袈裟自宋代開始就有人記述,后來賦予傳說的色彩。經現代學者考證,實為“一尊形體巨大的力士造像的下半身”(5)鄭 巖.山東長清靈巖寺“鐵袈裟”考[J].東方考古,2006(2):237.。依據實物高2.05米,寬1.94米,推測高度約為6—7米,如此高大的護法力士,一定為當時奉祀主像的大殿所護持。結合碑文記述的一系列營造工程,設計規劃者從配置的角度考慮,脅侍于供奉盧舍那佛而建造的大殿的可能較大。
從碑文記述的內容看,工程浩大,工藝繁雜,顯示靈巖寺盛唐時期的鼎盛景象,“遠而望之,云霞炳煥于丹霄;即而察之,日月照明□道耳”。如此工程規模的實施,“皆帝王之力,舍以國財”才能得以實現。宋張公亮《齊州景德靈巖寺記》描寫“寺有石三門、千佛殿、般舟殿、辟支塔,皆古剎”。其所記錄均在今院址內,說明宋代前期靈巖寺的佛教道場活動中心已徹底轉移于此。
經過高宗朝大力護持,靈巖寺宇繁盛,躋身于全國四大名剎之列。碑末頌文曰:“□□岳寺,臺之國清,岱之北阜(指靈巖寺),蒲之西陘。”這是最早提出四大名剎之說,比元和年間(806—820)李吉甫纂《十道圖》提出的“四絕”即齊之靈巖、潤之棲霞、臺之國清、荊之玉泉(其中有兩寺不同),約早了六十年。可知“四大名剎”的首提見于《靈巖碑頌》碑,而非《十道圖》。
五、碑石變遷與歷代著錄
《靈巖碑頌》自始置于魯班洞遺址內,便與遺址歷史命運共始終。魯班洞約始創于南北朝初期,是寺院早期的山門建筑,是宋代以前進入寺院的主要通道。北依山崖,南臨溝壑,具有要塞關口的作用,屬于我國現存寺院早期建筑遺跡之一。歷史上經歷過北周建德、唐代“會昌滅法”的劫難,幾經修復,災難深重。“會昌滅佛”事件使魯班洞徹底失去原有的建筑功能,由此廢棄至今。宋張公亮《齊州景德靈巖寺記》謂之“石三門”;元泰定三年(1326)《壽公禪師舍財重建般舟殿記》謂之“西三門”;元至正元年(1341)《泰山靈巖禪寺創建龍藏記》謂之“外三門”;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重修般舟殿并前三門之記》謂之“前三門”,諸歷代碑刻皆謂之“三門”,是從結構上命之。明萬歷五年(1577)太常寺少卿王世懋游靈巖寺作《游靈巖記》有“浮屠而南為魯班洞”,是為首提“魯班洞”者。相傳五花殿“備極壯麗”,系魯班所造,班死后葬埋于此,故名魯班洞。該文又載:“似為開山僧埋骨地云”,開始有靈巖開山高僧朗公墓地的傳說。
從魯班洞遺址結構上看,鑲嵌《靈巖碑頌》的墻體是后來為防止高大臺基坍塌而頂托的厚重墻壁。元泰定三年(1326)《壽公禪師舍財重建般舟殿記》載:“……本寺僧壽公禪師,特運虔誠……施寶鈔一阡五百緡,重修西三門。”碑文中所說的“西三門”,即是魯班洞遺址,對其進行了保護修復。從現存原始建筑臺基結構遺跡上看不出元代修復痕跡,故此修復是加固、修補工程而已,筑就臺基原體以南、東附加的厚重墻體。魯班洞原體西側緊鄰高大的人工石堰,北側趨平于地面,均無坍塌之嫌。唯南、東側地勢險要,石臺高聳,時有崩塌、撐鼓的可能。元代壽公和尚捐資壘砌厚重的“壯漢墻”,用以頂托、加固魯班洞臺基原體的東、南兩側。這次加固工程,將遺落于角落的《靈巖碑頌》鑲嵌于“壯漢墻”上,搭起拱券,使得一同通行,碑石亦得到有效保護,重見天日。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寺僧修建般舟殿、魯班洞、千佛殿,并修東西兩架僧房三十余間,至永樂三年(1405)四月竣工,前后修繕十五年時間。從以上所列殿宇跡象中,皆未看到此次的重修痕跡,應是常規的修補而已。1995年發掘魯班洞遺址《靈巖寺隋唐建筑遺址發掘收獲紀略》云:“四期建筑……為石室東門碎石壘砌的封門墻及磚券南口用碎石殘磚壘砌的擋土墻。這是在洞內外淤土進一步增高時增建的。因山洪淤塞,山門無法繼續使用,進而封堵石室和門洞,改作地宮使用了。”明萬歷五年(1577)太常寺少卿王世懋《游靈巖記》載:“下浮屠而南為魯班洞,洞上緣傾,崖周甃以石,而成二石門,內犍不可入,似為開山僧埋骨地云。”此時王世懋看到的魯班洞遺址,其上兩側的石門是被堵塞不能進入的。
筆者于上世紀70年代末始在靈巖寺工作,數次下至魯班洞,從遺址上西門進入,門側有壘砌的矮墻及散落的石塊。東門有封堵墻不能進入。洞內券頂的南端用不規則條石和磚塊壘砌封死,致使洞內黑暗,與明代王世懋看到的情景相同。當時,唯能從西門被后人扒開的墻洞得以遁入其中。此封堵的三門石墻,于1995年魯班洞考古發掘時予以清除,遺露出三門至今。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的普遍修繕,碑刻中提到“重修般舟殿并前三門之記”,這里重修“前三門”的內容,定是此次所為的魯班洞東、西石門及洞內南端的封墻工程。
《靈巖碑頌》形體高大,體量厚重,不易搬動,初將如此重要的刻碑放置于該處,說明唐天寶元年(742)制作此碑時,魯班洞遺址的建筑功能仍在使用。“會昌滅法”使其殘損斷為兩節,長久埋沒不見天日,導致后人不能目睹,出現一些歷史誤解。宋代張公亮《齊州景德靈巖寺記》首提“后魏正光元年,法定師始置寺,有青蛇白兔、雙鶴二虎之異。”查法定禪師史料無載。宋代張公亮不知據何始寫法定于正光元年(520)初建靈巖道場,證明張公亮沒有看到《靈巖碑頌》。宋代詩人朱濟道于宣和五年(1123)二月初九日游靈巖,題詩二首。第二首詩的后兩句“會有定師來指示,直須行到寶峰頭。”和末文跋語“□魏法定禪師,乃觀音化身。初居靈巖□□神寶峰,作釋迦石像”,直接將法定禪師與神寶寺聯系起來,說明宋代后期就有法定開拓神寶寺的傳說。宋代前期的張公亮極有可能將法定禪師創建靈巖寺的時間附會于神寶寺《大唐齊州神寶寺之碣》記載的神寶寺開創的時間,始誤記為北魏正光元年法定禪師創建靈巖寺。后來的宋代王逵《齊州靈巖千佛殿記》、金代陳壽愷《觀音托相圣跡序碑》、黨懷英《十方靈巖寺記》及以后文獻均如此記載,正是第一粒扣子系錯位,相繼錯下去的結果,與《靈巖碑頌》記載初創時間相差約100年的時間。
宋代金石學家趙明誠(1081—1129)于宋大觀三年(1109)九月十三日、政和三年(1113)閏月六日、政和六年(1116)三次來訪靈巖寺,所纂《金石錄》卷七載:“唐靈巖寺頌,李邕撰并行書,天寶元年(742)十一月十五日。”只記錄紀年,不見碑文內容,似是只見到了《靈巖碑頌》的右側,說明石碑向左臥地,亮出右側被人為毀壞碑體的三分之一。至清乾隆年間(1736—1795),學者阮元在山東學政任上遍訪山左金石碑刻,編纂《山左金石志》時記載該碑斷為兩截,嵌入魯班洞石壁之上。清嘉慶朝編纂《全唐文》時,僅錄碑文上部的361字。清代學者、書法家何紹基(1799—1873)于道光二年(1822)訪得該碑的殘碑上段,并做了拓片(證實清時下段被泥土淤積所覆蓋),所作《訪得李北海書靈巖寺碑殘石》一詩,詳細記述了其訪得該碑的過程:“湘西仙鶴刻,聞被兵火訌。《石室》與《云麾》,帖賈粗可供。全拓《北云麾》,落吾海南夢。《靈巖》一片石,卅年覓無縫。今秋名山游,風雨行倥傯。方值蝗旱余,餓盡天人眾。一二破衲僧,哀仰維摩俸。叩以金石文,渺莽墜云霧。導觀神寶石,不與鄙懷中。冬初再尋訪,始識魯班洞。草間就沿緣,石壁競摩控。幾曲方造深,忽破滕公甕。光出千載前,寒銷萬冰凍。拓出宛新硎,字字堪洛誦。略言定法師,得地矗云棟。惜僅半段存,莫睹全形礱。創獲壬午年,足補趙阮空。”(6)鄭 巖.山東長清靈巖寺“鐵袈裟”考[J].東方考古,2006(2):237.[清]何紹基.東洲草堂詩集(卷27)[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76.從中看出何紹基訪碑來寺兩次,第一次是秋天,沒有看到該碑;第二次初冬,訪《靈巖碑頌》于魯班洞內,“惜僅半段存,莫睹全形勝”,而沒有得窺全文。此后,該碑文收入陸增祥(1816—1882)《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七,載:“碑已斷缺,高無考,廣三尺八寸,存兩石。上截二十一行,行十九字至二十二字不等。中截存十三行,行九字至十八字不等。字徑九分許。”但未提到該碑文保留的字數。1995年對魯班洞的發掘,使得《靈巖碑頌》完整顯露,共識得殘存文字652字,千古名文遂再現其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