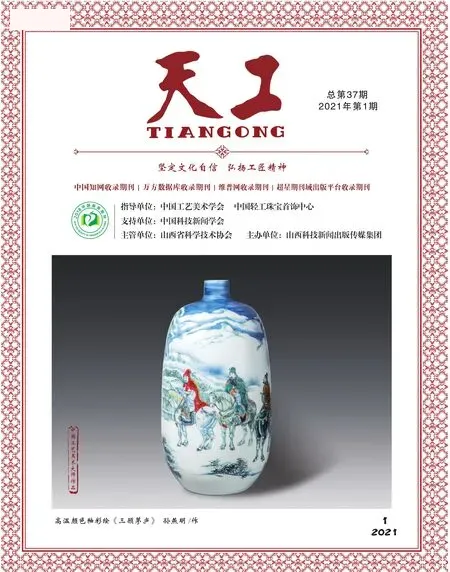品味宋代瓷釉開片藝術之美
文 李壯壯
一、前言
今人對宋代的評價褒貶不一,但不可否認的是中華民族的審美境界在宋代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宋代被稱為“瓷的時代”,全國各地瓷窯林立,各大瓷窯體系百花齊放、爭奇斗艷。在名窯體系中以哥窯開片為美,瓷釉的開片本為瓷器燒制的過程中因胎體與釉面膨脹系數不同而形成的碎紋裂痕。開片原本為一種自然現象,早期被作為殘次品丟棄,宋人卻獨具匠心,對這一現象加以點睛之筆,通過控制胎釉的膨脹系數使瓷釉的自然裂痕形成交錯縱橫的細絲線和形狀不一的紋飾美,呈現出一種“合于天造,厭于人意”的美感。[1]瓷釉開片藝術能獲得如此高的成就離不開精神文化的浸養,可以說宋瓷是宋代精神文化的物化形式。當今對傳統文化的研究與弘揚雖已引起足夠的重視,但有許多人只認識到傳統的重要性,且有意把傳統元素融入藝術創作中,但卻是本末倒置,只用其形而不知其根。因此,解讀宋代瓷釉開片藝術之美,必須從它根植的文化土壤入手。
二、宋代的政治社會背景與宋學思想
宋代文化藝術在中國古代社會達到了登峰造極之境,嚴復《致熊純如函》中:“古人好讀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2]
(一)宋代政治社會背景
史學家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同時,宋朝的經濟也是高度繁榮發展,在巔峰時期都城開封人口達到了一百多萬,同時期的歐洲各大城市僅僅十幾萬人口,可見宋朝繁榮程度之高。但是,經濟文化的高度繁榮卻彌補不了軍事上的孱弱。宋代歷代君主的防弊之政有效地維護了國內的統治,也使得宋朝無意于對外擴張,只求偏安一隅。加上軍事方面積貧積弱,飽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與騷擾。歷次戰敗都以賠款求和來換取和平。在文化上,宋人蔑視游牧民族的野蠻和不開化,但在軍事上卻屢次遭受游牧民族的蹂躪,成為每個宋人內心深處不愿輕示的傷疤。這為文化藝術的發展奠定了嚴謹內斂的基調,宋人思想由盛唐那種對外的“睥睨江山”轉為對內的“無可奈何花落去”的自省和自控。因此,宋人的審美境界既不同于盛唐的雍容富麗,也與清朝的煩瑣堆疊不同,追求一種陰柔、清凈幽雅的格調。
(二)宋學思想的形成
宋代的政治只是顯露在表面上的東西,政治上的發展實則以社會為根基,社會是在根源上對政治的發展輸送著源源不斷的養料。分析歷史的人,特別是分析宋代瓷釉藝術品的美,都要從政治上,尤其是文化上去找尋探索。
中國的文化在歷史上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為先秦、兩漢時代的諸子之學;第二時期為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的玄學和佛學;第三時期為宋、元、明時代的理學。[3]宋學的發展根起于隋唐時代的玄學和佛學,但又對佛學提出了質疑,佛教反動,是為宋學。我們看前兩個時期的文化就可以對宋學有個淺識。諸子之學起于春秋戰國,各諸侯國之間連年混戰,而此時的學術注重矯正社會的病態,可以說是“撥亂世,反之正”,各家各顯所長卻又殊途同歸。及至魏晉以后,文化由社會轉向個人內心的改良,認為個人內心上修養的好壞反映社會的好壞,如此社會的問題得以解決,這種現象從當時的文人儒士走玄學和佛學這條路就可以看出。文化思想是不會憑空冒出來,是在前人基礎上傳承和發展而來,宋學是在這兩種思想中取其精華進行融化改造。
(三)文人士大夫的情趣抒發
“重文抑武”的國策和較為寬松的政治環境為文人士大夫群體力量的形成提供了適宜的外部環境,由于儒家文化傳統的熏染和“濟世”精神的復振,古代的讀書人受其傳統思想的影響非常深,對孔子提出的鄴治盛世有著癡迷情結,這個大同社會激勵著文人參與國家政治活動的熱情。士大夫階級成為國家事務的管理層,使文人士大夫在那個時代綻放了絢麗的花朵。
文人士大夫的審美觀影響著這一時代的審美風格。他們都有很高的文化修養,飽讀前代的文學經典,對世界以及生命的理解更加深刻,同時文人重視自身的高尚品德,追求高雅、含蓄、清白的品質。我們暫不論宋儒的政治之治,在傳統儒家的君臣之義綱紀下,文人士大夫的氣節確實遠勝前朝,他們重于平時的修養,偏于內心。
(四)道家思想的“自然”“樸”
宋徽宗尊崇道教,大建宮觀,使得道教開始流行起來。老子主張“見素抱樸”或“復歸于樸”,“樸”是富有哲理的隱喻,原義是指未經刀斧砍斫的本始之木,老子用它描述理想人格,主張放下窮之不盡的欲求,復歸于嬰兒。“樸”與“自然”一樣都是用來闡釋“道”。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以說老子之“道”最深微、最親切的宗趣乃在于因任自然,即所謂“道法自然”。“自然”也意味著“無為”“不言”,在這里老子的“自然”與“樸”都可以理解為相對于人之施為的天然。遵循天道,不事雕琢的質樸天成,從而提出了以“質樸自然”為最高的審美理想。這種藝術標準在宋代瓷釉開片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三、宋瓷瓷釉開片藝術之美
宋瓷開片藝術之美吸引了一大批學者的贊賞,明代學者高濂在《遵生八箋》中評價宋瓷:“冰裂鱔魚上,梅花片墨紋次之,細碎紋,紋之下也。”宋代文人賦予了許多名詞來描述這些藝術品,“冰裂紋”就是紋片如冰破裂,裂片層疊,有立體感而稱之;“金絲鐵線”就是其紋片如網交織、如冰破裂,之后以墨汁為著色劑人工從裂紋中滲透進去,著色后顏色很深,就被稱為“鱔血冰裂紋”;“魚子紋”就是開片極小,因其形狀如魚子密集一般;“牛毛紋”指鈞窯的厚釉流淌的紋理形如細牛毛一般等。
(一)質樸自然
宋代文人恪守著儒家的禮儀傳統,但在思想上卻抒發著道家超然脫俗、凌躍于塵世的高雅格調。他們追求自然,不屑于人工雕飾,有一種“隱世”心態。
細觀哥窯的開片,其紋路走向曲折蜿蜒,開片大小不一,呈現出飽經滄桑、自然天成之感。我們細細品味就會發現其蘊含老子的“復歸于樸”與“因任自然”,開片中的紋路紛繁游走于器皿全身,沾染濃厚不一的色彩變化,具有一種水墨寫意的意蘊,但卻沒有絲毫人為雕飾之感,仿佛經歷萬古千桑的洗禮,沒有絲毫技巧、修飾,它是一種歸真,正如老子所說“復歸于嬰兒”。
(二)幽韻雋雅
宋代瓷釉開片藝術誕生于宋代“外儒內道”的文化語境中,生息于儒、道、禪共生的傳統文化中。[4]經濟高度繁榮,人民安居樂業,不僅整個文人士大夫階級文化水平較高,一些普通百姓也都能談詩論道。瓷器的制作者們不僅僅是一個工匠,其也有自己的獨特審美趣味,并把自己的審美表現在瓷器的制作上,這為瓷器藝術的發展帶來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受到了當時文人氣息濃厚的影響,瓷器制作工匠也有意無意地追隨文人的書生氣質。
文人積極參與國事,輔佐君主開創自己理想中的“圣人之治”,先后有范仲淹、王安石和司馬光等,雖然政治上有所不和但并不影響私下的相敬之情。他們自視為高雅的君子之風,只會在人前光明正大的行走,絕不背后陷人于不義。他們吟詩作樂,追求風雅,絕不與俗物為伍,那種“只留清白在人間”的氣質仿佛在他們的身上扎下了根。這種君子氣質在青瓷上表現得淋漓盡致。青瓷釉色晶瑩翠綠,類冰似玉,那種清風拂面的質感躍然于眼前。釉面有細小開片密布器身,既不要求濃妝艷抹的庸俗,又不失高雅麗質的格調,這種似揚又抑、似是而非的含蓄完美地詮釋了中國傳統文人追求的文質彬彬。瓷釉開片所呈現的殘破之美也體現了文人士大夫的高度自信,他們積極參與國事,與皇帝共商國是來施展自己的偉大抱負,這種破而后立的特性也只有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的身上得到展現。
四、小結
宋人所締造的文明猶如一個理想中的世外桃源,含蓄而精致,他們過于追求文雅,只求精神世界的抒發,而忽視了軀體的錘煉,像是一個文質彬彬卻又體質孱弱的書生,可這幻夢終究抵擋不住歷史的考驗。我們今人已無法體會當事人的思想和精神,只留下這些凝聚著他們心血的藝術精品供我們細細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