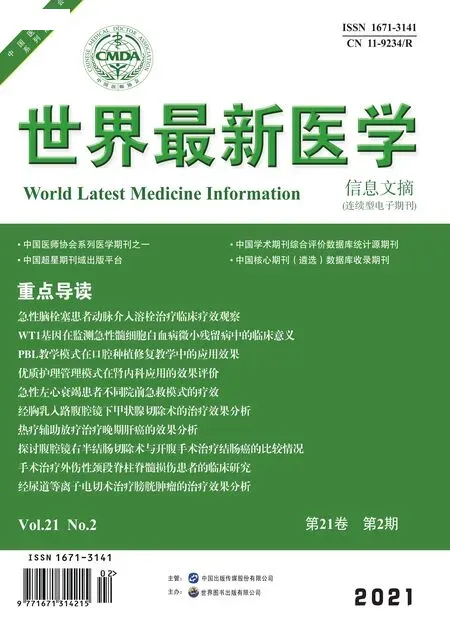辛開苦降法在阿爾茨海默病(AD)中的應用
魏本君,車敏通信作者,金曉萌,楊永琴,劉靚,安方玉
(1.甘肅中醫藥大學/敦煌醫學與轉化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甘肅 蘭州 730000;2.甘肅中醫藥大學,甘肅 蘭州 730000)
0 引言
阿爾茨海默病(AD)是指在老年前期或者老年期所發生的一種常見的以起病隱匿和進行性認知受損為特征的中樞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研究表明[1]其發病主要與大腦神經遞質的乙酰膽堿的缺失有關,主要以記憶力衰退、定向能力障礙、語言表達,生活自理能力不斷減退以及出現行為異常等為主要表現。結合臨床癥狀,阿爾茨海默病屬于中醫中的“癡呆”、“癲癥”、“善忘”等疾病的范疇。現代醫學中西醫主要通過提升膽堿功能,營養神經來治療該病,此法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善癥狀,但不良反應大,長期治療效果不佳;然中醫根據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的原則在防治阿爾茨海默病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筆者認為臨床中阿爾茨海默病患者屬“痰、瘀、火”病機者較為多見,辛開苦降燮理陰陽、調和寒熱、暢達氣機、調整升降等綜合性的功效,與AD在不同時期復雜的病機演變甚為契合,因此我們將常用于脾胃病治療中的辛開苦降法用于AD的治療之中。
1 中醫對AD的認識
中醫學認為,AD病機屬于本虛標實。由于人體機能隨年齡的增長逐漸衰退,臟腑逐漸虧虛,腎精、氣血精微物質難以上達頭部,濡養腦竅,從而出現腦髓漸空,神機失用的病理狀態,故本虛多為臟腑氣血之虛;標實者主要涉及痰、瘀、火等。病位在腦,與心、肝、脾、腎功能失調相關。其病名首見于《華佗神醫秘傳》。在《靈樞·天年》中有類似癡呆的論述“六十歲,心氣始衰,……,血氣懈惰,故好臥。七十歲,脾氣虛,……。八十歲,肺氣衰,魄離,故言善誤”指出人體機能的衰減與臟腑、年齡有關。《醫學入門》中記載“腦者髓之海,諸髓皆屬于腦,故上至腦,……,髓則腎主之”認為其發病與腦直接相關,此外清代醫家王清任在《醫林改錯》中有“腦為元神之府,靈機記性在腦不在心”以及“年高無記性者,腦髓漸空”首次提出阿爾茨海默病的病位是在腦,該理論的提出為阿爾茨海默病的研究開辟了新思路,又有腎主藏精,生髓,髓上通于腦,腦又為髓海,可見其與腎也有密切關系。在《三因極一病癥方論》中有記載“脾之意與思,意為記所往事,……,今脾受病則意舍不清……,使人健忘”可見五臟之脾土功能的健全與AD的發病也存在密切關系。同時心、肝、肺、大腸等其他臟腑也和該病有相關聯系[2]。
2 辛開苦降的功效與適應癥
2.1 溫清并用,燥濕化痰。脾胃為氣機升降之樞紐,思慮太過,最易妨礙氣機運化機能,使脾胃之氣結滯,氣結日久成郁,郁而化熱;脾主運化,又為生痰之源,運化不及,則痰濕內生,痰隨上逆之氣,上擾腦竅,脈絡失暢,神機失用而形成癡呆。正如薛生白所言:“熱得濕而愈熾,濕得熱而愈橫,濕熱兩分,其病輕而緩,濕熱交合,其病重而速。”在治療上,單純清熱和祛濕不能達到分消濕熱,濕去熱退的目的,而且清熱藥又易助濕,祛濕藥又易增熱,容易顧此失彼。辛開苦降法集辛苦一體,辛味藥如厚樸、枳殼、陳皮等能理氣健脾開痞;苦味藥如黃芩、黃連等能降胃清熱泄痞。辛熱藥與苦寒藥配伍,一辛一苦,一熱一寒,辛者開散升浮,輕清向上;苦者通泄通降,重著向下。同時《臨證指南醫案》也提出:“苦降能驅熱除濕,辛通能開氣宣濁”。
2.2 消補兼施,清化痰瘀。人至老年,五臟機能減弱,腎氣漸衰,腎精的溫煦、濡養功能減退,精不化血,血行滯澀,津液失布,濕濁內生,痰瘀互結。腎內寄元陽,為一身陽氣之本,元陽不足,濁瘀則無以消散。濁瘀相兼,互為因果,上蒙清竅,阻塞腦絡。腦絡受損或結滯、或弛緩、或破溢,均可影響血液正常流通,血脈不利則流通不暢,影響水液代謝容易化生痰濕,痰濕蓄積增多成水濁,濁又易與毒相合而成濁毒,濁毒壅結不散凝滯脈絡,阻滯氣機則血澀為瘀。
血瘀氣滯,筋脈失于榮養,或者血瘀阻滯經絡, 致氣血不能充養腦髓,久而造成癡呆。楊麗靜[3]用復方菖蒲益智湯治療痰瘀阻滯的輕度癡呆療效可觀,其中石菖蒲芳香走竄,宣竅豁痰,辟穢化濁,醒神益智;黃連大苦大寒,燥濕去濁,降火解毒;石菖蒲和黃連配伍,辛開苦降,使痰去熱清;赤芍、丹參味苦寒涼,當歸辛溫活血行氣,三藥合用,辛開苦降,血行氣暢,瘀去絡通;再加郁金、地龍、澤瀉、茯苓、益智仁等溫脾暖腎,利濕去濁,使痰濁生化無源。全方寒溫相宜,辛開苦降,攻補兼施,使熱清瘀消。
2.3 升清降濁,暢達氣機。脾升胃降,氣機升降正常者方可納運相助,維持水谷精微物質的消化、吸收及轉輸,從而達到“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臟,清陽實四肢,濁陰歸六腑”的正常機理。中焦脾胃氣機逆亂,則脾不升清,胃不降濁,運化轉輸功能失常導致痰、飲、水、濕等病理產物相繼產生。如《脾胃論》之語“脾胃之氣既傷…而諸病之所由生也”辛者能行氣血,理氣以助脾升清;辛者多溫,可驅散寒濕,苦能降能泄,泄胃熱,降上逆之胃氣,助其通降;苦者能燥,燥脾之痰濕。苦辛合用,一降一升,一寒一溫,一陰一陽,開散升浮兼通降沉降,共奏氣機調和之功。辛溫宣通之品可理氣散痞,溫陽散寒;苦寒降泄之品降泄通利,清熱燥濕。苦辛共用,可平調陰陽,調暢氣機,以達寒熱并調、開痞散結、清宣郁熱、交通心腎之功。葉天士所創制輕苦微辛之法是通過宣肺氣,宣通氣滯,化濕泄邪,使邪有出路[4]。
3 辛開苦降法在阿爾茨海默病中的應用
辛開苦降法源于《內經》,有“氣味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的論述,說明了氣味的陰陽屬性和作用,指出了辛味藥發散、苦味藥物降泄的特點。張仲景在《傷寒論》中有用到寒熱并用之辛苦通降的思想,首創了辛開苦降配伍法。葉天士在《臨證指南醫案》中提出“微苦以清降,微辛以宣通”,“辛開苦降法”首次被明確提出。后吳鞠通提出“非苦無能勝濕,非辛無能通利邪氣”指出苦寒藥物與辛熱藥物相組合有滲濕、通利的功效,揭示了辛開苦降法配伍的科學內涵。
其中《醫學心悟》中明確指出:“腎主智,腎虛則智不足”,年老腎衰,腎虛不能化精,髓海失充,造成髓少不能養腦,腦失滋養,神機不用而發為癡呆。故腎虛是癡呆病的核心病機。然顏乾麟[5]在治療心腦血管疾病中認為心腦血管疾病患者的特征以濕熱之邪挾痰瘀為患,主張以辛開苦降治之。筆者認為臨床中阿爾茨海默病患者屬“痰、瘀、火”病機者亦不少見,治療首應補腎,佐以辛開苦降法。不可因腎虛之候猛投補腎之品,應注意緩緩補之,通而不滯,補而不膩,兼顧他邪。
3.1 辛開苦降治分三期。AD可分為早、中、末三期,在疾病的早期主要是心腎功能不足,出現心腎不交,從而表現為健忘、反應遲鈍的表現。辛開苦降法,辛可升,激發腎氣,使得腎氣向上蒸騰,苦味可降,可使心火下行,心火下而腎水上,從而心腎相交,水火既濟,因心腎不交所致的健忘等癥狀也隨之得以好轉;在疾病的中期主要是在早期的基礎上,出現痰瘀上犯腦竅的病理機轉,因此在健忘加重的基礎上可見失語、失認、徘徊、失行等一系列表現,辛味可疏達氣機,氣行則水行,津液正常布散,水液代謝正常,可使痰濕得以化除,隨二便而排泄;氣為血之帥,氣行則血行,血脈通利,可使內積于體內的瘀血逐步消散;痰瘀之邪得以消解,則腦竅清明,心神得安,健忘、失認等癥狀自然得以緩解和消除。
病至末期,患者會出現嚴重的本虛標實之候,本虛是患者本身元氣大虛,標實是痰瘀互結更甚,從而出現運動不能、高度智能障礙、無言等表現,本階段除了大補元氣之外,辛開苦降之法也有不可替代的意義。辛味之藥辛通、辛散可化除痰瘀之結,苦味之藥可堅陰,更可納五臟之氣歸于下元,使元氣不至于耗散,進而固護元氣,促進病愈。
3.2 辛開苦降和調五臟。一般認為,AD的發病與腎精之虛損,有密切關系,但五臟之間互相生克制化,互相協調,彼此為用,而AD往往病情復雜,療程較長,五臟皆有涉及。從AD的癥狀來看,主要表現為神志失常的表現,屬于中醫學“失神”的范疇,其病位在腦,而五臟藏五神,神志活動的正常發揮是通過五臟的共同作用,相互協調而完成的。辛開苦降之法,可燮理陰陽、調和寒熱、和調五臟,通過協調五臟之間的關系,進而調節神志,達到緩解治療AD的作用。
肝主疏泄,可調達全身氣機,對情志活動也有很重要的調節作用,若肝氣郁結,舒達失常則可出現氣滯血瘀,久久不解,則會出現瘀血停滯,進而影響神志,辛開苦降之法,辛可散郁,苦可清熱,使郁氣解,郁熱散,恢復肝之疏泄,進而恢復神志;心主血脈,心氣可推動血脈運行,若心氣無力推動血液,則會出現血脈瘀阻,上至腦竅瘀滯,腦絡失榮,出現癡呆[6],辛開苦降之辛,可通達心氣,暢達血脈,從而改善血運,化除瘀滯,改善癡呆狀態。
脾主運化,脾失健運,水濕不化,水液代謝失常,水濕痰濁之邪蒙蔽清竅,出現清竅失養,元神失用,則可發為AD,辛開苦降,辛可以激發氣化,促進水液代謝,消除痰濕,辛苦合用可以調理脾胃,恢復中焦升降,從而恢復運化,開蒙去蔽,恢復神志;肺主氣,通調水道,肺之宣肅失常則津液代謝紊亂,濕停聚,阻礙氣血,腦絡失養,則可發為AD,辛可升散,苦可沉降,一升一降可恢復肺之宣肅,進而通調水道,通調氣血,緩解AD;腎藏精,主骨生髓,腎以封藏為本,腎精不能很好地封藏,則不能上榮腦,神機運轉不利,可發生AD,辛開苦降之法,苦可降,可將五臟之精納歸于腎,使腎很好地封藏,精氣上達于腦,則AD自然緩解。
4 結論
辛開苦降法源于《黃帝內經》之藥性理論,立方與《傷寒論》。其組方用藥有規律又靈活多變,臨床應用范圍較為廣泛。一般臨床多用于消化系統疾病,我們經不斷研究文獻和臨床實踐,將其引入到AD疾病的治療,我們發現其契合AD的病機,療效顯著。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們將進一步從臨床、實驗等各方面進行更深入的研究,為臨床治療AD開辟新的治療思路,造福廣大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