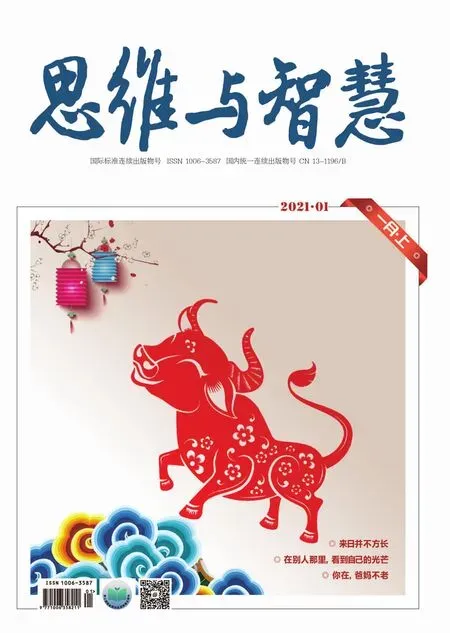“律呂調(diào)陽”安天下
●李艷霞

眾所周知,《千字文》問世已經(jīng)一千四百余年,它在中國古代的童蒙讀物中,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卻不知道《千字文》包羅著“律呂調(diào)陽”的乾坤智慧。
“律呂調(diào)陽”是《千字文》中的名句。意思是,用律呂來調(diào)節(jié)節(jié)氣,使得人們對(duì)時(shí)間有了節(jié)點(diǎn)的定義。律呂就是空竹管,用它來校定音律。這就讓人有些匪夷所思了,定音管和節(jié)氣怎么能扯上關(guān)系?
首先,從宇宙的初始狀態(tài)來看,宇宙形成于混沌蒙昧的狀態(tài)中。太陽正了又斜,月亮圓了又缺,星辰布滿在無邊的太空中。寒暑循環(huán)變換,四季更替: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shí),故五谷不絕,百姓才有余食也。而積累數(shù)年的閏余并成一個(gè)月,放在閏年里,古人就用六律六呂來調(diào)節(jié)陰陽。
《后漢書·律歷志》記載:黃帝時(shí)代的伶?zhèn)悾l(fā)明了律呂,用十二根空竹管,其中最長的九寸,最短的四寸六分,按長短次序?qū)⒅窆芘帕衅饋恚厦娴墓芸谝贿咠R,下邊長短不一,呈一個(gè)斜面依次排列,然后插到土里面。竹管里面灌滿暇莩(暇莩就是用葦子膜燒成的灰)。要將這些管子埋在西北的陰山,拿布幔子遮蔽起來,在外面蓋起房子,再密封好,保證絕對(duì)吹不到半點(diǎn)兒風(fēng)。然后等地下的冷暖之氣發(fā)生變化,管內(nèi)就出現(xiàn)了動(dòng)靜。冬至的時(shí)候,陽氣一產(chǎn)生,第一根九寸長的管子里面的灰,自然就飛了出來,同時(shí)發(fā)出一種“嗡”的聲音。這種聲音就叫黃鐘,時(shí)間為子時(shí)。把這個(gè)發(fā)出聲音的日子規(guī)定為冬至。用這種聲音來定調(diào),以此類推,十二律呂便推出了十二個(gè)節(jié),順著十二個(gè)節(jié)便能推出十二個(gè)氣,也就是閏年的月歷與四季氣候和實(shí)際的物候,至此二十四節(jié)氣便齊全了。
因?yàn)橛辛恕奥蓞巍眮硇U⒄{(diào)整的,才使時(shí)序正常。祖先的這種神奇發(fā)明與發(fā)現(xiàn),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智慧結(jié)晶。
根據(jù)“律呂調(diào)陽”,農(nóng)民遵循時(shí)序,進(jìn)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尊重自然種植規(guī)律,才能實(shí)現(xiàn)風(fēng)調(diào)雨順,五谷豐登。正如《淮南子·泛論訓(xùn)》所說:“器械者,因時(shí)變而制宜適也。”反之,與自然背道而馳,只能自取其咎,徒勞無功。
然而,起初“律呂調(diào)陽”是為了劃分農(nóng)時(shí)而發(fā)明的,在之后的過程中它發(fā)展成了古代校正樂律的器具,多由竹制或金屬制成。
《呂氏春秋·古樂》記載:伶?zhèn)惸M自然界的鳳鳥鳴聲,選擇內(nèi)腔和腔壁生長勻稱的竹管,制作了十二律,暗示著“雄鳴為六,是六個(gè)陽律”,“雌鳴亦六,是六個(gè)陰呂”。《古樂》篇還記載了伶?zhèn)愔茦返膫髡f。將十二根竹管分成六陰、六陽兩組。六根奇數(shù)的屬陽,叫作六律;六根偶數(shù)的屬陰,叫作六呂。六律的第一個(gè)是黃鐘,六呂的第一個(gè)叫大呂, 所以音樂里面有黃鐘、大呂之說。成語“黃鐘大呂”也是由此得來。
《周禮·春官·大司樂》記載:“乃奏黃鐘,歌大呂,舞云門,以祀天神。”鄭玄注:“以黃鐘之鐘,大呂之聲為均者,黃鐘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中國古代音樂分十二律,陰、陽各六律。黃鐘為陽律第一,大呂為陽律中排第四。黃鐘、大呂配合交響,形容音樂或言辭莊嚴(yán)、正大、高妙、和諧。
原來,“律呂調(diào)陽”是矯正變奏的至寶,是改弦易轍的辦法,是矢在弦上的行動(dòng),是弦無虛發(fā)的準(zhǔn)確,是家弦戶誦的傳承,是撥亂反治的利劍,是補(bǔ)偏救弊的良藥,是定乾坤,安天下的風(fēng)雅。
曲高和寡不是國學(xué)風(fēng)雅,《和諧頌》是另一種“合和”的風(fēng)雅。當(dāng)和諧成為社會(huì)的主基調(diào),陽氣自然上升,陰氣漸漸消沉,便形成了風(fēng)清氣正、朗朗乾坤的風(fēng)尚。
成大器者,就應(yīng)該像“律呂”那樣,奏響時(shí)代的“黃鐘大呂”,讓莊嚴(yán)、正大、高妙、和諧的氛圍四網(wǎng)張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