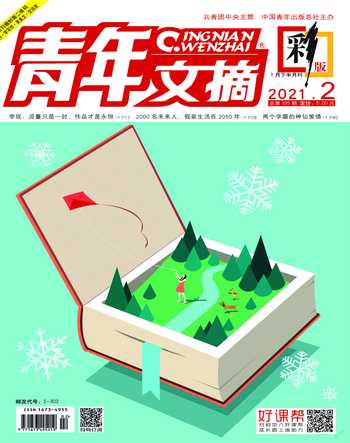廢棄物文明
維舟
家里的老自行車已銹跡斑斑,推到修車鋪找師傅看了下,他說,內外胎都已經磨損了,建議全部檢修更換,得要75元。這個報價讓我吃了一驚,脫口而出:“那我還不如買輛新車呢。”
在我小時候,自行車可算是家里的稀罕物什。爸爸對他那輛“永久”自行車的珍惜,按我媽的戲謔,簡直超過家庭成員——它很少受風吹日曬,萬一雨天沾了泥,那回家更是非仔細擦洗不可。
在父輩眼里,我們這一代的很多做法與其說是“消費”,不如說是“浪費”。齊格蒙特·鮑曼抨擊說現代工業文明是一種“廢棄物文明”,有意制造得不那么堅固耐用,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人們不斷地棄舊換新,從而有足夠的需求推動生產進行下去——但這隨之又造成了彌漫于社會的消費主義,以及難以處理的大量垃圾。這些觀點的潛在影響讓我有意無意中偏向一種道德立場——消費主義是欲望泛濫的結果,應對當下的環境災難負責。
但修車的經歷卻在無意中啟發了我從另一個視角看待問題:人們之所以傾向于棄舊換新,與其說是因為欲求過度,倒不如說是經濟理性的必然結果。在我父母那個時代,物品很昂貴,而勞動力成本卻很低廉。勢必是“物盡其用”,注重循環再利用的。
在中國,消費主義還是近20多年來才在發達城市逐漸顯現的新現象,年輕一代確實更大手大腳,也更容易喜新厭舊。這當然是因為人們日子好過了,但卻未必是因為道德敗壞了,倒不如說是因為一個簡單的經濟學原因:隨著工業化的迅猛發展,制成品價格日益低廉,而與此同時,人力成本卻越來越高。在這種情況下,修補已逐漸變得“還不如買個新的”合算了。
到了此時,全社會才會逐漸興起一種新的意識,認識到我們必須在垃圾吞沒我們之前,找到循環再利用的辦法——但此時循環再利用已經不是為了節儉耐用了,而是出于一種對環境和子孫后代的責任心。
毫無疑問,要解決“廢棄物文明”帶來的問題,我們有必要反思現有的生活方式、消費習慣和隨之而來的理念,但對一個尚未真正富裕的社會來說,想要人們多付出經濟成本去過一種更“環保”的生活,很可能對大多數人沒有太大吸引力。
在這方面,順應經濟學邏輯,由國家對制造業設定環保的基本生產標準、鼓勵綠色經濟、使循環再利用成為有利可圖的產業,恐怕才是更有效的。這并不是推卸普通消費者的責任,而只是人性的基本現實:如果一件事有利,那么讓人們接受要容易得多了。
//摘自《南風窗》2020年第24期,本刊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