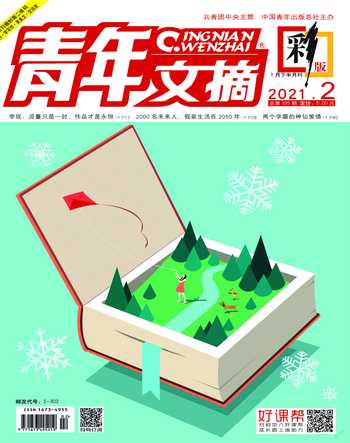未成年網紅與啃小族
懶懶
拍視頻、做直播可以賺錢,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共識。而在各種各樣的視頻平臺上,萌娃類賬號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兒童博主的吸金能力超過成年人早已不是秘密。有人靠拍娃甚至一年就能狂賺2600 萬美元……當越來越多的成年觀眾愿意刷視頻為孩子的表演“埋單”,當孩子不知不覺成為流量經濟大潮中的“弄潮兒”,一些家長開始為流量“啃小”。

“啃小”的背后,折射兒童成長隱患
縱觀視頻平臺上的未成年網紅視頻,雖然有兒童通過屏幕前的歷練,獲得超于同齡人的好口才;有兒童靠直播,幫助原本貧困的家庭漸漸走出陰霾。然而,當個例成為現象,當越來越多的孩子被徹底暴露在公眾面前,終日接受外界對其日常生活的窺探;當越來越多的孩子突破傳統的成長軌跡,過早地踏入紛繁復雜的成人世界,我們不得不開始擔憂,這對于孩子們來說,真的好嗎?
杰米是一個在社交平臺上擁有百萬粉絲的“小網紅”,他的賬號日常由其媽媽管理。曾經有粉絲在評論里認出了他們視頻拍攝的地點,說你們家肯定在這附近,為此杰米媽媽迅速刪掉了那條評論。這個情況恰恰暴露出了當前“小網紅們”以及他們的父母不得不面臨的一個問題——隱私泄露。
誰都不希望自家孩子的隱私遭到泄露,哪怕父母在日常拍攝視頻時多加小心,但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呢?更何況在當今這個“人肉搜索”“大數據”盛行的時代,哪怕是蛛絲馬跡,網友們都有可能因此挖出一大串千絲萬縷的聯系。
現實世界始終復雜,難測的人心往往就潛藏著攪擾正常生活的隱患。誰都不希望新聞中“被人跟蹤尾隨甚至偷偷潛入住宅”這樣細思極恐的細節真實地發生在自己甚至孩子身上。但誰都無法確保“小網紅們”動輒百萬甚至千萬的粉絲中全都是純粹之人,一旦他們的部分隱私被不軌之徒掌握,那么這些新聞中的“細思極恐”乃至更為嚴重的后果,便極有可能變成事實。
面對現實的挑戰,我們自然是希望家長們在做選擇時能謹慎再謹慎,哪怕已深入“棋局”,也要時刻保持警惕,把握好“度”,便是對孩子、對家庭最大的保護。(文/鑫光,摘自知乎)

對“啃小族”多些理性態度
對于“啃小族”,人們應該理性看待,不必苛責。一來這也是一種生存方式。如今萌娃們具有某種表演天分和帶貨能力,其業績并不亞于某些成年人。讓萌娃們盡情表演,擁有大量粉絲也是一種現實選擇。孩子上學也好,參加培訓也好,需要高昂的費用。對于那些沒有殷實家底的家長來講,通過萌娃們的表演和帶貨來賺取一定的費用,也是一種“取之于娃,用之于娃”的方式。
二來對孩子的生存和社會交往能力也是一種培養和鍛煉。萌娃們要具備相當的能力才能贏得人們的認可,而這些能力的培養會讓孩子盡早成熟起來。
當然,“啃小”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能以摧殘孩子的身心健康為代價。前段時間,3歲女孩佩琪被父母喂到70斤的新聞備受關注。視頻里,漢堡、炸雞、烤串等高熱量食物不斷被送到孩子面前,家長強調“馬上突破100斤”。這種以摧殘孩子身心健康為代價的“虐童直播”遭到了社會的強烈譴責,佩琪的父母也因此被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家長作為孩子的監護人,理當肩負起監護責任,為了“啃小”置一切于不顧,這樣的做法不足取。
我們常說凡事要有度,過猶不及。對“啃小族”,既不能隨意苛責,也不能任其野蠻生長。在適當的場合下讓孩子們表演一番,既滿足了孩子們的表演欲望,又能為家長帶來可觀收入,但前提是要把握度。孩子們正處在求知的年齡,讓他們過多地沉湎于網絡直播,對其的身心健康也會帶來某種傷害。
總之,對“啃小族”不妨多些理性看待,大可不必視為洪水猛獸,同時,讓未成年“小網紅”健康成長也是一道社會必答題,這個題必須答好。(文/李紅軍,摘自四川在線天府評論)

監管要應時而變
很多家長涉足短視頻、直播可能是無意為之,但隨著視頻關注度的提升,很多家長甚至放棄原本的職業,成為全職視頻博主。目前,10歲以下的萌娃已經成為“未成年網紅”中的主力軍,他們正以稚嫩的認知來應付成人世界的復雜,比如,某小學女生的賬號里,僅看視頻縮略圖就能捕捉到“買房”“ 結婚” “資產過億”“窮”這種成人世界里的詞。
而據相關數據,4.25億網絡直播用戶中,青少年觀看直播的比例達到45.2%。2017年,英國機構First Choice詢問了1000名兒童的理想職業,其中半數想成為網紅。2018年,日本學研對1200名小學生的調查發現,網紅在他們理想職業排名中升至第二位。2019年,新華網做過一個調查,叫《95后的謎之就業觀》,有54%的孩子,最向往的職業是當主播和網紅。
這些數據背后,反映出的恰恰是部分孩子價值觀的崩塌。而就直播平臺現狀而言,網絡直播內容良莠不齊,且亂象頻出。
雖然對一種新興的事物,我們確實不能動輒因問題初顯就“一刀切”式地打壓,然而,新事物亦有糟粕。2019年“兩會”上,全國政協青聯界別建議盡快出臺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一方面是出于對隱私泄露的擔憂;另一方面,他們也擔心直播平臺中的一些低俗內容,會對未成年人未成形的道德意識、價值觀等造成負面影響。
基于此,2020年7月13日,國家網信辦發布通知稱,嚴厲打擊直播、短視頻網站平臺存在的涉未成年人有害信息,嚴格排查后臺“實名”認證制度。如此語境下,涉及兒童的自媒體內容,必然會受到更嚴格的監管。
由此可見,雖然有些家長樂當“啃小族”,但對于國家的監管部門來說,要做到的卻是應時而變。倘若社會能出臺一套成熟且嚴密的關于未成年人保護條例,在對未成年人、家長、平臺施加約束的同時又能充分平衡好各方利益,不讓網絡直播中的暴力、低俗、危險內容和不文明語言危害未成年人的“視界”,同時又能切實保護好孩子們的童年不被金錢、流量腐蝕,那么,“未成年網紅”的這條路或許不會被直接阻斷,甚至還有可能在規范的體系內求得行穩致遠。(輯/大寫Z,資料來源:《中國青年報》、知乎、東方網、中國甘肅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