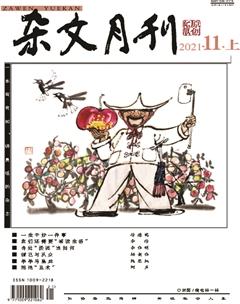文壇的“人、文反差”
鄭殿興

自古以來,文壇就有個怪相——“人、文反差”的怪相:有的人,人品雖很劣,但文品(準確說,是他們的某些作品)卻很好,很棒,很給力……婦孺皆知了。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如此《憫農》詩,許多孩童能倒背如流,卻對作者李紳不很知曉。為啥?就因李紳為官后變了,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漸次奢華”不說,更喜拉幫結派排異己,制造“吳湘冤案”……讓人很鄙夷、很憎惡,不愿提起了。
非詩人、非“粗人”的慈禧,歹毒無比人所共知了。但其名句“可憐天下父母心”,也人所共知了——說仍是今日許多人的口頭禪,決非夸大之詞了!也正因此,慈禧為母親富察氏寫的祝壽詩“世間爹媽情最真,淚血溶入兒女身。殫竭心力終為子,可憐天下父母心!”詩雖整體一般般,但因“名句”在,便讓人知曉了。同樣,因其人品忒惡,被人有意無意的“埋沒”,便無法避免了。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慷慨篇》一部分),詩作者是誰?汪精衛呀!早年,他參加反清革命,因刺殺攝政王被捕入獄……這首獄中詩,豪情滿懷、視死如歸,與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詩句,都能有一比了!此詩,雖未口口相傳,卻也史冊“留痕”了——不因為該詩多美、多豪情,就因作者是頭號賣國賊,是極具諷刺性的反面教材。
……
對“人、文反差”怪相,我們該怎樣評析?應如何對待呢?
我們應該看到,李紳詩《憫農》、汪精衛詩《慷慨》,皆早期詩作也!那時候,他們很有些朝氣、很有些才情,名詩、名句之傳世,當屬正常現象。然而,人是會變的——當李紳“漸次奢華”、汪精衛甘當國賊后,他們的“憫農”“慷慨”之心及讓人傳頌的詩篇,還有嗎?沒有了,全都沒有了!
不過,慈禧的名句“可憐天下父母心”,仍用“早期說”解釋,似有些不妥了,得另辟“蹊徑”了。比如說,人倫之情——兒女對父母的感恩之情,便是其“名句”的一大成因吧?此情,人之常情也!普通人有,不普通的慈禧,也可以有吧?哪怕“一閃而過”呢,也曾有過呀。如果,就因其惡、其丑,她在家庭領域“孝”的影子,就視而不見了,似有些思維僵化了。
循“君子……不以人廢言”古訓,對那些“人、文反差”的詩作、詩句或文章,我們可大度接納。但同時,還應、更應汲取教訓,愛惜自己的羽毛,牢記“一致論”,遠離“人、文反差”,如“詩圣”杜甫那樣,時時抒寫、表現的,就是、多是“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那樣的愛國愛民、憂國憂民情懷。
如果,已經“失足”了,勇于悔過自新,便是首選了。“早年……橫行鄉里,(讓)鄉人苦之”的地痞流氓(后期)逆襲成唐詩大咖的韋應物,便是此之標桿、榜樣:在蘇州刺史任上,因病主動辭官后,因無回家路費,只好寄住在寺廟,竟至貧病而死……絕對清官廉吏了;其詩《滁州西澗》“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千古流傳了……
古人韋應物,能有如此脫胎換骨判若兩人之變其他人,能將不自新、不思齊的理由說出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