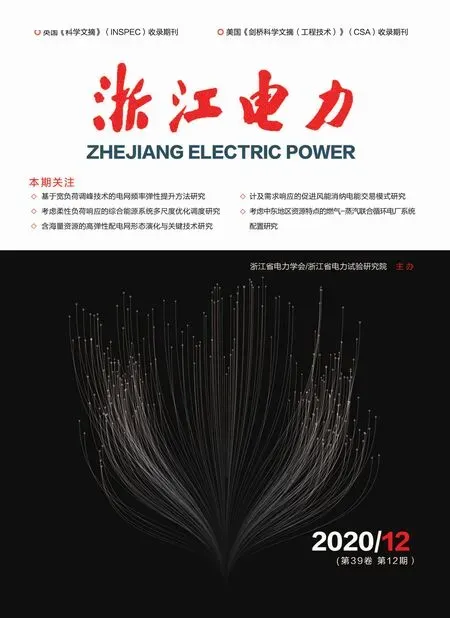基于LMDI 模型和K-means 聚類的中國電力消費因素分解
(華北電力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北京 102206)
0 引言
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能源的支持,而在中國終端能源消耗中電力的占比越來越大,2019 年中國全社會用電量達72 255.4 億kWh,是2006 年全社會用電的2.55 倍。當前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發展階段,經濟增速放緩,電力消費增速顯著下降,GDP 的增長與電力的增長逐漸脫離[1]。雖然中國已經控制了電力消費的過快增長,但近幾年的電力增長波動較大。因此,定量探尋中國電力消費的影響因素,在保證經濟平穩的前提下,對實現節能減排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對于電力消費的影響因素,國內外學者已經進行了很多研究,最常見的是從耗電強度、產業結構和經濟規模3 個因素對電力消費增量進行分解[2-3]。王海林等[4]選取經濟、強度、人口和活動4 個因素進行電力增長分解。王凌誼等[5]從人口、規模、結構、部門和強度5 個效應進行電力增長分解。
還有部分學者從不同的層面對電力消費增長進行分析。孫祥棟等[6]分行業對工業部門電力消費進行分解。郭麗萍等[7]采用空間計量經濟學方法對省域電力需求進行空間相關性及其驅動因素分析。黃天明等[8]從全國-地區-省/市3 個層面分析居民電力消費量增長的動因。
國內外學者進行電力消費增長研究時,研究方法主要包括:PLS(偏最小二乘回歸)[9]、多元回歸模型[10]、GDIM(廣義迪氏指數分解法)[11]、ISM模型[12]和LMDI 模型[13-14]等。
綜上所述,多數學者從全國、省域、產業或行業角度進行電力消費分解,無論是使用時間序列數據還是面板數據,一次都只對一個對象進行分解和分析,即使是全國性的省域研究,也只是對不同省份逐一分解,使得分解結果只適用于省份內部,而不能有效地對比不同省份。此外,基于多個層面分解的文獻較少,且部分文獻僅以省域、省域組合為不同分解單元進行多層面比較分析。因此,本文集成空間數據、產業數據和時間數據,從省域層面和產業層面分別對全國(不含港、澳、臺地區)電力消費進行分解,結合LMDI模型將電力消費影響因素分為經濟效應、結構效應和強度效應,并從省域和產業角度比較分析時間跨度下各因素的影響情況。對分解結果進行Kmeans 聚類分析,并給出優化中國電力消費結構的建議。
1 電力消費因素分解模型建立
1.1 LMDI 模型
LMDI 分解法是基于目標變量進行分解的,在分解過程中不會產生殘差。本文通過該方法將電力消費進行因素分解,可以精確衡量各分解因素對電力消費的影響程度。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本文將電力消費的影響因素歸納為經濟效應、結構效應和強度效應[15]。將總的電力消費量變動分解為:

式中:E 為總電力消費;Ei為因素i 的電力消費總量;為經濟產出;Qi為因素i 的經濟產出;Si=Qi/Q 為因素i 的產出份額;Ii=(Ei/Qi)為因素i 的電力強度。
乘法分解和加法分解可表示為:


式中:E0為初始時間的電力消費總量;ET為時間T 的電力消費總量;Dtot為從初始時間到時間T 電力消費的變動比率;Dact為經濟效應變動比率;Dstr為結構效應變動比率;Dint為強度效應變動比率;ΔEtot為從初始時間到時間T 電力消費的總變動量;ΔEact為經濟效應變動量;ΔEstr為結構效應變動量;ΔEint為強度效應變動量。
各效應變動比率和變動量的詳細計算方法如表1 所示。

表1 各效應變動比率及變動量計算公式
1.2 K-means 聚類
為簡化分析31 個省份的電力消費情況,提出具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本文選用比較經典的K-means 聚類算法,對31 個省份的電力消費分解結果進行分類。由于31 個省份對全國電力消費總量的影響差異較大,故本文以經濟效應、結構效應和強度效應為劃分依據,采用K-means 聚類法將31 個省劃分為4 類,以探究各省份電力消費的相似性與差異性。
K-means 算法為比較經典的聚類方法,應用范圍較廣,其輸入包括聚類數目k,n 個對象對應的屬性值;輸出包括最終迭代的k 個聚類中心及劃分的k 個聚類。
K-means 的計算步驟為:
(1)在給定的n 組數據集中,隨機選取k 個研究對象作為劃分初始狀態時的中心點。
(2)根據選取的中心點計算其他對象到各中心點的距離,將對象劃分到距離最近的中心點。
(3)迭代更新中心點。根據平方差值減少原則更新中心點。
(4)重復執行步驟(2)和(3),直到聚類中心不再發生改變。
2 省域層面和產業層面電力消費因素分解
本文分別從省域層面和產業層面對電力消費進行分解,探尋電力消費總量變動的影響因素。為方便分析各因素對電力消費的影響情況,將分解結果分為促進電力消費增長、基本無影響和抑制電力消費增長3 種情況。選取2006—2019 年電力消費相關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其中,分省份的GDP 和用電量源于各省、市歷年的統計年鑒,分產業的GDP 和用電量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部分數據源于國家統計局和國家能源局。
2.1 省域層面分解
根據表1 中的效應變動比率計算公式,以31個省份作為分解的單元,進行2006—2019 年全國電力消費變動的乘法分解,計算結果如表2 所示。表2 為電力消費變動率(ET/E0)的分解結果,若要計算電力消費增長率(ET/E0-100%)的分解結果,需要在表2 結果的基礎上統一減去100%,表3、表4 和表5 同理。
由表2 可知,2006—2019 年,經濟效應均促進全國電力消費的增長。其中廣東、江蘇和山東的經濟效應對全國電力增長的促進效應最大,在11%以上;青海、海南和西藏的經濟效應對全國電力增長的促進效應最低,西藏僅有0.09%。各省份結構效應對全國電力消費的影響有促進也有抑制,19 個省份為促進作用,12 個省份為抑制作用,其中湖北、貴州和安徽的促進作用最大,河北、遼寧、山東的抑制作用最大。大多數省份的強度效應抑制電力消費的增長,僅有內蒙古、西藏和新疆的強度效應促進電力消費的增長,說明中國多數省份的電力消費效率均在提高,電力消費較高的省份應注重科技引進和科技創新,降低電力消耗強度。2006—2019 年,31 個省份中,廣東、江蘇和山東3 個省份對全國電力消費的增長促進作用最大。

表2 全國電力消費在省域層面上的分解 %
圖1 為2006—2019 年分省份的經濟效應對全國電力消費增量的影響情況,其中,東部地區和北部的新疆、內蒙古對全國電力消費增長量的促進作用較大。
由圖2 可知,由于省域經濟結構的變動,全國電力消費量也會發生改變,整體的影響量比較弱。其中,南部和東北地區的影響差異較為明顯,南部多數省份的結構效應促進電力消費的增長,而東北地區多數省份的結構效應抑制電力消費的增長。
由圖3 可知,除內蒙古、西藏和新疆的強度效應為促進作用外,其他省份的強度效應均為負值,中部地區和東部地區的抑制效應最強。
2.2 產業層面分解

圖1 2006—2019 年分省份經濟效應變動量

圖2 2006—2019 年分省份結構效應變動量

圖3 2006—2019 年分省份強度效應變動量
根據表1 中的效應變動比率計算公式,以3個產業作為分解的單元,進行2006—2019 年全國產業電力消費變動的乘法分解,計算結果如表3 所示。

表3 全國電力消費在產業層面上的分解 %
整體來看,第二產業對全國電力消費總量的促進作用最大,達到200%以上;第一產業作用最小,2019 年與2006 年的電力消費水平基本一致。2006—2019 年全國第二產業迅速發展,促進電力需求增長達256.42%;近幾年,第二產業經濟占比在逐漸降低,促使全國電力消費總量下降15.39%;與此同時,第二產業也在提升用電效率,效果較其他產業更加明顯。
3 全國電力消費分解比較分析
以31 個省份為單位,計算每年各省份對全國電力消費的影響之和,將全國電力消費分解為省域經濟效應、省域結構效應和省域強度效應,根據表1 中的效應變動比率計算公式,進行全國電力消費變動的乘法分解,計算結果如表4 所示。

表4 分年度全國電力消費變動分解 %
由表4 可知,2006—2019 年全國電力消費總量一直在增長,2007 年、2010 年和2011 年快速增長,年增長率均在11%以上,其中2007 年最高,達14.80%;其余各年增長率均在9%以下;2015 年增長率最低,僅有2.33%;2014—2017 年增長率逐漸提升,但2019 年又下降到4.47%。經濟效應是電力消費總量增加的主要促進因素,2006—2019 年均促進電力消費增長,近幾年促進作用有所降低。2006—2012 年結構效應以促進電力消費增長為主,2013—2019 年以抑制電力消費增長為主,整體的影響很微弱。強度效應對電力增長的抑制作用在2008 年最為明顯,除了2018年,其余各年均是抑制電力消費增長。
以3 個產業為單位,計算每年各產業對全國電力消費影響之和,將全國電力消費分解為產業經濟效應、產業結構效應和產業強度效應,根據表1 中的效應變動比率計算公式,進行全國產業電力消費變動的乘法分解,計算結果如表5 所示。

表5 分年度全國產業電力消費變動分解 %
由表5 可知,2006—2019 年全國產業電力消費總量一直在增加,2007 年、2010 年和2011 年的電力消費增速在12%以上,其中2007 年最高,達13.52%;其余各年增長率均在9%以下;2015年增長率最低,僅有2.53%;2017—2019 年產業耗電量穩步增長,波動較小。產業經濟效應一直在促進電力消費的增長,2012 年之后促進比率在10%左右。產業結構效應對電力消費的影響較為復雜,大多年份為抑制效應,只有2007 年、2009年、2011 年和2001 年為促進作用。產業強度效應對電力消費起到抑制作用,除2013 年外,其余均起到了節能的作用,其中2008 年最為明顯。
如圖4 所示,基于全國消費總量(省域匯總)和產業因素分解的經濟效應影響比較相近,2006—2019 年,產業經濟效應對電力消費增長量的影響比省域匯總經濟效應略高。

圖4 經濟效應的乘法分解累積值比較
對于結構效應的影響,2 個層次的結果差異性較大。國家整體(省域匯總)經濟結構的改變對電力消費的影響不大;產業經濟結構的改變對節能的作用很大,具體如圖5 所示。

圖5 結構效應的乘法分解累積值比較
國家整體(省域匯總)強度效應對電力增長的抑制作用持續增加,但在近幾年出現波動。而產業層面電力消費強度對電力消費的累積影響在2012—2016 年基本不變,在2017 年擴大抑制作用,與國家整體(省域匯總)層面的強度效應影響逐漸接近,如圖6 所示。
通過對比分析可知,國家整體(省域匯總)經濟效應和產業經濟效應都會促進電力消費的增長;國家整體(省域匯總)結構效應對電力消費的影響較小,產業結構效應對電力消費具有抑制作用;國家整體(省域匯總)強度效應和產業強度效應對電力消費的抑制作用顯著。為實現節能減排的可持續性發展目標,并保證經濟的平穩發展,當前節能可行的方法包括調整產業結構、降低產業電力消費強度和降低省域電力消費強度。

圖6 強度效應的乘法分解累積值比較
4 省域聚類分析
由于31 個省份對全國電力消費總量的影響差異較大,本文以經濟效應、結構效應和強度效應為劃分依據,采用K-means 聚類法將31 個省劃分為4 類,以便提出具有針對性的節能建議。劃分的聚類中心如表6 所示,劃分的聚類結果如表7 所示。

表6 中國31 個省份電力消費聚類中心 %

表7 中國31 個省份電力消費聚類結果
由表7 可知,第1 類的省份最多,這一類區域的特點是經濟效應、結構效應以及強度效應對全國電力消費的影響均較小;第2 類區域經濟效應和結構效應促進全國電力消費增長,強度效應為中等抑制作用;第3 類區域的經濟效應對電力消費的促進作用較高,結構效應和強度效應對電力消費的抑制作用顯著;第4 類區域其經濟效應達到超高水平,強度效應對節能的作用十分顯著。
5 結論及建議
本文運用LMDI 模型從省域層面和產業層面分別對全國2006—2019 年的電力消費總量進行分解,量化了經濟效應、結構效應和強度效應對電力消費的影響,主要結論如下:
(1)從省域層面來看,經濟效應均促進全國電力消費的增長;各省份結構效應對全國電力消費的影響有促進也有抑制;大多數省份的強度效應抑制電力消費的增長,僅有內蒙古、西藏和新疆的強度效應促進電力消費的增長。
(2)從產業層面來看,第二產業經濟的增長對電力消費的促進作用明顯;第二產業在三產中的比重降低時,可實現節能;第二產業的用電效率提升較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顯著。
(3)比較分析省域層面分解和產業層面分解結果發現:省域經濟效應和產業經濟效應都會促進全國電力消費的增長;省域結構效應對全國電力消費的影響較小,產業結構效應對全國電力消費具有抑制作用;省域強度效應和產業強度效應對全國電力消費的抑制作用顯著。
(4)為實現節能減排的可持續性發展目標,并保證經濟的平穩發展,當前節能比較有效的方法包括調整產業結構、降低產業電力消費強度和省域電力消費強度。
(5)從聚類分析結果來看,第1 類區域為經濟效應較弱或強度效應較弱的省份,部分省份經濟效應較弱是由于其GDP 占全國GDP 比重較小。此外,北京和西藏電力消費強度已經達到較低水平,下降程度有限,應重點關注此區域中電力消耗強度較大的省份,出臺相應政策,提升電力利用效率;第2 類區域的經濟效應和強度效應均處于中等水平,應從兩方面同時優化;第3 類區域的經濟效應已經到了較高水平,需要通過繼續降低強度效應來實現節能目標;第4 類區域在全國電力消耗中起到重要作用,在經濟效用促進電力消費增長的同時,強度效應不斷抑制電力增長,優化了電力消費結構,應鼓勵其保持當前發展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