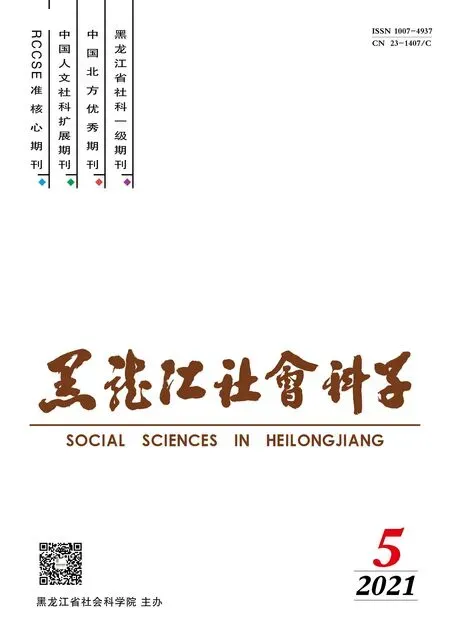關系與價值:五倫思想對現代道德生活的指引
延 玥
(聊城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山東 聊城 252059)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人必須生活在關系之中。孟子曾概括五種良好的人倫關系: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1]125。這種高度的概括和開辟式的創新讓儒家倫理進入了一個新的領域,而這五種良好的關系也被稱為“五倫”。
潘光旦梳理出“倫”具有的三層意義:一是秩序;二是類別;三是關系,而最重要的當屬“關系”[2]。五倫思想從創立之初至今已經走過了兩千多年的時間,似乎距離現代生活十分遙遠,是古代的、曾經的、歷史上的思想。那么,五倫思想是否具備對現代生活的啟發意義和指引作用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思考:一是五倫思想從何而來,二是五倫思想有何作用。
一、五倫與禮具有內在價值性
實際上,在儒家學者對道德生活人倫關系的設計中,孟子并非第一人。早于孟子五倫思想的有《尚書·舜典》的“五教”。《禮記·禮運》為五倫的關系中的十個角色進行了定位,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3]275,此所謂“五倫十德”或“五倫十教”。此外,《禮記·祭統》也有類似的敘述[3]639。
五倫思想概括的五種人倫關系,不僅區分了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十個角色的分內之事,還明確了這十個角色所體現的儒家價值觀,即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親、義、別、序、信來自何處?孟子認為其來自人的不忍人之心。孟子舉了一個“孝子仁人之掩其親”的例子,即孝子仁人埋葬去世的親人而非任由其曝尸荒野,是一種由孝子仁人“情感上的不忍”而導致的自覺行為,即不忍野獸昆蟲食之嘬之而自覺為其埋葬[1]135。這就是葬禮的來源,是人超越自然屬性、展現社會屬性的節點,是人的道德意識的覺醒。“情感上的不忍”擴充到場景與關系中,就會出現“殺牛釁鐘而不忍其觳觫”的不忍人之政和“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的出手相救[1]79,這也是孟子對道德的內源性即“非由外鑠我也”的論證。那么,道德生活的開展從何做起呢?孟子認為應遵循五倫的原則。遵循五倫原則是人之為君子、國之為國的象征,“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1]294。這里,五倫不僅具有道德性,還具有價值性。
與孟子所言的五種關系相同,荀子論禮的來源,同樣是基于對人的生活中之關系的思考。荀子曾明言禮來源于三種關系,即自然與人類的關系、祖先與子孫的關系、教化與服從的關系,即“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三者偏亡無安之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4]。而禮的內涵也來源于人的內心情感,孔子所說的“人而不仁如禮何”,就是在討論禮的道德內源性和價值性。
周敦頤從理學家的視角明確了禮與五倫的關系,他說:“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后和。”[5]清代李光地認為“仁”貫通五倫,他說:“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夫婦,倫也;仁、義、禮、智、信,性也。語其本之合,則仁貫五倫焉;義、禮、智、信,亦貫五倫焉。語其用之分,則父子之親主仁者也,君臣之義主義者也,長幼之序主禮者也,夫婦之別主智者也,朋友之信主信者也。”[6]這里,五倫關系不是出于先天的親近感或血緣關系的親疏,而是側重于道德生活的體現和道德角色的要求;也不是區分等級的簡單描述,而本質上是價值文化的集中展示。
可以說,儒家的五倫思想與禮具有同源的價值性。更進一步來講,兩者都表達了禮的兩方面意義:一是禮等級區分上的意義,二是禮價值文化上的意義。
二、道德生活的開展:踐行五倫
儒家側重關注人倫規范,認為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具備道德感,讀書即是學做人。賀麟談到五倫思想在中國思想文化中的地位時,認為五倫思想支配影響了中國人的道德生活,是中國傳統禮教的核心[7]。陸九淵說道:“今所學果為何事?人生天地間,為人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為學,學為人而已,非有為也。”[8]所謂“盡人道”,就是踐行百姓日用的道德倫常。而道德教育的核心內容就是“蒙以養正”,引導兒童踐行正確的道德生活。至于人為什么要“盡人道”,則是一個不用解釋、不容置疑的話題。
孟子有一個重要的童蒙教育觀點,即“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1]5。孝悌就是良好的父子關系和兄弟關系,引申為普遍良好的人倫關系。孟子認為,應把五倫教育放在學校教育的首位,即“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1]118。從大的方面來講,孟子強調開展道德生活能夠帶來社會效益,即人們踐行五倫有助于王者行王道;從小的方面來講,踐行五倫可以修身養浩然之氣,即強調個人修養工夫在道德境界上的成就。
以童蒙教育為植入手段的道德倫理教育,融入了儒家價值觀、文化觀,且以五倫為坐標,通過現實生活中的人倫交往,簡單直接地展現出儒家思想的精義,實現知行合一。朱熹的《童蒙須知》就是針對五倫關系而作的。例如,在教育兒童應對父子、長幼關系時,強調應“語言詳緩,不可高言喧哄,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首聽受,不可妄自議論”[9]。這種酷似《小學生守則》的書寫方式,只教兒童怎樣做,不講大道理,便是道德生活之學。
由此可見,五倫作為道德生活的踐行維度,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個是倫,另一個是理。倫是人的角色,理是角色的分內之事。倫理即根據關系中的角色,踐行角色的分內之事。這種倫理設計的基本原理就是:首先建立人倫關系的坐標或模式;然后再要求道德主體在倫理關系中定位,并恪盡自己的倫理本分——“安倫盡分”。《大學》所說的“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1]804便是如此。
三、五倫對現代生活的指引何以可能
五倫思想雖是一個“古董”,但在現代生活中仍具有存在的條件和適應的情境。
第一,兩千多年來,人類的五倫關系沒有發生大的改變。在傳統宗法社會的五倫關系中,人倫關系和個人角色都與家族息息相關。人有遠近親疏,差序格局就是倫理關系的特征。費孝通用水的波紋比喻差序格局,說道:“我們儒家最考究的是人倫,倫是什么呢?我的解釋就是從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系的那一群人里所發生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10]在現代社會中,在一定意義上,差序格局與千百年前并無二致,人仍然在遠近親疏的關系當中扮演各種角色。五倫中的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三種關系表明的是家族內部的人倫關系,君臣有義和朋友有信表明的是家族之外的人倫關系。這種設計與社會心理學理論不謀而合——社會心理學談到人的社會化,首先就是從家庭社會化開始的。人在童年與青少年時期主要受到父母、師長、同伴等“重要他人”的影響,其次受到社區、學校、公司等亞文化的影響,最后人們才實現對社會大文化的適應,五倫的設計符合人類社會化的發展規律。
在孟子的時代,五倫的設計意義在于給禮學一個執行標準,五倫的出現表明禮有條件全面貫徹到百姓生活當中。一方面,五倫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使“禮下庶人”,使禮代表的文明普及開來,是一個促進全民覺醒的舉措;另一方面,禮背后的價值文化有所變化。其變化在于:一是內容和形式的分離,即禮和儀的分離,孔子也曾說到禮脫離內容意義的虛無主義傾向,即:“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11]二是五倫出現后,學者多從仁這一角度解釋五倫,以仁、義、禮、智、信構成五倫;而以儀式、制度、規矩來解釋禮,使禮與五倫之間有所分離。
在現代社會,五倫仍然是社交情境和關系中的行為標準。家族倫理是社會倫理關系的原型,社會倫理關系是家族血緣關系的擴充與延伸,其他一切關系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定位。現代生活中的人倫關系與古代的人倫關系相比更加錯綜復雜,因此,現代學者提出了“六倫”“七倫”“九倫”“新五倫”“五緣”等說法,均具有極強的啟發意義。但我們仍然可以通過行動倫理層面將現實人倫關系與五倫實現對應,使五倫思想具備當下普遍性。《周易》中的“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12]可謂顛撲不破。
第二,五倫所依靠的人類內源性道德自覺沒有變。道德生活的前提是在厘清社會倫理關系的基礎上處理、調節各種人倫關系。然而,人們所面對的社會的倫理對象總是豐富的、復雜的,任何倫理體系都不可能窮盡一切倫理關系,也不可能指明一切人倫關系,更不可能向人們闡述面對一切倫理關系所應當遵循的倫理準則。所以倫理學的使命不在于建立一個包羅一切倫理關系的體系,而是要建立起特定時空條件下的人倫關系的一般原理,以及調節處理這些倫理關系的一般準則。孟子的貢獻在于把多樣性的人倫關系簡化為雙向的人倫關系,從而建立起一種人倫的坐標,為道德生活與倫理理論體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礎。五倫思想產生之后,中國倫理才有了內源性道德自覺的基礎。
在中國歷史上,五倫思想第一次建立起了道德生活的人倫標準。同前文所述,孔子、孟子、周敦頤、李光地等闡述內源性道德自覺和外在人倫關系的理路相同,現代學者也從這一角度出發,討論傳統倫理向現代發展的可能性。賀麟認為“以等差之愛為本而善推之”[13]是實現五倫思想對現代道德生活指引的方法。這一等差之愛,實際上就是費孝通所說的“差序格局”。陳來所提出的“仁包四德”[14],也同樣基于道德主體自覺的“仁”和等差之愛的理論。
不可否認的是,現代社會與古代中國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更加強調個人的發展,即對個人多樣化選擇的尊重。但經濟學的“理性人”概念并非五倫思想的破壞者,相反,強調個人發展與個性的同時更不能回避道德自覺。現代社會中人與人的相互尊重就是五倫思想對人際之間相互義務規定的一種體現。《中庸》中的“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表現出人倫關系中的相互性,強調的是角色的分內之責和道德自覺,其中并沒有強調角色的尊卑、貴賤。從這一點來講,五倫更適應提倡民主平等的現代道德生活。
五倫總結了人的倫理關系和角色定位,并明確了人應怎樣扮演好這個角色,依此可以建立起倫理關系的結構模式,其比禮學更加接地氣。“人倫”與“人際”的重要區別就在于人倫不僅是對偶的關系,而且其以血緣關系為起點,具有自我組織、自我組建的功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其才成為倫理的典范。雖然在中國古代社會中也提出過倫理關系的其他模式,但是影響力最大、最能體現中國倫理的民族特色、最具有生命力、被發揮得最系統的則是先秦時期所提出的五倫。所以,在一定意義上,五倫不僅是中國古代倫理的典范與絕佳設計,同時也是現代道德生活的踐履標準。五倫在現代道德生活中的規范作用和現實意義,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型發展提供了一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