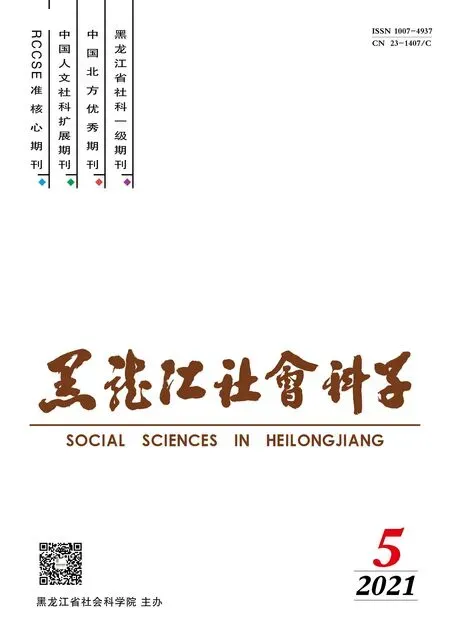后冷戰時期美國對外文化新宣傳路徑分析
王 智 麗
(同濟大學 藝術與傳媒學院,上海 200092)
一、新宣傳理念
宣傳自誕生以來,其觀念和實踐就在演化中不斷地修正自身。兩次世界大戰中,西方的宣傳實踐可謂登峰造極,極化的宣傳也使得這一語詞在西方逐漸成為一個貶義詞,人們對宣傳的反感使其逐漸由簡單粗暴轉變為精細節制,西方舊的宣傳開始改頭換面,以全新的理念和形式重新登場。到后冷戰時期,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國家尤其是在美國的崛起,使對全球化市場的追逐、資本主義向全球壟斷的發展、政治和經濟的宣傳融為一體,難分彼此。與此同時,社會環境對宣傳的約束也在不斷增強,公眾經歷過之前的宣傳和反思,已然接種了舊宣傳的“疫苗”,美國自由、民主理念也使得宣傳者變得克制,不敢再采取此前極端的宣傳手段,在新的社會環境中,舊宣傳逐漸失靈。
但是,美國對大眾的心與腦、情感與理智進行控制的企圖和做法始終沒有消失,甚至還在加強。“只要個人的選擇存在自由,追求傳播效率最大化的宣傳就一直會存在。”[1]后冷戰時期,無論是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還是作為其中一分子的美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強勢來襲的互聯網技術將世界聯結成一個統一整體,每一個國家或個人都成為網絡上的一個節點,麥克盧漢曾經預言的“地球村”在技術助力下成為可能。新的商業模式下的營銷為宣傳提供有益借鑒,新的媒介技術使得精細化、定制化的宣傳成為可能,而對社會科學的研究也不斷推進,這些對于處在全球網絡節點中的人的個體或群體的心理與情緒都有了更準確的把握。無論人們喜歡與否,作為現代治理術的一部分,通過算法、大數據等新技術手段對信息傳播進行精心計算進而“制造”共識、操縱大眾行為的新宣傳開始成為現代性的一個重要標志。全新的宣傳環境、宣傳技術以及宣傳渠道催生出新宣傳。在“萬物皆媒”的新媒體時代,無論是社會整合還是國家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的輸出,都更加需要新宣傳。
冷戰結束后,在大國之間的博弈、國際交往以及國際關系的維護中,意識形態觀念有趨于淡化的傾向,其中“歷史的終結”“意識形態終結”等論調時常被提起。20世紀90年代后,美國著名政治學家薩繆爾·P.亨廷頓曾經認為,冷戰后國家之間的沖突不再是由意識形態因素或經濟因素導致的,而是文化和文明的差異和沖突。
實際上,文化不僅僅是意識形態,文化差異也不僅僅是意識形態差異。然而,不論文化還是意識形態都要反映民族、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在這個意義上,后冷戰時期文化和文明的沖突實則是意識形態冷戰在和平與發展背景下的延續,即文化冷戰。正如美國學者貝利斯·曼寧所說:“未來的外交史家將會看到我們的時代是由兩個經典式沖突和一個新的與古老的宗教戰爭極為相似的新型沖突構成的:兩個經典式沖突包括圍繞均勢的斗爭和對經濟利益的爭奪,新型沖突則是圍繞什么是‘應該’支配經濟分配模式和個人、集體、國家之間正當關系的‘正確’原則的意識形態斗爭。”[2]
二、美國文化新宣傳路徑
冷戰后,美國意識形態的全球營銷非但沒有止步,反而以文化為主陣地,采用更加隱秘的宣傳方式與手段展開。其原因有三:一是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之間意識形態的交鋒在后冷戰時期還在延續,有學者將之稱為“文化冷戰”,約瑟夫·奈提出的“軟實力”在后冷戰時期成為國家實力的重要表現,美國也有意在全球建立葛蘭西所謂的“文化霸權”;二是冷戰后,美國政府熱衷于對全球推銷西方式民主,伴隨著直接的軍事入侵一起進入他國領土內的還有美國的文化,而文化的對外輸出顯然比戰爭更為隱蔽和有效,獨立的民族主義國家可以抵擋住美國的軍隊,但抵制不了精彩紛呈的好萊塢電影在民眾心中潛移默化的微妙影響;三是市場經濟全球化不斷追逐全球化的壟斷,美國輸出到海外的有形的商品中附著著更多的符號價值,美國式的生活方式借助商品營銷和文化宣傳完成了在全球范圍內的傳遞。
1.龐大的媒體帝國和對外宣傳網絡
美國不但有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還擁有強大的媒體傳播力。美國的媒體數量和媒體影響力的輻射范圍,都相當大。在傳統媒體時代,以《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每日鏡報》等報刊以及三大廣播公司為首的“新聞權勢集團”一直以來都是一種精英化的“化身”,是高質量原創新聞內容的提供者。在對外文化宣傳中,美國的紙質媒體如《時代周刊》《福布斯》《華爾街日報》等媒體,都會針對不同的地區,使用不同的語言,量身定制不同的版本。
美國廣播管理委員會(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管轄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自由歐洲(Radio Free Europe)、自由亞洲(Radio Free Asia)、馬蒂電視臺(TV Marti)以及中東地區廣播網——薩瓦電臺(Radio Sawa)和自由之聲電視臺(Alhurra Television)等用于進行國際傳播的機構,其通過電視、廣播、互聯網及其他新媒體以60余種語言向全球發布信息,每周的受眾量約達1.75億人次[3]26-33。“美國之音”在冷戰期間曾擔任著美國宣傳機器的重要角色,在對蘇東國家的意識形態宣傳中功不可沒。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后,“美國之音”似乎因此也修改了它的章程,并以具有公信力權威性的新聞媒體自居。然而事實是,后冷戰時期的“美國之音”依舊在為美國政府充當著宣傳工具[4]。“美國之音”的主要功能依舊是為美國政府的政治和外交需要作最大的努力,不斷向與其意識形態相異的國家進行意識形態的滲透和宣傳以期進行和平演變,只是宣傳戰的主要對象發生了變化。
美國有線電視網(CNN)、美聯社等新聞傳媒業的巨頭,開始與其他國家的機構合作,在海外開疆拓土,不斷成立自己的分支機構,構建廣泛的全球新聞傳播網絡。例如,美聯社有超過300個分支機構分布于全球,有3700名全球編輯、傳媒以及相關工作人員,其三分之二的員工是新聞采集人員[3]26-33。
及至新媒體時代,谷歌、Facebook、Twitter等大的網絡平臺公司開始搶占國內外新聞生產的市場。美國國務院倡導的“全政府外交”“全民外交”“互聯網外交”就是借助于社交媒體實現其“全天候的、立體化的”戰略傳播目標。
殖民時期的英國、西班牙、法國以及其他歐洲強國通過對全球土地的侵占來實現其殖民統治。現如今的傳媒巨頭則通過多樣化的媒介產品吸引全球受眾的注意力,進而將其資本主義的理念和價值在無形中灌注到受眾的思想中,進而實現對其心與腦的控制。“時代華納、迪斯尼、MTV、Blockbuster、好萊塢、CNN、BBC、福克斯、谷歌、MSN(微軟)、雅虎和互聯網等,都努力施加影響力……大眾傳媒和互聯網企業正引領我們建立一個新的王國。這一王國不是基于軍事力量或者國土面積,而是基于對人們頭腦的控制。”[5]美國密蘇里大學圣路易斯分校國際研究中心托馬斯·麥克費爾一語道破美國和其他西方媒體通過宣傳以期實現全球話語霸權的努力。
坐擁龐大的媒體帝國,如何讓其在對外文化輸出中發揮最大的宣傳效能?美國在這方面的成功皆因長期以來對受眾的重視。受眾研究甚至成為美國大眾傳播學的一個重要分支,除了對受眾個體以及群體心理的深刻洞察,新傳播技術手段也可對目標受眾群進行詳細的區分和選擇,進行精準宣傳。美國政府控制的廣播媒介、電視媒介以及新媒體均充分考慮到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受眾在價值觀、文化理念、生活習俗、喜好等方面的差異,從而有針對性地制作媒介產品吸引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受眾。美國在國際傳媒領域的霸權地位顯而易見。
2.作為新宣傳的好萊塢電影
電影可以成為一種重要的政治宣傳手段。阿爾都塞認為,電影、電視,以及報紙、文學、藝術、體育,等等,都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通過它們的狂轟亂炸,既可以用來輿論監督,也可以用來輿論監控;同時,通過其中的“意向文本”(Image Text),可以“建構意識形態,并確保其功能的發揮,將所有個體轉化為被社會結構所決定的主體,并使后者受控于這個無形的卻又普遍存在的社會法則之下”[6]。
將美國的意識形態巧妙地包裝在制作精美的電影中,通過電影宣傳美國的價值觀,在文化和心理層面進行滲透,早已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通過好萊塢電影對其他文化進行‘異端化、妖魔化’處理,為的是使觀眾接受‘美國救世論’。美國不僅在現實世界中,而且在虛擬現實中也想建立美國對世界的‘領導權’。好萊塢電影的熱賣,實際上表明了美國在文化上的霸權。”[6]
在文化政治學派看來,各種制度、法則、關系以及狀態,都能夠轉化成為不同的文本形態,而這些不同的文本形態又會通過電影這種文化產品形式表現出來,進而呈現給觀眾。第一,通過觀看電影,不同地區具有不同習俗和文化背景的群體或個體,可以完成趨同性吸引。第二,在建構外交政策上的話語權方面,身份認同會起到積極的作用;而且,通過傳播文化產品爭奪政治話語權,在很大程度上,比通過其他形式爭奪,所遭遇到的阻力要小很多。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可以通過時尚消費、新聞、廣告、電影、玩具等多種形式,做理念上的傳播與推廣。這也是美國利用文化來傳播自身的意識形態、建構霸權的一種方式。
3.持續的海外教育項目與學術交流
提到宣傳,人們往往想到的就是媒體。誠然,大眾媒體自誕生之日起就擔負起了宣傳的重要使命,成為宣傳者主要的宣傳工具,在人類現代文明的演進中曾發揮過重要作用,如報刊在早期革命中的革命宣傳、廣播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爭動員、電視在大選中的候選人形象展示,大眾媒介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大范圍的宣傳,甚至有學者認為只有面向大眾的勸服才是宣傳。
然而,后冷戰時期,各個國家都將注意力集中在經濟發展上,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不斷調整,社會組織形式也變得更加多元;同時,個人在追求自我發展的過程中隨著社會整體物質水平的提高,生活有了極大改善,社會需求也更加多樣,每個人的人生經歷、大腦思維和處事風格也都有很大的差異,此前希特勒、丘吉爾,以及艾森豪威爾等通過大眾媒介實現的“一呼百應”“萬眾一心”的大眾宣傳已很難實現。在新的媒介技術環境下,宣傳者再也不能任性而為,任何的宣傳都要建立在科學的數據分析基礎上精心籌劃、步步為營,方能實現預期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新宣傳的運行機制逐漸多樣化、立體化和泛在化。除新聞媒體的宣傳外,政治公關機制、高校等科研機構以及其他社會組織也被納入新宣傳的運行機制中,“教育交流和學術研究也成為一種新宣傳”,并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宣傳效果。
美國在對外擴張稱霸的道路上,對海外教育交流的投入從來都不遺余力。有美國學者從1953年對海外交流項目評估結果中發現,參與海外交流項目的外國人通過在美國的交流學習和生活逐漸改變了既往對美國的刻板印象,美國的家庭生活、宗教生活以及道德觀都受到他們的贊賞;此外,他們對美國的政治制度以及外交政策有了更為全面的認識,減輕了他們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帝國主義企圖的看法;最后,他們的到訪也加深了美國與其他國家的互相了解。根據美國文化官員對回國的受資助者專項研究結果來看,這些人中有一多半通過講演、發表論文、談活等將自己在美國的經歷介紹給本國人民[7]。美國政府對華的一個最大的官方教育交流項目就是“富布賴特項目”。美國政府每年會資助17至25名中國學者去美國研究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或教授中文。美國政府希望中國人以美國的思想觀念來理解西方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增強中國人對美國的理解。
除了政府層面推動的教育交流外,美國的一些私人組織也參與到教育交流中來,其中,大學發起或參與的對外學術交流活動為政府直接領導對外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起到了打前站的作用。美國在國家層面由國務院負責的教育交流項目僅占美國人員交流中的較小部分,而絕大部分人員交流是由私人贊助實現的[7]。
三、結論
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概念。認為“一個國家可以通過文化傳播來讓其他國家想己之所想”。“硬實力”依靠的是軍事干預和經濟制裁,“軟實力”則是依靠文化和價值觀等來進行意識形態傳播,這種意識形態傳播可以在文化與公共政策兩個層面上起作用。“軟實力”的核心理念是指:有能力吸引他人欣賞自己的觀點,并且誘導他人共享價值和目標,從而達到獲得他人支持的目的。“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有吸引力,其他國家的民眾便會樂于追隨,一旦它建立起與國際社會相適應的國際準則,便不會輕易更改,一旦它能輔助配合相關機構讓其他國家依照處于主控地位的本國政府的意愿去執行或限制執行他們的活動,那成本高昂的硬實力也就沒必要再放在談判桌上了。”[6]
無論是新聞媒體產品還是好萊塢電影,以及海外交流項目,等等,都成為了美國軟實力的象征,亦是美國對外文化新宣傳的重要載體,這些文化產品中呈現出來的美式生活方式、美國的價值觀念以及意識形態向海外傳播得雖然緩慢,但卻深刻地滲透進了人們的思維中。后冷戰時期,事實上在美國的對外宣傳中,冷戰思維還在延續,美國對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產品輸出正好乘著全球化的東風不減反增,而其制作也更加精良,宣傳意圖也更加隱蔽,前述的“美國之音”這樣的廣播節目、好萊塢電影,或是海外交流項目對他國民眾而言,都是巨大誘惑,而由麥當勞、肯德基、星巴克、蔻馳的手提包等日常生活物品中呈現出來的美式生活方式更是在這些品牌的全球化連鎖中讓他國民眾趨之若鶩。雖然看不到“宣傳”,但是長久地浸潤在這樣的美國式生活和文化氛圍中,他國不明真相的民眾對美國自然會充滿好感,心向往之。至此,美國的文化新宣傳也在悄無聲息中取得了預期的效果,完成了對美國意識形態的全球營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