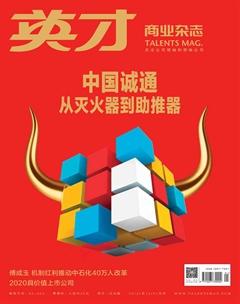地產三條紅線碧桂園與京東如何破局?
陶冶
在近年來中央的引導下,房住不炒的概念逐漸深入人心,而進入2020年后針對地產商的“三條紅線”更是正中各家房企七寸。房地產作為基礎型行業,其在過往的20 年中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面對如今的局勢,雖然行業崩盤企業大量死亡的情況不太可能出現,但在增量向存量轉化的過程中,行業整體降溫的大趨勢想必已是市場的共識。
在這個過程中許多房企在維系已有業務的同時也在不停尋找新的出路,造車、養豬、物業服務,究竟什么樣的轉型適合房企?舊有業務又該如何維系?面對如此艱難的2020,地產商這條大船能否順利掉頭?
碧桂園的選擇
2020年10月,龍頭房企碧桂園與滿國康潔簽訂了股權轉讓協議,碧桂園將以24.5億元價款收購滿國康潔70%股權。滿國康潔所經營的業務并不復雜,其主要負責多個城市地區的環衛清理工作。在地產商們另謀出路伊始,分拆上市、造車、養豬等操作頻頻刷新人們對地產公司的認知,但綜合來看可能碧桂園的選擇才是最適合的一條路。
碧桂園的物業服務在業內頗有名氣,業務主體在香港也順利完成了上市,本次收購滿國康潔的也同樣是這個上市主體,而在本次完成收購后碧桂園也就實現了從小家到“大家”,從小區到城市的大物業服務演變。
相較于過于遙遠的橫向跨界經營,碧桂園這次稍顯保守的拓展可能更適合當今局勢下的地產公司,在貼合主業的基礎上又擁有了較為穩定的現金流收益,聽起來顯然比跨界造車靠譜得多。
造車和環衛,這兩者不論在未來發展還是投入成本角度都不在一個量級,用來做比較好像稍顯不妥,但是從一個嚴重依賴融資的地產領域跨入造車這個同樣資本集中度較高的重資產行業,選擇進入環衛行業至少可以減輕碧桂園未來的資金壓力。
圍繞主業、輕資產、重服務,這應該是適合地產商們未來在主業之外做出選擇的大概方向,轉型一定是一個痛苦的過程,越是完善的傳統企業,掉起頭來就愈發笨拙。
但不論外部如何擴展,地產之外終歸屬于副業,我們不可能指望碧桂園在未來的某一天僅僅依靠環衛服務就可以繼續保持如今的地位,過多的關注主業之外是否會形成拖累效應也仍是一個問號,所以怎樣在存量的地產市場中挖掘更深的開發價值和提供更吸引人的服務,這可能才是地產商們未來的主要角力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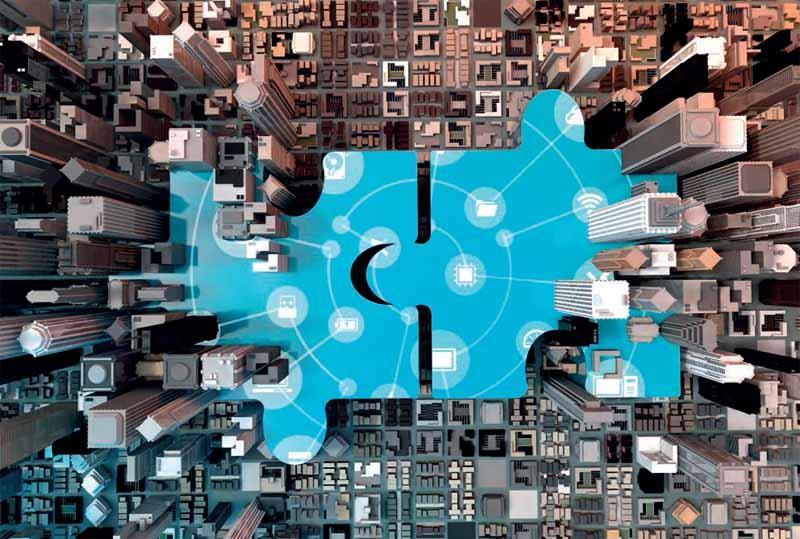
從住宅地產到產業地產
在過往我們熟悉的1.0地產市場中,住宅始終是舞臺最大的主角。不論是單純的競拍還是棚戶區改造工程,最終始終會回到圍繞住宅實現盈利,這其間政府調控的聲音也時有出現,相伴而來的產業地產、商業地產、文旅地產等新名詞卻大多雷聲大雨點小,圍繞住宅這一核心要素的開發思路仍未改變。
但現在以住宅為中心的盈利模式之路正在變得愈發難走,除了招拍掛的高溢價外,嚴苛的開發強度要求和政策限制都奪走了地產商們“躺著掙錢”的權利。
而參考近期京東在蘇州成功拿地的案例來看,在未來2.0版本的地產市場中,摒棄住宅這一思路,注重產業服務回歸產業地產本質,這一定會成為地產開發的未來趨勢。
蘇州作為國內經濟最為強勁的城市之一,其市內土地資源早已成為地產商們競相搶奪的香餑餑,而2020年10月,位于蘇州的兩宗土地卻意外落入了京東手中,17萬平的住宅加15萬平的商服用地,總價卻僅僅只有47億元,這優惠的價格背后就是“產業+地產”這一模式的真實體現。
在京東與蘇州政府的協議中,雙方針對開發強度以及其他各項條件的約定可謂是細致至極,其中“競得方必須引入一家財富500 強企業,否則不予辦理預售(銷售)證” 這一條就足以看出蘇州政府的本意何在。
除此之外其他開發強度上雙方也有多項約定,諸如“區域內需注冊成立不少于200家的電商、商貿、科研類公司”、“竣工后6個月內保證項目運營,同時確保5年內納稅不少于10億元”等,這些條件雖然與過往企業政府間的對賭條款大同小異,但如此巨大的量級想必任何一家普通的地產企業也會仔細考慮自己是否真的有這個實力完成“指標”。
產業引入、地產建設、后期培育與管理能力,京東在蘇州的勝利真實地揭示了地產開發2.0版本下土地市場供給與需求的明確關系。
反觀地產開發企業,種種嚴苛要求之下地產商們大都很難完全滿足要求,畢竟在產業層面,想要組織起如此龐大規模的產業集群并真實做到引入并非易事,但想要在土地市場中取得這樣的資源先機,主動尋求與實業企業的合作就顯得十分迫切。
以京東為借鑒,未來地產商的項目公司主體完全可以按照“產業方+ 地產方+ 建設方”三權分立的模式進行合作開發。
但與舊有的偽引入騙地騙補不同,如今形勢下更多的是要求地產商在早期協議約定、建設設計規劃以及后期管理等多個維度進行產業培育服務,加強與實業企業的合作切實做到有目的的開發,有方向的建設,取而代之的是原有“買地+ 蓋房+ 盈利退出”的粗曠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