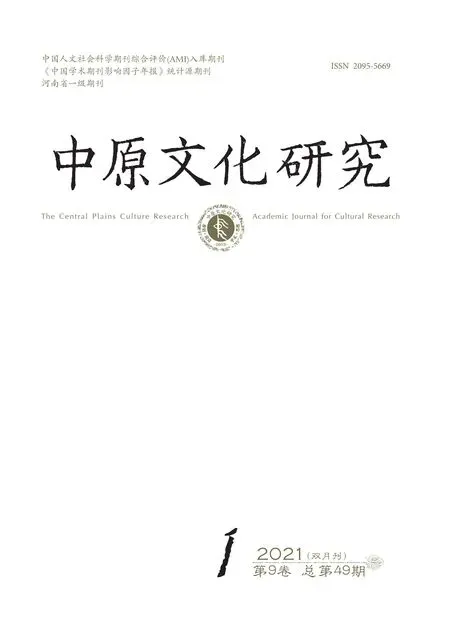殷周祭祖禮的因革與《周頌》的禮樂性質(zhì)
馬銀琴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詩序》把“頌”定性為“美盛德”以“告于神明”,讓“頌”作為“祭祀”樂歌的性質(zhì)突顯出來。因此,《兩周史詩》在考證“頌”之名義的演變之后,由“頌”與“庸”在“言成功”意義基礎上的通用,提出“頌”是“天子祭祀之樂的專稱”的看法[1]32。但是,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上述看法受到了越來越突出的挑戰(zhàn):既然是“天子祭祀之樂的專稱”,為什么“美盛德之形容”的《周頌》當中見不到祭祀周穆王及其后諸王的頌歌?是周穆王的功德不值得贊美嗎?唐蘭先生在《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一文中曾經(jīng)指出:“昭穆兩代應該是西周文化最發(fā)達的時代,拿封建社會來比較,昭穆時代是相當于漢代的漢武帝,唐代的唐明皇和清代的乾隆,都是由極盛到衰落的轉(zhuǎn)變時期。”[2]237《大雅》當中多次出現(xiàn)的對于周穆王的歌頌、《穆天子傳》所映射出來的當時的禮樂盛況,以及不斷出土的金文材料都在證實周穆王時代“是西周文化最發(fā)達的時代”的觀點,可是,為什么被認為“美盛德之形容”的《周頌》會在贊美周穆王的問題上缺席?班固《兩都賦序》中所說的“成康沒而頌聲寢”,究竟包含了怎樣的歷史認識?除此之外,《雅》中同樣存在許多屬于周天子的祭祀詩,那么“雅”歌之祭與“頌”歌之祭的區(qū)別究竟在哪里?基于多年來圍繞《周頌》問題的思考,在去年與同行學者就“《詩經(jīng)》與儀式”展開討論時,我提出了這樣的看法:“《周頌》并不單純只是祭祀樂歌,它更多的是和祭天儀式相關聯(lián)的。”“祭祀祖先的樂歌,只有和祭天禮儀關聯(lián)在一起的時候才能成為《頌》。”[3]那么,提出這個看法的依據(jù)是什么呢?在樂歌從屬于儀式的西周時代,禮樂制度發(fā)展演變的歷史實踐是否存在支持這種觀點的禮制基礎呢?這是本文試圖探討的問題。
一、對《周頌》作品時代與性質(zhì)的既有認識
依據(jù)筆者在《兩周詩史》中的考證,《周頌》作品的用途及以典禮歸屬可列表如下:

時代武王克商前后周公制禮作樂周康王周昭王周穆王作品①及用途《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賚》,大封于廟也。《酌》,告成《大武》也。《天作》,祀先王先公也。《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維清》,奏象舞也。《振鷺》,二王之后來助祭也。《思文》,后稷配天也。《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武》,奏《大武》也。《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豐年》,秋冬報也。《絲衣》,繹賓尸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廟也。《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也。《執(zhí)競》,祀武王也。《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訪落》,嗣王謀于廟也。《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小毖》,嗣王求助也。《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雝》,禘大祖也。《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載芟》②,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歌辭表現(xiàn)的典禮歸屬祭天祭河岳百神祭文王祭文王告功祭先公先王祭文王祭文王祭文王諸侯助祭后稷配天諸侯助祭祭祖合樂諸侯朝廟、祭祖合祭文、武祭武王報天祭祖繹祭酬尸合祭文王、武王、成王諸侯助祭成王配天合祭武王、成王、康王即位招魂即位求助即位戒王即位表決心薦新之祭祭祖祭昭王祈社稷報社稷
分析上表,有幾個地方非常值得關注。首先最引人注目的是《周頌》作品的時代,31 篇作品,集中出現(xiàn)在武王克商前后、周公制禮作樂以及周康王、周穆王時代。這幾個時期,都是周代禮樂文化發(fā)展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時期:武王克商,結束殷人統(tǒng)治,建立周人政權;周公制禮作樂,奠定后世禮制基礎;周康王時期,西周早期趨于成熟的祭祖禮程式化,“定樂歌”;周穆王時期,殷周禮制的分水嶺,真正意義上的“周禮”至此形成[1]104-166。
在此基礎上,以《周頌》作品的內(nèi)容為基礎再進行綜合分析,這些作品實際上又可區(qū)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類是與祭祀天地社稷百神相關聯(lián)的,這類樂歌的時間跨度最大,從武王克商前后的《時邁》《般》,周公制禮作樂時的《豐年》,到周穆王時的《潛》《載芟》《良耜》等,均屬此類。
第二類是與祖先祭祀相關聯(lián)的,又可區(qū)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專祭類,如祭祀后稷的《思文》,祭祀文王的“《清廟》之三”、《我將》,祭祀武王的《桓》,祭祀成王的《嘻噫》等;二是合祭類,如以太王、文王合祭的《天作》,以文王、武王合祀的《武》,以文王、武王、成王合祭而配天的《昊天有成命》,以武王、成王、康王合祭的《執(zhí)競》等;三是《詩序》說“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但詩言及“昭考”的《載見》。
第三類是關聯(lián)于祭天祭祖的典禮活動中某個具體儀節(jié)的配樂歌辭,如與助祭相關的《振鷺》《烈文》《有客》《臣工》等,與繹祭相關的《絲衣》等。
在上述分類中,最具標志性意義也最值得進一步分析的,是第二類與祖先祭祀密切關聯(lián)的詩歌。李山、蔣清宇在《頌歌獻給誰——論〈詩經(jīng)〉雅頌祭祖詩篇的“禮樂”品格》中專門討論過《雅》《頌》祭祖詩的歌頌對象問題,該文的回答是:“大約一百多年創(chuàng)作出來的諸多‘雅頌’祭祖篇章(就今天所見的《周頌》和《大雅》祭祖詩篇而言,沒有見到西周晚期的作品)所敬獻的對象只有周文王、后稷以及武王和公劉等幾個為數(shù)不多的先公先王。”[4]但是,若把討論的范圍限定在《周頌》部分,可以發(fā)現(xiàn),在《周頌》中作為受祭者出現(xiàn)的,除了作為周人始祖配天而祭的后稷,還有奠定周人基業(yè)的太王,以及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和昭王。而從周穆王之后,則再無周王進入《周頌》的歌頌視野。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恰恰是周穆王在《大雅》當中被作為歌頌對象的頻繁現(xiàn)身。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實際上,這與周代早期祭祖禮的發(fā)展及其在穆王時代發(fā)生的變革具有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
二、西周初年祭祖禮與殷禮的關聯(lián)與差異
周人的祭祖禮,最典型的就是昭穆制度。《禮記·祭統(tǒng)》云:“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于大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5]3184辨昭穆的目的在于明“親疏之殺”,這就意味著不是所有祖先都能得到祭祀,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祭祀先祖的權利,因此就有了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的等級差異。但是,《禮記·王制》所載“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的“天子七廟”,一直未得到更多資料的支持。在可以據(jù)信的文獻資料中,《逸周書·世俘解》在“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之后,以追述的方式記錄了伐商過程中一系列重要的事件,包括周人取得勝利之后一系列祭祀活動的整個過程:
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執(zhí)夫惡臣百人。太公望命御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戊辰,王遂柴,循追祀文王。時日,王立政。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wèi),告以馘俘。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王不格服,格于廟,秉語治庶國,籥人九終。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籥人造,王秉黃鉞正國伯。……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翼予沖子,斷牛六,斷羊二,庶國乃竟。告于周廟曰:“古朕聞文考修商人典,以斬紂身,告于天、于稷。”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曰:“惟予沖子綏文考,至于沖子。”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6]414-442③
文中多次出現(xiàn)的“告以馘俘”,指報告殺敵與俘虜?shù)那闆r。在周武王克殷殺紂,太公望狙擊來方之后,周武王于戊辰這一天舉行了滅紂之后的第一場祭祀活動,即“王遂柴,循追祀文王”。在這里,作為祭祀對象的只有“柴”祭的“天”或“帝”以及武王之父文王。至辛亥“薦俘殷王鼎”之后,武王“告天宗上帝”,然后“格于廟”,“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辛亥日的祭祀規(guī)模超出了戊辰日,除了“天宗上帝”和文王,從太王開始的直系祖先和包括太伯、虞公以及伯邑考在內(nèi)的旁系親屬都在祭祀之列。五天之后的乙卯日,又發(fā)生了“以庶祀馘于國周廟”“告于周廟”的活動,這次所告、所祭的對象,除了“文考”之外,還有“天”和“稷”。劉源《商周祭祖禮研究》認為,“這次祭祀活動的內(nèi)容與商人文化有很多近似之處”,具體來說,“可以指出如下幾點:一、兼祭直系、旁系。二、宗廟獻俘,并用以為人牲。三、告祭祖先以牛為牲,祭百神水土用羊、犬、豕等小牲”。同時他還指出:“這次祭祀活動與商人文化區(qū)別處,主要表現(xiàn)在祭天(帝)上。”[7]149就目前的資料來看,周初武王舉行的祭祖活動,總是與祭天同時進行,即“以祖配天”。學者們大多認為,周人的“以祖配天”,是對殷人“賓帝”模式的學習與繼承,可為什么劉源卻說武王的祭祀活動與商人文化區(qū)別處,主要表現(xiàn)在祭天(帝)上呢?這個根源需要從殷人的“帝”與周人的“天(帝)”之間的差異上去尋找。
胡厚宣先生在《殷卜辭中的上帝和王帝》④一文中,細致梳理了出現(xiàn)在甲骨文中的“帝”,最后得出的結論是:“殷代從武丁時就有了至神上帝的宗教信仰。”胡先生還同時指出,“殷人以為帝有全能,尊嚴至上,同他接近,只有人王才有可能。商代主要的先王,象高祖太乙、太宗太甲、中宗祖乙等死后都能升天,可以配帝”[8]。這里所說的死后升天配帝,在祭祀活動中即被稱為“賓帝”。那么,這位具有至上神屬性的“帝”,與商人的祖先是一種什么關系呢?王暉在《論商代上帝的主神地位及其有關問題》中集中討論了這個問題,該文指出:“殷人的上帝就是殷人的至上神,是殷人把祖先神和自然神結合在一起的主神。作為祖先神,殷人的上帝就是帝嚳,也就是殷人的高祖。……祖宗神和自然神結合是殷代帝權的特征。”[9]“作為祖先神,殷人的上帝就是帝嚳;作為自然神,帝嚳又管轄著日月神。上帝統(tǒng)領著日月風雨云雷等自然神。祖先崇拜與自然神結合是殷商時期神權政治的主要特征。”[10]除了“上帝”的祖神身份之外,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曾專門討論過河神、岳神的神性與祭祀問題,在細密的考證之后,得出的結論是:“在商人的心目中,祖先神岳與祖先神河一樣,也主要是掌管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神,他們都是殷人的高祖神。”[11]193這些研究,都肯定了殷人文化中帝祖合一的文化特征。
除上述說法之外,朱鳳瀚《商周時期的天神崇拜》一文,在細致梳理殷墟卜辭所見商人諸神靈的基礎上,系統(tǒng)論述了另外一種說法,即殷商時代的“上帝”“既非至上神也非商民族的保護神”[12]。該文將商人的神靈歸劃為四種類型:上帝,自然神(如社、方),由自然神人神化而成的祖神(如河、岳),非本于自然神卻具有自然或戰(zhàn)事權能的祖神。在敘述分析各類神靈的權能范圍之后,該文指出:
商人的宗教作為一種多神教,除上帝以外,自然神、祖先神仍在商人宗教觀念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不同等級的祖先神作用之突出與深入更是不能忽視的。……上帝與部分祖先神如岳、河、王亥等遠祖、高祖以及上甲之間在權能范圍方面差別似并不明顯,而且也并未形成諸自然神、祖先神各有分工,各司其職,而由上帝以萬能之神的姿態(tài)將一切神權總攬在手中的局面。[12]
這是一個不同于前述諸家觀點的說法。但值得注意的是,該文在否定上帝作為商人至上神的屬性,論證“上帝與商人的祖先神、自然神之間缺乏明確的統(tǒng)屬關系”時,卻也肯定了“上帝”與岳、河、王亥等祖先神“在權能范面方面差別似并不明顯”的情況。結合商人把部分死去的先王稱為“帝”的事實來看,在殷商時代,“上帝”與部分祖先神之間的差別或者界限實際上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如該文所言,“卜辭有卜‘帝其陟’的(30387),‘陟’在卜辭中常以‘陟于’某祖神形式出現(xiàn),當是指祭祀時上祭至某祖神。但在這條卜辭中,‘陟’的主語是帝,當是指上帝在降到人世后又返回天上之舉動”,而帝辛時的銅器銘文中也出現(xiàn)了“于上帝”的記載。依據(jù)這兩條材料,作者又提出了一個假設:“如此字(即‘’)與祭祀有關,則標志殷末對上帝的宗教崇拜及禮儀已較前有了重要的變化。”[12]這就是說,即使商代早期的“上帝”身份不明,但是到商代晚期,商人眼中的“上帝”已顯示出較為明顯的祖神化的痕跡。
因此,綜合既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在殷商時代,“上帝”的身份也經(jīng)歷了一個發(fā)展變化的過程,這位在早期與岳、河、王亥等權能無甚差別,看上去是天下共神、具有自然神屬性的帝,到商代晚期應該已經(jīng)兼具了至上神與祖先神的雙重身份。而這一點,從神話學的角度也能獲得印證。《史記·殷本紀》比較詳細地記載了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的商人始祖誕生神話。在這個神話中,這只玄鳥實際上就是契的父親。這位看上去非常神秘的“玄鳥”,其身份則是有跡可循的,他和《山海經(jīng)》中的帝俊、甲骨文中的高祖以及古史傳說中的帝嚳實為同一人。也就是說,在《史記》記載中除了“吞玄鳥卵而生契”的方式顯示出了神異的色彩之外,“玄鳥”的出現(xiàn)并沒有改變帝嚳作為殷人始祖的性質(zhì)⑤。因此,對商人而言,祭帝、祭河、祭岳,同時就是祭祖,帝祖合一或者說祖神合一是殷商祭祀文化的核心要義。因此,“上帝”以及賓從“上帝”、同時具備神格的歷代“王帝”,必然佑護殷人政權,是商王朝維護其統(tǒng)治合法性的精神支柱。正如王暉所言:“商王統(tǒng)治諸侯方國的唯一而且有效的方式是神權統(tǒng)治,其統(tǒng)治的方式是內(nèi)服的眾臣和外服的侯甸男衛(wèi)都沒有祭祀上帝鬼神的權力。甚至連自己的祖宗也只能靠商王在祭祀先公先王時配饗。”[9]《左傳·僖公十年》“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孔穎達疏云:“《傳》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則族、類一也,皆謂非其子孫妄祀他人父祖,則鬼神不歆享之耳。”[13]3910這種基于血緣聯(lián)系的天命神權觀念,讓商人天然享有被佑護的權力,這也給了商紂王虛幻的力量。當西伯征討黎國讓祖伊憂懼不已時,殷紂王仍然懷有“我生不有命在天乎”[14]107的自信。此時,對同樣需要“天命”佑護的周人來說,如何獲得“天命”,就是他們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在與商王朝對抗的過程中,他們找到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打破帝祖合一的神權觀念,切斷至上神“上帝”與殷人的血緣關系,同時推崇“天”的至高無上,宣揚“德”與“天命”之間的關聯(lián)。他們把“天命”解釋為“民心”,把行善積德作為獲得民心進而得到天命佑助的途徑,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15]385,以此消解殷人“有命在天”的合法性。《史記·周本紀》記載文王事跡云:“遵后稷、公劉之業(yè),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14]116西伯的積善累德不可避免引起了其他諸侯的警惕,于是發(fā)生了崇侯虎譖西伯而紂囚之于羑里的事情。之后在閎夭等人的努力下,殷紂王不但赦免了西伯,還賜之弓矢斧鉞,讓他獲得了征伐諸侯的權利。重獲自由的西伯繼續(xù)以德服眾,因“虞芮之訟”被諸侯稱為“受命之君”[14]117。
在“天命”與“民心”之間建立聯(lián)系,通過“立德”獲取“民心”以得到“天命”的佑助,這是周人對抗商紂王的有效手段。在“立德”的過程中,周人也實現(xiàn)了對“天”的推崇,對“帝”的改造。在武王克殷之后的“薦俘殷王鼎”的告功之祭中,“天宗上帝”就作為武王告祭的對象同時出現(xiàn)了。而在周初的其他文獻中,也保留著很多“帝”“天”同出的記載。如《尚書·召誥》:“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茲服厥命。”[15]450《尚書·康誥》:“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15]431在與“天”同出的過程中,被殷人視為祖神的“帝”,與殷人的關系變得疏離起來。《詩經(jīng)·皇矣》就記錄了“上帝”對殷人的拋棄:“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jiān)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詩序》說:“《皇矣》,美周也。天監(jiān)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詩贊“上帝”而“序”云“天監(jiān)”。正是在殷周對抗的過程中,“上帝”逐漸脫去了殷人祖神的身份,變成了與“天”等列的天下共神。
可以說,“德”的介入,讓殷周之際權力更替所帶來的族群對抗,同時也在天命神權的文化觀念層次上展開。周人以“德”為中介在“天命”與“民心”之間建立起來的聯(lián)系,動搖了殷人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天命神權觀念,掙脫血緣紐帶的天人關系表現(xiàn)出了更多人文理性的精神,由此凝結成為對后世影響深遠的政治理念:“皇天無親,唯德是輔。”
三、西周早期祭祖禮的特點
《說文解字》釋“禮”云:“禮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豊亦聲。”從事神致福的活動中發(fā)展起來的“禮”,與人們現(xiàn)實生活中思想觀念的發(fā)展變化息息相關。正如《禮記·禮運》所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夫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秌,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yǎng)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5]2065-3066經(jīng)濟、政治、文化、思想的發(fā)展變化,都直接表現(xiàn)在對“禮”的實踐上。“禮”有“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5]2263的功能和意義,都通過具體的行為規(guī)范表現(xiàn)出來。因此,殷周之際爭奪“天命”佑助過程中“德”的介入所帶來的思想領域內(nèi)對至上神權與人間政權血緣關系的割裂,最終一定會落在“禮”的實踐層面,通過“禮”的規(guī)定發(fā)揮更為廣泛的影響。那么,和殷商時代相比,西周早期的祭祖禮究竟有沒有呈現(xiàn)出相應的特征呢?
繼《逸周書·世俘解》所載武王克商,依循殷王帝祖合一的方式“告天宗天帝”,王烈祖之后,再次特祭文王并“告于天、于稷”之后,《天亡簋》等的記載也展示出了與之相似的“以祖配天”的祭祀模式:“乙亥,王有大禮。王泛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佑王,衣祀于王丕顯考文王,事饎上帝,文王監(jiān)在上。”在這時,作為祭祀對象的文王與上帝同在,這也就是《大雅·文王》所說的“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稍后出現(xiàn)在《何尊》當中的“初壅宅于成周,復爯珷王豊福自天”[16]275⑥,也表現(xiàn)出了以武王配天而祭的影子。《逸周書·作雒》云:“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明確規(guī)定祀“上帝”時以后稷配祭,“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反映出了祖先神與自然神合祭的特點。另外,《周頌·噫嘻》是在“春夏祈谷于上帝”的典禮儀式上使用的樂歌,祈谷的對象是“上帝”,但詩卻說“噫嘻成王,既昭假爾”,也明確地傳達出了“以祖配天”的祭祀觀念。
但是,《小盂鼎》銘文所記載的一次發(fā)生在康王末年的獻祭典禮中,卻出現(xiàn)了一些與“配天而祭”不同的內(nèi)容:
唯八月既望,辰在甲申。昧爽,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酒。明,王格周廟。□□□□賓延邦賓,尊其旅服,東向。盂以多旂佩鬼方□□□□,入南門,告曰:……以人聝?nèi)腴T,獻西旅□□,入燎周[廟]……大采,三周入,服酒。王格廟,祝延□□□□□邦賓,丕祼,□□用牲禘周王、武王、成王。□□卜,有臧。王祼,祼述贊邦賓。[17]417
這次活動從“王格周廟”正式開始,整個過程都在廟中完成,獻俘之后,除了“禘周王、武王、成王”及“卜”之外,沒有出現(xiàn)祭天或祭帝的內(nèi)容。李學勤先生在把《小盂鼎》與《世俘解》進行比較后指出:“武王隨后告于周廟,用牛告于天和稷,用小牲于百神、水、土社。這和鼎銘禘祀先王雖不相同,意義也是相當?shù)摹!保?8]⑦也就是說,同樣是獻俘之祭,發(fā)生在周康王三十五年的這一次活動中,禘祭先王的儀式取代了“告于天、于稷”以及祭百神、水、土的儀典。這其中就反映出了周禮與殷禮的不同。
正如孔子所言,“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西周初年祭祀禮儀的創(chuàng)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殷商祭祀文化的影響。劉雨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禮》中就指出,出現(xiàn)于西周金文的二十種祭祖禮,“除翟、禋、嘗三種次要祭禮外,其余十七種祭祖禮都是殷周同名的”,“周初幾乎全盤繼承了殷人祭祖禮儀的名稱”[19]。這種對于殷禮的繼承,從周公制禮作樂時依然采用“配天而祭”的模式,把祖先神與“天宗上帝”一起祭祀集中地反映出來。《周頌·思文》說“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大雅·文王》說“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逸周書·作雒》也說:“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6]533這些都是周公制禮作樂時“以祖配天”的祭祀觀念的反映。總結為一句話,就是《孝經(jīng)》所言:“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但“以祖配天”并不是周人祭祖禮的全部,除了“配天而祭”之外,獲得延續(xù)的還有族群內(nèi)部一直存在的近親三代之祭。這從《天作》一詩對于太王、文王的合祭中約略反映出來。而到周公制禮作樂時,就以《逸周書·作雒》所云“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的宮廟形式表現(xiàn)出來。孔晁注云:“太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6]537若如孔晁所言,太廟為后稷之廟,則周公制禮作樂時的宗廟之祭,是以后稷、文王、武王作為主要受祭者的,這似乎體現(xiàn)出了對宗廟之祭與配天而祭兩種祭祖方式的糅合。
從獲得王權的角度而言,“配天而祭”的意義遠遠超出了周人原有的宗廟祖先之祭。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周革殷命的思想斗爭中,對“德”的推崇割斷了以血緣為基礎的天命神權觀念,“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深入人心。在這樣的背景下,除了強調(diào)文王因文德而得受天命之外,對“天宗上帝”的祭祀實際上就不再顯得急迫而重要了。相反,通過祭祀祖先獲得祖先的佑助,通過效法文、武之德而得以永保天命,就成為周人更為看重的事情。《尚書·金縢》記載了既克商二年武王生病時周公為壇“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的應對之策,他在告辭中說:
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15]416
在這一次關涉周武王死生大事的祝禱中,周公旦所告的對象并非“天宗上帝”,而是太王、王季、文王,“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從這句禱文來看,周武王的疾病不但完全系牽在“三王”身上,而且,“三王”對于如何處理還具有相應的選擇權與決定權。這就與甲骨卜辭所顯示出來的具有至上神意義的始祖“上帝”對人間事務具有絕對的處置權,在上帝左右的其他先帝只具有轉(zhuǎn)為祈請與傳達帝命的權力有了本質(zhì)的不同。把這種情況和“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觀念聯(lián)系起來,可以得出一個推論,“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觀念疏遠了人與“天宗上帝”之間的直接聯(lián)系,人不再可能因為祭祀“天宗上帝”而獲得“天命”。在這個時候,因為“立德”而成為“受命之君”的祖先的意義與功能必然得到進一步的強化。《何尊》銘文記載了周成王誥宗小子之言:“昔在爾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茲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民,烏虖!爾有唯小子亡識,視于公氏,有勛于天,徹令。敬享哉。唯王恭德欲天,順我不敏。”[16]275在以武王配天而祭的儀式上,成王誥辭仍在強調(diào)“文王受茲大命”。這樣的強調(diào),和《周頌》當中對“文王之德”“文王之典”的歌頌一樣,一方面成功樹立起了“敬天法祖”的意識,讓文王成為后世子孫世代學習與效法的對象;另一方面,“文王在上,于昭于天”的“配天”而祭,讓割斷帝祖關聯(lián)之后失去“天宗上帝”之必然庇護的周人,在對祖先的祭祀中尋找到了可以替代“天宗上帝”來保護自己的力量。
因此,在“以祖配天”的祭祀模式下,對祖先神的重視逐漸超越了高高在上、與人無親的“天宗上帝”,祖先神成為最重要的祭祀對象。《禮記·祭統(tǒng)》云:“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于祼,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5]3481所謂“獻”,當指獻祭之事。而所謂“祼”,《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鄭玄注云:“祼之言灌,灌以郁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20]1636則“祼”是祭祀先王的典禮上用郁鬯灌地獻尸的儀節(jié)。“獻之屬莫重于祼”的“周道”,充分展示了祭祖禮在整個祭祀系統(tǒng)中的意義。由此,我們也就能夠理解在“春夏祈谷于上帝”的典禮儀式上,周人為何不直接向“天宗上帝”禱告,卻要通過“噫嘻成王,既昭格爾”來拉開春耕生產(chǎn)的序幕,因為對于持有“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之文化觀念的周人而言,血脈相連的祖先要比沒有任何親緣關系、僅僅作為至上神照臨下土的“天”與“帝”更能提供直接的庇護。因此,與殷商時代自然神與祖先神合而為一的祭祀觀念不同,從西周初年開始,在接受殷商文化影響而形成的“配天而祭”的框架之下,周人通過“立德”,讓文王在獲得天命佑助的同時,也獲得了取代天宗上帝來護佑子孫的神性。于是,在周文王立德積善而“受命稱王”的說法為周人奪取王權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論保障之后,法祖、修德就成為周人永保天命的努力方向。
周人克商伊始,“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至周公制禮作樂時,文王之文德與武王的武功,作為周人獲得“天命”的象征被大肆宣揚,所謂“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在這個時期,除了配天而祭的始祖后稷,與奠定周人興起基礎的太王之外,文王與武王是被祭祀、歌頌與效法的重點。至康王時期,成王亦得配天而祭,“郊祀天地”的《昊天有成命》,“是道成王之德也”,“春夏祈谷于上帝”的《噫嘻》,呼成王之神而告之。但是,以成王配祭的典禮,并沒有妨礙對文王與武王的推崇,“昊文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就是在充分肯定文武功德的基礎上對成王的進一步歌頌。到康王末年,《小盂鼎》的獻祭大禮中,也仍然是以“周王、武王、成王”作為禘祭的對象的。而金文所見西周早期與祭祖相關的銘文,大多會明確標注“某作某祖先某器”,“某祖先”,絕大多數(shù)為“皇祖”“皇考”“文考”或“皇祖皇考”,表現(xiàn)出了重視近祖的禮俗。正如劉雨在研究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禮之后所指出的:“周人的嫡庶、尊卑、親盡毀廟等制度在祭祖禮中是有反映的,綜觀二十種祭禮,所祭對象沒有超出三代者,這與殷人遍祀先公先王的制度明顯不同。”[19]
康王時代的《小盂鼎》記錄了周康王“禘周王、武王、成王”的典禮,這里的“周王”,學者們多對應于“文王”。《大盂鼎》記錄了周康王對文王、武王的歌頌:“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慝,匍有四方,畯正厥民。”[17]411但是,到昭穆時代,“祭不過三代”的祭祖習慣與對文王、武王的尊崇需要之間開始出現(xiàn)不協(xié)調(diào)的情況。在祭祖禮的實踐中,人們?nèi)匀蛔裱匾暯廊嫦鹊亩Y俗,如昭王時的《執(zhí)競》詩云:“執(zhí)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所祭祀的對象為武王、成王、康王。至《閔予小子》的“于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禱告對象仍然是“皇考”,期盼“皇考”以“克孝”之心,“念茲皇祖”而“陟降庭止”。這首《閔予小子》,固然有昭王野死帶來的特殊的“招魂”的性質(zhì)[21],但其中仍然表現(xiàn)出了重視“近祖”的傾向。而另一方面,宣揚文王之德、武王之功,又是這個時期迫切的政治需要。《逸周書·祭公》記述了祭公臨終前與周穆王的對話,其中“予小子追學于文、武之蔑,周克龕紹成康之業(yè),以將天命”等言,可視為周穆王追效文、武的宣言。而從祭公謀父“維我后嗣旁建宗子,丕維之始并……丕及有利宗,丕維文王由之”之言,我們能夠看出其對于文王的強調(diào)以及對宗族力量的重視。
由此而言,到昭穆時代,周人實際上執(zhí)行的“祭不過三代”的祭祖禮,與周王室尊崇文武的政治追求之間出現(xiàn)了顯而易見的矛盾。“禮樂刑政,其極一也。”[5]3311在政治上被重視、被推崇的人與事,必然通過躬行之禮反映出來。于是,應時而生的昭穆制度,完善地解決了周人推崇文王之德、武王之功的政治需要與文化習俗中重視近祖之祭之間的矛盾。
四、昭穆制度與禮樂新變
《禮記·祭統(tǒng)》云:“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于大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5]3484又《中庸》有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5]3534由此可知,“昭穆”是周人祭祀祖先、排列祖先之主時用以區(qū)分父子、辨析親疏的禮儀制度。
昭穆制度的起源與發(fā)展一直是學者們關注和研究的一個焦點問題。在眾多的說法中,王恩田《昭穆解惑——兼答趙光賢教授》一文對《酒誥》“乃穆考文王”中的“穆考”之義進行了細致的辨析,結論如下:“《酒誥》‘乃穆考文王’中的‘穆考’如果不是由于后人的篡改,那么唯一的可能是‘穆考’的‘穆’用作美稱,不是輩分,與昭穆制度無關。”[22]筆者贊同這個說法。但是,贊同“穆考”之“穆”非“昭穆”之“穆”,并不意味著就否定昭穆制度在西周初年的萌芽⑧。綜合史籍的相關記載來看,周人對于自己興起的歷史,實際上是由古公亶父遷居于岐山時開始計算的,所謂“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所以周人對于昭穆關系的辨識,也是以古公亶父為第一代始祖,此后則按照一昭一穆的次序排列: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依次類推,至昭王為“穆”,穆王為“昭”。話到此處,不得不涉及昭王、穆王的名號與“昭穆制度”之“昭穆”之間的關系。唐蘭先生在文章中就以“昭王是昭,穆王是穆”來證明他的觀點:“康王在周王朝的宗廟里面是作為始祖的。”在這個問題上,筆者更贊同王暉《西周金文“京宮”“周廟”“康宮”考辨》的看法:“這二者的來源、用意及制作方式都是不同的,是不應混同起來的。”“西周春秋周王和諸侯稱號很難都用宗廟里的昭穆次序來解釋。而且按照周代宗廟昭穆次序一昭一穆地排列下去,是不能隨意改變的。”[23]正如《祭統(tǒng)》所言,昭穆制度的本質(zhì),在于祭祀時區(qū)別父子遠近親疏的排位問題,因此,在其萌芽之初,當人們以父子一昭一穆、祖孫同昭同穆的方式排列宗廟祭祀時列祖列宗的神主時,未必在當時就產(chǎn)生了“昭穆”之名。更大的可能則是,當西周初年周公制禮作樂時所確立的“祭不過三代”的祭祖禮,經(jīng)過成康之世進入昭穆時代,遇到政治上需要尊崇文、武,但典禮中不祭文、武的現(xiàn)實挑戰(zhàn)時,為了滿足現(xiàn)實的需要,通過優(yōu)化祭祖禮,把周初即已萌芽并在實踐中得以應用的父子一昭一穆、祖孫同昭同穆的方式制度化之后才形成的。《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鄭玄注云:“自始祖之后,父曰昭,子曰穆。”[20]1653“父昭子穆”的說法,很可能就源自于該制度成熟于穆王之世,而昭王為穆王之父的現(xiàn)實。由此而言,作為制度名稱的“昭穆”,出現(xiàn)的時代應該更晚于制度本身,很可能是在穆王身后才得以確立的;而“辨昭穆”的說法本身,就包含了辨別父子倫次秩序的禮儀內(nèi)涵。
《周禮·大宗伯》云:“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鄭玄注云:“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20]1633這里所說的“吉禮”,就是《禮記·祭統(tǒng)》所云“禮有五經(jīng),莫重于祭”[5]3478的祭祀之禮。《周禮·大宗伯》繼續(xù)詳細地羅列了“吉禮”的內(nèi)容:
由此可知,所謂“吉禮”,實際上可劃分為以天神地祇為對象的郊祭與以先王為對象的廟祭兩個部分。在殷人帝祖合一的祭祀文化當中,沒有區(qū)分郊祭與廟祭的需要。西周早期接受殷商文化影響所采取的“以祖配天”的祭祀模式,并不能完全滿足周人帝祖分離之后的文化需要。實際上,在割斷了與“天宗上帝”的血緣聯(lián)系之后,周人選擇通過加強宗族的力量來拱衛(wèi)王室,這就是《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諫周襄王時所說的“封建親戚以蕃屏周”[13]3944。前引祭公謀父對周穆王也說過“維我后嗣旁建宗子……丕及有利宗,丕維文王由之”。作為“禮”之“五經(jīng)”中最重要的祭禮,則是維護宗法制度,凝聚宗族力量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作為宗廟之禮核心內(nèi)容的昭穆制度,就具有了兩個方面的重要意義:一方面,以祭祀之禮為核心,建構起了一個事鬼神有道、君臣有義、父子有倫、貴賤有等的等級嚴密、秩序井然的宗法體系⑨,強化了宗族內(nèi)部的秩序,使宗法制成為維護周王室統(tǒng)治的基礎。另一方面,昭穆制度使周人的祖先之祭從單一的配天而祭中分化出來,帝祖分離的思想觀念最終落實在行為上,通過郊祭之禮與廟祭之禮的分化表現(xiàn)出來。也就是說,祭祖禮上真正的“周制”,是以“祭有昭穆”為核心的宗廟制度的成熟為標志的。考古學家的研究成果實際上早就展示了祭祖禮方面存在的轉(zhuǎn)變:“十七種殷周同名的祭祖禮,大多盛行于穆王以前。”[19]
關于周人的廟制,《禮記·禮器》與《禮記·王制》都記錄有“天子七廟”的說法,但因為只記錄了數(shù)目而未明指,故說者眾多,莫衷一是。王暉《西周金文“京宮”“周廟”“康宮”考辨》在反駁唐蘭“京宮五廟”“康宮五廟”的說法之后提出,“先秦到漢初,一般都說的是‘七廟制’……而古文獻和西周金文資料看,周王室七廟制則是由近親父祖曾三代宗廟,加文武王太祖太宗廟,再加帝嚳、后稷二廟組成”[23]。這個說法能否成立呢?
《孝經(jīng)》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所與配食的只有后稷與文王。而《禮記·祭法》則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5]3444這就是說,按照《祭法》的記錄,帝嚳、后稷、文王、武王四廟,都享受著祭祀“配食”的特殊待遇。這種不同,實質(zhì)上反映出了周公時代祭祖禮與后世的差異:首先就是在《孝經(jīng)》的追述中與人無親、與“天”并立、并以文王配祭的“上帝”,在《祭法》中再次轉(zhuǎn)換為帝嚳,以祖先的身份出現(xiàn)。
從前文的討論可知,對殷人而言,帝嚳既是始祖神也是至上神。在殷周對抗的過程中,周人通過“立德”實現(xiàn)了對“天”的推崇、對“帝”的改造。西周初年與“天”同出的“帝”,逐漸脫去了殷人祖宗神的身份而成為天下共神。但是在《祭法》“禘嚳而郊稷”的敘述框架中,“嚳”無疑擁有周人祖先的身份。《喪服小記》說:“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5]3240如此則帝嚳當為后稷之父。結合《孝經(jīng)》的追述可知,在周公制禮作樂之后,周人對“帝”的改造并未停止。奪取政權的周人經(jīng)歷了一個構建自己族群歷史的過程[24],在這個過程中,之前去血緣化的殷周政治斗爭中被改造為天下共神的“帝”,似乎又一次回到了祖先神的位置上,只不過這一次是作為周人的祖先神。這種改造也給后稷的神異出身找到了落點,與發(fā)生在周穆王時代的對先祖的美化與神化傾向正相吻合。“帝”的身份在殷周時代的不斷變化,充分展示了人類意識中帝祖關系的復雜性。
除了“帝”或者說帝嚳身份的變化之外,《孝經(jīng)》與《祭法》所反映的祭祖禮的差異,還表現(xiàn)在對待文王、武王的態(tài)度上。與《孝經(jīng)》僅尊文王不同,《祭法》明確推尊文王、武王,通過“祖文王而宗武王”,非常有針對性地解決了昭穆時代祭祖禮儀與政治需要之間的矛盾。武王之后,成王與康王除了在《詩經(jīng)·周頌》的相關篇目中顯示出曾經(jīng)被配天而祭的痕跡之外,再無其他的文獻可以證明他們也享有配天而祭的特權。
由此來看,《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反映的正是昭穆時代祭祖禮的變革。在這場變革中,周人確立了帝嚳、后稷、文王、武王配天而祭,再加上一直受到重視的近祖三代之廟,才建立起了所謂的“天子七廟”。反過來說,以“天子七廟”為核心的昭穆制度,實際上是面對推尊文王、武王的政治需要,周人對周初就已存在的配天而祭與近親三代之祭的融會整合。因此,整合之后周天子的祭祖禮,就被自然地區(qū)分成了“以祖配天”的郊祭與以近親三代為主、專祭祖先的廟祭兩大類型。這個分類,實際上觸及到了以宗法制為基礎的周人禮樂精神的根本內(nèi)核,因而也必然對周代禮樂文化的發(fā)展帶來至為深刻而重要的影響。
為了更清晰地分析問題,我們擬依據(jù)《詩序》所載禮樂功能,從“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并結合“天子七廟”享祭者的不同對《周頌》作品進行歸類,列表如下:

天神地祇人鬼特殊典禮祭禮相關后稷文王武王合祭祖先《時邁》《豐年》《昊天有成命》《噫嘻》《桓》《般》《載芟》《良耜》《思文》《清廟》《我將》《執(zhí)競》《天作》《雝》《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維天之命》《維清》《烈文》《臣工》《振鷺》《有瞽》《潛》《載見》《有客》《武》《絲衣》《酌》《賚》
從上表可以看出,《周頌》31 篇作品,除了穆王登基典禮上使用的《閔予小子》四詩之外,與祭禮相關的各詩,大多可廣泛運用于表中所列天神、地祇、人鬼之祭的典禮中:如《維天之命》《維清》與“祀文王”的《清廟》為固定組合;《烈文》《臣工》是對助祭諸侯的訓誡,《振鷺》《有客》則專門為參與助祭的二王之后而歌;《有瞽》適用于所有在宗廟舉行的祭祖儀式,《絲衣》也適用于所有需要在正祭之后酬謝“尸”的典禮活動。
除此之外,通過該表還反映出來一個比較特殊的情況,就是有幾首詩歌的內(nèi)容與《詩序》所記載的儀式用途之間似乎出現(xiàn)了一些“錯位”:從詩歌內(nèi)容來看屬于祭祀成王的《昊天有成命》與《噫嘻》,分別用為“郊祀天地”“春夏祈谷于上帝”;從詩義而言明明是合祭武王、成王、康王的《執(zhí)競》,被當成了“祀武王”的樂歌;而從詩義來看應是祭祀昭王的《載見》,被用于“諸侯始見乎武王廟”的典禮。在儀式樂歌大多針對專門的典禮儀式而創(chuàng)作的西周早期,這些作品的儀式功能出現(xiàn)“錯位”是令人奇怪的。但是,如果把它們放置在周代祭祖禮發(fā)展演變的歷史過程中,尤其是把這種錯位與周穆王時代昭穆制度的定型關聯(lián)起來之后,我們似乎可以找到這些“錯位”發(fā)生的原因:在康王、昭王及穆王初年,周人遵循著“以祖配天”的方式把周成王、周康王以及周昭王都納入了“配天而祭”的行列,于是留下配合相應典禮的歌辭。在周穆王時代祭祖禮的整合與變革中,成王、康王、昭王作為近世三代祭祀的對象,不再具備與文武等列配天享祭的資格。于是,曾經(jīng)在他們被配天而祭的典禮儀式上使用的樂歌被挪作他用,變身成為“郊祀天地”(《昊天有成命》)、“春夏祈谷于上帝”(《噫嘻》)或者“祀武王”(《執(zhí)競》)、“禘太祖”(《雝》)的樂歌。
按照上述思路,在《左傳》的記錄中被歸為《大武》樂歌辭的《武》《賚》《桓》等詩,在《詩序》的解說中表現(xiàn)出不相連屬且游離于《大武》之外的狀態(tài),似乎也可以得到一定的解釋:周公制禮作樂時隆重歌頌文王、武王文功武績,重現(xiàn)開國平天下的歷史,以告功于神明,垂鑒于子孫的《大武樂》,在經(jīng)過昭穆制度的重新規(guī)定之后,其規(guī)模大為縮小,除《武》仍為“奏《大武》也”之外,《賚》與《桓》均被挪作他用,“《賚》,大封于廟也”,“《桓》,講武類祃也”。因此,結合穆王時代祭祖禮發(fā)生整合與變革的歷史,我們可以推測:雖然上述樂歌的創(chuàng)作發(fā)生在穆王之前,但《詩序》所記載的儀式功能,應該是在昭穆制度定型化的過程中,之前用于配祭典禮的儀式樂歌被重新組合,配入相應的典禮之后才確定下來的。
如前所言,昭穆制度下的“天子七廟”,周人的祖廟實際上被區(qū)分為可配天而祭的帝嚳、后稷、文王、武王廟和近世三祖廟兩種類型。《毛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頌”的功能被定位于“告神”。宋人易祓釋《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時說:“神位者,別而言之,則天神獨謂之神;合而言之,則人鬼、地皆神也。”也就是說,在“鬼”“神”“祇”并立的時代,“神”本身即有偏指“天神”的意味。帝嚳的神性無庸置言,配天而祭的后稷、文王與武王,也在周人的推崇中被逐漸神化。因此,“頌”之“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當中,本就包括了指向天神的意味。在經(jīng)歷了西周早期近世祖先均“配天而祭”的過渡之后,隨著昭穆制度的定型,“頌”成為周天子專享的用來祭祀天地以及可與配祭且被神化的后稷、文王與武王的郊祭之樂的專名⑩。成、康等諸王都不再具有配食享祭之資格,曾經(jīng)被用來配祭成王、康王、昭王的《昊天有成命》《執(zhí)競》《雝》等詩被挪作他用,成為郊祭典禮相關儀程的配樂之歌。祭祀對象確定之后,“頌”不再有創(chuàng)制新樂的需要,“頌”樂的規(guī)模與形態(tài)趨于定型。班固在《兩都賦序》中說“昔成康沒而頌聲寢”,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而言,這一句話非常準確地概括了周代“頌”樂的創(chuàng)制歷史。
余論
一旦把《周頌》的禮樂性質(zhì)定位為郊祀天地以及與天、帝配食的有德有功之祖的樂歌,這個看法必然會影響到對“雅”的理解與定位。所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頌”的對象是“神明”,即“頌”歌是獻給天宗上帝、以及神性先祖后稷、文王和武王的,也就是說,“頌”的主要功能在于娛神。如此,“雅”的功能當主要在于“立政”,所謂“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考察《雅》詩的發(fā)展歷史,“言王政之所由興廢”的“立政”功能,實際上是通過一系列具體作品的先后制作一步步實現(xiàn)的。就周人文化建設階段而言,伴隨著周人的逐漸壯大,周人記錄本族歷史的《綿》詩出現(xiàn);至武王克商、周公制禮之時,歌頌“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的《大明》,與在祭祀文王的典禮上訓誡“商之孫子”的《文王》先后產(chǎn)生。《大明》和《文王》這兩首詩,分別代表了《雅》詩在構建“言王道之所由興廢”的政教系統(tǒng)時,所設定的頌贊與陳誡這兩個向度。之后至穆王時代,雅頌之樂的儀式功能得到清晰區(qū)分之后,雅樂文化的發(fā)展獲得巨大推力。以社會經(jīng)濟的大發(fā)展為背景,大量的“雅”歌被制作出來,“尊祖”之《生民》,“美周”之《皇矣》,“繼文”之《下武》,“繼伐”之《文王有聲》、“大平”之《既醉》、“守成”之《鳧鹥》,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這些作品,一方面建構起了周人得天命佑助而興起、而壯大的光輝歷史,全面展現(xiàn)了周人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通過禮樂配合的進退有度、周旋有節(jié),“雅”樂成為通行于貴族社會的最主流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力量,成為維系以宗法等級制為基礎的政治統(tǒng)治秩序的重要力量。
穆王之后,周王朝由極盛轉(zhuǎn)衰,“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25]3744。于是,在《文王》一詩所確立的陳誡的向度上,諷刺詩的大發(fā)展進一步完善了“雅”詩“言王道之所由興廢”的政治功能。此后一系列的《雅》詩作品,都未能超出“言王朝之所由興廢”的范圍,即使西周后期產(chǎn)生的個體抒情特征非常明確的《小雅》作品,也被認為是“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之所作。由此而言,從西周初年開始,“雅”詩通過《大明》與《文王》所展示出來的歌頌與訓誡的功能,就從正反兩個方向上奠定了周人建構和維護王道統(tǒng)治思想的基礎。因此,在“頌”作為天子專享的郊祭天宗上帝與配食祭享的睿圣先王的音樂而存在時,雅樂以及配樂而歌的《雅》歌,就成為支撐起周代宗法制社會禮樂文明的真正的核心力量。以“雅”樂為中心,通過宗廟祭祀、慶賞封賜、饗宴賓客、朝覲會同等一系列禮樂活動,周人最終建構起了一個等級嚴明、體系完整、政教特征突出的禮樂文明,以其“郁郁乎文哉”的文化影響力,對后世文化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注釋
①此處所引《詩序》及《詩經(jīng)》原文均出自《毛詩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2009年影印本。②《兩周詩史》中把《載芟》與《良耜》的創(chuàng)作時代系于周宣王時。隨著研究的深入,筆者對這兩首詩歌的相關問題有了新的認識,故移之于穆王時代。具體的討論筆者擬另外撰文,此不涉及。③引文中部分文字及標點根據(jù)校注修改。④該文分上下兩篇,分別發(fā)表在《歷史研究》1959年第9 期和第10 期。⑤相關討論參見馬銀琴《論殷商民族的鴟鸮崇拜及其歷史演化》,出自《天問》,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馬銀琴《〈詩經(jīng)〉史詩與周民族的歷史建構》,《學術論壇》2017年第1 期。⑥部分文字參考李學勤《小盂鼎與西周制度》(《歷史研究》1987年第5 期)一文的隸定做了改動。⑦另外,丁進《小盂鼎反映西周大獻典禮》(《學術月刊》2014年第10期)把這次典禮概括為“獻俘”“禘祖”“大饗”三個階段。⑧唐蘭《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唐蘭先生金文論集》,紫金城出版社1995年版)一文討論昭穆制度在周初已經(jīng)應用的問題時,對相關資料做過細致的梳理。本文不再一一羅列。⑨此即《禮記·祭統(tǒng)》所謂“祭有十倫”:“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詳見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清嘉慶刊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482 頁。⑩《禮記·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勛勞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升歌《清廟》,下管象……”(參見《禮記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225-3226 頁)這一段話,解釋了魯國何以有“頌”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