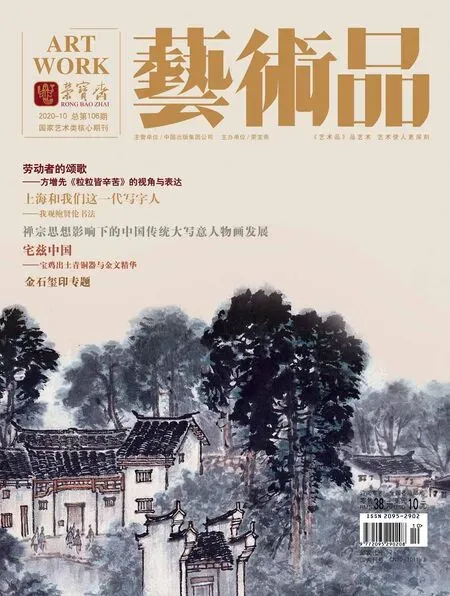緩慢的樹
——關于張樹的書法與篆刻
文/陳亦剛

張 樹
1960年生于吉林省吉林市、九三學社社員、榮寶齋書法院篆刻導師,現居北京。

以寫我心

山河無恙
名正而言順。有的時候,一個人的名字甚至成為一種隱喻。
讀張樹的書印,會漸漸在作品里,感覺到一種大樹一般的、緩慢的生長。這種生長,不急不躁,又與內心的氣息彼此呼應。幾乎可以肯定,這其中內在螺旋上升的力量,與日月星塵的旋轉,密切相關。
在文字與藝術之初,墨痕與朱跡,是作為薩滿的藝術家在通靈的過程中,所留下的證據。因而,我們習慣視為神話敘述的,在創字之初,那使得天雨粟、鬼夜哭的神秘而巨大的力量,難道其實不是一個極為準確的、關于文字藝術的寓言嗎?
這種與生生不息的自然的連接,讓作品聯通了造物之奧秘,點畫的一呼一吸,具備著萬象的儀態萬千。因此,以自然諸般意象為喻,描述品評書作,順理成章成為古典書論中最為經典的描述方式。
神龍、鳳鳥、巨石、流云、山岳……成為支撐作品的隱秘后盾。
然而,這里面存在著嚴密的生成要求,不妨援引張璪論畫的妙語來說明——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通過感通內外,然后形諸筆端,方能化現自然妙韻。如果忽視這一點,而僅僅將書法篆刻視為純粹的視覺藝術,就會割裂自然、自我以及作品間美妙而關乎生死的聯系。

常清靜

和光同塵

閑中至樂

肝腸若雪
對這種聯系的忽視,無論對于創作者,甚至包括欣賞者,都將導致誤入歧途的危險。
阿甘本感覺到了這種危機,在《最詭異之物》一文里,他憂心忡忡地指出,對于欣賞者而言,如果僅僅沉迷于作品的表象,是無法看到藝術品真正的強大力量,要真正地貼近作品,必須從慣常的審美模式里跳脫出來:
對于藝術的觀察,僅僅抱著對于視覺的玩味之心,缺乏設身處地的深入,則對于作品的深意無法真正悟入。
虞世南則從創作者的角度,提出了對片面執著于視覺表現的警醒:
然則字雖有質,跡本無為,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達性通變,其常不主。故知書道玄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機巧必須心悟,不可以目取也。

佛造像

佛造像

不聞不見
這里面的提醒,對許許多多的、片面沉迷于視覺花樣的當代書人印人而言,實在是遠隔千年的警告。
局限于視覺的玩味,終究是輕的,它無法承載天道、自然以及人心之重——或者可以更極端地說,許多從藝者所理解的視覺修養,其實只是為蒼白內容粉飾裝扮的花樣。當我們面對悲愁痛苦、生死離別,單純視覺的花樣根本無所助益,然而,對于藝術家而言,藝術“關乎作者的生死存亡,或至少關系到他的精神健康”,本該是一個“幸福的承諾”——在這一點上,東西方的古典藝術有著奇異的一致性。
當我們獲得以上認識,再返歸到張樹的篆刻與書法,方有可能真正體會到作者的用心與用力所在。在長期的書法與篆刻實踐中,張樹耐心地傾聽著內在的波瀾,在平靜生活的表象之下,用盡生命之力,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寧靜而激烈地生長,而這種努力的指向,也同時由里及表,化生出外在風格面貌。無論是形式的選擇,以及風格的變化力度,亦牢牢地聯系著內心經驗的變遷。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張樹是一個真正的古典主義者。他明了與承接古典藝術的核心精神之所在,平靜地工作與努力,而道蘊含于其中——在安寧的作品之湖深處,一直涌動著生死拼搏的暗流。張樹的篆刻和書寫,綿里藏針,以太極拳般的節奏,平和了浮華世界的大紅大綠,直接契入傳統深山的幽密之處,并從中獲得永恒生長的力量。同時,這種與浮世風氣相抵抗的堅持,使得張樹的作品安靜獨立,呼應著古典的道統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