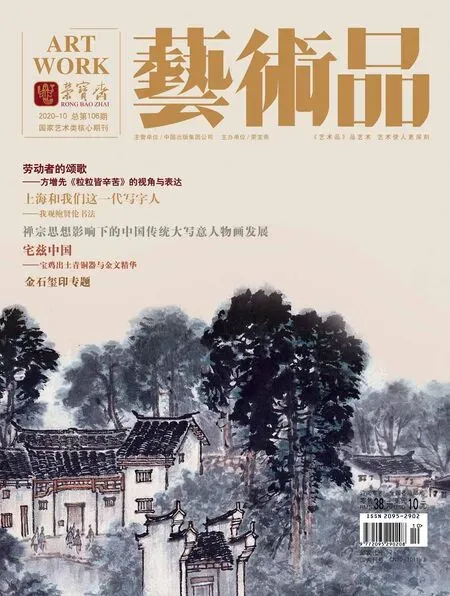故宮博物院藏歷代名家篆刻概述
文/方 斌

陳鴻壽 馮氏孟舉
印章的收藏與研究行為,大約從北宋始,歷代沿承不輟。由實物的搜集開始,繼而對其所包含的文字、文獻、制度、鑄造、書法、篆刻、流派、雕刻工藝等內(nèi)容進行研究,尤以三百年來為盛。近現(xiàn)代以來,將印章進行先秦古璽、兩漢、魏晉印章、隋唐宋元、明清乃至近現(xiàn)代篆刻,在時期與內(nèi)容方面進行的劃分與歸類,已經(jīng)得到印學(xué)界的基本共識。如果說印章的收藏與研究,作為銘刻類重要組成內(nèi)容,傳統(tǒng)上屬于金石學(xué)范疇,那么以先秦古璽、兩漢魏晉印章,乃至隋唐以降官印等主體內(nèi)容作為對象,似乎有著更多的關(guān)聯(lián)內(nèi)容和體現(xiàn)。盡管先秦、兩漢魏晉以前的印章材質(zhì)上已有玉質(zhì)、石質(zhì)、骨質(zhì)、琉璃等等,印面內(nèi)容已經(jīng)具備儆語、圖案,制印方法采用了鑄文、鑿文,乃至于印臺邊側(cè)圖案刻紋。相對于前者而言,元明清以來的印章篆刻,雖然仍屬于銘刻印章序列,并且與前者有著明晰的繼承發(fā)展脈絡(luò),但更多的是以明確的創(chuàng)作思想與主觀藝術(shù)行為的表達,成就了一個專屬的藝術(shù)門類。
明確體現(xiàn)主觀篆刻治印之風(fēng),最晚應(yīng)該出現(xiàn)在元代,明代已經(jīng)蔚然成風(fēng),乾嘉時期金石學(xué)復(fù)興,印章收藏、研究與創(chuàng)作并盛,篆刻遂為大興。
宋元時期,出現(xiàn)了形式、內(nèi)容與前代截然不同的一種主體私印,后人稱之為押,印鈕多變,印廓形態(tài)不拘,印面內(nèi)容繁多,尤其以各類圖案、文字或組合不可計數(shù)。以各種書體入印殆始于此時。各式“押”一度盛行,雖以面目一新而出現(xiàn),但鑄造粗劣,表現(xiàn)出的印文書體遠離規(guī)范。宋元時期是我國書法繪畫藝術(shù)之大成時期,受書法繪畫創(chuàng)作與收藏的影響,用于此類藝術(shù)品賞鑒與收藏為內(nèi)容的鈐蓋印章,成為文人與書畫家極為重視的內(nèi)容,“押”作為在當(dāng)時社會生活交往中的憑信證物,在當(dāng)時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和審美層面,接受程度還是十分有限的。而稍早一些的兩宋金石學(xué)的興起,使古代印章的搜集與欣賞成為一種主動行為,早期著錄出現(xiàn),對古印形制、印文等多方面的審視和推崇,已表現(xiàn)出思考創(chuàng)作的萌動。印章篆刻的創(chuàng)作,需要得到自主表現(xiàn),在書法繪畫與金石審美這兩方面,具備了藝術(shù)層面的成熟條件,書法繪畫、文人領(lǐng)域的治印之風(fēng),遂得開啟。
以大量石材治印出現(xiàn)在明代末期,兼以象牙、竹根、香木等紋理色澤美觀而易施刻的多種印材,易于人們創(chuàng)作發(fā)揮和欣賞接受,印石的應(yīng)用,也是石章篆刻發(fā)展的一個契機,而篆刻創(chuàng)作的勃發(fā)也始于此。明代后期篆刻創(chuàng)作的代表人物有文彭、何震、蘇宣、歸昌世、汪關(guān)、朱簡、程邃等。諸家繼起,印人輩出,遂有門派。盡管他們的篆刻技法與表現(xiàn)不盡相同,但在創(chuàng)作思想方面基本是一致的,就是宗秦漢印風(fēng),推崇秦漢印章規(guī)整的文字精神與布局風(fēng)貌。相對秦漢印章的整體風(fēng)格來看,明末印章篆刻雖有規(guī)整的風(fēng)格特點,但仍未表現(xiàn)出秦漢印章的風(fēng)貌精髓,不如清代中期金石學(xué)復(fù)興時期及以后對印章篆刻更全面的認(rèn)識和理解。明末及清初的篆刻家對后世篆刻藝術(shù)的影響,最主要在于真正開啟了篆刻創(chuàng)作之風(fēng),并為其發(fā)展起了重要的倡導(dǎo)與推動作用。
清代中期是篆刻藝術(shù)得到極大發(fā)展的時期。金石學(xué)家輩出,深究鼎彝,窮盡碑刻,精研篆隸魏碑,引入治印,篆刻理論與成就巨大,名家相繼而起,逐漸形成了中國印章篆刻創(chuàng)作的兩大流派——浙派和皖派。浙派以丁敬為首,蔣仁、奚岡、黃易繼之,后有陳豫鍾、陳鴻壽、趙之琛、錢松為代表人物,號稱“西泠八家”;皖派以歙縣巴慰祖、胡唐、王振聲、董洵諸家為代表,作品風(fēng)貌古樸蒼勁。浙派和皖派在金石學(xué)的復(fù)興背景下,將印學(xué)的研究融入金石學(xué)范疇。篆刻思想多方面的認(rèn)識、技法的總結(jié)與創(chuàng)新,造就出一個繁榮的篆刻時代,也最終確立了石章篆刻作為一種特有藝術(shù)而存在。而自清中期以降,印人如林。及至晚清以遞民國,名家繼起,如趙之謙、吳昌碩、黃士陵、陳衡恪、徐石雪、王褆、齊白石、丁世嶧皆馳譽印壇,多有篆刻能自成一家之法者。近代西泠印社的成立,不但使篆刻創(chuàng)作在思想和技法方面得到交流與弘揚,更將印學(xué)總結(jié)提高到更全面的理論高度。

丁敬 家有詩書之聲

陳鴻壽 松垞白事

趙之謙 鄭盦

趙之琛 甄胄書生

趙之謙 鄭盦

趙之琛 鄉(xiāng)里高門

趙之琛 蓉舫

奚岡 張尗未

趙之琛 張慶榮印

趙之琛 書中不盡心中事

趙之琛 惟適安居

趙之琛 求真

趙之琛 讀書觀大意

趙之琛 金石千秋
故宮博物院成立90年以來,印章類文物除清宮璽冊之外,入藏數(shù)量已逾兩萬余件,成為今日收藏印章文物最多的博物館。自20世紀(jì)20年代故宮博物院成立,其后文物整理與入藏規(guī)劃的范圍,一度以紫禁城皇家珍藏歷代文物或明清宮廷舊有之物作為收藏內(nèi)容與范圍的底界,至20世紀(jì)50年代之前收入者,也非原清宮流散于外者不收。自20世紀(jì)50年代開始,始大力充實各時代各門類的文物收藏。印章類文物的入藏時段,也同上述情況一致。20世紀(jì)50年代以前故宮收藏的印章文物,內(nèi)容方面除璽冊類別之外,以賞鑒為目而收藏者大體分為兩個部分:一是魏晉以前古璽印部分,以乾隆十六年(1751)輯成《金薤留珍》為主要內(nèi)容體現(xiàn)(現(xiàn)藏臺北“故宮博物院”)。二是歷代玉印和石章篆刻作品。其中歷代玉印部分在乾隆朝由諸臣奉敕檢鑒,恭跋分列,輯成《綠字凝輝》《文府云章》《晁采流輝》《浮筠煥采》《鑒古席珍》《珍羅芝檢》等數(shù)匣冊,參與者有蔣溥、梁詩正、汪由敦、嵇璜、董邦達、裘日修、觀保、錢維誠、于敏忠、王際華、張若澄、王杰、董浩、彭元瑞、吳省蘭、阮元、瑚圖禮、那彥成、金德瑛、錢汝誠等甚眾。從今日文物鑒定內(nèi)容來看,這些玉印的時代內(nèi)容較為復(fù)雜,既含少數(shù)先秦兩漢古玉印,也包括了大量明代以來琢制作品。清宮中所收藏的篆刻石章,則基本上是乾嘉時期托名文彭、何震諸名家的摹刻,印文取用《蘭亭序》《圣教序》《醉翁亭記》內(nèi)容等,形式上聯(lián)句成文為成套印章或為石刻筆架山形。與上述玉印一樣作為陳設(shè)與賞鑒,曾分別置于紫禁城內(nèi)的永壽宮、景仁宮、鐘粹宮、養(yǎng)心殿、懋勤殿、太極殿及頤和軒等處。摹印行為早期出現(xiàn)于明代,萬歷十七年(1589)《考古正文印藪》譜成,是為目前所見篆刻家摹古印成譜之始,參與者有吳丘隅、董文凌、何震、吳嶺南等人,萬歷三十五年(1607)陸鑨輯有姚書儀摹刻古印成《片玉堂集古印章》。蘇宣楊當(dāng)時亦有摹刻古印而成的《集古印范》傳,以上等等均屬于印人為汲取與體驗的篆刻行為。至如同一時期前后以秦漢魏晉原印為范而成木刻本印譜如《印藪》等,印面體現(xiàn)則為刻版技術(shù),與摹刻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語了。此時前后,印人輯自刻印成譜也成為普遍的行為。萬歷二十八年(1600)何震以自刻印成《何雪漁印選》殆為印人匯輯自刻印成譜之始,其后蘇宣的《蘇氏印冊》(后又成《蘇氏印略》),吳迥的《曉采居印印》,曹一鯤、何濤、方逢吉、朱簡、汪關(guān)等印人紛紛輯自刻印而有成。繼而出現(xiàn)他人集輯諸家印人印作,據(jù)篆刻年表統(tǒng)計,明末到清康熙朝以前的篆刻家們所輯有的自刻印譜有100種左右,而清朝中期泛輯成譜已經(jīng)達數(shù)百余種。篆刻大興,固然是以創(chuàng)作為主流的藝術(shù)盛舉,然終致不免出現(xiàn)托名偽刻之濫觴。上述清宮所列存的篆刻石章,就屬于此,作品了無生趣。而以和珅諸臣進呈祝壽的《元音壽牒》《寶典福書》套印,則務(wù)求辭藻華麗與印文工整秀麗而已。

高鳳翰 神彩煥發(fā)

桂馥 臣心如水
20世紀(jì)50年代以后,故宮博物院入藏的印章類文物,極大地改變了這一文物門類的收藏前狀。其入藏來源有三個方面,一是文物局撥交,二是有計劃地從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區(qū)的文物商店和市場收購,三是衷心熱愛此類文物的諸藏家、學(xué)者與熱心人士的捐獻。自戰(zhàn)國、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以遞于宋元,品類之眾、內(nèi)容之富、系統(tǒng)之詳,在系統(tǒng)性和完整性方面,成今日舉世之淵藪。明清及近現(xiàn)代的篆刻印章,亦萃然而聚。故宮博物院所藏的篆刻類印章,就是以這一時期的入藏為主要內(nèi)容和范圍的。

丁敬 杉屋
九思堂藏印是收藏最為完整而集中的一批篆刻作品,計有155件,未有所失。永瑢是乾隆帝第六子,封質(zhì)莊親王,號九思主人,其本人在書法繪畫領(lǐng)域具有造詣。九思堂藏印內(nèi)容包括了永瑢的名號印、書畫印、收藏印和數(shù)量較多的閑文欣賞治印,印材大多取用名貴的青田凍石,印體本身無雕飾。諸多印材所留印款表明,應(yīng)該是取材舊有印章,磨去原有印面,取其名貴石材而為篆刻之用。內(nèi)中篆刻名家朱文震刻款是準(zhǔn)確可信的。這套以永瑢為印主人的九思堂藏印,其創(chuàng)作時段較短,應(yīng)是在一定時期之內(nèi)相繼而完成的作品,篆刻風(fēng)格與技法的體現(xiàn)如出一家之法,留下了一批內(nèi)容完整的清中期篆刻的珍貴例證。
以陳介祺為印主人的自用印,是又一批內(nèi)容完整而豐富的篆刻作品,體現(xiàn)了兩個方面的重要內(nèi)容。一方面是篆刻作者準(zhǔn)確,篆刻人物眾多,諸家作品集中,楊澥、朱方、翁大年、王石經(jīng)等諸家篆刻于此多有體現(xiàn),并顯示出一時的以藝術(shù)鑒賞為關(guān)聯(lián)的人文交往和關(guān)系。陳介祺自用印之中,有一部分是未具作者名款,從風(fēng)格與技法表現(xiàn)來看,似乎亦多不出以上諸家手創(chuàng)范圍之外。另一方面,保存了直接與間接體現(xiàn)陳介祺金石收藏和研究的最為主要和可信的旁類例證。陳介祺收藏金石文物品類之富,數(shù)量之多,一時冠絕海內(nèi),其自用印于收藏內(nèi)容和鈐蓋功用方面,進行分門別類的刻治和使用,表現(xiàn)出突出的相應(yīng)內(nèi)容。由56歲時藏有十鐘而自稱“十鐘主人”,由藏數(shù)百枚戰(zhàn)國、兩漢時期錢幣陶范自屬“千貨范室”。由藏古陶器、陶片、漢代畫像石而自稱“古陶主人”“三代古陶軒”“君車漢石亭長”,由藏多種越王劍、戈戟矛及漢代弩機古兵器,治印“簠齋古兵”。陳介祺在收藏有銘文青銅器多種之外,曾與友人賞析各家之藏,大力推行留存金石銘文拓片并借拓多種銘文,故有“簠齋吉金文字”“簠齋先秦文字”“簠齋兩京文字”“簠齋西漢器圖”等印。古璽印收藏尤其以萬印樓藏印最為著名,又有“簠齋藏三代鈢”。
吳熙載精書法,擅長篆隸,尤其重視將書法引入治印,其篆刻作品往往體現(xiàn)出渾厚書法筆意,篆刻成就顯著,為皖派中重要代表,他的篆刻作品在故宮的收藏主要體現(xiàn)在為岑镕、姚正鏞治印。
吳昌碩治印初取皖浙各派,上溯秦漢印風(fēng),后不蹈常規(guī),風(fēng)格樸茂蒼勁,篆刻藝術(shù)成就頗高。故宮圖書館藏有一件題簽“吳缶翁刻印拓存”的手卷,內(nèi)中印譜都是原印鈐蓋排列裝裱成卷,共四個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吳昌碩為蒯壽樞篆刻的名印,后有蒯氏題跋,是吳昌碩晚年創(chuàng)作時間集中而內(nèi)容完整的名章,這批作品與其他為數(shù)眾多的吳氏篆刻之作,合而成為故宮收藏序列中吳昌碩篆刻作品的重要內(nèi)容。

馬衡篆刻作品與自用印,是又一批內(nèi)容豐富而完整的篆刻類藏品。馬衡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對秦石鼓、漢魏石經(jīng)及古代度量衡等方面的研究有貢獻。著有《漢石經(jīng)集存》《凡將齋金石論叢》等。1928年輯自刻印成《凡將齋印存》。他的藏品在1957年和1958年分兩次由捐獻而入藏故宮。內(nèi)中其自治印有65方,另有吳昌碩、鐘以敬、吳隱、王禔、唐源鄴、方巖等諸名家為他篆刻的印章,包括了他的姓名、別號、室名、收藏印,涉及古器物、藏石、甲骨、審定金石文字及珍藏品、手校書稿、閑文欣賞等各種內(nèi)容的篆刻作品。馬衡篆刻采用了鐘鼎、詔版、漢印、碑刻諸體文字入印,多白文少朱文,推崇漢印風(fēng)格,尚美趙撝叔、吳昌碩篆刻。
齊白石的篆刻作品入藏故宮博物院,是在1962年通過收購?fù)緩蕉傻摹S嬘?20件,此前大多未見舊著或發(fā)表。這批篆刻作品內(nèi)容十分豐富,有名印、室名別號印、閑文印等,涉及自用印20余方,為他人治印涉及20余人,閑文印多是作為自己欣賞的雙面印,有許多晚年作品,風(fēng)格愈發(fā)蒼勁有力。
徐宗浩的篆刻作品和自用印在故宮篆刻藏品中也是較多的一項,包括名印、收藏印、鑒審印等多種內(nèi)容。其自刻印存印16方,自用印另有有金德樞、王禔、王光烈、壽璽、高源諸人之作。
王禔工治印,尤善朱文印,風(fēng)格流暢挺拔,得浙派精神,為西泠印社創(chuàng)始人之一,存印25方,基本是徐家浩的名印、書畫印與鑒藏印。
除以上簡述所涉相對集中的治印與用印內(nèi)容之外,故宮博物院藏有的篆刻作品涉及印人更有陳炳、高鳳翰、丁敬、桂馥、董洵、奚岡、阮元、吳文征、陳鴻壽、張廷濟、趙之琛、王應(yīng)綬、孫三錫、釋達受、曹世模、吳咨、俞樾、胡震、何昆玉、趙之謙、濮森、姚寶侃、胡镢、黃士陵、徐新周、王大炘、趙時棡、童大年、袁勵準(zhǔn)、陳衡恪、陳年、金城、趙石、丁世嶧、樓村、于照、張志魚等數(shù)十家,而篆刻藏品之豐富,更非列述以能詳。
印章篆刻的創(chuàng)作,在以印面、印款內(nèi)容為主體表現(xiàn)的同時,包括印材、制鈕、薄意等方面也是篆刻藝術(shù)的多彩輔助。故宮博物院所藏篆刻作品,印材紛呈,名貴田黃印材數(shù)以百計,各類凍石浸目潤心。楊玉璇與周彬的治鈕,兼以博古、螭文,俱妙,工藝特佳,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名家治石作品。以薄意表現(xiàn)花草翎毛、山林野趣的印材雕刻,不時體現(xiàn)在各時段篆刻作品之中。

王石經(jīng) 海濱病史

吳讓之 仲海書畫

吳讓之 長宜子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