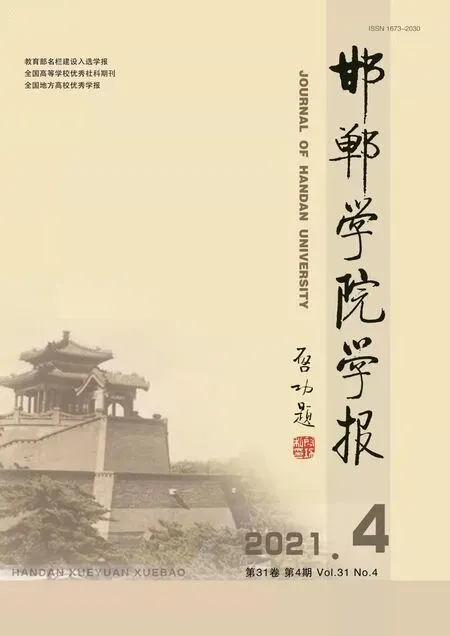荀子人性論的創造
——以“情性—知性”二元結構為線索
2021-01-15 00:16:37馮碩
邯鄲學院學報
2021年4期
馮 碩
(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院,北京 100872)
梁濤先生認為《荀子·富國》篇(以下行文中《荀子》引文,只具篇名)提出了以“欲”“求”所代表的情性,和以“可”“知”所代表的知性[1]。“情性-知性”結構貫徹荀子各篇,只不過在提出“偽”概念以后,“情性-知性”結構過渡到了“性-偽”結構。通過分析“情性-知性”結構,我們認為在知性對治情性這一理路背后,還潛藏著情性和知性相互合作、配合而化性成善的理路,荀子其實對情、欲均持有正負性兩種評價。最后我們集中分析了《正名》篇荀子對性、偽二義的界定,認為荀子的人性論由于知性具有后天完成性、集天性與人成于一身的特殊屬性,沒有安置在“性”中,而是被安置在“偽”中,由此引起了“偽”的提出和性偽之分、合的理論結構。在人性論的現代語境中,我們應該有意識地把“偽”中的知性部分還原到荀子的人性體系中來,以補全荀子的人性論。確切地說荀子人性論是一種性偽論,人性的先天所予性和后天完成性是統一的,這反映出荀子天生人成的理論面向。
一、從“情性-知性”結構到“性-偽”結構
梁濤認為《富國》《榮辱》是荀子早期的作品,在《富國》篇中,知性-情性說已經被提出,并都被看作是性。知性可以指先天的認知能力(能知),也可以指認知的后天運用(所知),前者屬于性,而后者則不屬于性。在《富國》篇中,荀子沒有區分能知和所知,直到后來的《正名》篇提出“偽”概念后,才把前者稱為性,而后者稱為偽。然而,在《正名》和《性惡》篇,性往往指的是以情、欲為內容的情性,作為“能知”的知性和以情、欲為內容的、動物性的性似乎很難兼容。……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黨課參考(2021年20期)2021-11-04 09:39:46
雜文月刊(2021年11期)2021-01-07 02:48:01
攝影與攝像(2020年12期)2020-09-10 07:22:44
文苑(2019年24期)2020-01-06 12:06:58
小哥白尼(軍事科學)(2019年6期)2019-03-14 05:49:56
黨課參考(2018年20期)2018-11-09 08:52:36
中國蜂業(2018年6期)2018-08-01 08:51:14
影視與戲劇評論(2016年0期)2016-11-23 05:26:47
工業設計(2016年10期)2016-04-16 02:44:06
都市麗人(2015年4期)2015-03-20 13:3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