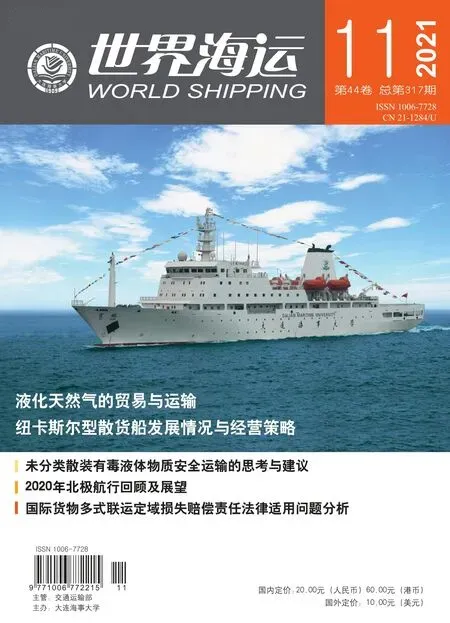國際貨物多式聯運定域損失賠償責任法律適用問題分析
劉 丹
一、引言
近幾年,我國不斷加速推進多式聯運產業的發展。交通運輸部于2016年12月28日發布了《交通運輸部等十八個部門關于進一步鼓勵開展多式聯運工作的通知》(交運發〔2016〕232號)。該通知強調多式聯運是依托兩種及以上運輸方式有效銜接,提供全程一體化組織的貨物運輸服務;并要求積極開展綜合交通運輸促進法、多式聯運法等立法研究論證,強化不同運輸方式間法規制度的相互銜接與協調。2019年5月14日,交通運輸部又發布了《交通運輸部水運局關于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提案第0259號的會辦意見》,再次明確將發展多式聯運作為推進各種運輸方式創新融合發展的重要抓手。多式聯運產業的加速發展必然會要求與之配套的法律和機制不斷健全和完善。我國目前關于國際多式聯運合同的定域損失法律適用缺乏具體和明確的規定,造成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混亂,多式聯運經營人無法對其承擔的責任進行合理預期,必然會對行業發展造成一定阻礙。本文所關注的定域損失是指貨物的毀損、滅失可以確定發生在國際多式聯運某一運輸區段的情況,旨在分析國際貨物多式聯運定域損失情況下法律適用規定存在的問題和爭議,結合我國自身的特點并借鑒國外成熟的法律制度,提出對相關規定的修改思路和完善建議。
二、在定域損失情況下的國際多式聯運經營人的賠償責任法律適用制度介紹
(一)我國法律的相關規定
為了平衡貨方、多式聯運經營人和區段承運人各方的利益,國際上對多式聯運經營人的責任采取了不同的制度。多式聯運經營人的責任形式主要有責任分擔制和單一責任制兩種。單一責任制又有網狀責任制和統一責任制。[1]我國《海商法》和《民法典》均采用的是經修正的網狀責任制,明確多式聯運經營人應對全程運輸承擔責任。對于定域損失,多式聯運經營人的賠償責任和責任限額適用調整該區段運輸方式的有關法律規定;對于非定域損失,則分別適用《海商法》和《民法典》中特定章節的規定承擔賠償責任。
我國《海商法》第四章(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第八節中專門設立了“多式聯運合同的特別規定”內容,共有五個條文(102~106條),其中對于定域損失,第105條規定:“貨物的滅失或者損壞發生于多式聯運的某一運輸區段的,多式聯運經營人的賠償責任和責任限額,適用調整該區段運輸方式的有關法律規定。”
《合同法》第十七章(運輸合同)專門設立了第四節“多式聯運合同”,也有五個條文(317~321條)。《民法典》第三編(合同) 第二分編(典型合同)第十九章(運輸合同)中第四節“多式聯運合同”基本沿用了《合同法》關于多式聯運合同的上述五個條文的規定(838~842條),其中第842條規定:“貨物的毀損、滅失發生于多式聯運的某一運輸區段的,多式聯運經營人的賠償責任和責任限額,適用調整該區段運輸方式的有關法律規定;貨物毀損、滅失發生的運輸區段不能確定的,依照本章規定承擔賠償責任。”
(二)國際公約和國際規則中的相關規定
國際社會一直在努力積極地推進國際多式聯運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統一。《聯合國國際貨物多式聯運公約》(簡稱《多式聯運公約》)于1980年5月24日通過,但迄今并未生效。《多式聯運公約》第19條規定:“如果貨物的滅失或損壞發生于多式聯運的某一特定區段,而對這一區段適用的一項國際公約或強制性國家法律規定的賠償限額高于適用第18條第1款至第3款所得出的賠償限額,則多式聯運經營人對這種滅失或損壞的賠償限額,應按該公約或強制性國家法律予以確定。”
《UNCTAD/ICC多式聯運單證規則》(國際商會出版物第48l號,“多式聯運單證規則”)由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及國際商會(ICC)聯合工作小組起草,由國際商會通過并發布,于1992年1月1日起生效。該規則取代了國際商會于1975年制定的《ICC聯運單證統一規則》(ICC出版物第298號)①The Uniform Rules for a Combined Transport Document,首次由ICC在1973年發布于第273號文件上。。《多式聯運單證規則》僅為示范規則,不具有強制性。第6.4條規定:“如果貨物的滅失或損壞發生在多式聯運中的某一特定區段,而適用于該區段的國際公約或強制性的國家法律規定了另一項責任限額,如同對這一特定區段訂有單獨的運輸合同一樣,則多式聯運經營人對此種滅失或損壞的賠償責任限制應當按照此種公約或強制性國家法律的規定計算。”
2008年12月11日通過的《鹿特丹規則》②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2008年12月11日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上正式得到通過,大會還決定于2009年9月23日在荷蘭鹿特丹舉行簽字儀式,開放供成員國簽署,因而該公約又被命名為《鹿特丹規則》。雖然創新了對多式聯運領域的規定,但該公約也沒有生效。《鹿特丹規則》第26條規定,發生在貨物裝上船舶之前或卸離船舶之后發生的貨物滅失、損壞,優先適用于其他國際公約。
國際立法層面至今仍沒有統一的多式聯運立法,對于定域損失,《多式聯運公約》和《多式聯運單證規則》均規定適用發生損失區段的國際公約或強制性國家法律規定。但《多式聯運公約》適用發生區段的國際公約或強制性國家法律規定還有一個前提,就是適用該規定計算的責任限額需要高于根據《多式聯運公約》計算的責任限額,否則仍將適用《多式聯運公約》的責任限額。《多式聯運公約》中將“強制性國家法律”定義為有關貨物運輸的成文法,該法律規定不得通過合同條款加以背離以損害托運人的利益。《多式聯運公約》和《多式聯運單證規則》都將具體的法律適用留給每個成員國通過自身成文法加以規范。而我國法律在參考不同的公約或規則的規定時,將“強制性國家法律”轉化為“調整該區段運輸方式的有關法律規定”。
三、提出問題——在定域損失情況下國際多式聯運經營人賠償責任法律適用的困境
我國《海商法》第105條和《民法典》第842條僅簡單規定了“調整該區段運輸方式的有關法律規定”,在定域損失發生在國外某個運輸區段的情況下,對于如何識別和確定“有關法律規定”沒有明確界定,給司法實踐中的法律適用帶來了困擾。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四庭于2008年12月發布的《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實務問題解答》(簡稱《問題解答》)第127條對國際多式聯運合同糾紛應如何適用法律的解答為:依照《海商法》的規定,國際多式聯運的貨物發生滅失或者損害的,多式聯運經營人的賠償責任和責任限額,適用調整該區段運輸方式的有關國家或者地區的法律。該有關法律無法查明或者沒有規定的,適用我國參加的國際公約和我國的相關法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理解,《問題解答》中的“有關國家或地區的法律”似乎并不是指我國法律,而是指外國法律。但該《問題解答》并沒有明確如何識別和認定“有關國家或地區的法律”。
(一)學理上的爭議
根據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理解,有學者認為在定域損失發生在國外時,《海商法》第105條和《民法典》第842條看似具有沖突規范的功能,即將多式聯運經營人的賠償責任和責任限額的法律適用指向了適用調整該運輸區段的外國法律。該觀點值得商榷。首先,在定域損失發生在我國境內的情況下,顯然只能適用我國調整相關區段的法律。在這種情況下,該條款并不具備沖突條款的功能。其次,從構成要件來看,該條款并不滿足沖突規范的構成要件。沖突規范由“范圍”和“系屬”兩個部分組成。“系屬”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連結點”,是用以確定國際民商事法律關系應當適用什么法律的依據。連結點是把沖突規范“范圍”中的法律關系或法律問題與特定地域的法律聯系起來的橋梁或紐帶。[2]傳統的“連結點”包括物之所在地、法院地、住所地、合同訂立地、侵權所在地等;當代更為靈活的“連結點”還包括當事人合意選擇地、最密切聯系地等。但該條款“適用調整該區段運輸方式的有關法律規定”并沒有通常意義上沖突規范的“連結點”,即不具有能夠確定的事實因素。僅憑該規定并不能排除有兩個以上國家法律調整某個運輸區段的可能性。此外,適用《海商法》第105條和《民法典》第842條的首要前提是法院已經根據沖突規范或根據當事人的選擇確認了多式聯運合同的準據法是我國法律,如果再根據《海商法》第105條和《民法典》第842條指向了外國法律并不符合我國不適用反致/轉致的原則。
(二)對運輸區段性質認定規則的缺失
如果貨損發生在特定運輸區段,對該區段進行定性是識別適用法律的首要條件。如果國際多式聯運中包含跨境的內陸運輸,損失僅發生在某一國內的內陸運輸區段,將該內陸運輸區段識別為國際運輸(由于整個內陸運輸為跨境運輸)還是將其識別為國內運輸(由于貨損僅發生在一個國家內),對于適用法律至關重要。有學者認為盡管國際多式聯運合同的履行通過不同運輸方式完成,但各個不同運輸方式的區段不能視為獨立的運輸合同。因此,無論某一運輸方式的區段是否完全在一國境內完成,都不得將區段視為該國的國內運輸。[3]筆者并不認同這一觀點。在某一運輸區段完全在一國境內的情況下,如果將該區段也視為國際運輸,多式聯運經營人對貨主的責任適用的是調整國際運輸的法律,但在其向區段承運人追償的過程中,其合同僅是針對一國境內的單式運輸,法院很可能將適用調整國內運輸區段的法律確認區段承運人的責任,因此存在多式聯運經營人和區段承運人責任不對等的情況,使各方利益失衡。
(三)我國司法實踐中的混亂局面
2019年12月9日檢索到的以“多式聯運合同糾紛”“法律適用”為檢索條件的相關案例僅為8篇。[4]筆者能夠查詢到國際多式聯運合同糾紛中適用國外法律的案例也屈指可數。通過以下幾個案例可以看出由于《海商法》第105條和《民法典》第842條的規定模糊不清,我國法院在處理定域損失情況下國際多式聯運經營人賠償責任的法律適用上沒有明確的依據,因此造成了司法實踐并不統一,在大多數多式聯運案件中法院很可能適用了我國法律。
在“(2014)甬海法商初字第639號”案件中,涉案貨物滅失發生在墨西哥國內的陸路運輸階段,寧波海事法院適用了《海商法》第105條的規定,認為承運人的賠償責任和責任限額應適用調整該區段運輸方式法律即損失發生地的墨西哥法律。法院在這個案件中顯然適用了“貨物滅失或損害發生所在國家的法律”①法院經審理認為,雙方當事人均確認涉案貨物采取多式聯運方式,涉案貨物系在運抵交貨地的墨西哥合眾國墨西哥城的陸運途中被盜搶,根據我國海商法的規定,承運人及即該多式聯運的經營人應當負賠償責任,但其賠償責任和限額應適用調整該陸運區段的有關法律規定。對此,承運人提交了經公證、認證的法律意見書,該意見書及所附材料指出墨西哥法律關于承運人限額的規定和計算的限額。。
在“(2016)粵03民終10255號”案件中,涉案貨物從深圳先經陸路運輸到香港機場,隨后經空運到荷蘭阿姆斯特丹機場,再經陸路運輸運往目的地斯洛伐克。貨物在荷蘭清關后,在運往斯洛伐克的陸路運輸過程中,在德國境內運輸卡車被撬,貨物丟失。一審法院、二審法院以及再審法院均認為多式聯運合同適用中國法律。但對于多式聯運經營人的賠償責任,法院認為因中國并未加入《國際公路貨物運輸合同公約》,當事各方也并未特別約定適用《國際公路貨物運輸合同公約》,因此并沒有支持多式聯運經營人主張依據《合同法》第321條②《合同法》第321條規定:“貨物的毀損、滅失發生于多式聯運的某一運輸區段的,多式聯運經營人的賠償責任和責任限額,適用調整該區段運輸方式的有關法律規定。貨物毀損、滅失發生的運輸區段不能確定的,依照本章規定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規定適用《國際公路貨物運輸合同公約》的主張。在該案例中,法院并沒有識別該陸路運輸是國內還是國際運輸,也沒有主動查明并確認“調整該區段運輸方式的有關法律規定”,而是依據當事人的主張認為中國沒有批準加入《國際公路貨物運輸合同公約》,當事人也沒有約定適用該公約,因此排除適用《國際公路貨物運輸合同公約》,而適用了中國法律。
在“(2018)最高法民再196號”案件中,涉案貨物也是在墨西哥內的陸路運輸階段滅失,法院均認為關于涉案糾紛承運人責任及責任限制等應適用墨西哥當地陸路運輸法律,即“貨物滅失或損害發生所在國家的法律”。但對于查明墨西哥法律,一審法院通過各種途徑試圖查明墨西哥法律,但均未能查明。二審法院認為承運人提供的墨西哥法律相關章節并不足夠,而且提供法律意見的專家資質和內容都沒有得到核實,因此也沒有適用墨西哥法律。最高人民法院綜合了以下三點主要因素最終確定適用了墨西哥法律:①承運人在三次審理中分別提供了三個不同外國專家的意見,他們的意見基本一致;②承運人補充提供了完整的墨西哥法律條文和墨西哥法院案例;③對方沒有就墨西哥意見和法律提出相反意見和相應依據。
筆者在2020年代理客戶在深圳法院向多式聯運經營人提起了貨損索賠訴訟,該案件貨物先從捷克通過陸運運往德國,原計劃從德國通過空運運往中國香港后通過內陸運輸到深圳。貨物在運至德國時在從卡車上卸載時發生貨損。國內一審法院認為貨方和多式聯運經營人簽訂的多式聯運經營合同中適用的法律為中國法律,而且貨損并未發生在空運階段,因此直接適用中國法律認定多式聯運經營人承擔責任。法院并沒有適用《合同法》第321條的規定識別和確認調整損失發生區段的相關法律規定。
(四)根本原因——在定域損失發生在國外的情況下適用外國法律的障礙和弊端
如果將《海商法》第105條和《民法典》第842條“調整該區段運輸方式的有關法律規定”認定為“貨損發生區段所在國家的法律”,在定域損失發生在國外某個運輸區段的情況下,法院無疑需要查明該區段所在國家調整該區段的法律,但查明外國法律往往比審理案件實體問題更耗費時間和成本,這也成為適用上述條款的最大障礙。
1.國外司法實踐中適用法律存在不確定性
適用調整該區段運輸方式的有關法律規定,不應僅限于有關國家或地區加入的國際公約和本國實體法的條文,也應該考慮該國司法實踐中對特定運輸區段的識別和適用法律的情況。如果僅將有關法律規定簡單理解為國際條約和國內實體法條文,則無法反映出調整特定運輸區段的實際法律適用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多式聯運經營人承擔責任后,向區段承運人追償的過程中法院適用了不同的法律進行審理并確定了區段承運人的責任低于多式聯運經營人向貨方承擔的責任,則無法有效保護多式聯運經營人,失去了該條款設立的目的和意義。如何適用國國際公約和國內法律,筆者認為并不能簡單地依據法律條文,還應當查明外國法院的司法審判實踐和判例。
國際上對于調整跨境單一運輸方式存在不同的國際公約和規則。每個國家和地區加入的公約和規則不同,而且每個公約和規則的適用條件和范圍也并不相同。目前調整不同運輸方式的主要公約有《國際公路貨物運輸合同公約》(CMR①The Conventions on the Contract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by Road,1956年在日內瓦簽訂,1961年生效,目前已有45個簽約國,主要是歐洲國家。)、《國際鐵路貨物運輸公約》(COTIF-CIM②The Convention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Carriage by Rail (COTIF) of 9 May 1980 as amended by Protocol of Modification of 3 June 1999 (Vilnius Protocol) Appendix B: Uniform Rules Concerning the Contract of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by Rail(CIM),目前已有50個國家或組織批準加入Vilnius Protocol,主要是歐洲國家。)、《布達佩斯內河貨物運輸合同公約》(CMNI③The Budapest Convention on the Contract for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Inland Waterway of 22 June 2001.)、《海牙規則》(Hague Rules④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of Law Relating to Bills of Lading,1924,1924年8月25日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簽訂。)、《海牙維斯比規則》(Hague-Visby Rules⑤The Hague Rules as Amended by the Brussels Protocol of 23 February 1968.)、《華沙公約》(Warsaw Convention⑥The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Carriage by Air, signed at Warsaw on 12 October 1929.)、《蒙特利爾公約》(Montreal Convention⑦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for International Carriage by Air, signed at Montreal on 28 May 1999.) 等。
在歐洲適用的公約中,適用范圍最常被討論的是《國際公路貨物運輸合同公約》(“國際公路公約”)。《國際公路公約》主要調整跨境公路運輸法律關系,但并沒有明確如何適用多式聯運中的公路運輸區段。因此,《國際公路公約》是否能調整多式聯運區段中的公路運輸區段存在爭議,主要取決于不同成員國法院對《國際公路公約》適用范圍的理解和適用。以英國的典型案件Quantum Corporation Inc.and others v.Plane Trucking Ltd and Air France⑧[2001]3Lloyd’s Rep.133,[2002]2Lloyd’s Rep. 25.為例,1998年9月,貨物計劃先從新加坡空運到巴黎,然后從巴黎經過陸路和海上運輸到愛爾蘭都柏林,但在英國陸路運輸階段被偷走。承運人主張適用空運單并入的標準格式條款,根據該條款11.7,其責任限額為每公斤17個特別提款權。而貨主則主張適用《國際公路貨物運輸合同公約》,根據該公約承運人不能享受責任限額。該案的爭議焦點是從巴黎到都柏林的運輸區段應適用什么法律。一審法院認為《國際公路公約》適用于特定的合同而不是運輸,應把從新加坡到都柏林的運輸作為整體看待,因此巴黎到都柏林的運輸并不符合《國際公路公約》的適用條件,因此本案不適用《國際公路公約》。二審法院推翻了一審法院的判決,認為《國際公路公約》適用于從巴黎到都柏林的內陸運輸。顯然,對于同樣的事實,一審法院和二審法院對于《國際公路公約》適用條件的理解并不一樣。
在荷蘭,同一家法院對《國際公路公約》的適用范圍也有不同的理解。在相似的兩個案件中,貨物均在多式聯運中的公路運輸區段發生損壞,由于發生貨損的公路運輸區段在一個國家內,并沒有跨境,所以在一個案件中,法院認為該公路運輸區段不符合《國際公路公約》的適用范圍,因此沒有適用《國際公路公約》。而在另外一個案件中,法院認為是否適用《國際公路公約》要看整個多式聯運所跨越的地區,即貨物從自運輸開始到交付給收貨人已經跨越了不同國家,因此,該案件適用了《國際公路公約》。德國法院則不認為《國際公路公約》可以適用于多式聯運中的不跨境的公路運輸區段。即使對于多式聯運中跨境的公路運輸區段,如果其不符合《國際公路同公約》第2條中的滾裝運輸(roll on,roll off),德國法院也不認為可以適用《國際公路貨物運輸合同公約》。[5]
《國際鐵路貨物運輸公約》、《華沙公約》和《蒙特利爾公約》都對自身調整的運輸區段進行了延伸。如果國際運輸包含了某一成員國國內公路或內河運輸,其作為鐵路運輸的補充,《國際鐵路貨物運輸公約》也同樣適用該國內公路或內河運輸。《華沙公約》和《蒙特利爾公約》也延伸適用于機場外履行的任何陸路、海上或者內水運輸過程,前提是此種運輸是在履行航空運輸合同時為了裝載、交付或者轉運而辦理的。不同的公約的適用范圍有重合的部分:如果某一區段既是《華沙公約》或《蒙特利爾公約》調整的范圍,也是《國際鐵路貨物運輸公約》調整的范圍,法院應當適用哪個公約呢?歐洲不同國家的法院采取的看法不同,理論界也沒有統一的觀點。
可見,國外法院在適用國際公約和規則時也面臨著區段運輸性質識別規則缺失以及公約適用范圍不確定的困擾。在外國法律對相關法律適用不明確的情況下,我國法院如何適用國外法律并沒有明確的指引和標準,實踐中可能會導致法院傾向于認為國外法律無法查明從而適用我國法律。
2.我國法院查明外國法律的現實困境
2011年4月1日起實施的《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10條規定:“涉外民事關系適用的外國法律,由人民法院、仲裁機構或者行政機關查明。當事人選擇適用外國法律的,應當提供該國法律。不能查明外國法律或者該國法律沒有規定的,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根據《海商法》和《民法典》的規定,對于貨損損失發生在國外特定區段的,應適用調整該區段的相關法律。如果該條款被理解為指向國外法律,則可以認為是法定選擇外國法律,似乎并不是當事人選擇適用外國法律的情況。因此,該外國法律應由人民法院、仲裁機構或者行政機關查明。但在司法實踐中,法官能借助的平臺有限,尋求外部機構意見也存在溝通機制不暢、反饋周期長、查明效果不理想等障礙,且在現階段與法院的審執效率相沖突,在法官面臨大量辦案壓力與結案任務的現實情況下,再要求法官主動查明外國法幾乎不可能。[6]
即使當事人提供法律,其形式通常限于法律意見書或法律條文,其證據形式往往存在瑕疵,例如法律意見書未經公證認證,或者法律意見書出具人身份未經確認和公證認證,引用的相關法律、案例無法查明,案例與涉案案情不符或案例之間存在沖突等,法官往往不能確信當事人提供的外國法的真實性及含義的準確性。
從上述“(2018)最高法民再196號”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見不難看出,適用“貨物滅失或損害發生所在國家的法律”的關鍵問題在于是否能夠查明該外國法律。查明外國法律無疑需要提交大量的證據并履行相關的司法程序。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見,當事人提供的外國法律意見一定要經過公證認證才能作為證據使用。但根據2019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除了公文件和涉及身份關系的證據,其他證據已經不需要履行相關公證認證的證明手續,這意味著外國法律意見很可能不再需要進行公證認證。但出具外國法律意見的外國專家的相關資質,就屬于涉及身份關系的證據,可能仍需要履行公證認證手續。提供一份外國法律意見可能僅是孤證,可能還需要其他的法律意見相互支持和印證。而且,對于一個國家的法律,不但要提供外國法律意見,還需要提供完整法律條文和相關案例,用以證明當地的司法審判規則和實踐。此外,對方是否能提出相反的觀點和依據也是考量因素。如果損失發生在歐盟或聯邦國家,其本國和區域法律規定和適用更加紛繁復雜,這無疑給司法審判加大了難度,延長了訴訟時間,增加了各方訴訟成本,不利于高效訴訟。
綜合以上分析,即使能夠確定損失發生的特定運輸區段,要確定外國法院適用該區段運輸的法律也并非易事。正是因為查明外國法律難度大,雖然《海商法》和《民法典》均規定了貨物滅失或損壞發生在區段運輸的適用調整該區段運輸方式的相關法律,但在司法實踐中對確定調整該區段運輸方式的法律取決于法官對案件的理解,真正能適用外國法律的案件很少。該條款實際并沒有在司法審判實踐中發揮到應有的作用。
四、解決方法——明確《海商法》第105條和《民法典》第842條中的適用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將《海商法》第105條和《民法典》第842條中的“調整該區段運輸方式的有關法律規定”理解為外國法律,筆者估計當時更多考慮的是將多式聯運經營人向貨主承擔的責任和國外區段承運人承擔責任保持一致,避免多式聯運經營人賠償完貨主后無法向國外區段承運人追回損失。但在定域損失情況下適用外國法律的弊端也很明顯。由于查明外國法律耗費時間和成本,增加法官辦案的負擔和各方當事人的訴訟成本,不利于提高訴訟效率、保護當事人權益,我國司法實踐中很多法院最終還是適用了我國法律,無法實現適用外國法律的目的。這也造成各地法院的判決不一致,導致司法不公正,當事人擇地訴訟。而且,適用外國法律并不利于當事人預測風險。當事人在現實交易過程中了解外國法律非常困難,而且外國法律包括了國際公約、規則和本國法律,具有復雜性而且不確定性,因此當事人無法對在特定運輸區段發生貨損需要承擔的責任進行預測。由于責任的不確定性,在安排商業責任保險時,也不利于當事人分擔風險、控制成本、尋求最優保障。這也是阻礙多式聯運經營人責任保險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筆者認為結合我國以上情況,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在立法層面從修改《海商法》第105條和《民法典》第842條入手,將該條款中的適用法律明確為我國法律。
(一)借鑒國外經驗
德國商法典第452條規定,如果貨物的運輸是基于一個運輸合同由多種運輸方式進行的,并且,如果締約方之間就運輸的每個區段(包含一種運輸方式或區段)訂立了單獨的合同,則這些合同中至少有兩份合同將受不同的法律規定調整,除非下列特殊規定或適用的國際公約另有規定,否則合同應適用第一分章的規定。這也同樣適用于運輸的部分區段是海上運輸的情況。452條是一個總括的規定,規定了對于多式聯運合同,應當適用德國商法典第四本書第一分章的規定。
第452a條規定,如果能夠證明滅失、損壞或導致交貨遲延的事故發生在特定的運輸區段,承運人的責任,如果不同于第一分章的規定,應適用調整該運輸區段合同的法律規定。這一規定和我國《民法典》和《海商法》的規定相似。
德國大部分學者和法官認為第452a并不能指向另一個國家的法律:首先,德國法院在確定一個多式聯運案件適用德國法律時,已經適用了國際私法/沖突規范。在確定了適用德國法后,再次根據損失發生的運輸區段選擇外國法違背了國際私法/沖突規范的規則,也不符合德國法律的規定。其次,德國商法典第452條是實體規范,而不是國際私法/沖突規范;該條規定只能指向德國法律或德國加入的國際公約,而不能引起外國法律的適用。
荷蘭民法典第8:41條規定,在多式聯運合同中,運輸的每個階段適用調整該階段的法律。如果損失發生在特定運輸區段,那么將適用調整該區段的法律。荷蘭司法實踐中和德國采取同樣的觀點,即調整該階段的法律指荷蘭加入的國際公約或荷蘭法律。
日本2018年5月通過了《商法》(有關運輸/海商部分)的修改法案,修改法案自2019年4月起施行。其中第578條規定:“將路上運輸、海上運輸或者航空運輸中兩種以上的運輸方式以同一合同進行承接的,導致貨物滅失等的原因發生于各區段時,承運人的賠償責任,依照各區段運輸方式所適用的我國的法律法規或者我國締結的國際公約規定確定。”[7]該條款明確了對于定域損失,承運人的賠償責任按照損失原因發生區段運輸方式所適用的日本法律法規或者日本締結的國際公約規定確定。日本法律已經將調整特定運輸區段的法律限定為本國法律。
(二)明確“調整該運輸區段的相關法律”為我國法律
《海商法》第105條和《民法典》第842條中的“調整該區段運輸方式的有關法律規定”并未明確“有關法律”是我國法律還是外國法律,如果是外國法律,是損失發生區段所在國家法律還是其他有管轄權的法律,因此造成了對該條款存在不同解釋和適用。為了促進多式聯運產業快遞發展,筆者認為應統一將《民法典》和《海商法》中關于適用特定運輸區段的有關法律明確為我國法律,從而排除外國法律的適用。筆者建議將《海商法》第105條和《民法典》第842條修改為“……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調整該區段運輸方式的有關法律規定”,明確無論定域損失發生在我國還是國外特定運輸區段,均應適用我國調整該運輸區段的有關法律規定。修改后的條款既解決了原條款在法理上的爭議,也可以避免司法實踐中法院對原條款適用的混亂局面。適用我國法律,法院和當事人無須再查詢并證明國外法律和案例,不但節省了各方當事人的司法成本,也有效簡化了司法程序。此種修改有助于國際多式聯運合同相關方合理預測責任和風險。為了防控并降低風險,各方還可以在多式聯運合同中對承運人的責任及限額進行進一步的約定。多式聯運經營人在確定其對委托人可能需要承擔的責任后,也可在與區段經營人之間的合同中約定區段經營人的責任,從而保障其向區段經營人追償的權利。對所承擔的責任和風險有了合理預測后,多式聯運經營人也可以為整個運輸期間安排合理的責任保險,責任保險人對于可預期的責任也可以合理收取保費并制定保險條款,有助于與多式聯運配套的保險產品的快速發展。
(三)對運輸區段性質認定規則的構建
如果《海商法》第105條和《民法典》第842條將適用特定運輸區段的有關法律明確為我國法律,那么法院在定域損失的情況下將根據該條款適用我國法律,但具體適用我國哪個法律還需要對特定運輸區段進行識別和確認。如筆者在上文中舉的例子,國際多式聯運中包含跨境的內陸運輸,但損失發生在某一國家內的內陸運輸區段。筆者認為應將多式聯運中單一運輸方式區段視為一個整體,根據該運輸區段的性質決定適用調整該區段的法律。如國際多式聯運中包含從德國到法國的內陸運輸,但實際損失發生在德國境內,根據前述觀點,由于內陸運輸實際是跨境運輸,因此應當適用我國調整國際內陸運輸的法律。但由于我國和這兩個國家之間沒有關于內陸運輸的公約,因此只能適用我國《民法典》調整公路運輸合同的相關法律規定。如果國際多式聯運運輸區段包含的內陸運輸僅是一國內的運輸,如貨物經德國境內內陸運輸,再經空運到中國,損失發生在內陸運輸區段內,則該內陸運輸應視為國內運輸區段,適用我國《民法典》調整公路運輸合同的相關法律規定。對于其他運輸方式也是基于同樣的原則進行識別。
(四)對調整各區段承運人責任法律制度修改和完善建議
如果將多式聯運定域損失的賠償責任指向我國調整特定區段的相關法律規定,為了構建與國際接軌的各區段責任制度,避免多式聯運經營人在向區段承運人追償的損失數額之外對貨損另作賠付,筆者認為還需要對我國單式運輸方式中承運人責任制度進行系統的構建,對相關賠償責任和責任限額的法律法規進行修改和完善,這樣才能使國際多式聯運經營人的責任的法律適用制度形成體系化和配套化,從而有效保護各方利益。
關于海上運輸和國際航空運輸,我國關于承運人責任限額的規定和主流國際公約基本一致,如果貨損發生在海上運輸或空運區段,適用我國相關法律規定或加入的國際公約基本可以有效保護多式聯運經營人,原則上不會使其承擔的賠償責任高于其追償的區段承運人承擔的金額。
我國鐵路區段的法律規定比較雜亂,而且法律規定的承運人責任限額非常低,已經無法適應我國目前經濟發展水平。筆者建議對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調整和統一,我國可以借鑒相關國際公約(如《國際鐵路貨物運輸公約》)和其他國家的相關責任限額,明確承運人對于發生在鐵路運輸區段的貨物損失的賠償責任和責任限額。
對于內河運輸和陸路運輸區段,我國法律并沒有規定適用的責任限額。如果貨損發生在多式聯運期間的內河運輸或陸路運輸區段,則承運人將不能享受任何責任限額,需要根據實際損失進行賠償。這可能導致多式聯運經營人在賠償實際損失后,向區段承運人追償時,區段承運人可以根據國際公約或本國法對其責任進行限制。
隨著《海商法》的修訂工作全面展開,2018年11月的《海商法(修訂征求意見稿)》已經將國內水路貨物運輸合同納入第五章進行了規范,并且將貨物滅失或者損壞的賠償額規定為與海上貨物運輸合同適用標準一致。這更加有利于國內水路貨物運輸合同下的承運人,也為多式聯運中貨損發生在內河運輸區段的承運人責任適用法律統一了標準。筆者認為應加快《海商法》的修訂工作,盡早將內河運輸合同納入《海商法》中,從而明確內河運輸合同下承運人的責任。
對于內陸運輸,筆者建議,我國可以效仿國際上其他國家的做法,對國內陸路運輸承運人賠償責任限額進行規定。托運人和承運人可以在合同中約定賠償的限額,但不得低于法定限額。這一做法的好處是使合同雙方可以預見到承運人的最大賠償責任,貨方出于預防風險可以在合同約定高于該限額的賠償責任,或安排貨運保險,承運人也可以有效地安排承運人責任險,節省成本,避免承運人為貨物購買高額責任險。
五、結語
隨著國際貿易的不斷深化和供應鏈物流的一體化,國家加速推進多式聯運產業的創新和發展,法律界更應借此契機積極推動多式聯運相關法律制度的探索和完善。我國目前《民法典》和《海商法》中關于多式聯運有相似的規定,但由于條款少、規定簡單,在司法實踐中引發了很多爭議,亟待修改和完善。在國際多式聯運定域損失的情況下,多式聯運經營人的賠償責任和責任限額將適用調整特定區段運輸方式的相關法律,但該條款規定和性質并不明確,如何認定調整特定運輸區段的外國法律,以及外國法院適用國際公約和本國法律本身具有不確定性,而且我國國情和法律決定查明外國法律確實存在較大困難。因此,為了有效調整多式聯運合同關系,提高訴訟效率,降低訴訟成本,避免適用法律的不確定性,建議從立法層面和司法層面對定域損失多式聯運經營人的責任的法律適用明確為適用我國調整特定區段運輸方式的相關法律,確定對特定運輸區段的識別制度,完善調整各個運輸區段多式聯運經營人法律責任法律適用的配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