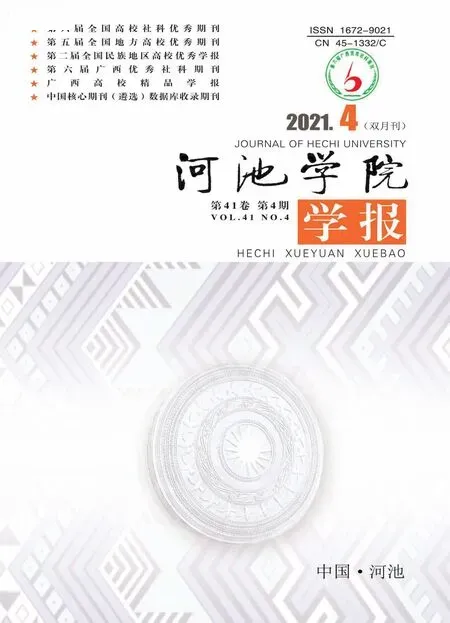清末民國壯族詩人韋繡孟的詩學思想
葉官謀
(廣西科技師范學院 文化與傳播學院,廣西 來賓 546199)
清末和民國壯族詩人韋繡孟(1856-1929)是廣西鹿寨縣中渡鎮人,字峰芝,自號“茹芝山人”。其平生大半時間游歷祖國各地,并在山東為小吏17年。宣統元年(1909年),其自魯返桂,之后基本上只往來于廣西桂林、鹿寨、中渡數地,與文朋詩友切磋文學創作技藝。其詩歌既有游歷和為官期間所作,亦有回桂期間對于所見所聞之抒寫。其所著詩集有《茹芝山房吟草》,共收入其按創作時間先后自行編定的詩歌500余首。韋繡孟是清末和民國期間廣西壯族頗具思想光芒且有詩集留存于世的典型代表人物,正如學者顧紹柏所言:“他是一位既有個性又有代表性的詩人,無論就其思想的閃光點還是從其種種局限性來說,他都算得上是壯族知識分子的典型。”[1]韋繡孟的好友陽顗更是在閱畢韋詩之后給出“清雅雄健,卓然名家”[2]2的評語。綜觀韋繡孟所著的詩歌,可知其不僅較好地繼承了前人尤其是清代詩人詩歌創作中一些具有共性的特點,還能在詩歌內容和創作藝術等方面提出某些頗具創意的新觀點新要求,并以大量創作予以踐行。無論是從廣西還是從全國范圍而言,韋繡孟都是一位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清末和民國時期的詩人。鑒于目前關涉到韋繡孟的詩學思想以及創作實踐的研究成果頗少且過于粗略,筆者試對其作一個相對專門和深入的探究,以為后人深耕細作提供一定參考。
一、在詩歌思想內容方面的重要主張
綜合觀之,韋繡孟在詩歌內容方面的重要主張首先是認為詩歌內容要能體現憂國之心和具有雄直之氣,其次是認為在詩歌創作方面要有超越前朝舊代的銳氣甚至傲氣,最后是認為在詩歌創作方面要有客觀評價所生活時代社會不平現象的勇氣。
詩歌內容要具有憂國之情和雄直之氣是韋繡孟尤為重要的詩學主張。韋繡孟在《茹芝山房吟草》中云:“詩家輩世出,一言為君陳:雄直山川氣,憂危君國身。”亦即詩人要以詩歌為主要方式來為國家和君主大事心存憂患和深謀遠慮,并且所作詩歌應當具有如高山大川那般的雄直之氣。諸如此類詩歌在韋繡孟詩集中,可謂隨處可見。如《感事六首》云:“泣血摧肝敵滅無,諸公畢竟昧良圖。坐看妖焰風云變,那有神兵草木驅。累葉簪纓歸劫燼,九朝陵寢廢邱墟。全權倘副鈞衡任,日月重輪大雅扶。”[3]146此詩表達了其內心的恨敵滅敵和無限愛國憂國之思,極易引起強烈共鳴。此類詩歌更具代表性的是詩人在青年時期所作的《甲申感事》,詩云:“變守為攻戰復和,風云擾攘日生波。塵氛交廣飛鷹疾,秋入淇黔怒馬多。五月渡瀘懷諸葛,十年按劍有廉頗。戎機一誤南疆挫,大笑先生魏絳訛。”[3]40詩歌顯然是對祖國南疆遭受侵略,戰事頻仍,雖時有勝績,但最終卻因李鴻章等人為謀私利而使國家利益受到損害的痛斥。詩人通過此詩表達了強烈憤慨和對國家的深切憂慮之情。細究韋繡孟,可知其對于以杜甫為代表的唐代諸詩人高度敬仰,不僅學習其精神品質,還學習其詩歌創作精要。經筆者統計,韋繡孟所作詩歌中有如杜甫那般憂國憂民之思以及體現出雄直之氣的作品占其詩歌總數的五分之三左右,可見其不僅在言論上大力倡導,還在行動上付之實施,其在言行一致方面完全稱得上是具有代表性的清末民國壯族詩人。
諸如此類詩歌由于深懷或憂或喜之情,往往會自然流露出或多或少雄直之氣,這是韋繡孟詩歌中頗為常見卻十分重要的現象,也是韋繡孟詩歌在內容上勝于諸多前賢的一個重要方面。
詩歌內容要力求做到“睥睨千古,藻繪三春”是韋繡孟第二個重要主張。韋繡孟在詩歌創作中,提出“或睥睨千古,或藻繪三春”的觀點,即認為在詩歌創作中應力求開拓創新,敢于超越前人甚至于傲視前人,尤其是在所涉內容方面。韋繡孟主張將一切人事景物作為對象,而不必拘泥于某一種或幾種題材。綜觀韋繡孟所作的500余首詩歌,其內容確實頗為豐富多彩,其中不僅有對祖國美好山川的摹寫,還有對歷代人情物事生發的無限感慨,既有對家國民生不幸的憂思,亦有對親朋好友離去的傷慟,既有對他人詩歌的唱和回應,也有對后世文人為詩原則的提倡,等等。不管大情小事,均被韋繡孟納入到其創作題材視域中,使其詩歌實際上成為清末民國期間中國的一個個或細或巨的片斷和恒久記憶。
在韋繡孟頗具創新性題材的詩歌中,頗具特色值得特別提到的《滬上感言》云:“昊天忽放光明界,一笑豁我胸襟隘。泛湘兩月苦跼促,入滬百物逞雄怪。洋場事事極精工,美麗何只風月叢?天巧畢露元氣泄,千年閉塞一朝開而通。小儒戔戔那窺其涯涘,惟有神移目駭漸染歐西文化風。即如火攻一門始諸葛,日新月異造化為之奪,海艦無虞魚雷轟,礁桿志將蜃霧遏;又如指南之車始公旦,開物成務何嘗不淹貫?竟籌鐵軌達全球,火車綿亙功倍而事半。電接朔南信息靈,聲留胡越音容煥。化機物理窮微茫,影館汽燈紛浩瀚。闤阓連云寶馬馳,桂蘭得露朱櫻璨。時髦到此競流連,志士望洋殊感嘆。吁嗟乎樂哉,靜安寺,上海樓,張園散,愚園游,鬢影衣香猶在眼,李三三獨占千秋。滬俗繁奢滬水清,春申江上月華明。吮毫北望殷憂切,又聽明朝賽馬聲。”[3]79-80全詩表面上是寫作者看到上海日新月異景象后生發出的無限感慨,實際上要表達的卻是因對當時中國在全球發展中已然落后的現實狀況而萌生出的無限憂悵之情。正因為對國家愛得深沉,所以作者對于其耳聞目睹的那些自國外引進的新奇機器等等的記錄,無不打上或大或小的問號,并無比希望自己深愛的國家能夠得到諸多啟發而迅速發展進步。同樣具有代表性的是其所作的關涉近代煤礦工人遇難的現實作品《哀水火夫行》,詩中有許多完全可以稱為“空前絕后”的真切描述,如“攻煤之人性本愚,縋幽鑿險日爭趨。誤穿古空水來矣,本為謀生翻送死。水泉噴涌似洪濤,百尺深淵難覓篙。入地無門山無路,山摧海泣群呼號。是時洪爐甫安就,電機左右飚輪救。……生既同井死同穴,九京相對毋幽咽。”[3]143韋繡孟不僅敘寫了類此反映礦難等頗為特殊的民生大事,還記錄下了清末民國期間外國侵略者入侵中國時令人憤怒的各種言行物象情狀等細節,如“越雉不聞再入關,狼封豕突又連山。中朝將帥辜恩久,異族旌旗列陣殷”,實可謂令人悲痛與憤恨交織。諸如此類,是韋繡孟詩歌內容所具有的頗為重要的特點,也是值得人們進一步深入研究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
詩歌創作中要具有“恥于頌新朝”的思想是韋繡孟的最后一個重要主張。韋繡孟在詩歌中提出“處晚力追盛,扶衰恥頌新”的觀點。可以說這是他相對獨具的詩學思想。綜觀中國歷代詩人,有不少都具有對新朝盲目歌功頌德的思想和行為,以求得到新朝的青睞并謀得一官半職,或在此后自身的順利晉升等方面有所助益。較為典型的歌功頌德詩人群體以明代“三楊”及其追隨者形成的臺閣體詩人群為代表,他們的創作以對新朝的歌功頌德為主旨,使得詩歌大多缺乏真情實感而受到后人的批評指責。此后朝代盡管不如明代那樣令人側目,但同樣還存在不少歌功頌德題材的詩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文化大氣候使然。然而令人詫異的是,壯族詩人韋繡孟極少受到晚清和民國此類文化大環境大氣候的影響,能夠大膽提出“處晚力追盛,扶衰恥頌新”的觀點,這在當時是十分難能可貴的。韋繡孟此思想觀點主要體現在其一些詩作中,如《民國成立紀念日書感十二首》中有詩云:“普籌公債難成繭,遍置私人亂若麻。仍蹈制科舊惡習,空談無補恨無涯。”“鼓吹幸成新世界,變更直送好河山。”“登場傀儡魚龍戲,失勢英雄蛇蝎磨。慘憶去年今日事,華燈一照滿庭蛾。”[3]108對于中華民國的成立,韋繡孟沒有盲目頌贊,而是冷靜觀察,對其存在的一些丑惡和不合理現象給予頗為尖辛的嘲諷,而這無疑是需要很大勇氣的。
由此可知,韋繡孟對于新朝的情況,能夠作出較為冷靜客觀的分析,并從自身的標準出發來判定其是非曲直,顯示出自己的鮮明態度。其不隨意順應時勢的做法是前朝諸類詩人所罕有的,體現了其頗為獨立的人格和甚為稀見的膽色和骨氣。
二、在詩歌創作藝術方面的重要主張
韋繡孟在詩歌創作方面的重要藝術主張,一是強調要有言外之意和做到清新脫俗,二是強調要兼具韻險辭達和情深語純,三是反對規仿前人,提倡自我開新,四是強調要做到熟練用典。
韋繡孟在詩中有云“要參味外味,肯墮塵中塵”,亦即強調詩歌要有言外之意和做到清新脫俗,這是他所提出的十分重要的觀點。著名的“味外味”一詞出自蘇軾《東坡志林》第十,其中有云:“司空表圣自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中國傳統詩歌所追求的一個理想境界,便是力求讓人感到詩歌具有味外之味,而令人良久甚至永久不能忘卻,而不是簡單地展示人世間各種人情物事。正因如此,中國的詩歌才具有了永恒的魅力。飽讀詩書的韋繡孟深諳此理,其不僅概括性地提出“要參味外味,肯墮塵中塵(亦即‘拒絕塵中塵’)”的觀點,還努力踐行之。其所作500余首詩歌,有一半左右循此原則,使其詩歌呈現出第二層意境即“味外之味”,而杜絕膚淺乏味。如其所作的《登黃鶴樓》云:“幾經兵燹尚巍然,納漢吞江氣萬千。才似青蓮猶擱筆,人乘黃鶴已登仙。云山四壁自今古,風雨一樓無后先。擊節試吟崔顥句,芳洲鸚鵡黯前川。”[3]70詩人表面上是寫自己對前賢無比崇敬之情,而另一個層面則是表明自身正在向他們學習,以圖向前賢看齊甚至奮力趕超的思想。此言外之意只要深入分析便可明了。又如《甲辰新正朔日寅正試筆》云:“爆竹響中宵,桃符換門首。一事喜非常,明朝四十九。伯玉仕衛年,子輿客齊后。車塵馬跡間,且醉迎春酒。春風如相識,拂我庭前柳。”[3]247作者在詩中以東周時期的蘧伯玉和孟子不見用的典故來曲折表達自己的懷才不遇,在其49歲之際更顯苦悶難訴。詩歌在講述前賢故事之際將自己的不順境遇融入其中,其味外之味甚濃。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韋繡孟所作的500余首詩歌當中,可以看出其對杜甫的高度景仰和尊奉,也可看出其詩歌創作欲力追杜甫的雄心壯志。另外,其中還有一個頗為明顯的相似點,那便是杜甫不少詩歌均力求達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境地,而韋繡孟所提出的“參味外味,拒塵中塵”的要求,其實與杜甫所提出的此一觀點和追求在很大程度上相近。
如果說韋繡孟于此觀點上有所創新或補充的話,便是其提出了“拒塵中塵”的思想,亦即其具有千方百計追求清新脫俗的思想傾向,而這也是符合詩歌創作規律的一個重要觀點。因為只有不斷追求清新脫俗,詩歌創作才能異彩紛呈,詩歌才能不斷推陳出新。也只有這樣,詩歌才會擁有更撼動人心的力量和更具生命力。
主張做到“韻險辭達,情深語純”是韋繡孟在詩歌創作藝術方面的第二個重要思想。韋繡孟在《津門舟次與友人論詩》中云:“韻險辭能達,情深語卻純。”詩人也在創作中努力踐行著這個觀點。其中“韻險辭達”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為其用世人熟知的東坡押險韻之典型詩歌作為參照并力求超越的對象。其所作次前人韻詩《雪后蒲臺查賑,與陳嘯山大令夜吟,用東坡〈北臺〉原韻》,全詩為:“萬里塵沙沒點纖,宵分風雪扣關嚴。隔簾少女爭吟絮,煮海人家誤撒鹽。鶴氅夜游尋舊夢,牛衣對泣痛窮檐。詩成何用催銅缽,六出奇葩上筆尖。賑票紛投亂抹鴉,災黎競渡蹴冰車。梅含綠萼成霜果,篙插黃流作浪花。耐冷驢騎湖岸客,牢愁貂換酒人家。朝來筆硯都僵凍,白戰輸君手八叉。”[3]214詩歌以蘇軾《北臺》原韻進行創作,總體上文從字順,罕有澀語,能較好地表達出作者對友人陳嘯山作詩神速的欽佩之情。此詩盡管總體水平達不到蘇軾的高度,但亦有可圈可點之處。
韋繡孟所作更多的是那些具有情深語純特點之詩。如《奉和周榕湖大哥(嵩年)尊甫慕陔老伯〈辛卯出都留別同人〉原韻四首》其三云:“重逢未老桂山春,霞寺星巖照眼新。廿載鵬翔天畔雨,一廬蝸寄客中身。榕陰舍古定誰主,棠社花開欲絆人。珍重臨歧無限意,尚書方進酒三巡。”[3]106此詩雖談不上用險韻,但卻較好地體現了其詩歌創作中語辭暢達,情深語純的特點,表達了作者對友情的珍愛之意。《初夏感懷七首用香山九老會詩原韻》《河上送逯鏡緣大令差竣言旋得四十韻》《之罘觀海書感得三十韻》以及其所作的關于悼念類內容的詩歌等均大體如是。總體而言,韋繡孟較為講究詩歌的用韻,并具有高水平的詩歌創作素養。其所作的500余首詩歌中,既有僅為8句的律詩,亦有長達500字以上的排律,盡管詩歌類型不一,但其講究韻律的特點卻始終如一。其不僅能夠像大多數詩人那樣創作出符合一般要求的詩歌,還能夠創作出超出常人的押險韻卻不讓人覺得“艱險”之詩。而這也是他超越常人的一個方面。
若與前人詩論相較,在“韻險辭達”方面,其與唐代大詩人韓愈在《南陽樊紹述墓志銘》中所提出的“文從字順各識職”和宋代魏了翁在《跋康節詩》中所提出的“文從字順,不煩繩削而合”等為代表性的觀點有不少相通之處,但其同時提出的“情深語純”觀點卻是前人基本上未曾直接提出過的具體新思想新觀點,其意義和價值同樣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
反對規仿前人,并力求達到“結體自輪囷”即自我創新、自我圓融之境是韋繡孟又一個重要的詩學觀點。在反對規仿前人,強調自我創新方面,韋繡孟在詩中寫道:“‘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坡公創此語,意實有所因。后儒懵莫識,鑒貌而遺神。……匪規仿李杜,結體自輪囷。不模擬陶謝,得句自渾淪。”[3]82縱觀前朝舊代尤其是清代,韋繡孟所提出的觀點與清代一些壯族詩人的觀點頗為相似。例如清代壯族著名詩人鄭獻甫(1801-1872)就曾經反復提出作詩要反對模仿古人,應努力追求創新的思想,其云:“器用皆宜今,文字必學古。心追而手摩,陋哉不足數。譬如臨古帖,顏柳歐虞褚。凡云酷似處,必是最劣處。神氣骨肉血,妙不在毫楮。類狗與類鶩,勢反累其主。馳驅馬躡云,醞釀云行雨。淺深視根柢,巧者不能取。名將無陣法,循吏無縣譜。”[4]與前人所提出的類似思想相較,韋繡孟于此方面的觀點顯得更為豐富,其不僅繼承了前賢強烈反對規仿前人的觀點,還在此基礎上提出反對模仿能帶來的良好效果即有可能達到“結體自輪囷”“得句自渾淪”的美好完滿的理想境界。這是韋繡孟對前人的超越之處,也是作為壯族詩人的他對中國文學創作理論的有益補充。
這里需要強調說明的是,韋繡孟反對規仿前人,并在詩歌創作上大量采用率性自然、自由大膽的表達方式以求達到“結體自輪囷”即美好完滿的理想境界。縱觀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文學家,他們提出的與“率性自然”相關的觀點不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大概是明代文學家李贄的“童心說”、湖北公安派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以及清代以著名詩人袁枚為代表所提出的“性靈說”。“二說”和“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主要內涵,都具有“率性自然”之意味,而袁枚所論較之李贄所論又顯得更為深入一些。從韋繡孟的詩集可知,這些理論對韋繡孟的影響很大也最為直接。韋繡孟不僅較好地繼承了李贄的“童心說”和袁枚主導的“性靈說”的核心內蘊,還通過自身大量的詩歌創作實踐,形成了較之二者在詩歌創作上更加“率性”“自然”和“自由”“大膽”的鮮明特點。竊以為其中原因,很可能與壯族人民具有的勇猛無畏、追求自由無拘的天性和酷愛山歌并自由傳唱之傳統有關。因為縱觀壯族歷史,可知古代壯族人民在與各種惡劣生存環境斗爭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以歌代言的淋漓展現自身思想的交流方式。“在壯族民間,很流行唱‘歡’(山歌)。人們不僅在逢年過節時唱,就是平時逢人遇事,也往往唱山歌以應答、抒情。”[5]103“凡農隙之日,每值圩期,即會歌聚飲于此。”[6]178“在生活的一切領域里,都無事不歌,往往以歌代言。”[7]48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在古代和近代的廣西,一般壯族文人所作的詩歌不過是一種或多或少受到山歌影響的更正規化的文學表達樣式而已。而作為壯族子弟的韋繡孟能夠在繼承前賢的基礎上勇于創新發展,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總之,就此點而論,韋繡孟對前人的超越,就在于其作為壯族詩人,能夠在詩歌創作方面更加堅定地反對規仿前人,同時在性靈詩歌創作方面受到壯族傳統文化浸潤而顯得更加率性自由和大膽創新。
熟練地運用典故是韋繡孟在詩歌創作藝術方面提出的最后一個重要主張。為此,其在詩歌創作中專門強調指出“八音咸有托,四始妙無垠”,并要求詩人做到“吮毫矜腹稿,運典數家珍”。事實上,這些要求在具體的文學創作實踐中便是要努力做到“征圣宗經引史。”而“征圣宗經引史”是中國文學史和學術發展史上一個頗為重要的特點。據現存文獻可知這一特點自先秦時起便代代相傳,至宋代時達到第一個高峰,到清代時幾乎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例如清初詩人、藏書家黃之雋,在“征圣宗經引史”方面可謂“空前絕后”,其作品中有一篇序文,每個句子均是從唐代文人的著作中抽取而來。而清代與其相類之人尚有不少。亦正因此,清代一個頗為重要的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方面的特點便是“掉書袋”,這是被后世學者詬病最多的一個問題。廣西雖然地處僻遠,但是由于在清代以后較之此前朝代更多地得到著名文學家之沾溉,“到廣西來的詩人、詞客、名儒、學者、代不乏人,經清代而有增無減。”[8]67確實如此,如在清代便有名家袁枚、趙翼、汪森、舒位、梁章鉅等到訪或宦游過廣西一段時間,并在文學創作上對廣西一些文人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指導。大詩人袁枚就存留數首石刻詩歌于桂林市區,成為聞名遐邇的一段佳話[9]。因此清代廣西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當時文學風氣之先的,文學創作上亦有了很大的發展:在清代末期,廣西在詩詞創作方面出現了兩個詞學大家即況周頤和王鵬運,他們引領著全國文人的詞創作,其文學影響和作用在廣西可謂空前;在散文創作方面也是頗受注目;詩歌創作上則是詩人詩作眾多,質量亦從整體上呈現出對前人很大的超越。關于清末廣西文學發展之盛,龍啟瑞曾說:“方是時,海宇承平既久,粵西僻在嶺嶠,獨文章著作之士未克與中州才俊爭鶩而馳逐,逮子穆與伯韓、少鶴、仲實先后集京師,凡諸公文酒之宴,吾黨數子者必與。語海內能文者,屈指必及之。梅先生嘗曰:‘天下之文章,其萃于嶺西乎!’”[10]由上可見,廣西文學類此迅速發展的局面確實是前所未有的。
由于在清代之際得文學風氣之先促使廣西文學創作發展崛起之故,廣西文人的自信心(據研究,古代廣西壯族人至少在明代及以前具有較強自卑心理,但這種心理隨著廣西的不斷發展而逐漸得到稀釋[11])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許多廣西文人甚至認為自身完全不亞于文學先進地區的一流文人,如鄭獻甫、黃煥中等詩人便如是。在此種心理的影響下,清代廣西文人在詩歌創作中有意地使用大量典故,以顯示個人學識之廣博非凡和高度自信,這一點在韋繡孟的詩歌創作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更值得一提的是,韋繡孟還在前人大多只注重在引經用典據史的基礎上,增加“四始妙無垠”的新觀點,因為在他看來,只有善于“征圣宗經”方能使詩歌變得高妙難及,認為這是詩人應當追求的一種理想境界而努力付諸實施。故而他所作的每一首詩歌,都或多或少地用到典故,有時候一首詩歌用到十幾個甚至幾十至上百個典故。如《晴川閣上眺鸚鵡洲》:“鸚鵡洲邊冢,春來草尚萋。三撾人已杳,片土客爭題。世難懷才忌,天荒入漢低。晴川留杰閣,高并鄂樓齊。”[3]69短短8句40字的律詩,卻用了6個典故,使全詩能夠較好地體現出作者的學識水平和呈現出豐厚的意蘊,“雅”量大增,但也讓讀者尤其是文化水平較低之人在理解上產生一定困難。
除了以上原因外,韋繡孟提出此觀點并予以踐行很可能還與其所處的大環境有關。中國文學發展至清代,由于時局對文人思想的控制較為嚴厲,尤其是雍正時期翰林院庶吉士徐駿因詩集中有“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二句而冤死之后,許多文人對政事時局噤若寒蟬,不少學者甚至由對時局的關注轉至對古代文獻的考據,于是便出現了以翁方綱等人為代表的肌理詩派和考據學派等。盡管他們也創作詩歌,但卻將詩歌作為顯示自身“博古”的一種方式,而不是通過詩歌來反映社會現實,更不敢用詩歌來嘲諷時弊。作為清代末期的一位詩人兼學者,韋繡孟或多或少地受到這種學術環境和創作氛圍的影響,通過運用大量典故顯示自己博學的同時也適時地避開政治漩渦。當然他在運用大量典故的過程中也反映了當時一些社會現實和其對朝廷的態度,這是韋繡孟與許多缺乏骨氣的詩人的不同之處。
總之,若與前人理論相較,盡管自南北朝時期起的劉勰等前人就已提出“征圣宗經”的要求,但這些要求往往不甚直接和具體。而韋繡孟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提出“吮毫矜腹稿,運典數家珍”的要求,則是對前人相關思想和要求的具體化和細化。更為重要的是,“運典數家珍”這一內容是許多前人心中所有但所未提及的新要求新觀點,是韋繡孟對自己和文友、弟子所提出的殷切期望。事實上,這些要求對于豐富文學創作者的知識素養意義重大,這是許多人不得不承認的客觀事實。因此,韋繡孟繼承和發展歷代前賢這些觀點和要求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都是具有一定積極意義和參考價值的。
三、余論
韋繡孟的詩學思想可以說既是對前人詩學思想的良好繼承,亦是對前朝舊代重要詩學觀點的總結和創新。在詩歌思想方面,他提出“具有憂國之情和雄直之氣”“處晚力追盛,恥于頌新朝”“睥睨千古,藻繪三春”,在創作藝術方面,提出“要參味外味,肯墮塵中塵”,反對規仿前人,力求做到“結體自輪囷”,主張“韻險辭達,情深語純”“吮毫矜腹稿,運典數家珍”等思想。這些詩學思想大多令人耳目一新并為之一震,可以說這是他對中國詩歌創作理論進行了值得稱道的繼承、豐富和發展。他對前人詩歌創作經驗的總結和一系列新觀點的提出,以及其言行一致的詩歌創作實踐,或多或少地對清末民國期間的詩人產生了影響,而其詩集中所提到的與其交游或贈詩或唱和的50多位詩人,更可能在有意無意中受其熏陶。正是韋繡孟與受其影響的一系列詩人,更多地將筆觸指向社會和人生,敢于敘寫前人未曾或未敢涉足的領域,努力抒寫記錄人世間的天地山河和大愛小情,促使清末民國詩人詩歌創作尤其是壯族詩人的詩歌創作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呈現出十分可喜的振興局面。“據統計,清初至道光中期,有作品流傳至今的壯族文人逾百,詩作逾千,而且出現了近三十種詩集或詩人合集。到了近代,文學發展更快,據不完全統計,存詩上萬首,詩集或詩文合集亦有三十種以上(現存二十六種左右)。”[1]倘若根據完全統計數據,則有可能達到兩萬首左右,帶給我們更多的驚喜。
而這些壯族詩人所作的詩歌,也是頗多不俗之作,正如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原副主席張聲震所言:“廣西壯族文人詩歌具有值得繼承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其中有一部分近代詩篇充滿愛國主義激情,有較強藝術震撼力。將它置于近代愛國主義詩人的詩篇中,很難分出伯仲。”[12]396認真研讀清末民國壯族詩人韋繡孟等所創作的近代詩篇,可知此說法并非過譽。事實上,正是壯族與漢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文學家一道,為繁榮中國詩歌創作和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出了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