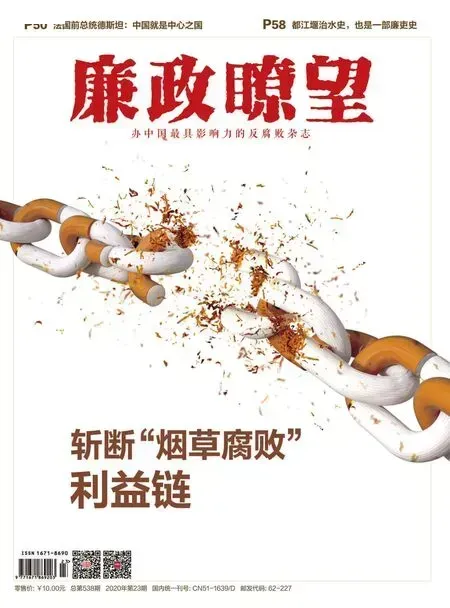張藝謀的《一秒鐘》太短,歷史滾滾向前
文胡椒
一 個米粒大點兒的人踉踉蹌蹌地走在漫無邊際的西北荒漠——張藝謀最新電影《一秒鐘》開頭的取景和構圖方式,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他拍攝于上個世紀的電影《黃土地》。對于熟悉張藝謀的觀眾來說,這種真實粗礪的電影質感實在是久違了。
毫無疑問,張藝謀是第五代導演里把作為視聽語言之一的色彩用到極致的一位。不管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品《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還是新世紀以來拍攝的商業電影《英雄》《滿城盡帶黃金甲》,通過色彩的鋪排、渲染和對比來輔助敘事,是張藝謀自成一體的電影風格。然而,當故事情節有“硬傷”,人物形象不夠飽滿的時候,再高超的藝術技法也只能表現出敘事的空洞無力,電影最終淪為奇觀式的視覺盛宴。
如果說張藝謀的上一部作品《影》仍然延續了他對電影“美”的極致追求,那么《一秒鐘》則完全相反。和張藝謀合作了20年的攝影趙小丁說,《一秒鐘》是張藝謀拍得最篤定的一部電影,他把顏色的飽和度抽掉了30%,一個接近自然的色彩還原。沙漠的光線、明暗很容易拍得很美,但張藝謀不要沙漠的美感。
褪去濃烈的色彩和一切華麗的表現形式,張藝謀再次回歸電影的內核,即敘事。影片講的故事并不復雜,角度卻很新奇。上世紀70年代,三個毫不相關的小人物因為電影結下了緣分。為了看一場電影《英雄兒女》,勞改犯張九聲從監獄逃跑了。因為他聽說,女兒在電影正片開始前的新聞簡報里出現過。孤兒劉閨女,一心想著偷一段膠片,給弟弟做燈罩。在民眾里極具聲望的放映員“范電影”,想著保住自己的鐵飯碗。三個人物,因幾卷電影膠片而糾葛在一起,從爭奪到搶救,隨著片中電影的放映,三個人的故事也抽絲剝繭地展開,各有各的缺失,各有各的苦楚。
《一秒鐘》聚焦歷史洪流中小人物的喜怒哀樂,可以說是張藝謀近年來難得的現實主義作品。張藝謀本人說,這部影片有《活著》的意思。但目前看來,《一秒鐘》有《活著》的氣質,格局卻小了一些。在這部自己擔任編劇的電影里,張藝謀有了更多發揮的空間,但也摻雜了不少“私心”。
影片在宣傳時打出了“張藝謀給電影的一封情書”這樣的標語,但《一秒鐘》發生的歷史卻充滿了血淚。勞改犯張九聲因為被定義為“壞分子”,他的女兒為了擺脫“出身”的影響,在14歲就爭著去扛面袋子。“那時候人是不能左右命運的,我自己深有體會。”張藝謀說,在那個時代,他不敢想自己能上大學、拍電影,因為自己的“出身”不好,他一直活在恐懼里。正是因為很早就有這樣的出身意識,張藝謀更加懂得電影的珍貴。在北京電影學院學攝影的時候,張藝謀很自卑,周圍的同學很多出身于藝術世家,見多識廣,他只能用最笨的努力奮起直追。

知道張藝謀早年的成長經歷,就更加能體會到《一秒鐘》中范電影這個人物的悲劇色彩。范電影號召群眾搶修膠片的情節看起來很夸張,甚至顯得可笑,但他之所以對自己的工作小心翼翼,是出于那個年代對生存的渴望,尤其是當他還有一個因為喝了膠片清洗液變成智障的兒子。他不斷向別人證明,放電影這個工作,只有他能做。張藝謀的經歷多少帶一點這種悲劇性,這是時代局限。他曾對作家方希說:“我一開始就有這個意識,讓自己迅速工具化。工具化你就會對別人有用,人有了用,有些東西就不會找到你身上,你就會有空隙生存。”
即便帶有自傳色彩,《一秒鐘》仍然是一個動人的故事。我們看到了時代是如何在個人身上留下烙印的,也會因為小人物的真實情感產生共鳴。當張九聲重復看著那一秒鐘有關女兒的影像,臺下的觀眾也難免淚流滿面。是的,一秒鐘,太短了。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你我都是如此短暫而又微不足道的存在。就連那唯一證明過存在的膠片,最終也被吞噬在無盡的黃沙里。
從美學回歸敘事,從奇觀回歸真實,《一秒鐘》確實是張藝謀在古稀之年,回歸初心的一部電影。電影的技術和美學不管怎么演進,最后還是要落到對人性的關注。在這個流量為王的時代,第五代導演們對現實的人文關懷顯得十分難能可貴。這樣一部影片,也許是對當下電影創作者的一種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