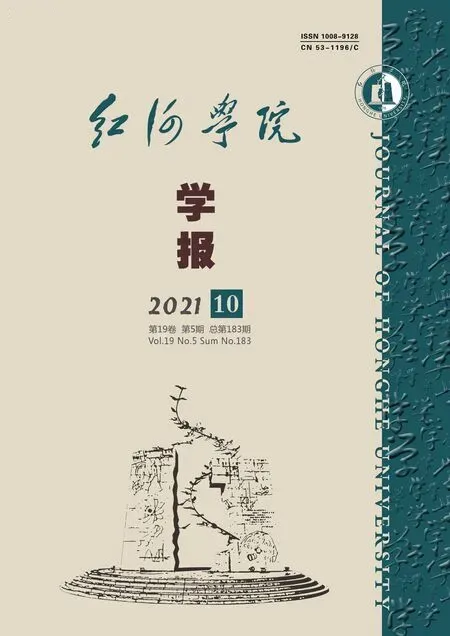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視域下探析孟子的“知人論世”
王 健,趙敏凱
(貴州師范大學,貴陽 550001)
孟子在《萬章》篇中教育萬章如何交友時提出“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好也。”[1]329孟子在這段話中提出的交友方法,即“知人論世”。從其內涵而言,中心是“交友”。孟子認為,應該與善士交友,如果同時代的善士無法滿足交友的需要,可以追溯古代的善士。在對待古代善士時,首先要確證與之所交者是否為善士,這就需要依托古代善士的著作,不僅如此,還需要進一步了解這個人的自身的情況,而對其了解不能脫離當時的時代環境。由此可見,孟子所提出的“知人論世”其核心概念是詩、書、人和世,也就是與之交往善士的著作、個人自身情況和社會歷史背景。具體而言,通過閱讀詩書,可以了解到所交往善士的才情、學術見解和政治主張等方面,但這被文字記錄的信息與本人的真實情況是否相一致,還需要進一步考察本人的行為。但是由于要和非同時代的古人交友,只能依靠已有的文獻資料,從這些文獻資料中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跡。孟子認為僅僅如此還是不足以判定是否為善士,因為“詩書”所記錄的信息和“知人”所傳遞的信息未必完全一致,還需要將“詩書”和“知人”所傳遞的信息納入作者所處的時代再進一步考察,也就是要“論世”。通過分析古人所處的“世”,把握社會歷史環境,進一步判斷古人的“善士”身份,最終確證是否可以交友。從詩書、個人生平和社會歷史環境三個方面可以看出孟子“知人論世”的豐富內涵。關于孟子“知人論世”這一方法,學術界廣泛其應用于文學領域研究,例如胡銀林認為“知人論世”是研究散文的必要支架[2]。陳麗麗[3]認為“知人論世”是中國古典文學批判的重要模式。林繼中[4]認為蕭滌非在研究杜甫時用歷史唯物主義使“知人論世”的方法得到升華。縱觀學術界關于孟子“知人論世”的研究,大部分學者直接將其運用于作品解讀,而對于這一方法本身并未作深入剖析。孟子雖然提出“知人論世”的方法,但是方法的具體內涵有待進一步闡明。將“知人論世”從文學批評研究視域下回歸到其本身,并置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語境中予以考察,具有重要的價值意義。因此,以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來探析“知人論世”,既可以使孟子“知人論世”的方法內涵明晰彰顯,也是對此方法的豐富和發展。
一 一切從實際出發——“知人論世”前提
侯惠勤認為“歷史和邏輯相一致,理論和實踐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基本命題,其中首要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5]。馬克思主義這一方法也是探析孟子“知人論世”的首要命題。孟子提出了知人論世的方法但并沒有說明這一方法的前提條件。從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分析,其前提是一切從實際出發。
孟子“知人論世”的方法是針對交友而言,認為如果和天下優秀人物交往還不能滿足交友需求,便可以上溯到歷史中去了解古代的優秀人物。但是與古人交朋友僅僅是吟詠他們的詩,品讀他們的書,而不知道他們是什么人是不可取的,因此要研究他們所處的社會時代背景,要研究他們個人的事跡。孟子的“知人論世”不僅只限于對古人的了解,也可以作為對當今世人的分析方法。“知人論世”作為一種方法其前提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無論古代的歷史記載,還是現存的客觀事實,都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而不能僅僅從文本出發,所以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1]372。
馬克思從德國的社會現實以及當時的世界背景對德國哲學予以批判,是從社會實際情況出發。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曾明確指出“我們且從當前的國民經濟學事實出發”[6]156,批判了國民經濟學家只是抽象分析私有財產,沒有說明私有財產這個事實。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到“社會、政治以及精神生活受物質生活生產方式的制約”[7]591-592,正是由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所以“知人論世”并非是認知主體的主觀臆斷,而是要尊重社會客觀現實,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應該從客觀事實為出發點,以此找方法。”[8]853鄧小平則回答“唯物主義者的根本立場即從實際出發。”[9]244實際就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因此,一切從實際出發就是從客觀存在的事物出發。這一方法的前提就是從客觀現存的事物著眼看待所要評價的人以及當時的社會背景。朱熹對孟子作注時認為“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跡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1]329在朱熹看來,論世要分析當時的具體情況,知人要考察其言行。
“知人論世”因遵循一切從實際出發為前提,應該把握客觀存在的事物。這不是將關于客體的客觀情況簡單羅列,而是應該把握事實之間的聯系。列寧認為“在社會現象方面,運用亂拼事實或者擺弄實例的方法去研習,是最無意義的。因為任何事物的出現,都有具體的所處環境,潛在誘因,僅僅從部分事實入手,不穩妥且不全面,應當從整體上來聯系把握事實。”[10]364知人論世不是對客觀事實孤立的認識,而是應該運用聯系的眼光將他人的事跡進行整體把握,對當時的歷史背景全面分析,從整體和全部聯系中做到“知人論世”。
由此可見,“知人論世”的前提是一切從實際出發。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分析了意識和存在的關系,認為“人的存在是指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意識僅僅是被意識到的存在。”[6]525馬克思認為“如果凡事都可以從事物的真實情況入手,任何深奧的哲學問題……都可以十分簡單地歸結為某種經驗的事。”[6]528對哲學問題的研究,不能脫離事物本身以及產生情況。意識是由于人和他人交往的需要所產生的,所以“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而且只要人們存在著,它就仍然是這種產物。”[6]533認識社會中的人,所以“知人論世”要在社會關系中考察他人的言行,不能脫離社會關系而研究抽象的人。
二 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視域下蠡測“知人”
以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分析孟子的“知人”,主要可以從肯定人的主體性、強調人的社會屬性和階級屬性三個方面來分析研究。
“知人”要考察人的言行,所知的人必須是現實的人,要肯定人的主體性。馬克思將人看作是社會的人,現實的人,活生生的人,認為以往唯物主義的不足點主要在對事對人的理解上,以往的唯物史觀更多運用的直觀感受,未從事物或人的主體性、實踐性來理解,沒有認識到人的主體地位和能動性,只是將人看做直觀的現象。因此“知人”不能簡單將人作為現象的客觀形勢,還要充分認識到人的主體價值。王陽明與友人游南鎮時,友人對山中花樹與心的關系發問,王陽明認為“你未看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11]101-102以往學者大多批駁王氏此言是唯心之談,但實質上王陽明并沒有否認了花的客觀存在,只是從個體價值選擇的角度闡釋了花在心內的觀點。錢穆激烈批評王陽明的心外無物學說好比佛家之言,是將山河大地都放諸于自己的內心。陳來則不滿錢穆之說,在《有無止境》中做出解釋“陽明在這里不說無是意即無是花,只是說‘此在與汝心同歸于寂’。寂對感而言,如說‘應感而動者謂之意’,心未為花所感時未動此意,但心不可謂之無;花未進入知覺結構,在意象上處于‘寂’的狀態,但不等于花的不存在。陽明既然沒有對‘自開自落’提出異議,表明他所說的不是指自開自落的存有問題。”[12]53楊國榮認為王陽明所說的“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更多是在意義關系上而言,“所謂花自開自落,著眼的是本然的存在;花的顏色明白與否,則是相對于觀花的主體。就本然的存在而言,花之開與花之落與心體似乎并不相干;但花究竟以何種形式呈現出來,亦即花究竟對主體來說具有何種意味,則很難說與心體無關:花的顏色鮮亮(明白)與否,已涉及花的審美形式,這種形式并不是一種本然的存在,它只有對具有審美能力的主體來說才有意義。”[13]501可見,王陽明此說暗含了對人的主體價值的肯定。所以“知人”的主體要能認識到所知之人的主體價值。
“知人”要在社會關系中展開,不能脫離社會環境。馬克思提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即是人的本質。”[6]501認識社會中的人,社會是由人所創造的社會。馬克思認為“人不是抽象的棲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6]3人是世界的人,是社會的人。馬克思探討了現實的人,認為“歷史既沒有過多的豐富性,也無法進行爭斗,這其中最重要最關鍵的要素在人,正是現實中的人創造擁有了這一切并進行戰斗。”[6]295現實的人是社會中的人,不是抽象的人。對人有所了解,需要在人類社會中進行,不能將人看作脫離社會的人,就是在社會關系中考察人的言行。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強調“首先應當避免重新把‘社會’當做抽象的東西同個體對立起來。個體是社會的存在物。”[6]188個人作為社會的存在者,是無法脫離社會而存在。所以“知人”不僅要認識到個人的主體性,同時也要將個體納入社會關系之中。因此,馬克思在分析工人的生存狀態時,不是拋棄資本主義社會的空談,而是依托社會發展形態總結分析了社會財富變化與工人個人的關系。第一種狀態是社會衰落狀態,工人遭受最大痛苦。馬克思贊成亞當·斯密的觀點,認為在社會財富衰落的狀態,沒有一個階級會像工人階級一樣遭受深重的苦難。第二種狀態是社會豐富增長。這一狀態看起來是對工人有利的。但事實上,工資提高導致工人過度勞動而縮短壽命,社會財富增加使得工人勞動產品越來越多的被資本家占有,工人自己的勞動與自己對立,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工人面臨的往往是過早死亡與過度勞動,工人被當成機器使用,作為資本家的奴隸,時時發生新的競爭,導致部分工人流落乞討或者餓死街頭。”[6]121
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指出“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作用的產物。”[14]42強調了人們交互作用產生了社會,并且在這一過程中,人與人之間又形成各種社會關系,由此可見如果沒有人就沒有人類社會,沒有社會關系就沒有人類社會。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進一步明確指出社會是由個人彼此發生的那些聯系和關系的總和所構成的,所以社會本身就是所處社會關系中的人本身。馬克思分析的人類社會并不是抽象的實體,而是人通過實踐所創造的一種關系總和,表明人與社會不是決然對立,人創造了社會,同時人也是社會中的人。因此,“知人”的方法運用應該在社會現實中展開。
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是社會的產物,所以“知人”既不能脫離社會現實條件,又要認識到人在階級社會中的階級屬性。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7]31,并且詳細說明“對于始終處于相互對立地位的壓迫者與被壓迫者而言,接連不斷的斗爭不論是隱藏還是公開,其每次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收到革命改造或政斗爭的各階級同歸于盡。”[7]31馬克思恩格斯認識到人類歷史就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并運用階級分析法分析了當時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通過這一方法的運用分析,提出了“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7]43重要論斷,通過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認知,馬克思恩格斯明確了觀點,“想要達到所求目標,就必然需要動用暴力推翻現存的社會制度,無產者雖然在這個革命中失去了一部分,但他們終將獲得整個世界。”[7]66所以,他們明確指出“《共產主義宣言》的任務,是宣告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必然滅亡”[7]8。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根據“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作了分析,將中國社會各階級劃分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以及游民無產者,并對上述階級進行詳細地分析,回答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一革命的首要問題,認為“革命的領導力量指的是工業無產階級,對于小資產、半無產階級是我們的朋友;對于中產階級,則一分為二看待,右翼可能成為敵人,反之左翼可能成為朋友,對于此,我們應時時警醒,而作為大地主、買辦、勾結帝國主義的官僚、軍閥等反動階級則為敵人,時刻提防。”[15]9由此可見,毛澤東運用階級分析法正確地認識區分了社會各階級。
因此,孟子所提出的“知人”不僅要在社會關系中認知了解他人,也要關注所知知人的階級屬性和社會地位,將階級分析法作為“知人”的方法內涵之一,正確認識所了解對象的地位和立場。所以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觀照孟子提出的“知人”的方法,就是要肯定人的主體性,在社會關系中把握他人關系,并運用階級分析法認識其社會地位和階級屬性。
三 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視域下探析“論世”
《康熙字典》中闡釋了“世”的三種含義:一是“三十年為一世”;二是“世謂同居天地之間界,謂各有彼此之別”;三是“世與生同”[16]77。朱熹將“論其世”解讀為“論其當世行事之跡也”[1]329。清代吳淇在《六朝選詩定論》中解釋了“世”含義,認為“‘世’字見于文有二義:從(縱)言之,曰世運,積時而成古;橫言之,曰世界,積人而成天下。我與古人不相及者,積時使然;然有相及者,古人之詩書在焉。古人有詩書,是古人懸以其人待知于我;我有誦讀,是我以其知逆于古人,是不得誦其詩,當尚論其人。然未可以我之世例之,蓋古人自有古人之世也。茍不論其世為何世,安知其人為何人乎?”[17]156焦循在《孟子正義》中分析了“論其世”的作用,認為“讀其書,猶恐未知古人之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次之,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也”[18]726。清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文德》篇中闡釋了論世作用,認為如果不了解古人所生活的社會條件,就不能妄議古人的言辭。魯迅也認為如果要論文章,最好是要顧及整篇文章,并且也要顧及作者,以及作者所處的社會狀態。國內有學者在分析孟子“知人論世”時認為孟子所說的世是指作者生活年代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背景以及時代精神。通過研究作者的身份,進一步判斷其行為,最終確定是否可以作為交友的對象[19]。也有學者提出“為了把握那種理解部分所依賴的整體意義,我們必須探究精神、意圖,所說作品被寫的時代和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條件,因此,文學的歷史、個人教育的歷史、作者生活的歷史,對于理解每一個別作品是必要的。”[20]12學術界普遍認為“論世”要充分考慮到作者的生活年代的社會歷史背景以及個人的生活情況,基本將這一方法運用于文學作品的解讀,認為文本應該置于時代背景與時代精神之中并加以互證,才能確定其可靠性。
通過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觀照孟子“論世”的方法,可以進一步了解“論世”的內涵,以及方法的運用。從矛盾分析法著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豐富“論世”的方法內涵。
孔子說“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1]78認知一個人不能只聽信其言論,還要考察其行為,而考察一個人的行為應該從社會現實及其生活的現實狀況。對于社會現實狀況的分析應該遵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批判了費爾巴哈、鮑威爾和施蒂納所代表的德國哲學,認為“從古至今人類經常按照自己想象中的標準或者上帝去構建自己的聯系,其中頭腦的產物并不受自身支配,作為創造者卻經常順從于自己的創造物,他們往往在臆想、幻想的創造物中日漸消極,我們需要將其從中解放出來。”[6]509馬克思通過對青年黑格爾派的批判,轉向唯物主義,形成了唯物史觀。
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作出了關于“社會存在”的表述,認為社會存在是“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釋意識的不同理論產物和形式。”[6]544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所以孟子所提出的“論世”要認識了解社會存在,并且對社會存在客觀認識,不能是主觀的臆斷。而要了解社會存在,就需要以物質生產為前提。馬克思認為“整個社會、政治以及精神生活受物質生產方式的制約。”[21]所以歷史人物的著作都是基于當時的社會大壞境,要理解歷史人物的所作所為,就要充分了解當時的社會存在。例如唐代杜甫沒有考取功名,浩然歸去,并作詩云“氣磨屈賈壘,目短曹劉墻。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而北宋的梅堯臣雖由于恩蔭得到官職,但并非是進士及第,所以倍感羞慚,詩云“慚予廷蔭人,安得結子韈,心雖羨名揚,才命甘汩沒。”同樣是考取功名不中,但二人心境卻不同,除了個人因素之外,還與唐宋兩代的不同社會風氣有關。唐代士子可以通過多種途徑成賢得名,而在宋代科舉主要是士人進身之階。因此,對他們詩作以及言行的認識就要了解當時的社會經濟現實和歷史情況,就要論世。因此“論世”就要從物質生產方式出發,考察他人當時所處的社會現實情況,通過對當時的社會生產形式的分析,從而更清晰地認識到政治、文化等社會現象,并在此基礎上了解他人的言行。
基于社會現實的考量,還要掌握矛盾分析法,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列寧認為“對于具體情況的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需要運用矛盾分析法來豐富孟子“論世”的方法內涵。毛澤東認為“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15]299他還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闡釋了矛盾的普遍性,認為“簡單的機械位移本身已包含矛盾,那么作為物質的更高級運動形式比如有機生命及其發展,就更包含矛盾。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間是它自身,同時又是別的東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體和過程本身中的不斷地自行產生并自行解決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來。同樣,我們已經看到,在思維的領域中我們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內部無限的認識能力和這種認識能力僅僅在外部受限制的而且認識上也受限制的各個人身上的實際存在這二者之間的矛盾,是在至少對我們來說實際上是無窮無盡的、連綿不斷的世代中解決的,是在無窮無盡的前進運動中解決的。”[22]126-127認識社會現實既要認識到矛盾的普遍性,也要認識到矛盾的特殊性,因此,毛澤東反復說到“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可以探求事物運動發展的原因及依據;認識矛盾的特殊性,則是在探求此事物不同于彼事物的本質區別,有助于辨別事物的不同,區分研究的領域。”[15]309所以運用矛盾特殊性來“論世”就要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毛澤東還提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論世”要認識到當時的社會背景,要找到事物的主要矛盾。毛澤東認為抓住主要矛盾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告訴我們的方法。列寧和斯大林在研究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總危機、蘇聯經濟的時候,也曾運用這種方法。”[15]322所以“論世”對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現實的認識應該抓住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規定了事物的性質,所以認識社會現實也需要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更好地理解當時的社會性質。綜上而言,孟子所提出的“論世”的方法內涵和具體應用應該置于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視域下,從社會存在著眼,掌握矛盾分析法,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四 小結
孟子在《萬章》篇中提出的“知人論世”的方法,主要是針對交友而言,而學術界大多將其運用于文學作品的解讀,但對其方法內涵和具體運用并沒有深入探討。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回望孟子的“知人論世”可以明晰其方法內涵。一切從實際出發是“知人論世”的方法論原則,從現實的人著眼“知人”的方法,就要尊重人的主體性,了解人的社會性和階級性,運用矛盾分析法認識社會現實,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也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豐富了“論世”的方法內涵。由此可見,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視域下探析孟子“知人論世”,可以使“知人論世”的方法內涵更加明晰,方法運用更加具體,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