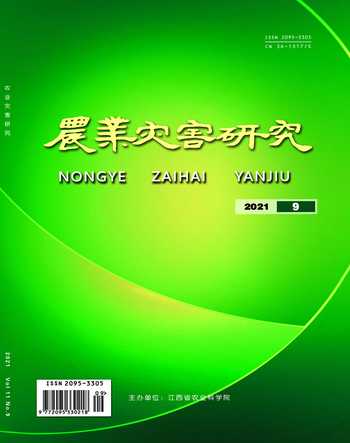小麥條銹病自然危害損失率研究報告
楊久濤 公義 張輝 郝國芳 司元明 國棟


摘要 為科學評估春季流行區小麥條銹病自然危害損失,明確科學植物保護措施在防災減災中的貢獻程度,制定科學防控策略,開展小麥條銹病自然損失率測定試驗。試驗測得發病嚴重度1~5級的自然危害損失率分別為10.34%、26.85%、40.79%、57.29、66.13%。結果表明:春季流行區小麥條銹病一般不會造成絕產,但嚴重威脅生產安全。
關鍵詞 春季流行區;小麥條銹病;自然危害;損失率
中圖分類號:S432.4+4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2095–3305(2021)09–0108–02
小麥條銹病是影響我國小麥安全生產的重要生物災害,發生范圍廣、流行頻率高、暴發性強,對小麥生產具有毀滅性危害[1-2]。大流行年份,病害向東發展至江蘇、安徽、河南、山東,向北擴散至華北麥區[3]。山東是小麥主產省,常年種植面積約400萬hm2,為小麥條銹病重要的春季流行區,繼2017年在全省大流行后,2020年又在全省16市103縣(市、區)流行發生。為進一步明確大田生產中小麥條銹病對小麥產量的影響,明確植物保護措施在防災減災中的貢獻程度,科學制定防控策略,開展了小麥條銹病自然損失率評測研究。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地點
試驗在山東省農業科學院作物研究所育種場進行,此育種場為該院作物研究所開展小麥等作物良種選育培育基地,種植總面積約66.64 hm2,周邊10 km以內無其他小麥種植田塊。
1.2 管理情況
試驗小麥品種濟麥22,為山東主栽品種[4]。將田塊平均分為面積為13.3 m2的種植小區。2019年10月10日進行種衣劑包衣處理后播種,11月15日進行化學防治雜草1次,保持肥水條件和田間長勢一致,一次性施足底肥,未追施肥。為觀察小麥不同品種抗病表現并測定自然危害損失率,除對照田分別在2020年4月21日和4月30日施藥預防外,未采取其他防治措施。
1.3 發病情況
條銹病全部為自然侵染、自然發病和自然傳播,未施加任何人工影響。4月21日起,DH320小區自然染病;4月28日起,發病中心DH320小區周邊各小區相繼擴展侵染;5月5日起,全田均發病。
小區間總體呈現階梯式感病發病狀態,同一小區發病相對一致;田間有輕微白粉病、葉銹病、蚜蟲、紋枯病;全田統一防治一次蚜蟲,生長期未施用殺菌劑。
1.4 調查方法
根據山東小麥生長發育進度,在5月20日病情基本停止發展時調查。每小區采用對角線五點取樣,每點固定調查10株,每株調查旗葉和倒二葉,根據病葉病斑面積占葉片總面積的百分率確定嚴重度。
嚴重度分為5級:1~5級病斑面積分別占葉片總面積的1%~5%、10%~20%、30%~40%、50%~60%、80%~100%,處于等級之間的取接近值(圖1)[5]。從200個種植小區內,選擇確定發病嚴重度等級比較一致的小區確定條銹病嚴重度等級。
1.5 測產及損失率計算方法
6月5日收割測產。分別測量千粒重、容重、小區產量,計算出每667 m2產量、每667 m2自然損失量以及自然損失率,防治區每667 m2產量為2個防治對照區的平均產量(表1)。
每667 m2自然損失量=防治對照區每667 m2產量—發病區產量。
自然損失率=(每667 m2自然損失量/防治區每667 m2產量)×100%。
2 結果與分析
2.1 各級病情對千粒重、容重、小區產量影響
小麥條銹病產量及自然損失率測定結果表明,防治區與對照區小麥千粒重、容重、小區產量有顯著差異。其千粒重、容重、小區產量逐級遞減,其中5級千粒重、容重、小區產量分別為29.1 g、0.278 kg/L、4.52 kg,分別是防治區的31.29%、66.67%、65.78%。
2.2 各級病情對產量的影響和自然損失率
小麥條銹病產量及自然損失率測定結果表明,防治區折合平均產為550.4 kg/667 m2,1~5級發病區有明顯減產,分別比對照區減產56.9 kg、147.8 kg、224.5 kg、315.3 kg、36.4 kg,發病嚴重度1~5級的自然損失率分別為10.34%、26.85%、40.79%、57.29、66.13%。
3 討論
3.1 條銹病是小麥生產的巨大威脅
試驗結果表明,3~4級自然危害損失率均在50%左右,5級高達66.13%,即使是1級的自然危害損失率也在10%以上,其自然損失率高值超過全國范圍內農作物病蟲5級自然損失率大多在15%~45%區間[6]。相關部門應高度重視,實施綜合治理,務必控制其擴展蔓延。
3.2 山東作為重要春季流行區,但未造成絕產
從實驗觀察,實驗測得5級的自然危害損失率為66.13%。沒有造成絕產的原因如下。
(1)春季流行區初侵染為小麥生長中后期,山東始發病一般在4月中下旬,小麥即將進入揚花期,病情擴展有一定過程,很難絕產。
(2)小麥穎殼、秸稈、麥芒的光合作用效率較高,有一定代償作用,在發病達到5級的情況下,仍能造就干物質積累形成一定產量[7]。
(3)后期氣溫升高,田間干燥、濕度小,不利于條銹病流行蔓延。
3.3 控制發病中心是防控條銹病的關鍵
從試驗觀察,試驗中小麥條銹病呈現明顯的周期性梯度發病狀態。該地塊發病中心顯癥后,7~10 d后周圍相繼染病,再7~10 d全田幾乎染病。因此,控制發病中心是防控小麥條銹病的關鍵舉措,生產中要把握好防控時間節點,必須堅持“帶藥偵查、打點保面”和“發現一點、防治一片”的防控策略[8]。
3.4 關于本試驗采用的分級標準
《農作物主要病蟲測報辦法》中的分級標準分為5%以下、5%、10%、25%、40%、65%、80%、100%等8級,其中級別較多,級距較亂,實際生產中不易判別。且80%時病葉已經枯黃,與100%時產量差距不顯著,再分等級已無實際意義。故本研究采用李復寧提出的5級分級標準。
3.5 關于本試驗有關說明
農作物田間病蟲害很少是單一發生的,往往是多種病蟲害同時發生,存在不同病蟲之間交叉重疊為害的現象[9]。本試驗重點關注了小麥條銹病單項病蟲對小麥產量造成的危害損失,鑒于該田塊紋枯病、白粉病、銹病、蚜蟲及雜草影響較小,其造成的損失未考慮在內。
小麥條銹病自然危害損失率受侵染時間、為害時長、溫濕度、品種特性等多種因素有關,不同區域、不同人員試驗結果可能不同,因此,本次實驗所得數據可供春季流行區參考。
參考文獻
[1] 馬占鴻.中國小麥條銹病研究與防控[J].植物保護學報,2018,45(1):1-6.
[2] 康振生.中國小麥條銹病及其綠色防控策略探索[C]//中國植物保護學會.綠色植保與鄉村振興——中國植物保護學會2018年學術年會論文集.中國植物保護學會,2018:1.
[3] 黃沖,姜玉英,李佩玲,等.2017年我國小麥條銹病流行特點及重發原因分析[J].植物保護,2018,44(2):162-166,183.
[4] 楊正釗,王梓豪,胡兆榮,等.小麥主栽品種濟麥22與良星99的基因組序列多態性比較分析[J].作物學報,2020,46 (12):1870-1883.
[5] 李復寧.小麥條銹病嚴重度分級標準的研究簡報[J].植物保護,1991(2):30.
[6] 李春廣,劉夢澤,湯金儀,等.農作物病蟲發生級別與自然危害損失率關系辨析[J].植物保護,2015,41(5):13-16.
[7] 李玉萍.不同倍性小麥穗部光合特性及相關基因功能研究[D].楊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7.
[8] 郭海鵬,范東晟,馮小軍,等.陜西省2020年小麥條銹病防控實踐與體會[J].中國植保導刊,2021,41(3):86-88.
[9] 李春廣,劉夢澤.農作物病蟲草危害損失評估與分解方法[J].中國植保導刊, 2013,33(12):51-56.
責任編輯:黃艷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