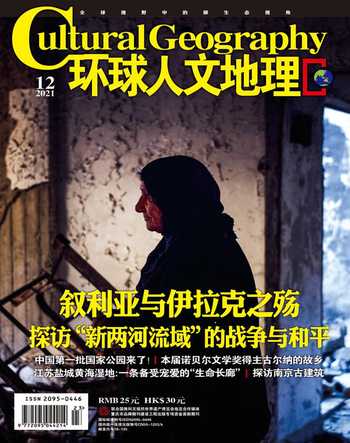唐代民族混血和復合型民族文化的出現
湯勤福
唐朝時期,胡漢混血造就了全新的民族觀念,消彌了傳統的民族偏見。
唐代民族間通婚一般是在自愿的基礎上進行,在這種情況下,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是沒有市場的。這種氛圍中誕生的混血兒從小就在“胡漢一家”的觀念薰陶下成長,新型的民族觀念就更深入到千家萬戶中。由于唐代皇帝本身就是混血兒,他們用早已習以為常的嶄新的民族觀念去制定民族政策,這對消除民族偏見與民族隔閡起到了一般民眾無法起到的極為重要的作用。
唐太宗曾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聯獨愛之如一”,這種漢胡貴賤如一的帝王言論在中國古代史上是極少的,正因如此,唐一代的民族觀念是嶄新的,而民族政策也較為開明。例如,允許京師內胡漢雜處;廣置羈糜府州,給予胡族在聚居區內享有較多自治權,向胡族聚居區推廣先進技術,傳播先進文化;蕃兵蕃將作為軍隊主力,胡酋及子弟宿衛龍廷,納大批胡族成員進入中央及州縣學校深造……這種開明的民族政策導致周邊胡族對唐中央的擁護,造就出唐代民族關系和睦的主旋律。
混血在改鑄民族構成的同時,也促成了唐代統治階級和階層的新變化。例如,唐朝皇帝是混血兒,因而他們不排斥其他混血兒或者胡族成員擔任朝廷職務。這就必然使唐統治階級和階層產生明顯變化。在唐朝,混血兒宰相有杜鴻漸、裴光庭、楊收等人;胡人宰相則有匈奴人劉崇望、鮮卑人長孫無忌、契丹人李光弼、西域人李抱、玉陀人李克用等。
除了文官,唐朝軍隊藩人將領尤多,建功立業的人也不少,《新唐書》還專為他們設立《蕃將列傳》。唐朝每次重大軍事行動、政治事件,幾乎都少不了蕃將蕃兵的參與,這可看出胡族在唐代統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朝從中央到地方有大量混血兒和胡族人擔任官員,唐朝權力的中央崛起了一股混血和胡族的政治力量,這對兩晉以來的舊有門閥勢力是個很大的沖擊。到唐代推行科舉制度,使原有的門閥統治基石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實際上,隨著時間推移,舊有的門閥家族也不得不從“血統”“門第”等狹隘的門閥觀念的泥坑中掙扎出來,投入到科舉制中去搏取名利。到唐末五代時期,就已經是“取士不問門第,婚姻不問閥閱”的時代了,門閥制度終于壽終正寢。
唐代民族混血帶來民族觀念的改變,這種觀念的改變又使大量混血兒或胡族人通過建功立業、科舉制等途徑進入到統治階級中去,改變了統治集團內部的成分,沖擊了舊的政治制度,給中國封建社會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混血還促進新的復合型文化的產生。
唐朝所產生的復合型文化,既不是大漢族主義色彩濃厚的文化,也不是排斥漢文化的胡族文化,而是指一種一掃上述兩種文化弊端,采漢胡文化的兼并包容的新型文化,它既保持了漢族傳統文化的精華的主導因素,又充分吸收胡族文化生機勃勃的內容,使胡漢文化互補共化,從而孕育出中華文化絢麗多姿、爭奇斗艷、恢宏燦爛的新面貌。
唐代保持漢族文化是不必多說的,這里僅舉胡族文化(包括外國文化)在中華大地流行的概況。例如,太宗所迷戀的馬球,玄宗所傾心的揭鼓,西域樂舞進入深宮禁苑,這僅是統治集團上層對胡族文化的認同。實際上,胡食胡衣早已散入尋常百姓之家,胡醫胡藥流行于城鄉各地,大食寶刀、中亞鎖子甲武裝了大唐曉騎,沉香木、于閡寶石裝禎著貴族住宅臥榻,西域幻戲演出于街黃巷里,西域油畫技法豐富了華夏畫苑,梵文、龜茲文、粟特文、突厥文、藏文、于聞文豐富了中華語言的寶庫,火化之類喪俗也為人熟識……駝鈴陣陣,運來了異域文化,千桅萬帆,傳去了大唐文明。正是這樣的文化交流,才產生了迥異于前代的大唐文化——一種異彩紛呈的新的復合型文化,一種在中國文化史上有著輝煌一頁的,值得中華民族驕傲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