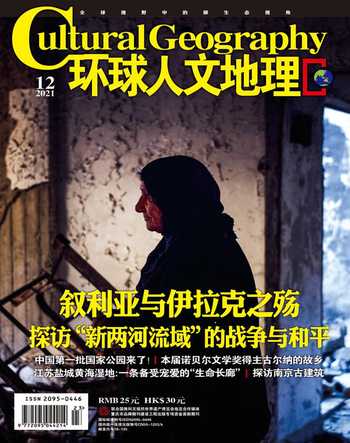食鹽的千年往事
火火
一個人可以不吃辣,也可以不吃酸、不吃甜,但絕不能不以咸味來點綴生活。因此,作為咸味最重要來源之一的食鹽,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小小的食鹽看上去平淡無奇,卻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在古代,鹽的重要性更是遠超人們的想象,它甚至是決定國家生死和富強的關鍵所在。
中國人很早便發現了鹽。在古代,人們稱自然鹽為“鹵”,《說文解字》中也記述“天生者稱鹵,煮成者為鹽”,即“鹵”經過加工后,才能被稱之為“鹽”。

至于鹽的發現,還有一個傳說。先秦古籍《世本》說,黃帝時期有個叫夙沙的諸侯,以海水煮鹵,煎成鹽。后來,關于夙沙的傳說越來越具有戲劇色彩:相傳有一天,夙沙從海里打了半罐水剛放到火上煮,這時一頭野豬從眼前飛奔而過,夙沙拔腿就追。等他扛著打死的野豬回來,罐里的水已經熬干了,底部留下一層白白的細末。夙沙用手指蘸了一點嘗嘗,又咸又鮮。他用烤熟的豬肉蘸著吃了起來,感覺味道很鮮美。這白白的細末便是鹽,而這位發現鹽的夙沙氏,也被后世尊為“鹽宗”。
也有觀點認為,“夙沙”或許并不是一個人名,更有可能是沿海一個部落的名稱,是這個部落掌握了煮鹽的技術。當然,遠古傳說的真實性難以考究,夙沙的故事也不排除是后世編撰加工。但根據考古發現,在中國,使用鹽的時間確實超過五千年,至少在黃帝時期,古人就已經掌握了用海水煮鹽的技術,經過上千年的發展后,煮鹽技術歷代相傳,不斷成熟。在北宋時期,著名詞人柳永就寫過一首《煮鹽歌》,提及當時的鹽民早出晚歸,前往深山中砍柴禾,然后堆積起來燒火,經過日夜不休的看守,最終得到潔白的食鹽。
海鹽的發展日益興旺。唐代之后,從中國北方的幽州,到南方的嶺南等沿海地區,都有海鹽生產,其中“兩浙鹽”和“兩淮鹽”最有名。
中國也是井鹽的發明地。川鹽作為中國井鹽的代表,在歷史的長河中扮演過不可或缺的角色。
戰國末年,秦國蜀郡太守李冰在今成都雙流地區開鑿了廣都鹽井,這是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的第一口鹽井。自此開始,一座座鹽場應運而生。歷史上,自貢鹽場是四川最重要的產鹽基地,民國初年,1.2萬多口鹽井遍布在自貢的土地上,密集程度堪稱全國第一。鹽井中最著名的當屬燊海井,深達1001.42米,是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的大井。
對古人而言,鹽的意義就像是冰箱對現代人的意義。鹽可以用于保存菜、肉、魚等食物,因為這些食物容易腐爛變質,不像谷物可以長期保存,但用鹽將其腌制成酸菜、火腿、咸魚,就可以保存數月甚至數年。

此外,鹽還催生了許多美食的誕生。例如,川菜中的水煮牛肉就出自于自貢鹽場。古時,自貢鹽場的牛用來拉車汲鹵,是鹽場的一大勞動力。明清時期,鹽場增多,所用的牛也增多,所以不斷有退役的牛供人們食用;于是,自貢出現了很多以牛肉為原料的美食,如水煮牛肉、火邊子牛肉、菊花牛肉火鍋、牛尾湯等,尤以水煮牛肉最為有名。而在湖北利川柏楊鎮,由于地下水中含有天然鹵水成分,且含鹽量恰到好處,因此用柏楊鹵水做出的豆腐,自然成形,香咸可口。
除了食用之外,鹽還有殺菌消毒、護齒、清潔皮膚、去污等作用。更重要的是,鹽富含人體所需的鈉元素,如果長期不吃鹽,容易導致肌肉痙攣、頭痛、無力、惡心等癥狀。所以,人類離不開鹽,在“五味”之中,鹽當之無愧排在首位。
既然鹽如此重要,所以歷史上許多朝代的統治者都對其進行了控制。
根據《周禮》記載,周朝就已設立了“鹽人”,專門管理鹽政。到了春秋時期,齊恒公手下的名相管仲第一次提出“官山海”的思想。官山海,亦稱“管山海”,山即礦場,海是用海水煮鹽。所以,“官山海”主張由官府專營鹽業、礦產。政策出臺后,齊國很快富了起來。與此同時,管仲還嚴格控制食鹽出口:和平時期,把鹽賣給地處內地、不產鹽或產鹽很少的諸侯國。這樣,齊國不但賺了別國的錢,還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不聽話就不給鹽吃,這也是齊國能成就霸業的重要原因。
漢武帝登基后,常年對外征戰,尤其是與匈奴的戰爭,更是曠日持久。行軍打仗,花錢如流水,國家財政吃緊。為了創收,漢武帝任命桑弘羊理財,并在其主持下“籠鹽鐵”,實行鹽、鐵、酒官府專營制度。
后來,安史之亂讓唐朝財政陷入困境,于是唐朝統治者也打起鹽的主意。當時,一位叫第五琦的“理財專家”創造了“榷鹽法”,即在產鹽的地方設鹽官,將鹽民編入亭戶,產的鹽由官府統一收購、銷售,禁止私賣。這比桑弘羊的措施更徹底,連鹽的生產環節都控制了。第五琦的方法讓唐朝統治者很滿意,因為僅僅一年,朝廷便增加了40萬貫收入。后來,朝廷進一步改革:將鹽稅加入鹽價,批發給商人,再由商人賣給普通消費者。搞批發的改革很成功,到了大歷年間,“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從此以后,食鹽專賣成了歷代封建統治者的重要財源,掌握了鹽業資源,就如同掌握了一座“金山”。
后來官鹽生意被一些鹽商壟斷,這導致鹽商暴富。乾隆六下江南,耗資巨大,很多費用都是由鹽商出的。當年有這樣的俗語:“一夜堆鹽造白塔,徽菜接駕乾隆帝。”可見鹽商財力之雄厚。
但是,食鹽帶來的豐厚利潤只是讓統治階層和鹽商獲利,尋常百姓想要吃鹽是難上加難。
《新唐書》如此評價第五琦的改革:“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本來在市面上花10文錢就能買一斗鹽,結果改革后,鹽的價格暴漲了十倍。唐德宗貞元年間,長安的一斤鹽是40文錢,合約每斗400文錢。很多老百姓吃不起鹽,甚至拿著數斗谷子,也只能換一斗鹽。
官府抬高鹽價,也就導致私鹽擁有了巨大市場。到了晚唐,鹽梟甚至成為影響社會治安的大問題。
由于唐朝統治者對私鹽打擊十分嚴厲,為了對抗官府緝捕,鹽梟不得不組織武裝自衛,一遇到災年,鹽梟就可能成為農民起義的中堅力量。晚唐起義軍領袖黃巢,祖上幾代都以販鹽為業。后來黃巢響應王仙芝起義,從鹽梟成了農民起義軍首領。五代十國中,吳越國的開國之君錢镠,前蜀開國之君王建,年輕時都販過私鹽。這些鹽梟,無疑都是唐朝的“掘墓人”。
由鹽引發的還有腐敗問題。由于鹽商十分富裕,鹽官自然少不了借商人之手中飽私囊。比如,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有位叫尤世拔的兩淮鹽政,剛上任就對鹽商理直氣壯地索賄。當時,鹽商必須憑“鹽引”這種經營許可證才能認購食鹽銷售,鹽引成了搶手貨,鹽官往往通過鹽商回扣的數額來分配鹽引。但尤世拔的前任太貪心,不僅吃了當年的回扣,還預售了下一年度的鹽引指標。所以,鹽商拒絕了尤世拔。氣急敗壞之下,尤世拔直接向乾隆皇帝實名舉報,由此引發了乾隆時期最大貪腐案之一的“兩淮鹽引案”。據查,從乾隆十一年開始,20年間,歷任鹽官共侵吞稅銀1000余萬兩。當時,清政府每年財政收入也才5000萬兩上下,幾任鹽官竟吞掉了國庫的五分之一。

鹽,本是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調味劑,鹽業專賣本可以維持鹽供應以及價格穩定。然而,古代的封建統治者卻以鹽來斂財,最終免不了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鹽,雖然被許多封建統治者當作一種斂財工具,但那并不是鹽的錯。實際上,鹽在歷史上有著積極的作用,甚至還推動了歷史文明的發展演變。
作為一種硬通貨,鹽曾經作為貨幣使用。例如我國古代的西南地區,就曾出現過鹽幣。成書于晚唐的《西南志》記載:“(當時的西南地區)鹽每顆約一兩二兩,有交易即以顆計之。”這是鹽被貨幣化的最直接記錄。顆鹽超越一般商品,而成為特殊的商品流通于市場,充當等價物和反映各種商品的價值。
當然,這里的顆鹽并不是我們印象中極其細微、一粒一粒的散鹽,而是未經煉制的粗鹽,其質量要比散鹽大得多。人們在交易的時候,以“顆”為單位,例如青菜價值多少顆鹽、蘿卜價值多少顆鹽。
這種貨幣化的食鹽,在后來的《馬可·波羅游記》中也有記載。馬克·波羅記錄的時間為元朝初年,比之幾百年前的唐朝,“鹽幣”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那時的鹽幣已經不再是粗糙的顆粒,而是先進行煮鹽,然后用模印將煮出的鹽制成塊,統一重量,上凸下平,置于熱磚上烤硬,最后還得蓋上官印。這樣制作出的鹽幣甚至與黃金掛鉤,尤為珍貴。
在一些交通不便、文化閉塞的地方,鹽還促進了當地的商品流通以及商業發展,并因此衍生出一條條鹽道。在西南地區,隱藏著眾多古時的鹽道,這些道路因鹽而興,也因鹽而繁盛。它們影響著巴蜀地區的社會與經濟格局,間接催生了民族間文化與商業的交融。雖然沒有茶葉的芬芳,沒有絲綢的華麗,但其歷史意義卻絲毫不亞于茶馬古道和絲綢之路,因此被很多學者稱為“中國西南的陸上大運河”。
地處云南的鹽津縣,就因為有專門的運鹽渡口而得名。秦開五尺道,漢代修南夷道,隋唐時又將這里的鹽道拓寬,修筑了石門古鹽道。自秦以來,這里就是中原文化、滇東文化與巴山文化相互交織之地,四川的鹽、云南的山貨和藥材都從鹽津的古渡口出入。控制著川滇門戶的石門關,被稱為川滇第一關,也是鹽津鹽道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今天的鹽津縣城,我們還能聽到來自鹽都自貢的方言,而鹽業也仍是鹽津商貿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過去運鹽的古渡口,被現代化的公路與橋梁相連接,但鹽業帶給鹽津的繁榮與輝煌,卻始終不變。
這就是鹽,看似毫不起眼,卻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它既能引發帝國政權動蕩,維系百姓民生,也能帶動商業貿易的繁榮,推動歷史的發展演變。今天,當你在生活中看到它、使用它時,是否會覺得神奇且有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