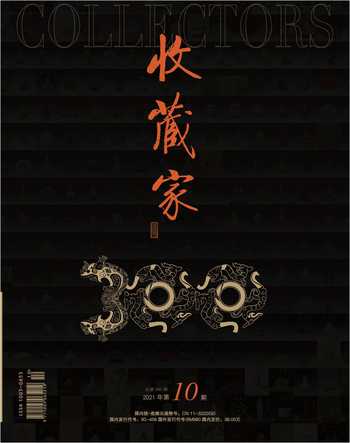李苦禪的收藏觀
李燕
先父李苦禪教授一生同國家民族的命運休戚與共,平生困厄環生,唯老來欣逢盛世。以如此人生經歷,囊中自不富裕,但其收藏文物之志始終未泯,且有一番自家見解。
先父曾對我說:“天下收藏文物古董有兩種藏法:一是富藏,二是窮藏。富藏好說,有的是錢,聽什么稀罕瞧什么貴就買什么,一般賣假古董的多半是騙這種藏主,騙多了倒把人家騙成了內行,人家花大錢練成了鑒賞家;窮藏就是不憑市價貴賤、不盲目人云亦云,全憑自己的學識和鑒賞眼力去尋找藏品,這種藏法不必多花錢也能收來好東西。”那么,什么樣的藏品是“好東西”呢?先父也有自家之見,他說:“稀世之珍、名人手跡、三代重器、名窯瓷器之類,是人家皇上大內和富貴藏家的東西,好則好矣,只是老百姓們難得有緣染指。我們說的有些好東西,它不但是文物——可珍可貴,更可令子孫萬代看著它油然而生愛國之心、立不忘國之志,雖其身價不及大內珍寶,但其生發之長遠意義當遠在大內珍寶之上,不可不留意收藏、整理之,可別任它們自生自滅,或塞在那里無人認識。”今僅舉數件老人所鐘愛藏品,或可說明李苦禪教授的收藏觀吧!
銅柱墨
赤金皮,凹鑄小篆四行,小篆文字俱填石綠色。文字內容是:“光緒十二年四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吳大、渾春副都統依克唐阿奉命會勘中俄邊界。既竣事,立此銅柱。銘曰:疆域有表國有維,此柱可立不可移。”
此墨產生的背景是,光緒十二年(1886年),著名金石家、書法家吳大主動要求放棄魚米之鄉的官不做,而要到荒蕪寒冷的黑龍江去任職。原因是他得知沙皇俄國一再命人偷偷將石界碑向南移,每次都趁夜色刨出界碑,用馬向南馱,當地百姓稱之為“馬馱碑”。吳大有愛國之心,聞此而怒火中燒。開明的光緒皇帝滿足了他的拳拳忠心,派往東北與俄國談判邊界問題。吳的副手則是依克唐阿——扎拉里氏,滿洲鑲黃旗人士。史載:“時俄人以議改伊犁條約有違言,烏里雅蘇臺參贊喜昌夙念依克唐阿諳戰術,請敕就近募獵戶守琿春……琿春(即渾春)故重鎮,其東南海參威,俄尤數窺伺,廷議設副都統鎮之,于是又改調琿春。十年,被命佐吉林軍事。十五年,擢黑龍江將軍。”此后他又為捍衛我東北領土而與入侵之日寇殊死搏戰,僅一戰即“以千人抗日軍數千,故依軍聲譽遠出諸軍之上”。他協同吳大在與俄談判勘定邊界之后,鑒于以往“馬馱碑”的教訓,二人特命人將界碑鑄成“定海神針”似的巨型銅柱栽于界碑處,上面鑄的如上銘文即是吳大所篆。但吳大對“虎狼之國”絕然放心不下,又命人依此柱原型縮小,作成一批“銅柱墨”傳布世間。果然,未過多久,英法聯軍侵入北京,北邊失防,俄兵遂將銅柱劫走,存于伯力(俄名哈巴羅夫斯克)博物館。但他們絕不會想到,這個侵略者的“恥辱柱”與被侵略者的“國恥銘”仍存于世間,沒有被中國人民忘記!然而,因歷經磨難,存世的“銅柱墨”太少了。據我所知,存者不多于一位數字,而我能見的僅兩錠而已。先父當年并非以重金購得此墨,但他十分珍視之,并不時取出來給我們當子女的看,說:“別忘國恥啊!”今日撫摩著此墨,老人音聲依如昨日。
《好大王碑》
此碑建立于414年,屹立于鴨綠江我國一側的吉安境內。此碑甚巨,系火山巖制成,鐫刻文字甚多,是研究中、朝、日三國古代關系史的不可或缺的珍貴史跡。但在國外,有少數“考古專家”曾對此碑文做出過不利于維護相互尊重領土主權完整之原則的片面解釋與“考據”。先父與同志者自然不能與之茍同,一直留意此碑之研究動態。可是,由于此碑發現甚晚(約在清末光緒初年左右),且碑體附著物很多,故極少好拓本,而且早拓且好的拓本能保持整幅(未裁裱裝冊)者尤為稀少。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竊據東三省時曾完全壟斷了對此碑的一切權力,不準中國人與朝鮮人染指。抗戰勝利后內戰又起,世人無暇顧及此碑。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始將《好大王碑》并周圍古跡——古高句麗王室成員墓群等列入重點保護文物,除少數經有關部門批準后拓成的資料之外,再無私人拓本,故此碑拓本益顯珍稀。對此碑,世間收藏古碑帖者多不重視以上內容,對其書法的特殊藝術價值也未給予應有的評介,甚而不列入“名碑法帖”之中。但先父自六十年代初就留意搜集此碑的拓本與有關資料。在我父子的努力之下,先后搜集到此碑整幅原拓本一套(四幅),系早期的“鍋煙子”拓本;裁裱成冊的原拓本一套(兩函四冊,其一有先父親筆題簽);民國初年石印縮小本(整幅)一件(有先父親題);民國初年石印中縮本(依裁裱本印制)兩冊,其一封面有先父親題,所題內容是:“近方研究好大王碑,巧遇縮小本,益感對校便利,幸甚幸甚!嘗謂北京為全國人文薈萃中心,茍致力諸學術,有所征求文獻資料,稍經常留心無不附合愿志者!辛丑(1961年)秋八月苦禪即識。”“字完整,尚少缺泐,或是初(“明”字點除)拓。此碑拓工多粗率,裱工多顛倒行誤等等,實則字行尚未甚殘泐也。燕兒購于廠肆。壬寅(1962年)正月禪記。”先父多次說:“我一輩子多少次要親自去吉安看看好大王碑。我不光喜愛它古拙豐厚的書法,更關心它的有關內容……好好研究它,不但對發揚書法藝術有利,也對國家領土疆域歷史的研究有利。可惜我沒機會出關(山海關)啊!”我一直記住先父的這個未竟之愿,于前年趁應邀赴渾江市講學之機,造訪了久已神交的“好大王碑”。我有幸被允許在大碑前留影,當時我覺得碑側不止我一個人在茲,還有在任何時候任何事情上都以“愛國至上”為做人準則的父親。(摘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