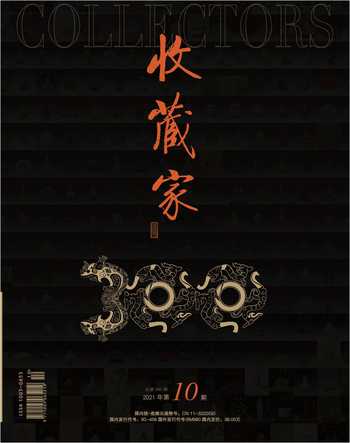小莽蒼蒼齋收藏紀事
陳烈


諺云:“五日京兆,宦海沉浮。”這是人們對舊時京城做官人的看法,意思是官場險惡。新中國誕生了,舊官場覆滅了,新體制建立了,用毛澤東的話說,不論擔任什么職務,“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并不是做官。田家英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一干便是十八個春秋,參與了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和重要決策。然而,他并不熱衷于仕進,最使田家英癡情的還是自小養成的酷愛讀書的習慣和解放后他一直堅持收藏清代學者墨跡的雅興。他不看中官位,不追逐名利,始終認為“書生”這詞對于他比較貼切,也符合意愿。田家英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之后,囑托梅行為他鐫刻的“京兆書生”印章,邊款便是他那年所作的一首詩:“十年京兆一書生,愛書愛字不愛名。一飯膏粱頗不薄,慚愧萬家百姓心。”詩中所說“愛書、愛字”便是上述他的兩個愛好。他把“書”和“字”都收藏在自己的書齋,并起了一個很有意義的齋名—“小莽蒼蒼齋”。關于齋名的含義以及田家英的收藏內容和藏品體系,筆者在《田家英與“小莽蒼蒼齋”》(刊于《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法書選集》)一文中已有較為充分的敘述。本文旨在記述一些史實,以便讀者對田家英的整個收藏過程有個大致的了解。
1949年北京解放,對于酷愛讀書的田家英,真是天賜良機。北京城專賣古舊書籍的店鋪比比皆是,除琉璃廠外,西單、東單、東安市場、前門、隆福寺都有,不但書多,價格也便宜。那時候清人字條、信札一類也歸在古舊書市。五十年代初,田家英常常在晚飯之后去琉璃廠逛舊書店,每次都抱著一捆書回來。好幾次,毛澤東有事找他,衛士還把電話打到琉璃廠。
田家英買書注意出版者,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出的書是他的首選,他認為這兩家的書水平較高。短短的幾年里,他買了《四部叢刊》《古今圖書集成》《萬有文庫》《中國近代史叢書》等一批叢書,許多都是從各書店、書攤兒一本本分散配齊的。此外,田家英還喜歡收集雜文一類的閑書,算下來也有十幾書架之多。他的閑暇時光,幾乎都沉浸在書中。他比較喜歡周作人的雜文,認為與他的其它作品相比,雜文寫得最好。聶紺弩的雜文集他也收集得相當齊全。他還多次提到簡又文、陸丹林編的《逸經》雜志。他從馬敘倫的《石屋余瀋》看到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史料,蔣介石作出“清黨”決定時,做會議記錄的竟是馬敘倫。在中央黨校審議《中國史稿》現代部分“抗日”一節,有人提到陳布雷為蔣介石起草的《文告》,田家英說,陳寫文章有他的特色,遂即將《文告》背誦了一遍。
田家英除自己購書外,還承擔為毛澤東置辦個人圖書室的重任。凡買來的書,首先看主席那里是否有。例如新中國成立初期,合作總社的鄧潔告訴田家英,他們從沒收敵偽的財產中發現一部乾隆武英殿本的《二十四史》,問田可有興趣?田家英馬上想到主席那里還沒有,便立即差人送去。從此這部毛澤東最為鐘愛的書籍,伴隨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歷程。最近線裝書局便是根據這部經毛澤東評點的史籍,影印出版了《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以后琉璃廠“松古堂”的老板又費盡心思為田家英搞到一部百衲本的《二十四史》,并親自送到中南海的新華門,算是圓了田家英渴求得到一部《二十四史》的夢。
田家英看書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并每每與現實情況相聯。他看班固的《賈誼傳》,以為《治安策》中歷陳的弊端,與中國當前狀況隱約相似。他贊同1954年中央撤銷六大中央局的建制,不贊同后來又形成的六大協作區,也有以史為鑒的因素。他認為秦始皇功不可沒,惜“焚書坑儒”遭世人咒罵。唐代建藩,擁兵自重,是自亂天下。歷代明君大都既能治國又能治家,兩者兼備不易,但非如此不可。他看《金瓶梅》,以為穢文文體不同于潔文,有可能是出自市井之手的偽文。
毛澤東一向欣賞田家英的讀書精神和“過目成誦”的天賦,曾戲言田家英將來的墓碑上篆以“讀書人之墓”最為貼切。毛澤東還喜歡和田家英閑聊歷史掌故、臧否歷史人物。他們的閑聊有時無所不包,從麻將牌中的“中、發、白”各代表什么意思到算命先生如何看手相等,每次都有新的題目。有一次田家英和孩子們散步,還專門到故宮筒子河請教了算命先生,孩子們笑父親迷信,田家英卻說,這里面有辯證法。
我們在已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中看到毛給田的信,其中有幾封是要田查找某歷史人物、某古詩詞的出處。如1964年12月,毛澤東讀《五代史》時,想起早年讀過的一首詩《三垂岡》,是講李克用父子的,但記不起作者的名字,于是在25日寫信請田家英幫助查出,并將全詩憑記憶寫下來附上。田家英告訴主席,該詩是清代詩人嚴遂成所作。夫人董邊很驚異,像這樣冷僻的人名,田家英怎么脫口而出?原來,田家英不但熟悉清代著名詩人的主要作品,而且旁及一些次要的作者,在他的“小莽蒼蒼齋”中,就收有嚴遂成親書的《吟稿》,上有嚴遂成描述李克用的另一首詩,詩中就有“老淚秋灑三垂岡”的詩句。田家英憑藉長期讀書積累的知識,每次都能及時地完成任務,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1958年,黨中央號召干部下放,有幾位省委書記希望田家英下放到他們那里,毛澤東說:“田家英我不能放,在這個問題上我是理論與實際不一致的。”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派田家英到東北各城市作調查。路過本溪時,東北局的柴樹藩請田家英到家中小敘,并特地拿出新近買到的《唐宋元明清畫冊》給田家英觀賞。柴說這本畫冊是從大帥府(張作霖)流散出來的,印制相當考究,足足花了他一千斤小米。田家英一邊欣賞一邊想到主席日理萬機,操勞過度,能在間歇中看看古代藝術作品,不失為一種調劑,一種休息。在田家英的提議下,柴樹藩割愛了。這是我們所知田家英最早的一次與收藏有關的活動,盡管收藏者并不是田本人,所收物品也還不能算是真正的文物。
田家英開始收集清代學者墨跡是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起因是他打算完成在延安馬列學院任近代史教員時就想撰寫一部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點指導的《清代通史》這一愿望。由于擔任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暫時將這個愿望埋藏在心底,企望有朝一日告老還鄉后能了卻自己年輕時的夙愿。他開始有計劃地購買清史方面的書籍,并分門別類地收集清代學者的墨跡,有條幅、楹聯、手卷、冊頁、手稿、書札等。經過經年不懈的努力,到1966年的上半年,“小莽蒼蒼齋”已經收有一千五百件藏品。如今我們翻閱這批墨跡,有如翻閱一部近代歷史的圖卷。這里有太平天國、甲午戰爭、義和團等重大歷史事件的史料,也有文字獄、評點《紅樓夢》的史料。田家英常對友人說,搞學問要有專長,收集這類東西也要隨學問而有所專注。現在許多人欣賞繪畫而不看重書法,更不看重年代較近的清人的字,倘不及早收集,不少作品就有散失、泯滅的危險。一次在東安市場的古舊書店,田家英遇到陳英、金嵐夫婦。金嵐與田家英曾同在延安陜北公學學習,老同學相見,十分親切。但看到他們夫妻花二百八十元買一幅徐悲鴻的“奔馬圖”,卻很不理解,事后還專門打去電話表示自己不贊同的意見。田家英對喜好收藏繪畫的辛冠潔也曾表示了同樣的看法,即文人書法不僅是難得的藝術,更能留下一些難得的史料。古人常說“畫是八重天,字是九重天”,可見字的品位遠在畫之上。辛冠潔說他后來也收集一些著名文人的字,就是受田家英的影響。
田家英除了在古舊書店、地攤上尋覓以外,有機會也從收藏者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藏品。趙翼的后人,著名收藏家趙藥農過世后,其家人有意將藏品轉讓,田家英因而獲得了一批高水平的藏品,其中有趙翼、張惠言、伊秉綬、孫星衍、黃景仁、劉逢祿、吳咨等幾十位著名學者的墨跡。田家英很看重趙藥農的這批藏品,認為其學術價值重于藝術價值。譬如清初詞人顧貞觀的《金縷曲》扇面,不僅因顧在當時已聲傳海外,與陳維崧、朱彝尊并稱“詞家三絕”,還在于該扇保留了三百年前顧貞觀以情真意切、催人淚下的情感寫的幾首《金縷曲》,感動了著名詩人納蘭性德,并通過其父的幫助,營救出因科場案受牽連,流放塞北長達二十二年的江南詩人吳兆騫的真實故事。趙藥農在這件扇面上寫下了長篇題跋,對整個事件做了翔實的考證。
田家英在尋覓清人墨跡中,對文人間往來的墨跡最為關注。他常以唐人劉禹錫的“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為例,說自古文人見面,所談多不會是些生活瑣事,文字往還也往往有學問政見在其中,他日研究歷史,從這些資料中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的確,在“小莽蒼蒼齋”的藏品中,常有記述文人之交的墨跡,例如孫星衍書與武億的篆書聯和武億致孫星衍的信,便是田家英在不同的時間、地點收集到的兩人交往的墨跡,其內容均與當時發生的某個歷史事件有關,值得一談。
孫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以一甲第二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充三通館校理。1789年翰林院散館,按規定,這一科入翰林院的應經考試后量才任用,或留館,或改官,考試專試詩賦。孫星衍在做《厲志賦》時引用了《史記》中的一個古體字,主考官和不識,指為錯字,孫星衍因此被列為二等,降職使用。武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進士。1791年,武億出任山東博山知縣。赴任前,他辭別好友孫星衍,并索書對聯“為藝亦云亢,許身一何愚”以為紀念,而孫星衍當時“匆匆不及應命”。第二年,上任只七個月的武億因得罪和而受劾罷官。當武億再次來京都時,孫星衍在自己的書齋“問字堂”中“始踐前諾”,為他書寫了拿手的玉箸體聯對,并用工整的隸書小字在跋中記錄事由的緣起。前后不到三年,孫、武二人同因莫須有的罪名得罪和,這也就使他倆的友誼平添了幾分“惺惺相惜”的色彩。
武億致孫星衍的信札寫于1795年10月11日。那時武億已免職多年,迫于生計,他在山東各地講學,后又在阮元幕編錄史志。武億在信中講述,因“中間為謬人更張,冗舛龐雜,慮為他日笑柄”,不得已,“未及終局,遂各散去”。這是武億結束游蕩生涯前寫給孫星衍的最后一封信。一個月后,他返回故里,就再也沒有離開偃師。四年后,和受到懲處,所有受和之害者,均已復官,朝廷乃召武億復職,但公文送達偃師時,武億已卒。
武億一生懷才不遇,憂郁早逝,孫星衍對此深感受悲痛。他撰寫《武億傳》,其言辭恭美,情真意切,對武億的人品、才華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張惠言篆書八言聯也是田家英十分看重的作品。張惠言,字皋文,江蘇武進人。嘉慶四年進士。張年輕時得朱賞識,特經皇帝恩準改授編修,充實錄館纂修官。張惠言于經學、小學、駢體文等均有專學,還是常州詞派的開創者。他和惲敬一起創立了陽湖派,專門提倡寫短小簡潔的散文。張惠言于不惑之年,染疾猝亡,十分可惜。他生前儼然是毗陵地區(今江蘇武進)文界領袖,這從他作品的邊跋中也可感受其氛圍。一人題字,九人側立,其中丁履恒、陸繼輅、劉逢祿都是享譽當時的經學、小學校勘學家,李述來、魏襄等亦是本地名賢,這些人統屬于毗陵地區的學者,他們往來之頻繁,由此可見一斑。
此外,像趙翼的詩軸、張燕昌的飛白對、黃景仁等的唱和詩軸、李慈銘的聯對、張廷濟臨虢叔旅鐘銘文軸等,都記述了文人之交的雅趣,也是“小莽蒼蒼齋”中最能體現齋主收藏意圖的作品。(摘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