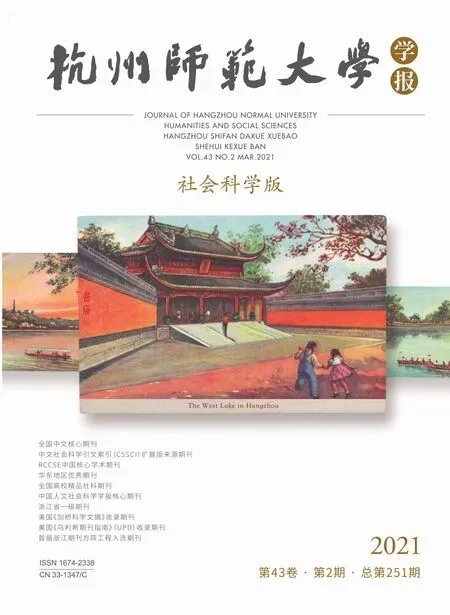《莊子·養生主》的在世修養與中道調節
賴錫三
(臺灣中山大學 中文系,臺灣 高雄 80424)
一、“養”“生”“主”之解題:以調中之道來定調養生大旨
《養生主》涉及《莊子》對“養生”的洞見,尤其“生”(養生)與“知”(是非)的關系,觸及“成心”(成見之心)所帶來的偏見,導致人我關系掉入“是非”爭端的相刃相靡,因而遠離了依存關系的善養之道。要善養吾生,則無所逃于處理自我與他人之間,或“礙”或“游”的辯證關系。亦即,如何在關系之間,轉化相刃相靡為相養相游?如何“礙而無礙”地豐饒彼此?這可能是“庖丁解牛”所要隱喻的養生之理。
我先從“養生主”三字作為解釋起點,再落實《養生主》的文脈肌理,來疏通生命之河的養生通道。首先,《養生主》的“生”不可狹隘化為身體的“身”,現代人的養生大多只聚焦在身體保健上,然而《養生主》卻是指向了全幅度的生命養護。《莊子》并不否認具體生命無法脫離身體的物性向度,但不應只停留在形體、物質的養形,因為養生還涉及了長養心性與精神。值得注意的是,“精神”這個概念在《莊子》中,本來就涉及了“形-氣-神”的身心連結,“氣”往上牽連到“神”,往下落實到“形”,而“形氣”連結著身體,“神氣”則牽連到心性。大不同于西方主流傳統的身心二元論(如笛卡兒),“形-氣-神”之間具有存有連續性的可轉化關系(1)有關《莊子》的形、精、氣、神等等觀念的存有連續性與工夫轉化義,可參見賴錫三《〈莊子〉“精”“氣”“神”的功夫和境界——身體的精神化與形上化之實現》,《莊子靈光的當代詮釋》,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125-172頁。。一言以蔽之,“養形”不離“養神”,“養神”不離“養形”,形神之間互相增益,通達“形神俱妙”,可謂善養吾生。
上古神話時代,容易相信有獨立于肉身之外的靈魂,甚至認為人有復數靈魂,“魂縈夢牽”經常被視為靈魂的脫體遠游;那么,《莊子》的“精神”是否也像靈魂般似乎可以獨存的靈體呢?據學者研究,《莊子》的“精神”概念應該是批判轉化了神話的靈魂思維,進而揭露出更深刻的智慧洞見(2)例如徐復觀和余英時皆指出,《莊子》已將先前帶有靈魂意味的精神,轉化為內在心性的精神。我也認為《莊子》的“精神”不宜再以“自我”的實體性概念去理解,因為《莊子》的“精神”屬于“我化故我在”的游乎無窮狀態,它正好是在破除恒固不變的自我之默認后,無法單位化、本質化的“恒變”“恒流”狀態,所謂“精神四達并流”之“游乎天地一氣”。此種解脫生死掛礙狀態要如何描述之,仍有待三思。。《莊子》書中再三出現轉“悅生惡死”為“死生一條”“死生一貫”之“縣解”智慧(3)有關《莊子》對“悅生惡死”的超越,以及“死生一條”的智慧,還有它對神話思維的“超克”,可參見賴錫三《〈莊子〉的死生一條、身體隱喻與氣化永續:以自然為家的安身立命》,《莊子的跨文化編織:自然、氣化、身體》,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9年,第231-273頁。。耐人尋味的是,《養生主》最后一段剛好談到“薪盡火傳”,而“火傳”到底隱喻著什么?是否暗示人身窮盡之后(薪盡),存在著不滅的靈魂(火)可以離體而持續留存呢(傳)?佛教東傳之后的魏晉時期,曾有過類似的爭論:“形”滅之后而“神”滅不滅?人類總是不免好奇肉身消亡之后,是否仍有不滅的靈魂存在,甚至輪轉不息?而《養生主》的最后段落(“帝之懸解”與“薪盡火傳”兩段),暗示了全面性的養生也將觸及安頓死亡這個終極向度。由于對“生”的內涵,有了不同的理解,有些人可能偏向形而下的保身,容易將養生簡單化為養形。另外有些人可能偏向尋找靈魂永生的形上追求,容易將養生極端化為養神。然而正如《莊子》的“形-氣-神”之間,具有存有連續與轉化關系,不管是極端的養神,還是簡化的養形,恐怕都沒有把握到“形神相即”的中道修養。
“養”具有長養與變化的生生意涵,消極講是“不中道夭折”,積極講能“盡其天年”。文化(culture)、農業(agriculture)等詞匯具有培育的隱喻意味,供我們可以思考:如何避免傷害而“不中道夭折”,如何讓生命的養分源源不絕,如何與環境形成良性互動而“盡其天年”。《老子》的“歸根曰靜”,《莊子》的“盡其天年而不中道夭折”,大抵帶有植物生長的自然隱喻性。但植物常因人為濫砍濫伐而失去該有的天然年壽。天地萬物本該有它的時命,有它物質性、身體性的基礎構成,自然有其該享的生命天年,但是許多人并沒有享盡天年,反而日消夜損而提早枯槁,終而失去生命力該有的豐饒歷程。如陶淵明所嘆:“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1](《歸去來辭并序》,PP.453-454)又如《齊物論》所悲:“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2](PP.51-56)
然而,如何讓生命力盡可能地生長?其所涉及的全面性存養、修養、保養,當不只是“個我式”的獨養其身,更得要涉及人我之間、物我之間的關系呼應與相互調節。一般誤認為道家的逍遙是純粹自我的逍遙,這還是太表淺的理解。回到植物的終其天年或中道夭折的隱喻來說,哪有一棵樹木能夠獨活于天地間?難道不需要土壤、陽光、水分……等等有形、無形的環境支撐與長養嗎?我們只要打開眼睛,觀察“夫物蕓蕓,各歸其根”的生命萬象,自然會發現相依相存的共生網絡,每一個體生命都生化在層層的關系網絡中,面對無數順逆之間的情境適應與環境造就。沒有所謂純粹的個體存在,凡是存在總是活在“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關系情境中。而這些與我“并生為一”的萬化生命,它們不只是獨立于我的外部存在,我所遭遇的人事物都會進入我生命的內部根柢,不斷促成我的生成變化。正如土壤情境中的各色成分,經由須根吸收成為植物根莖葉的成分。土壤不獨立于植物,植物不獨立于土壤。同樣道理,人的主體也離不開這種“內在待外性”的生成變化過程(4)任博克(Brook Ziporyn)以“內在待外性”一概念來詮釋《齊物論》,參見任博克《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以“是非之相待即其不相待”概念為中心的齊物論整解》,發表于上海華東師范大學主辦“《齊物論》學術研討會暨第二屆兩岸《莊子》哲學工作坊”,2019年8月31日—9月1日。。而內外交織地“并生為一”,指出了人生的長養與變化,必然將涉及人我(包括物我)關系的智慧回應,這便是本文繼承《逍遙游》的“關系性自由”,所要凸顯的“關系性修養”的在世養生之大旨。(5)將《逍遙游》解釋為在關系與阻礙之中的游刃過程,參見賴錫三《〈莊子〉的關系性自由與吊詭性修養——疏解〈逍遙游〉的“小大之辯”與“三無智慧”》,《道家的倫理關懷與養生哲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337-370頁。
至于《養生主》的“主”,則是打開養生之門的那把關鍵鑰匙。沒有養到“主”(最關鍵處),就可能盲修瞎練、錯用工夫,掉入《德充符》所反諷的“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忘了最不該遺忘的真正要點,卻對于不那么重要的事物斤斤計較、念念不忘,這不是顛倒錯置嗎?時下流行的養生健康食品琳瑯滿目,命理、瑜珈、星象之說大行其道,許多談話內容信口開河、言語不誠,但觀眾卻不在少數,反映出現代人的精神空洞與“淺碟”思維。(6)對于當代養生風潮的觀察與批判,參見何乏筆《養生的生命政治——由法語莊子研究談起》,收入何乏筆編《若莊子說法語》,臺北:臺大高研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2017年,第339-375頁;賴錫三《〈莊子〉的養生哲學、倫理政治與主體轉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015年第47期,第49-90頁。在古典時代,人總要立大志以引導心的方向。“心之所向,身之所往”,例如《孟子》說的“大體”“小體”之分,要認取良知良能做為修養的大體所在,哪怕“人之異于禽獸者”只是極微,卻是讓我們打開超越“食色性也”的生命道路。所以《孟子》注重“存心養性”“善養浩然之氣”,順此而有“盡心知性以知天”,步步走向天爵歷程的“超越”之道。古典時代的超越性追求,相信有超越個我生命的永恒向度可以被打開,并對此孜孜不倦而熱切追求。
然而歷經宗教除魅化的所謂現代人,古典時代的神圣性超越性追求,不免被視為邈遠迂闊。加上西方科學主義、資本主義在現代社會盛行,古典世界那種帶有形而上的性靈追求幾乎失靈。現代人逐漸滑向現代性的世俗化生活,從宗教一端(唯神)擺蕩到世俗一端(唯物)以后,許多人也就掉落到物欲橫流的沉淪處境,在及時行樂之后染上虛無主義。這種當代的去神圣化傾向,讓原來帶有超越性追求的“養神”,擺蕩到以“養形”為目標的衛生、保健、醫療,健康檢查變成最普遍的例行公事和管理身體的基本活動。然而對于《莊子》而言,不管是極端化的宗教性追求(純粹養神),還是片面化的世俗性追求(純粹養形),都沒有得到“緣督以為經”的養生中道。《莊子》的養生之“主”,在于“形神之間”的“能移”過程,也就是形神之間“相互轉化”的不偏不住之“中道”。這樣的中道養生,或許才更能涵蓋“保身、全生、養親、盡年”的全幅向度。
換言之,“中道”作為養生之“主”,可視為要避免或“偏滯養神”或“偏滯養形”的各一邊見。也可以說,想要避開或“偏滯內養”或“偏滯外養”的兩種極端。這里我們不免想到《莊子·達生》篇所描述的牧羊人智慧,那種“瞻前又顧后”的“不落兩端”的生活智慧。從中或許可以啟示“瞻內又顧外”(“瞻神又顧形”)的中道養生之吊詭智慧: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游,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倚門庭,亦何聞于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愿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后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后者也。”[2](P.649)
單豹的養內就是一種極端的往內修行,向往追求一種內心的精神寧靜與超脫,但由于他對主體構成的理解太過簡化,或以為單純透過離群索居的萬緣隔離,可以找到類似于本心具足、絕對適性的獨我本真之生活方式。但這種隔絕社會、遠離世間的“去關系化”之內修方式,在《莊子》看來或許因為減少人我交涉所帶來“陰陽之患”的干擾耗損,也就是稍稍降低自我矛盾與人我沖突,因而獲得“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的保身好處。但這種偏滯內養的一偏之修,卻遺忘了牧羊人“鞭其后者”的中道智慧,經常掉入了“瞻前不顧后”的片面化養生陷阱。例如,內修之人在追求超越性的時候,經常以為往內修養才是前往彼岸樂園的人生唯一目標,但在“勞神明以為一”的內向極端性追求的同時,卻遺忘了人的內在精神其實不能離開身體境遇,而身體境遇又不能離開“在世存有”。而在世境遇除了人和人的“共社會性”,也包含了人和萬物的“共自然性”。可以說,任何修養者的主體之構成,都不是孤零虛明的精神獨存。精神與肉身、肉身與他人、肉身與萬物,彼此環環相扣而共構了人與境遇的“并生為一”。人不可能脫離世界的因緣關系性,倘若想象有個絕對先在的內心本原做為修養的起點與終點,很容易遺忘處身境遇的豐富性與變化性。結果極端養神的內養方式,不是掉入了錯失關系性的豐富交織而導致主體的貧乏,不然就是掉入了低估處身境遇的復雜而成為了老虎食物的反諷處境。所謂“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未必一定要實際指為遇上山中餓虎,亦可視為情境變化不測的隱喻。任何自以為可以長存不壞的精神或靈魂,都可能被變化無常的“猛虎”給吞去。
餓虎之譬,也可再延伸為人生境遇中無所不在的潛藏傷害。所以當人們活在純粹想象的內在自我中,進行純凈化與純粹化的自我修養時,卻可能完全低估人際關系的錯綜復雜,而將自身放在一個極其天真的無知處境,結果更容易受到傷害。而相對于偏執內養的單豹,另一種極端則是偏執外求的張毅的處境,那大概是從內養的超越性祭壇走下來,走向世俗性的功名利祿之“外求”,其結果“高門、懸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這種汲汲追求眼前利益的“名尸”者,在競逐名利的過程中,經常行不在行、吃不在吃、睡不在睡,好像行尸走肉般被名利抽魂而去,心緒焦慮、勞精費神,搞得陰陽失調而難免中道夭折。
從否定辯證(不住兩端)的中道智慧來說,牧羊人的“鞭其后者”,正是為對治“瞻前不顧后”的偏失一端,因為不管是以內養精神為前瞻,還是以外求名聞利養為前瞻,當他們片面地以某一端為前導而一心追逐時,都可能錯失了主體“內外交織”的豐富性,以及“瞻前顧后”的辯證性。所謂“顧后”之譬喻,乃是深刻體認到“以一端救一端”的中道平衡智慧,以便能促使:前后、內外、形神,不要墮入二元斷裂的極端邊見。因此《莊子》的養生主智慧,大體可定調在“兩邊不住”地保持動態轉化的中道調節。下面我將進入《養生主》的文本脈絡,來嘗試追蹤并描繪這條養生中道。
二、“生也有涯”的河流隱喻
對“養”“生”“主”做了“中道調節”的基本定位以后,下面嘗試解讀“庖丁解牛”的養生隱喻。而在進行解讀庖丁解牛的“刀刃”隱喻之前,《養生主》的第一段開場白,也很具有關鍵性的引導作用,它所蘊含的河流隱喻(人生如河流),尤其值得再三推敲: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2](P.115)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這句話常被淺層地解讀為:人生時光有限而人類知識無邊際,用有限時間和無限知識相較量,將是追逐不完的不歸路!這樣的解讀相對空洞,甚至可能將讀者引到知識無用的“反知”方向去。(7)簡化地把《莊子》理解為反知識、反文化、反語言,將導致對《莊子》的根本性錯解。事實上,《莊子》書中反映出來的知識性、人文性、語文性,放在先秦時代甚至跨文化的世界性文本來觀察,它都可被視為最高水平的創造性知識之作。我嘗試重新闡釋如下:首先這句話出現兩個關鍵性對比,一是“生”與“知”的對比,二是“有涯”與“無涯”的對比。“涯”與“崖”相通,《秋水》更完整表達為“兩涘渚崖之間”,不管是水涯或是山崖,它們通常都是傍隨著流淌“兩涘渚崖之間”的河道中流。以具體意象來說,河流中道總是要在兩邊涯岸(或崖岸)“之間”,才能展開長河大流的綿延不絕。因此“生也有涯”可視為用河流來隱喻生命,喻示我們生命之流必然要在不同情境下的——時空關系、人我關系、物我關系——也就是在重重不同涯岸“之間”來流淌、沖刷,如此才能綿延出巨流河的風光(8)筆者對河流隱喻與涯岸關系的解讀,啟發自任博克(Brook Ziporyn)的英文翻譯:The flow of my life is always bound by its banks, but the activity of the understanding consciousness is constrained by no such limits. 見Brook Ziporyn, Zhuangzi: The Complete Writing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20, p. 29。。如果以河流喻人生,說“生命之流”就像河水流淌的意象,那么“涯”便可象征著水流兩岸的自然情境與人文局勢的關系性因緣。“涯”雖然顯示限制、界線等分際,它也是河流與涯岸在“彼/此”的關系互動下,所共同創造出來的風景姿態。任何河道中流必然要與左右兩邊的涯岸同時共在,才可能成為中道之流。由此可見,“生有涯”的生命河流,總要在具體的涯岸關系中,響應情境而因循漫游。相反地,“知也無涯”則象征著以自為尊,想要以“知”強行主宰自己的生命之流。因此“有涯隨無涯”便意味著,關系性的人我之間、物我之間的雙向互動,被簡化為“成心自用”的獨我單向道。而“殆”反映出由“知無涯”帶來過分自我中心的人格形態,很容易造成相刃相靡的荒蕪人生,甚至使得“生之流”干枯殆盡而中道夭折。(9)掉入《齊物論》所謂:“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見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1年,第56頁。
《養生主》“知無涯”的“知”有其特殊意義,最好透過《齊物論》來理解。《齊物論》所談的“知”,主要跟“成心”相關聯,而“知”又連結到“言”。簡單來說,《莊子》對于“知”的反省,關涉“心”“知”“言”三者的交相作用,并容易由此構筑“自我”的封閉化與中心化。“知”在《齊物論》的脈絡理解中,經常導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無窮爭執,結果讓人我關系落入了是非觀點的相刃相靡,并在爭執爭斗的過程中,像兩把刀彼此割折而兩敗俱傷。“知無涯”的自我中心化與封閉化,用上述河流與涯岸來隱喻,就像是一條橫沖直撞的泥石流,無視于河流兩邊涯岸的自然地勢、人文風土,所到之處總要沖垮兩邊涯岸。這種獨我橫流的心態,《秋水》篇曾以河水暴漲后的河伯形象,傳神地將其描述出來:“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2](P.561)河伯自以為“天下之美盡在己”的自大膨脹,造成河岸與河流的沖突與破壞,結果導致了“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的一片荒蕪。河伯這種“知無涯”的主體狀態,反映出類似于《老子》所謂“自是、自見、自明、自伐、自有功”一連串“以自為光”的夸大膨脹。可以說,《老子》跟《莊子》都敏銳意識到主體中心的自戀、擴張、主宰,容易無視于關系性情境的邊際(涯岸),從而帶來一連串人我沖突而互相折損。以“知”為中心的好辯爭勝(知勝)的人格形態,也可以用《天下》篇的惠施那種“自以為最賢”“說而不休”“以己異彼、無以自寧”的失養形象加以印證。(10)《天下》:“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遍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于德,強于物,其涂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于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見郭慶藩《莊子集釋》,第1112頁。在《莊子》文本中,莊周與惠施的交誼顯得極為獨特(莊周對這位老友,可說是極為疼惜與不舍),兩者所各自代表的思維形態也具有辯證關系,參見賴錫三《〈莊子〉藝術思維與惠施技術思維的兩種差異自然觀:與海德格的跨文化對話》,《莊子的跨文化編織:自然、氣化、身體》,第181-230頁。另可參見劉滄龍《身體、隱喻與轉化的力量:論莊子的兩種身體、兩種思維》,《清華學報》(新竹),2014年第2期,第185-213頁。
我上述嘗試不從一般只用“(時光)有限”解“有涯”的觀點,而是從河流與涯岸的關系隱喻,從非控制性、容納偶然性、肯定變化性來解釋“生也有涯”這個活的隱喻。如此活讀隱喻可呈現出如下圖像:生命原本像河流那般,隨著涯岸的變化而變化,它隨物婉轉、迂回蜿蜒、風姿綽約。然而人們那種“自事其心”“自以為知”的“成心”知見與習癖,卻經常硬以自我意志要去主導、要去強制“生之流”,“有為”地截彎取直、一意孤行,以至于破壞了生命河流“無為”地在兩邊涯岸的自然蜿蜒。可以說,“以有涯隨無涯”的結果,將使“無為”的生之流變,被“有為”的知之定見給強行取代,于是讓“生之流”原本隨境回應的抑揚頓挫、變化無常,簡化成同一性之“知”的有為計算下的預定人生。可見采取“河水”這一蜿蜒流轉的活隱喻,來活讀“有涯”“無涯”,也可以顯題化“知”的主宰性、控制性、擴張性等(權力)意志向度。
泰半學者在對《齊物論》的“知”進行分析時,大都著重認知觀點的對偶性來分析說明,較少注意“知”同時也是一種控制欲、主宰欲。可以說,“知”也是權力意志的欲望變形。如《人間世》“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2](P.135)就明白地將“知”與“爭”連結起來。而作為“爭之器”的“知”,也可以呼應“知無涯”的解讀,就是人們在堅持“自是非他”的我知我見的同時,其實也是自我意志的宣示與擴張。而這種自我意志的過度擴張,一者將導致回應情境而隨機蜿蜒的自然“生機”,處處受到裁抑甚至扼殺;二者將導致我和他人關系的交互主體性,變成了“相刃相靡”的折沖耗損。此二者,既不利于自我之生命的有機生長,也不利于人我交互關系的相互長養。(11)對“知”的解讀有相當多豐富的角度,如陳赟以人類在追逐無窮盡知識過程中容易陷入“無知之幕”的陷阱,而背后指向的仍然是基于人的意欲、謀慮的自我意志擴張與善惡是非判斷,放任“人”的機制而不循其“天”。而“緣督”“順中以為常”,聚焦于善與惡、刑與名之間的幾微虛空,實質上是人與天之間的“邊界體驗”。相關的詮釋脈絡可進一步參考陳赟《“緣督以為經”與“養生”的哲學——以〈莊子·養生主〉首章為中心》,《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從河流與涯岸的“生也有涯”之活隱喻來解讀,便意味著人必然要與他異的存在物共同存在于天地中,自然也要與各種矛盾沖突觀點共處于人間世。這種處境脈絡的涯岸際遇,看似限制了我們的自由,但也正是這些無所逃離的關系依傍,同時豐富了生命之流的千姿百態。正因為“生也有涯”,人不可能由獨我孤零的主體欲望控制一切,反而必須“依乎(情境中的)天理”(12)“天理”一詞語出《養生主》對庖丁之解牛過程的描述:“依乎天理,批大郄,導大窾,因其固然。”方萬全由技藝活動的哲學反思(從身體與外在處境所形成的協調關系)作解,指出此處的“天理”不是普遍的規律、原理,而是具體情境中的紋理、肌理,亦即下文所相因的“固然”。參見方萬全《莊子論技與道》,載劉笑敢主編《中國哲學與文化》第6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59-286頁。,來進行物我之間、人我之間的迂回婉轉之“兩行”運動,彼此調適又相互豐饒。正如長河巨流必須與兩岸地形地勢、風土人情產生有機對話,顧盼有情地融會兩岸風土人情于己身。如此一來,我的生命才能與他者生命,交織成相互美麗的風光,讓他者有機地匯入我的內在之中,從而豐饒了我的生命之流。反之亦然,我河亦是他河。換言之,河流之美,從來不單是一條孤零零的獨流河,而是伴隨兩岸的自然與人文風景,形成輻射流域而一起美麗。(13)敏銳的讀者或能意識到,個體生命之流與兩岸情勢的彼此調適又相互豐饒,此語將引向《莊子》對于差異共存的思考,一種朝向“我與你”互相調節、彼此豐富的論述潛能。對于《莊子》文獻中一、多問題的重新闡釋,參見賴錫三《先秦道家的自然觀:重建老、莊為一門具體、活力、差異的物化美學》,《莊子的跨文化編織:自然、氣化、身體》,第129-179頁。
在這樣的解讀之下,“養生主”的全幅度養護,便涉及關系性的全面回應與修養,關涉自我與他者的交互主體性之回應,以及自我的內在他者性之充盈。而欲達此效果,則必先將“心知固我”的主體封閉與控制,給予十字打開,轉而敞開于不斷變化的關系性情境。就像河流必須敞開于不斷改變的地理趨勢與人文景觀,如此才能“我中有他,他中有我”地兩相成全,長養出“可保身,可全生,可養親,可盡年”的生命巨河流域(14)王叔岷認為:“此言養生之義,忽及‘養親’,與上言‘保身’‘全生’,下言‘盡年’,皆不類。親當借為新……下文庖丁解牛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硎。正所謂‘養新’也。《達生》篇‘正平則與彼更生’,郭注:‘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亦可證此‘養新’之義。”參見王叔岷《莊子校詮》,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01-102頁。“養親”解為“養新”,義雖通達,亦可呼應“吐故納新”,故可備為一說。但直接釋為“養親”,亦可發揮“生有涯”的關系性之“在世養生”之義。《人間世》云:“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正合此處“養親”之義。。
總的來說,“生也有涯”指涉生命與情境的具體變化歷程,“知也無涯”則帶有強烈的有為控制性。“知”傾向焦點化,“生”傾向流動性。“知”帶有抽象性、理念性,容易流于遺忘身體與生活,進而遺忘了生活的具體性。其實生活的復雜性并不亞于知識的復雜性,生活有它的千姿百態的情境脈絡之變化豐富性。而知識為了進入非常精細的抽象世界,常常抽離具體,進入符號世界而聚焦在單一焦點上,避開了生命隨著時間與情境的流動變化性與不可確定性。如此,人們常在一偏知見的求知過程中變成知識孤島,在天羅地網的符號世界里遺忘了身體、社會、文化、自然等不同向度的關系性情境。于是,孤立的認知主體將很難進入“我河即他河”的關系性養生與相互性成全。一旦困在自我認知的封閉主體中,生命的回應能力將會流失,對他人的關懷能力也會流失,還有體驗生活的能力也會流失。一般人掉入“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即掉入了自我單行道,并在偏執的過程中導致相刃相靡,走向失養貧乏的耗損之路。由此可知,《莊子》并非簡單地批判知識是無用的,也不是要取消知識(15)司馬遷就曾評點莊周“其學無所不窺”,即此可見以反知、反智視莊周,是種膚淺見解。。其實知識本身也可以帶來生命的豐富,重點在于能否將“成心”轉為“虛心”,“虛而待物”地與變化處境保持柔軟的回應關系。對此有待下文進一步來加以闡述。
三、“緣督以為經”的清虛中流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這句話歷來有許多爭議,我嘗試把它跟前面的“知”連接起來解讀。首先,“為善無近名”,是指一般人的“為善”大都透過“知”來刻意為善,并預期想要得到善名。而相對于“為善近名”的“為善‘無’近名”,則是要透過“無”的修養智慧,亦即要以“不知”“無為”來調節為善求名這一端的有為偏執。同樣的,“為惡‘無’近刑”的“無”,也是要以“無為”來調節以有知有為而可能遭致惡刑的另一極端。換言之,以“知”為善的近名,和以“知”為惡的近刑,都不離一偏之知的成心偏執,而一般人很容易掉入這種兩端對立的戲劇性折騰與耗損。《老子》對這種自以為“知”的二分對裂有其獨到洞察:“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而且這種自是自見的有為之知,容易讓人掉入“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的“患得患失”(16)以上所述,參見《老子》第二章與第十三章:“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是以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一般人的刻意(有心)為善,通常預期著想要得寵(近名),而一般人的刻意(有心)反善(為惡),也通常容易遭辱(近刑)。對于《老子》來說,一個有修養的智者,不僅面對可能的遭辱(近刑)要保持敏覺(驚),面對可能的榮寵(近名)也一樣要保持敏覺(驚),正是這種不讓處身境遇掉入榮寵(近名)與遭辱(近刑)的任一極端化,才能獲得“寵辱若驚”的中道(不滯一端)智慧。對于老莊來說,得到他人的肯定是別人眼光下“他適”的實現,可是“他適”的“寵”(近名),本身同時隱含著“失寵”(近刑),“得與失”“寵與辱”正是一體之兩面。而當我們的生命價值全然寄托在他人眼光,那么寵(近名)與辱(近刑)的得與失,就會像蹺蹺板那樣,把我們帶入“患得患失”的兩端擺蕩。“寵辱若驚”的“驚”,正是要人們對“自是自見”的有為之“知”,對于人生在世的“名/刑”兩端,應當依循“緣督以為經”的清虛中道,以便保有敏覺的調節能力。
上述解讀,跟養生有何關系?因為“知”透過語言的二元對立,讓我們的一偏之見容易擺蕩在“此一是非,彼一是非”的斗爭中,人們很容易掉入善惡、美丑的二元論,所以“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是要透過“無”(或無為)的智慧(例如“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17)見郭慶藩《莊子集釋》,第307頁。對于“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任博克的英譯可資參考:Not doing, not being a corpse presiding over your good name; Not doing, not being a repository of plans and schemes; Not doing, not being the one in charge of what happens; Not doing, not being ruled by your own understanding. 見Brook Ziporyn,Zhuangzi: The Complete Writings, pp. 71-72。我翻譯如下,以呼應本文觀點:“要無為,不要變成求名的行尸走肉;要無為,不要變成計慮謀畫的貯藏庫;要無為,不要想全權管控任何發生的事物;要無為,不要變成一己知見的主宰者。”),來同時調節“為善近名”和“為惡近刑”這兩種各落一邊的成心偏執。對于《莊子》來說,這大概跟《齊物論》分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一偏知見”有關(18)“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見郭慶藩《莊子集釋》,第66頁。。而這種“無”的調節智慧,《養生主》更透過“緣督以為經”這個活隱喻來傳達。亦即要在錯綜復雜、枝枝節節的關系性背后,找到督脈中道。而因循著這條清虛無為的“調中”之道,以便能夠從刻意有心的“為善近名”與“為惡近刑”之兩端邊見,轉化為“為善‘無’近名,為善‘無’近刑”的無為“適中”之道。
順著前面“生也有涯”的河流隱喻,我們可再進一步來解讀“緣督以為經”。“督”解為督脈,有先秦身體觀的根據。而《莊子》以督脈的身體圖像來描述養生,重點乃在于督脈與身體場所關系的隱喻發揮。“緣督以為經”,可視為延續“生也有涯”(人生如河流與涯岸關系)的活隱喻。可以嘗試想象“督脈”本身(19)目前先秦也已考古發現多種不同的穴道經脈版本,參見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漢脈學之源流》,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00年。,就像是處于身體流域的“中脈”河道。就先秦時代對身體的經脈想象而言,人身中的督脈之中道巨流,其實是由眾多支脈支流的交織相匯,才能形成橫布全身氣化的身體景觀(20)參見李建民《評石田秀實著〈氣:流れる身體〉》,《新史學》,1994年第3期,第193-208頁;石田秀實《氣·流動的身體》,楊宇譯,臺北:武陵出版社,1996年。。督脈中流絕非獨立于這些錯綜復雜的支流之外而能獨成其大,反而必借由眾多差異支流的參與、會歸、延展,才能促使這條“緣督以為經”的精氣河流,既“不左不右”又“可左可右”地灌溉渾身流域。
王船山對“緣督以為經”的批注,可以參考:“奇經八脈,以任督主呼吸之息。……身前之中脈曰任,身后之中脈曰督。督者居靜,而不倚于左右,有脈之位而無形質者也。緣督者,以清微纖妙之氣循虛而行,止于所不可行,而行自順以適得其中。”[3](PP.30-31)根據督脈中流的“清虛”“無形”“循行”等特質,我們可以領會到河道中流的“中”,乃是處于不斷情境化的“適中”“調中”,而不是單一軌道的單點單線的靜態之“中”。若進一步再和“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的養生問題連結起來,所謂因循兩涯情境的“活動之中”或“調適之中”(21)《養生主》:“緣督以為經。”(郭注:順中以為常。)《達生》篇:“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后者而鞭之。”(成疏:鞭其后者,令其折中。)“為善近名”便是掉入一種極端(后者),“為惡近刑”也是掉入另一極端(后者),因此“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乃是一種以“無”的智慧來“鞭其后”,以令“生也有涯”常入“折中之流”。引文注疏參見郭慶藩《莊子集釋》,第117、645頁。,有何深意呢?由于督脈善處“環中”與“虛空”特性,故而喻示了“不偏左亦不偏右”“不執善亦不執惡”的義蘊。也因為督脈中道這種不偏不執,反而可容納或左或右的差異支流,也才能“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地同情各種情境,而敞開“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體諒人生。
如上所言,由于“生也有涯”的人生,必屬關系性的存在,因此人的所做所為,必然受到世俗眼光以肯定(近名)與否定(近刑)的價值進行規范與裁判,因此總要提醒“在世養生”的倫理回應之道,不要掉入“極端化”的世俗偏執。所謂世俗化偏執?也就是,一般人或者掉入為善以求善名的一極端,又或者掉入戲劇化對抗善行(為惡)而遭刑的另一極端。然對善于在世養生的智者,其行住坐臥雖無法全免他人眼光的善惡標簽,卻非常靈敏地意識到要避免自己言行,不自覺掉入他人眼光下的善(名)、惡(刑)兩極標簽。因為當你的某種行動被固定化為“善行善名”時,自我便可能束縛在“名”這一端。反之,當你的行動被固定化為“惡行惡名”時,自我便也可能被捆綁在“刑”那一端。然而對于《莊子》而言,“近名”與“近刑”的兩極化,都容易“固而不化”地遠離了“化而無常”(婉轉能移)的清虛督脈之中流(22)另可參見周策縱的觀點:“此二句必須依‘養生’主題和全篇推理來解釋,卻是不刊之論。照我前文分析,此篇開始是要指出兩種最基本、最重要足以妨害養生的事情,即在知識、道德追求兩方面都走極端。所以‘已而為知’是危殆,‘為善近名’‘為惡近刑’也是危殆,都足以傷生。他在這里只是要人不傷生。《駢拇》篇末說:‘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因為都可‘殘生損性’。”參見周策縱《〈莊子·養生主〉篇本義復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992年第2期,第19頁。。根據這樣解讀,《養生主》的“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也就間接相應于《老子》“不棄人”“不棄物”的“無棄”倫理學。[4](PP.109-144)即不以自己的“一偏知見”“一己信念”的道德正義感,去獨斷裁判自己和他人,而是讓“定名”“定刑”所圈定的善惡二分,獲得更大脈絡的寬諒與包容。這就像生命督脈“不偏左右”的中河大流,既不抗拒左右也不排斥大小,讓它們一一匯入督脈的中河巨流,一一獲得更新轉化的契機。從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共在于世”而豐富彼此的人生流域。
如果我們能找到這條“虛而中”的督脈,能因循“生也有涯”而回應關系、轉化關系,并以“無(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的中道智慧來與世俗處,那么我們也就可能達成“保身、全生、養親、盡年”的全幅養生。亦即不只形體的保養,也還可成全德性精神,甚至還可以養親。這個“養親”既可指親密性的倫理關系(血緣),也可以擴大而泛指與你發生親近關系的任何存在,亦即與你相親相近者皆能與你共生共養(23)任博克對“養親”的英文翻譯,正有推擴“親”之含意:“to nourish those near and dear to us”, 見Brook Ziporyn,Zhuangzi: The Complete Writings, p.29。。而這樣的所謂“盡年”,就不只是避免中道夭折,更要在有限生命中豐富自己、豐富他人,這才更是“盡年”的豐富意義。
四、庖丁解牛的依乎天理:無厚之刃的隱喻
如前所述,“善養生”意味著必然要面對著復雜的關系性,更考驗著我們的處世智慧。而“庖丁解牛”給了一個傳神寫意的故事隱喻,讓我們可以再進一步挖掘“緣督以為經”的妙義: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郄,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硎。雖然,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2](PP.117-124)
庖丁解牛可以做多種譬喻。例如技藝實踐中的“技進于道”(從技術通向藝術),可從書法、舞蹈等藝術實踐來觀察,許多藝術家從庖丁解牛的隱喻,獲得藝術實踐的覺察與啟發,體會技藝轉化的身體感知(體知)與工夫修養。當然庖丁解牛也可以脫離解牛技藝,成為多元意蘊的活隱喻,所謂“觸類旁通”,這只可被引譬聯類的牛,也可化身為名利之牛、政治之牛、語言之牛等多重關系隱喻的“見牛非牛”(24)“庖丁解牛”具有多重的可能解讀潛力,以技藝與身體活動作解者,如方萬全《莊子論技與道》、楊儒賓《技藝與道——道家的思考》、宋灝《逆轉回收與任讓狀態——從莊子與海德格批判當代性》、賴錫三《〈莊子〉身體技藝中的天理與物性》,這類研究大抵取徑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博藍尼(Michael Polanyi)、德雷福斯(Hubert L. Dreyfus)等作為對話資源;在法語莊子研究內部,如朱立安(Fran?ois Jullien)、畢來德(Jean Fran?ois Billeter)、葛浩南(Romain Graziani)、樂唯(Jean Levi)、布什亞(Jean Baudrillard)等人,則傾向將“牛體”解作無所逃于其中的名言權力結構,這使得《莊子》被看成是富含批判性的生存與政治隱喻文本。漢語學圈對“法語莊子學”的引進與討論,參見何乏筆主編的兩冊論文集《若莊子說法語》《跨文化漩渦中的莊子》。另外,在古典注疏傳統中,王夫之亦將“牛體”視為無從逃乎其外、只能游刃其中的人間世:“大名之所在,大刑之所嬰,大善大惡之爭,大險大阻存焉,皆大軱也。而非彼有必觸之險阻也,其中必有間矣。”參見王夫之《莊子通·莊子解》,臺北:里仁書局,1991年,第32頁。。而庖丁解牛正是活活隱喻了處身境遇,乃至人生實況,故而具有共法般的隱喻潛力,可以指向藝術原理,也可以是養生智慧。倘若你像文惠君那樣,處身在錯綜復雜的倫理關系、政治權力當中,那么這只錯綜復雜的“牛體網絡”,也就可能被領會成人生在世所遭遇的龐雜交錯之互動關系。
《莊子》透過“庖丁解牛”的故事,以庖丁與文惠君的一場虛擬對話,展現高度文學敘事的力量。在先秦時代“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層網中,知識階層是高高在上,并強調君子大人們要遠離庖廚。庖廚之地難登大雅之堂,是血腥、暴力、污穢之地。儒雅君子不忍看殺生場面,不愿聞動物哀嚎之聲,但《莊子》卻把儒家不喜談論的廚房內事變成養生之地。而庖丁這等卑微、平凡的人,竟成為智慧(道)的代言者,上位者文惠君反倒成了聆聽者、受教者。空間場景的生殺易位(廚房殺生之地變成養生之地)、故事人物的上下易位(庖丁成了傳道者,君王變成受教者),帶有很強的沖擊效果,展現高度的顛覆手法與反諷思維,可視為《莊子》運用文學的虛構想象,進行價值重估的批判轉化(25)耐人尋味的是,庖丁解牛設定的對話人物為文惠君(梁惠王),并將充滿殺機的屠宰獻祭之牛,轉為令梁惠王領悟養生之場景,不免令我們懷疑《莊子·養生主》的文本制作,似有和《孟子》文本對話之興味。因為《孟子》與梁惠王、齊宣王的對話,也涉及了“君子遠庖廚”“不忍牛之獻祭”之場景。換言之,我們可以想象《莊子》反轉了《孟子》的廚房,將道德不善的庖廚轉化為技藝美學(或力量美學)的“善哉”。《養生主》在描述庖丁解牛的過程,既出現了關鍵性的“依乎天理”(依循牛體的紋理),又出現“善”的系列修辭(如“善哉”“善刀”),然而《養生主》文本脈絡的“天理”與“善”,和《孟子》那種崇高的天理道德之善,差異性的對比張力不可謂不大。。
首先,它描述了庖丁的身體活動:“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如此勾畫身體的韻律,因為實踐技藝不能離開身體,而且活動中的肉身主體有一種力量韻律、運動節奏,正在活生生地流動著。庖丁解牛時的身體,就像舞蹈般的身體律動,而文惠君則身臨其境,親眼親身見識到庖丁充滿活力的流動身體。如果說,“手”“肩”“足”“膝”等動作描述,重點在于側寫身體操刀而入于牛體脈絡中的力量節奏;那么,“砉然”“向然”“騞然”的聲音描述,便在于身體、刀體、牛體的互相遇合又穿梭游離的美妙音韻。庖丁解牛的過程,我們感覺到的不是噪音而是樂韻律動,它幾乎被描述成一場力量美學的官能饗宴!這種藝術韻律感,隱含了美妙的流暢性(如流河蜿蜒有致的flow)(26)現今西方學者,經常將老莊這種無為(“忘”)的游刃有余,所能發揮最佳的活動效果,稱之為“flow”狀態。我建議可嘗試將“flow”翻譯成“行云流水”狀態,或者更精簡地譯為“游”之狀態。而任博克也將“生也有涯”之“生”譯為“the flow of my life”。,所以使用“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來譬喻庖丁解牛這場技藝盛宴。(27)“桑林”,為湯舞樂名;“經首”,為堯咸池樂章。而“中音”“合舞”“中會”,意指庖丁解牛的抑揚頓挫之婉轉過程,有其力量彈性曲線之協調韻律。若呼應上述河流隱喻,將“游刃”比喻成“河流”,那么庖丁游刃有余的善刀,也自然會呈現蜿蜒有致、曲徑幽通的游刃風景。于《孟子》,君子遠庖廚;于《莊子》,庖廚亦有道。
以主攝客、以主宰客,難逃相刃相靡的折損關系,因為當主體(庖丁)把意志(刀)強加在客體身上(牛)的時候,必然也會受到客體反作用力的抵抗,而在這種硬碰硬的過程中,不免人傷刀折,彼此耗損。“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代表將“技(術)”提升為“藝(道)”。而藝道特別重視協調與共鳴的游戲特質,協調共鳴對照于沖突矛盾,它不同于主體意志單方強加于客體,迫使客體淪為被宰制的對象。相反地,《莊子》透過中音與合舞來描述庖丁解牛,代表庖丁能讓原本緊張沖突的傷害性關系轉向彈性的游化關系,把“主客對立”轉化為“主客相游”。這便將藝術的美學意味被帶入,暗示我們藝術人生的“技進于道”之訊息。(28)于阻礙中“游”,在當前的《莊子》研究中,已經成為關鍵語,如何乏筆強調“形氣主體”的“曲通”,我強調“游化主體”的“即礙而游”,相關討論參見楊儒賓《游之主體》,《儒門內的莊子》,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173-224頁;楊儒賓、何乏筆、賴錫三《“何謂游之主體?”對話紀錄》,《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017年第1期,第91-107頁。
文惠君贊嘆:“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技”,乃專注于操刀意志的方法或技術。“道”,則是松開操刀技術而以身體性去感知并響應牛體內勢空間的情境脈絡。“道”進乎“技”,意味著能在“牛我之間”(或物我之間),進行著雙向的調節與轉化。庖丁解牛之“道”,是在牛與我的互動關系中,共同協作出來的“間隙之道”。就像前幾節的河流隱喻,巨河長流的“中道”,是河流與兩邊涯岸不斷進行力量交會所相互創造出的蜿蜒風景。由此可見,“道也,進乎技也”,須將“我”之意志“虛化”,使“權力主體”轉化為“游化主體”,而這種“游化主體”必須將他人、他物的看似外在性,轉化到我的內身主體中,如此才能雙游、雙化于人我之間、物我之間。(29)以工夫論的角度來理解,如柯小剛的解讀,“庖丁解牛”的“以無厚入有間”可能是最基本的“游之主體”寓言,而對于莊子式的“氣化—物化—兩行主體”來說,兼體而無累的“游之于間”或許會是關鍵的活動機制,并能指向一種工夫論的美學進路的政治哲學。參考柯小剛《〈莊子〉與主體轉化的工夫論——從畢來德、楊儒賓、何乏筆的跨文化對話出發》,《長白學刊》,2019年第2期。
接下來,庖丁進一步描述“技進于道”的心路歷程。“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全牛者”,一開始牛就像陌生的龐然大物兀立在前,我也不知要從何處下刀。那看不透的牛體就像迷宮,刀刃隨意進入,牛便頑強反抗,搞得我精疲力竭而狼狽不堪。對一個生手而言,面對牛體時,就像進入一塊完全陌異的荊棘險地,亂入即傷。這種“所見無非全牛”的主/客隔礙狀態,心/手之間、手/刀之間、刀/牛之間處處充滿看不見的膈膜與距離,讓人無法跨越。龐然大物的牛與我的鋒利刀刃相對撞,兩敗俱傷,刀折手傷,人仰牛翻。最后,我精疲力竭,牛血肉模糊。這真是一場慘烈的暴力進行曲,哪里有“合《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的美妙韻律。換言之,生手在解牛的初期,眼下只見全然牛體的外在表象,既未能“牛我一體”地感知牛體內里結構,也未能“手刀一如”地游刃操刀。一方面技術生疏,另一方面未能體物。勉強以“我”強操刀而硬解牛,如此暴力宰物的結果,便落得了“族庖月更刀,折也”的“中道夭折”之后果。
接著“三年之后”,生手庖丁經歷不斷揣摩與嘗試,刀牛之間、手刀之間、心手之間從對立性的隔礙與沖突,逐步轉化為相互調適的新互動模式。關系慢慢產生變化,逐漸進入“由生入熟”的第二階段。此時,牛不再是龐然大物的陌異客體,代表你開始從純粹的外物陌異感,慢慢體會牛的內勢理路,身體跟刀也開始慢慢協調,身體運動感也開始在牛的內勢空間中摸到理路。先前手刀在某些地方似乎過不去,但現在微轉個角度也就能順手,而對于力道的拿捏也開始有了較細微的分寸感。所謂“未嘗見全牛也”,大概是指庖丁不再單純依憑外部視覺,而開始有了身體感的內部覺知,進到物我之間的力量交涉,即當手刀進入牛體時逐漸有了“內在待外性”的交涉感,此時庖丁的身體慢慢以隱默之知的方式,漸漸揣摩快慢之間的律動。牛從純然的“我之外在性”轉化為“我之內在待外性”,內外之間已經透過身體感的互動而有了連結,并重新建立“心—手—刀—牛”的內部關系性。可見“未嘗見全牛”代表著身體與牛體發生了一定程度的韻律共感,只是這個共感通道,尚未熟透。換言之,此時的“我”逐漸對“物”(牛)產生更具肌理式的領會,物我之間從原先的單向關系,開始進入雙向關系的“來應”與揣摩。
身體經驗性有種特質,當我們對它熟悉到相當程度,甚至“由熟而忘”時,便無需任何思考而能任其自然運行。此時,身體會自然而然如行云流水(flow)般地自發運作。如音樂家感覺不是自己在彈琴,琴聲就這么自然而然流動出來。如作家談到頂峰的創作經驗會說“下筆有如神”,不是“我”之主體在書寫而恍如神之手所創作。這都是類似“忘我”的flow(神游)經驗。同樣地,當庖丁進入“官知止而神欲行”的“神行”狀態時,就是進入“技進于道”“由熟而忘”的flow(神行流動)。這時候客體會轉介到主體里,例如刀變成你的手的延伸,而手刀再進入牛體內部深處后,牛體也會轉介成你的身體感,身體感因循牛體天理,而自然游行其間,此乃終而領會“方今之時,官知止而神欲行”。不知什么時候開始,已經不再只用目視而是任隨神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由于吾人眼睛總是容易停留在對象的表象上,很難揣摩或想象內部狀態。官與知“止于所當止”的時候,有一種“神乎其技”(神遇神行)的現象發生了。(30)這種“神行”狀態,完全是在肉身場所中所發生,而不是指向任何超越性或形上性的純意識或純精神。而且只有當肉身主體和牛體脈絡,產生了力量交涉的時間性過程,雙方都獲得了轉化,才有所謂“神行”的現象。用宋灝的身體現象學、轉化現象學之詮釋角度,“神行”只能發生在庖丁“獻身于牛體情境世界”之時間性歷程中,其中完全無涉任何形上世界。參見宋灝《逆轉與收回:〈莊子〉做為一種運動試驗場域》,《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012年第3期。
由此可以說,“神”是身體感的特殊狀態,“官”是想要自我作主的官能習癖,“知”則是想要自我操控的意志沖動,當身(官)與心(知)這兩種長久以來的“有為”習性,逐漸被轉化進而忘懷時,一種“神遇神行”的身體潛能將被打開來。這時的每一舉手投足,能與物處在美妙的合音中舞之狀態。換言之,“目視”“官知”是指以“我”視物、以“我”宰物的單向活動,經由“由生而熟”“由熟而忘”的“技進乎道”的體知過程,整個身體感已將“身心關系(刀手關系)”、“物我關系(牛我關系)”,轉化為力量協作時的“適而忘,忘而適”狀態。《莊子》向來喜歡運用“神”這一概念來描述這種狀態,例如庖丁的“官知止而神欲行”、承蜩丈人的“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渡口津人的“操舟若神”、梓慶樂師的“器之所以疑神”。總之,這種身心互滲、物我往來的身體感,是相互轉化的內在時間性狀態,由于它不再處于“以我操物”的“我思”狀態,而是“因循于物”“物我相游”的“我化”狀態,故以“神行”擬狀之。庖丁解牛的“神”不是有一獨立靈魂的神,而是經過技藝的不斷熟悉與習練,由生到熟到忘,使身體的創造性潛能被展現出來。因此,所謂“神行”并沒有離開身體,而是一種“以天合天”的身體活力狀態(31)“以天合天”是《莊子》用來描述技藝高峰經驗的另一重要用詞:“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后成見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見郭慶藩《莊子集釋》,第658-659頁。另外,有關《莊子》技藝經驗的“以天合天”之詳細解讀,參見賴錫三《天人之間與養生達生:〈莊子〉身體技藝中的天理與物性》,《莊子的倫理關懷與養生哲學》,第419-448頁。。
接著庖丁告知文惠君,提到極為關鍵的要領:“依乎天理,批大郄,導大窾,因其固然。”依(依天理)、因(因乎勢)、循(循境遇)、順(順變化),都是道家的重要觀念。而“天理”這個概念,第一次就出現在《莊子》,它無涉于任何抽象的形上原理或形上實體,反而完全具體化在當下情境脈絡的物之紋理中。例如庖丁解牛時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便是意味著庖丁能因循牛體不同部位的內在結構而行。而“批大郄”“導大窾”的批導(32)又據王叔岷之引證,“郄”(或卻)借為“隙”,“窾”乃“空”也。參見王叔岷《莊子校詮》,第106-107頁。由此可再進一解,由于神庖能“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故能處處發現牛體內里的“間隙”與“空隙”,因此這把“無厚之刃”乃能避開刀與牛的“相刃相靡”,甚至“游刃有余”地“以無厚入有間”來相養相化。,絕非由強力意志主宰而強行操刀的任意切割,而是順著牛體固有的內在紋理,“自然”使其批解與化導。龐然的牛體自有它內在的肌理世界,如果不去理解其內在結構與紋理,自以為可強行支配,自以為可硬生砍劈,那么你這把刀也就注定要遍體鱗傷,三個月或一年,便要更換了。
上述“依乎天理”的批導場面,以及“技進乎道”的棒喝話語,不正充滿著處世哲學的隱喻嗎?如何善養在世之刀?涉及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中,你必須尊重情境天理、響應固有脈絡。你的主體要懂得柔軟,要轉化過度自我中心的剛強堅硬,使人我之間的關系保持彈性空間。就像舞蹈之天理,有人進就要有人退,一進一退之間,才能共成曼妙舞步,否則只會相互碰撞而不成“舞道”。又如“生也有涯”的水流與涯岸的活隱喻,但凡存在必然是與世界有關系性連結的存在,既然是關系性的存在,世界就不會只以我們為中心而運轉,只有懂得敞開與柔軟,才足以回應千變萬化的關系情境,尊重物之理、社會之理、文化之理、世俗之理,才能“批大郄,導大窾”地找到各種紋理間隙。有了間隙你就能夠批刀游行而過,能夠順著骨節中空順道而去。所以“窾”“郄”,代表了間隙或余地,也就是事物交接處,所產生的微妙空隙,那里藏著雙方相互回轉的圓轉之道,順著那個自然而有的紋理與空隙,方能“游刃必有余地”,否則可能會將自己帶向渾沌不明的沖撞狀況而遍體鱗傷。懂得“依乎天理”而“因其固然”的庖丁,才能“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就連骨肉相連的脆弱處都不輕易觸碰,更何況去砍折那些生硬大塊的牛骨呢?
庖丁繼續跟文惠君說,最差的是“族庖月更刀,折也”的情況(大約呼應所謂“所見無非全牛”的生手狀況),幾乎每個月就要換一把刀,這是因為刀經常砍折牛骨的關系,也可說是暴力血腥的人牛關系。而稍有經驗者則是“良庖歲更刀,割也”的情況(大約呼應所謂“未嘗見全牛”的由生入熟狀態),也大概要一年換一把刀,這是因為刀經常不免于切割,不免仍有相互刃靡的耗損現象。最佳的情況則是“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大約呼應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的由熟而忘狀態),不再用“砍”與“割”的方式,而是以“依”“因”“批”“導”的“化解”的方式來“解牛”。所以這個“解”很精微,不只代表輕輕解開,更是在變動的雙向互動關系中,產生游戲般的和諧與協調。知道哪些情境可以順暢,哪些情境要緩慢細致,必須依循著牛體不同局勢之本然天理,給予差異化的精微回應。“彼節者有間”,所有的關系網絡中都有間隙存在。“而刀刃者無厚”,關鍵在于你這把刀要是一把幾乎沒有厚度的刀。這又如何可能呢?這大概是在進一步隱喻:空隙的大小其實是由刀的厚薄所決定,而刀就代表人的自我主體狀態。當你這把刀能薄,空隙就相對變大;當你這把刀厚,越想宰制事物,事物的抵抗力就可能越大,相對空隙就變小,甚至沒有了空隙。你若是無厚之刃,便可處處找到“無厚入有間”的大郄與大窾,你遭遇的所有關系都可重新轉化。無我的人與他人會較少沖突,而且較能夠產生轉化余地,“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從容之間,就有了余裕與寬心。這是看似平常卻不容易做到的道理。
如何修養刃之無厚?如何將自我有為轉化為無我因循?無厚之刃隱喻著游化主體,“游化”表示主體跟他人的關系之間的空隙開始有了彈性,當游化的空間不斷地在運動,原本緊迫僵化的節奏與張力都有所改變而產生余地,機會總在余地空隙間,悄然生長出來。總言之,“刀刃無厚”,正是“技進乎道”的最關鍵,將“自是、自見、自伐、自有功”的“自我中心”的鋒芒厚刃,轉化為能因循物之天理、因順物之固然的“無厚游刃”,將“自我”有為,轉化為“忘我”的“為無為”。
盡管由生到熟,由熟到透,由透到忘,最后進入游刃有余的狀態,但這不代表什么時候都順暢無礙。人生有些時刻與情境,仍然不時出現“每至于族”的困頓(33)《養生主》:“每至于族。”(郭注:交錯聚結為族。)此指人際關系、物我關系的糾纏、糾結處境,稍一不慎,將物我刃靡,愈解愈傷。參見郭慶藩《莊子集釋》,第123頁。。這個“族”就像是錯綜復雜的十字路口,或者讓人生處境再度渾沌不明的難關,這時好的庖丁一定要“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這里同時用了“怵、戒、止、遲”四字,代表了非常謹慎且細膩地對待每個當下的危地。這是一個好庖丁的修養,當新的難關出現或碰到最難處境時,都必須“見其難為”。宛若第一次遭遇般地“怵然為戒”,要謹慎地應對而“動刀甚微”。速度變慢而動作更精微,然后才能“謋然已解”地度過難關,讓難關“如土委地”地松解開來。這個時候你才能“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稍微放松下來,“為之躊躇滿志”地感到難關化解,生命又柳暗花明了。最后,還要“善刀而藏之”地把刀鋒回藏,像寫毛筆字一樣,筆勢在走到最后,要有逆轉收回的回鋒修養(34)《養生主》:“善刀而藏之。”(郭注:拭刀而弢之也。)善保刀刃而無所用之,不宜時時處在解牛狀態,宜有“無所用之”的休歇自在時刻,尤其在化解“每至于族”的難為事物之后,更宜韜光養晦地“藏鋒”于無用之地。參見郭慶藩《莊子集釋》,第124頁。。
文惠君聽完了后,贊嘆說:“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你剛說的一席話,解開了我的困惑,讓我真正得到了養生的領悟。然而《養生主》似乎沒有進一步告訴我們,文惠君所領悟的是什么?但我們現在可以揣想:文惠君是位君王,不太可能親自解牛,而在開解牛體這件具體行為之外,那他領悟到的又會是什么?從《養生主》的前后文脈讀來,文惠君之所以能觸類旁通而領悟養生主旨,正因為文惠君也是時時刻刻遭遇他自己的人生“大牛”,面對各式各樣的政治權力、倫理關系的矛盾與沖突,因而能將牛體迷宮和人際關系的迷宮給引譬聯類起來。如此一來,庖丁的解牛無疑變成了一項可以啟悟人生的行動公案或行動藝術。身處在錯綜復雜的關系情境中,如何把相刃相靡的惡性關系,轉化為游刃有余的游化關系,如何養出一把無厚之刃而依乎天理與因其固然,讓人際的糾結關系轉向處處有間隙的游戲關系,恐怕這才是文惠君大有感慨而深有所悟之處。讓我們的生命得以與他人一起游化,變得更有智慧,變得更幽默,這才是雙養雙化的“緣督以為經”之處世中道。而當關系由糾結變為游化時,進而能推動親密性的原初倫理的發生,也就是脫去僵化的單向為善,而對人我的生命處境敏感化,并擁有細膩的回應能力,讓彼此的關系因為相互轉化而變得更加豐富,這可能是文惠君對在世養生與倫理轉化的重要領悟。(35)從游化而能通達自由的角度而言,個體自由的獲得,不是一個孤立式的自我實踐過程,而是在與天地萬物自發而和諧的協同運作與共同創生的共鳴性中,得以彰顯自身,可參考陳赟《“居間體驗”與人的自由》,《人文雜志》,2020年第7期。
五、養生余味:安于天命、走出樊中、懸解死亡
上述透過“關系中的養生”來解讀養生之主,說明養生終可通達“保身,全生,養親,盡年”的身心贍養、關系成全、倫理轉化、生命豐富的全幅內涵。而《養生主》在庖丁解牛之后,其它的三段小文獻,或許也可嘗試往這個方向來解讀:
(一)安于天命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2](P.124)
右師“介”而遭人議論的例子,顯示了人與人在相互觀看的細微過程,一不小心,就會挾帶偏見而輕慢他人。“介”者,獨腳踽行,在世俗眼光下,經常會被預設是“為惡近刑”之人,因而暴露在被鄙視的處境中,例如當公文軒看到右師介足形象,第一直覺的驚異反應,似乎就已經透露歧視端倪。不管是天生的自然殘疾(天與),還是后天的人為殘疾(人與),在“正常人”的集體審視之下(如公文軒所代表),“介”總是會被視為“異常”,而公文軒的“驚”大概是種近乎嫌惡的無意識反應,或許嫌棄右師的丑惡,或者嫌棄右師的罪惡。也可以說,這種“驚”對照出了自己的優越感。這就像是《德充符》所描述的那些兀者、丑者的社會遭遇,他們幾乎一開始就被世俗眼光貼上:無德、犯過、天譴,種種可能性“污名”標志。尤其在先秦那種流行肉刑的時代氛圍下,被政治暴力刑罰而留下肉身印記者(如刖刑等),經常會被當成污穢不潔之人而只能從事低賤工作(如暗夜守門之閽人);而且在古代流行疾病盛行的年代,天生殘疾人恐怕不在少數,但他們卻容易被誤認為犯罪者而受到歧視。(36)關于閽人、刖刑的描述,以及《莊子》對療愈的特殊思考:讓自然運化撫平傷口,參見何育儒《論〈莊子·德充符〉之創傷療愈》,《清華學報》(新竹),2016年第1期,第1-40頁。將氣化與疾病現象連結,闡述《莊子》對“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思考,參見李志桓《風與麻風:試論〈莊子〉會如何思考生活本身的不確定性》,載《中國哲學與文化》第19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即便經由當事人(如右師)的辯解與澄清:“我是天生自然的殘疾,并不是后天錯誤惡行所遭致的罪罰。”(天也,非人也。)但在一般自以為身形健全、價值正確的“常人”看來,仍然可能認為這是“天刑”,是先天無德或祖上禍延的原罪印記。由于人是社會性存在,個體活在群體的社會脈絡與集體規范里,本來就很難不被社會眼光所影響,而古代的價值體系又可能處于相對封閉狀態,對于善/惡的價值標準也可能相對固定,也更容易形塑一般人“為善近名,為惡近刑”的善惡嚴明之道德裁判眼光,因此也就容易犯上以善為名的道德暴力。換言之,右師這個小小故事,可能要傳達兩個消息:一者,如何避免自己犯了公文軒這種高高在上的道德裁判,尤其在我們對每個人背后的人生故事缺乏理解的情況下,應避免以道德俯視他人的“光之暴力”;二者,如果和右師有類似的命運處境,則要避免自哀自憐或怨天尤人,人生在世本來就可能遭遇各種“不可奈何”,或先天或后天的不完美,或自然或人為的身體殘缺,別人一時的或理解或不理解,我們都可以向右師學習“天也,非人也”的坦然,那種“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納受。
(二)走出樊中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蓄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2](P.126)
澤雉這一暗喻,似乎要告訴我們:養生絕不宜養尊處優、困守在同一性的人為環境中(蓄乎樊中)。“蓄乎樊中”的“樊”,可以是有形的圍境局限,也可以是無形的觀念控制。例如將一棵榕樹收納在盆栽空間來養植,榕樹將無法發揮它的生生之德,因為封閉空間中的養分相對有限,它的生命力被囚在盆中而難以發揮。植物如此,動物亦然。動物如果被囚拘在樊籠中,失去與外在處境相互變化的回應能力,久之必然肌肉松弛、靈識呆滯,成為動物園中了無生氣(甚至精神官能癥)的寵物。而生為靈長類之冠的人類,一旦“蓄乎樊中”,更是如此。問題是,什么是人類的“樊”?一成不變的環境,都可以是“樊”的變形。例如“同一性”的成長環境、人際關系、價值觀念、文化系統……都可能是樊籠的象征,久之會“固而不化”地制式化我們的身心,讓我們的身心或習慣或安穩于這種封固狀態。或許它會帶來一時的舒適安穩,但也可能造成我們習慣于特定性依待,而降低了回應差異性處境的變化能力。換言之,“樊”讓我們習慣依賴、習慣固定,讓我們在一成不變的處境中,被處境所反控。結果,“我化,故,我在”的生命變化能力,會在樊籠的同一性中,日日退化。這就像《莊子·德充符》筆下那些高雅士大夫,處在“成規成矩”的禮教環境太久,高高在上而好逸惡勞,反而失去了百工技藝身上的質樸生命力。(37)王博即指出,當身處于樊籠之中,心靈陷溺,失去自由,而名即是刑。相關討論參考王博《莊子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64-79頁。例如庖丁生命所散發的力量美學(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相較于“蓄乎樊中”的文惠君(神雖旺,不善也),便反而突顯出生機活潑的生命力來。(38)如以海德格爾的概念來模擬,雅層階級的“蓄于樊中”,猶如將自己懸擱在較為抽象的意識狀態,并與生活世界的身體操持產生距離。而“不期蓄于樊中”的庖丁俗層,反而處在“上手狀態”的勞作中,時時與生活世界產生原初交涉關系。由此,“養生”并非抽象理念、也非純粹心性、更非隔離世界,而是整體身心與生活世界的遭遇、調節與轉化。海德格爾的“手前狀態”(手前之物)向“上手狀態”(上手之物)的回溯,代表了意識我與對象物的認識架構回溯身體與世界渾然交織的原初存有狀態。從海德格爾的觀點可得到啟發:任何養生或修行實踐都應打開各種樊籠,迎向生活世界的挑戰與機遇,此可為《養生主》的“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做一跨文化對話之腳注。有關海德格爾“上手狀態”與“世界情境”的現象學描述,參見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98-125頁。
正如前文再三提及,生命的河流必然伴隨涯岸的關系情境才能成為風景。而涯岸所象征的互相關系,總會隨著河流流動而轉換局勢處境,這才是人生長河大流婉轉漫延的養生圖像。人生因交互關系而存在,生命力量會因循環境挑戰而展開它的創造性響應,并由消化外在阻力轉為增長內在活力的律動。這就像澤雉離開了樊中的人為控制之同一性環境后,迎向了“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的自我渴望與他異處境,每一步都是在敞開的處境與機遇中,或順或逆的變化處境中,抑揚頓挫地創造出來的力量線條。換言之,養生也是一種生命力的鍛煉與培養,它必然在各種變化處境中遭遇差異的人事物,并在“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順逆之間,調節辯證而有機生長,如此才能長養出堅毅的生命力度及豐富的生命意義。倘若將自己封閉在抽象而單調的人為環境中,在預先設定的同一性環境中慣性重復,就算一時表面光鮮而養尊處優,但最終必然因孤離于自身與世界的交織變化,從而導致力量耗弱與意義貧乏。所以《莊子》提醒我們,想要善養生命活力并充實人生意義,就必須勇于脫逸“蓄乎樊中”的鳥籠人生,剛健地勇于走向“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的境遇變化與機遇挑戰,這樣我們的“人生—世界”之雙向轉化,才會跟著律動起來、豐饒起來。由此可見,養生必須打開樊籠來面向世界,并讓充滿他異性的世界局勢,來啟動我們回應世界并轉化自我的生命力。(39)用生活現象學的概念說,養生實踐不可停在觀念或意義的抽象樊籠中,必須回到“生活世界”的他異場所,來展開具體而活生生的身心實踐。“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便暗示著這個充滿未知而等待我們理解與詮釋的生活世界。宋灝曾透過身體現象學的肉身場所來詮解佛教(如華嚴宗)的實踐修行,也應該要逆轉收回到當下十字打開的生活世界中來,而不是去遙想一個形上的繁華世界(如一即一切的世界觀之類)。換言之,任何的“形上理念”,也可能會墮化為一種樊籠。參見宋灝《意義、時間與自我:從哲學詮釋學的角度看唐代華嚴宗思想》,《東吳哲學學報》,2009年第19期。
(三)懸解死亡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2](PP.127-130)
人作為有限存在而終有一死,因此完全的養生之道,也就不得不觸及“生死事大”這終極關懷的“命限”問題。而《莊子》提供的藥方,則是要我們在死生一條一貫的眼光下:知命、安時、處順。《養生主》最后安排老聃之死,好友秦失吊喪時,看見老少弟子如哭其子、如吊其母那般傷心,秦失不以為然地指出,弟子那種面對死亡的偏激態度根本未能善體其師的“以道觀復”的智慧,結果和常人所承受的“倒懸”之苦沒有分別。對于死亡帶來的壓迫之苦,《養生主》用人被懸空倒吊喻之。“倒懸”這個同時帶有“時空”與“身體”雙重意象之隱喻,就好像有人被蒙眼而掛吊在無底深淵的崖邊,身被捆綁而腳上頭下,崖底則是幽暗的深淵死地。這個意象也傳達出“生命乃朝向死亡而存在”的“時間性”連結,由此帶給我們苦感與省思。可以說,“倒懸”意味著:人一斷臍出生便仿佛像被剪斷了倒吊著的繩索,開始倒頭凌空墜落,任誰都改變不了垂直落下的命運方向,任誰終究都要命喪崖底,更可畏的是,任誰都無法預知何時將要粉身碎骨。而“縣解”便是這死亡命限之苦迫的解除、脫開。一般人都怖畏死亡,所親之人的逝去,必然都帶來傷感苦痛。然對真人而言,過分怖畏與哀傷的痛苦,實因人之主觀意志拂逆于天道的自然韻律。而人所自遭的折磨,即是所謂“遁天之刑”。《莊子》并非意指有一位人格之天神降下懲罰,而是強調人因自我成心情執做主,不愿正視天道無私,不愿順從自然變化,便如螳臂當車一般,無謂地獻祭傷痛之心,但這實在是無知和自戀所造成的自苦。倘若人們能順從變化無私之天道,以宏觀的道眼看待力量運動的整體變化,那么人的“生/死”便只是道之“來=去”運動的一環,人唯一能做的便是放下主體強烈做主的成心有為,以便平等地看待死生,平淡地隨順來去。這樣自然能超然“悅生/惡死”之哀樂交纏,解脫死亡帶來的倒懸之苦。而“哀樂不能入”,便是對“悅生/惡死”兩端情執之超脫。《莊子》既不在死亡之外尋求永恒,也不依傍神奇儀式來安撫慰藉。它不逃避與死亡正面交鋒的契機,接受了死亡焦慮乃生命之內部事件,并由此化除死/生對立的恐懼,以便從悅生/惡死的二元輪轉中,頓入“死生無變于己”的安然,如此《莊子》便在接受死亡“不可解決性”的天命前提下,吊詭地化解了死亡焦慮。而解除上述吊懸之苦,《養生主》命之為“(帝之)縣解”,亦即要用“帝(天地自然之道)”之眼光和手法來解開倒懸的死結,以便重獲“不死不生”之自由。(40)相關討論見賴錫三《“藏天下于天下”的安命與任化:〈莊子〉“以不解解之”的死生智能》,《應用倫理評論》,2015年總第59期,第103-122頁。
《莊子》為不可解決的死病,提出了另類的解決之道。只是解方并非來自人的任何發明,而是回歸變化自身、接納自然命運而已。“薪盡火傳”的薪火隱喻,并非重回古神話所說的靈魂流轉與再來,而是肯定人的形體(有)之殆盡,然此殆盡亦非化為虛無,而是回歸氣化流行的力量運行之自然自身。所以宇宙的力量(氣化)歷程是“無盡”的,可以用“火”的意象來隱喻,但肯定宇宙氣化偉力的不生不滅、不增不減,并未由此肯認個體般的靈魂不滅之實體。換言之,“火”并不意指“靈魂”或“靈體”,而是非單位非實體的宇宙氣化力量的存有連續(而火之隱喻或許又可扣合大冶鑄金之喻)。因此人的形體有所殆盡,但宇宙氣化之火力依然不增不減地相繼運動下去。而真人認同的不只是形體之薪,更是不生不滅的氣化永恒之火。真人至此,“化而不化”地活在永恒流變的宇宙大化中,薪盡火傳而生生不息。(41)“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一語,吳怡的解釋可做參考:“這句話,一般都解作薪木如軀體,會燃盡,而精神如火焰,卻傳之永遠。我們另有一解,不必把‘窮’字刻板的當作盡字解,而是描寫忙于不斷的取薪,此薪化為火焰,然后再取另一薪而燃。這個指不一定是人的手指,而是象征大化的‘指’,‘取薪’就是生物,物有了生,便有死,死了又轉化另一種生,生命的轉化不止就像火傳也,不知其盡。我們個體的生命,就像許多薪木中的一根而已……個人的生命縱有燃盡,但這大化的流衍,卻是無盡的。”見吳怡《新譯莊子內篇解義》,臺北:三民書局,2014年,第136頁。
六、結論:“方內即方外”的內外相養
我們可以把《養生主》與《齊物論》作勾連,并和《人間世》作意義脈絡的串連,這樣更能看到《莊子》在“關系性思考”下,涉及各種倫理、政治等人際情境的“在世養生”,并將“養生”視為在各種關系情境下,全幅度的“保身,全生,養親,盡年”。“內圣外王之道”典出《天下》篇,若說“內圣”看似偏重個我生命的安身立命,而“外王”看似偏重自我與他人的關系性轉化,然《莊子》的內圣與外王應為“相即”關系,也就是內外不離、自他不二。從“不二”的圓即思維來說,真正的養生就必須破除“內外不相及”的二分,圓頓地思考“內外相即”的一貫之道。一言以蔽之,逍遙游必須落實為人間世。逍遙必須“入游其樊”于人間關系之“樊”,就像庖丁必游刃于牛體的錯綜情境。關鍵點在于“心”能否游于“虛”?“刀”能否游于“薄”?若能有虛心無厚之游化主體,便能在人間世的牛體樊籠中,發現余地而游化間隙,“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地發揮:關系性的逍遙與關系性的雙養。
西方形上學的思考模式,通常區分本體與現象,形上本體的真理是在超越的彼岸界,形而下的現象則是流變而不真實的幻相。因此生命的安頓要歸屬于本體世界,舍離世間流變,向上攀升以求得形而上的永恒寧靜。形而上的真理與樂園是在此岸(方內)之外的本體界,永恒只能存在于時間之外的、流變之外的超越界(方外)。若我們采用西方的形上學思考來理解《莊子》的道,那么“道”就會離開萬物、離開人際、離開倫理,離開一切的變化關系。倘若“道”割裂了變化,那就代表《莊子》要在萬物變化之外肯定不變化的實體之道。倘若如此理解老莊之道的超越性,《莊子》的養生會被引導成向上超越、往上修養,走向“方外養生”而不是“在世養生”。這種解讀方向,將使《莊子》成為遠離關系的隱逸遁世之學,或者外在超脫性的宗教遠求。此時的“方內/方外”呈現“道/物”割裂狀態,背離了“道無逃乎物”的“周、遍、咸”之當下一切處(42)《知北游》:“東郭子問于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后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于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見郭慶藩《莊子集釋》,第749-750頁。。
《齊物論》提及“與接為構,日以心斗”,即人在與物相交接的緣構過程中,我們通常容易以“成心”的一偏“知”見與是非“言”辯,去進行“名以定形”的封常活動,而在這個“非我無所取”的過程中,人也就容易把“未始有封,未始有常”的“化而無常”之道行運動,墮化為“為是而有其畛”的固與常,而自以為能穩固地占有與私藏。正是這種“藏天下于我”的取、固、封、常,造成了占有與失去的自苦循環,而《莊子》的養生之道并非要我們終極性地離開這個“化而無常”的變化之道,而是要我們轉化自我(喪我)以便能“藏天下于天下”(43)《大宗師》:“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見郭慶藩《莊子集釋》,第243-244頁。。某個意義下,情境化的在世養生其實就是不斷調整自我的歷程,而不是取消變化流行的歷程。因為人終究無法背離這個變化流行、化而不固的世界,而氣化流行就是“化而無常”的道之實相,人終究只能“知其莫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面對變化力士而納受無私無藏的大化流行。
由此可見,對于《莊子》來說,問題不在于方內本身是不可轉動的苦,而是我們要如何轉化成心以面對當下緣起的方內。若只以成心去“與接為構”,那么方內當然會是充滿人與人之間“名以定形”的糾結(隨假名有而執實),即《養生主》用牛體迷宮比喻人際錯綜復雜的“知/言”結構,所以陷溺在“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的名樊陷阱,掉入“執假為真”“以虛為實”的名言名利之網罟。當我們缺乏一種“虛”的能力,以強力主導的意志去強行運作主體自我這把厚刀利刃,就必然會產生人我之間的相刃相靡,刀跟刀、劍跟劍的相刺相砍的雙傷邏輯。薩特(Jean-Paul Sartre)就曾說“他人就是地獄”,其實“我何嘗不成為他人的地獄呢?”這種惡性關系反而造成自我與他人的不斷損耗,人際關系成為剪不斷理還亂的厲鬼糾纏與相害。面對這種“他人成為我的地獄,我成為他人地獄”的污濁惡世、方內亂相,一般人自然容易興起方外樂土的形上想象與追求。若說《養生主》將“方內”比喻為牛體的錯綜復雜,而我們每個人的處身境遇都像是一把“刀入牛體”的游刃過程,問題是刀牛的相遇是相刃相靡還是游刃有余?如果說,關系性的方內世界,必然是個相刃相靡的痛苦場域,那么我們似乎只能擺脫一切關系而往方外去求解脫。然而從不二的角度來思考,方外必須與方內不相離,逍遙必須在人間世。這個時候,超越性與在世性具有“二而一”的圓即關系。(44)以佛教的概念來類比,“方外”類于空性體悟之真諦,“方內”類于隨名起執之俗諦。方內、方外不相及的二元論思維,意味緣起性空分離為“真諦”(空性)與“俗諦”(緣起)的兩個獨立界,這樣的修養解脫,大體屬于小乘佛教的析色入空、斷煩惱證菩提、離輪回住涅槃。而大乘佛教認為煩惱/菩提相即,緣起/空性不二。色相界既是無常世界,而無常是苦之來源,但更深入看實非無常本身苦,人的無明執著才是自苦之源由。亦即人的“五蘊”執取活動,養成了五“取”蘊的甚深習性,背離了緣起無自性而硬把無常執定為常,這時無常才間接成為了苦因。如果我們能夠把這個“五取蘊”轉化為“五蘊無我”,把六根轉為清凈六根,這時候六根六境六塵的“合和觸”,不再是“五取蘊”的“與接為構”之占有與執定,而是“接而不接”“入而不入”的“五蘊皆空”。對大乘佛教來說,無常即佛性,無明即是法性,色法界就是真如界,色界之外并未有獨立之空性。若以為離色有一個獨立的空性存有或空性本體,那便會退回涅槃與世間的二元世界觀。大乘佛教要回到當下即是的緣起世界、甚至假名有的世俗諦,真正的唯真諦就是唯俗諦。禪宗講挑水砍柴行住坐臥,這些平常心底下的平常事都莫非妙道,這都是類似于《莊子》方外方內相即不二的圓教之思。
最后,我們似可發現一條貫穿《養生主》全文的軸線,亦即天人的辯證關系。從文章開頭的“生有涯”與“知無涯”的對比開始,已經暗示我們:當人的有為之知對生之流的過分管控,將造成天機的干擾而不利養生。換言之,“生”與“知”的對舉,多少暗示了“天/人”“無為/有為”的辯證端倪。而“緣督以為經”的不落“刑”“名”之任何有為之極端,也透露出“以天養人”“為無為”的中道調節契機。而庖丁解牛的“依乎天理”,則進一步明示:庖丁的手刃要修養成“刀刃無厚”,象征人的主體從有為(有厚)調節成無為(無厚),這樣才能將“人”之自我意志的強行操控(知無涯),轉為因循牛體內勢情境的脈絡紋理(依乎天理),如此才能“以無厚入有間”地人牛不傷。換言之,當人能夠“為無為”地從“人”適度往“天”調節時,才能“依乎天理”(甚至“以天合天”),以保持共生、雙養的最大余地。由此可見,庖丁解牛的“依乎天理”,也含藏著人天辯證的調節轉化路線在其中。
而公文軒與右師的對話,更直接從“天與?人與?”的問題意識切入。而對右師的心境而言,不管他人如何從外貌的善/惡(“人”有與)角度來評論他的“獨腳”(介),他都能以“天”使其獨一無二(“天”使獨)的心境,來安然自處(“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換言之,公文軒和右師的對話,完全是在天人辯證脈絡中來展開的。而澤雉的“蓄乎樊中”,可視為居處人為造設的養尊處優之境遇,一旦久居其間,將造成自然生命力的天機衰退。而“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則暗指敞開于自然變化的天機境遇,此時生命回應情境而變化的生機,會自然地活躍起來。最后,透過老聃的“死”,告訴我們《莊子》的“養生”納受了“死”,因為“死”也是天道變化的體現環節。我們不能用“人”的眼光,硬將“死”“生”判分為二而拒絕死亡,這種“遁天倍情”的人為態度,反而讓自己掉入了“遁天之刑”。因此《莊子》經由老聃的喪禮而對比出:一般人“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人情),以及老聃好友秦失的“安時處順,哀樂不入”(無人之情的天情)。由此依然可見,《養生主》最終透過老聃的喪禮,以生死不二來契接天人之際的軸心問題。由上觀之,《養生主》全篇文獻,有一條天人辯證的意識河流,穿過其中的養生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