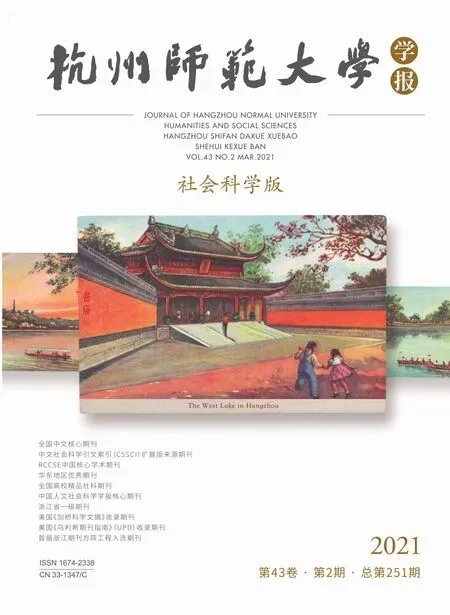文變:蔡元培文章改造思想的發端及實踐
段懷清
(復旦大學 中文系,上海 200433)
一
如果從其著述史來看,蔡元培(1868-1940)在1900年之前的著述,有幾個較為明顯的特點或變化:其一是從科途經傳類著述為主,向個人詩文類著述的擴展轉移;其二是從國天下主題向個人交游、地方治理教化關注的擴展轉移;其三是從本土經史類知識為中心,向西學或外來新知的擴展轉移。上述特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蔡元培此間的著述興趣、知識結構、文化身份以及價值取向的基本形態,以及因應世情、時序所開始發生的一些或隱或顯的“改變”。這些改變盡管在此期間尚不明顯,且亦并未造成原有知識結構、文化身份以及價值取向的根本動搖或徹底顛覆,但如果與后來蔡元培思想的發展走向關聯起來考察,就會發現這些著述方面所出現的新現象,事實上正是后來所發生的那些思想與著述變革之發端與濫觴。
1898年“維新變法”前后,蔡元培著述中的思想言論,出現了一些較為具有內在張力的波動。一方面,他至少看上去依然忠實于對于傳統知識體系、價值取向以及信仰堅守的具有個人主體意識和學術自覺的探索,“太史公謂儒者博而寡要,劉子駿謂博士專己守殘。傾群言之液而衷諸經,非有要乎執經之權而擬議于古今賾動之跡以窮其變化,非愛古而廣己者乎”[1](《會稽徐氏十四經樓藏書記》,PP.205-206),同時對于那種“無雜賓,無雜言”的讀經治學環境,以及對于那種“主人出,窺其容,頎然者;聆其欬,鏗然者;試其行,肫然者;從之游,效其威儀,遫然者”[1](《為陶在銘題扇》,P.207)一類修身境界的向往推崇。但在另一方面,對于當時官紳士大夫之中所出有關新知識、新策論一類的著作,蔡元培亦表現出并不盲目排斥的清醒和開明。在《馬建忠〈適可齋記言〉〈記行〉閱后》一文中,蔡元培肯定了馬建忠“于西學極深,論鐵道、論海軍、論外交,皆提綱挈領,批郤導竅,異乎沾沾然芥拾陳言、毛舉細故以自鳴者”[1](P.209)。其中不僅肯定了馬建忠的治學態度,而且也肯定了他的新知識與新學術,即在本土傳統經傳詩文之邊沿所進行的新的嘗試與探索。這似乎昭示出蔡元培的思想中已隱約存在著的立場與傾向的某種程度之調整。但調整顯然并沒有一般想象的那么明顯和激烈,譬如《宋育仁〈采風記〉閱后》一文中,對于這位進士出身、以翰林院檢討身份充任駐英二等參贊官的文官所著《采風記》,蔡元培顯然嚴肅認真地閱讀過,而對該著所肯定者,除了“記事有條理,文亦淵雅”,更關鍵的是,該著之宗旨,“以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國古制,遂欲以古制補其未備,以附于一變主道之誼,真通人之論也”[1](P.212)。并欣然指出:“以西法比附古書,說者多矣。余嘗謂《周官》最備,殆無一字不可附會者。得宋君此論,所謂助我張目者矣。”[1](P.212)對于西學與中學之關系的如此認知及堅持,一方面反映出蔡元培當時對于西學了解的方式及水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甚至塑造了他對西學與新知的判斷;另一方面亦可以看出,蔡元培當時盡管并不排斥西學與新知,但這種西學與新知,是“暗合中國古制”的西學與新知,而不是在中國古制之外另自主張的西學與新知。換言之,很大程度上,蔡元培此間所關注、了解并接受之西學新知,是“殆無一字不可附會”于本土古書的西法,是可以被納入到本土現有知識體系、典章制度、價值標準之中的知識與學術。也正因為此,西學與中學、舊學與新知,并不是處于不可調和的緊張對立狀態,而是處于可以兼收并蓄的結構性調和關系之中。所以,一直到1899年1月28日《嚴復譯赫胥黎〈天演論〉讀后》一文之前,蔡元培思想中的“變革”傾向,依然不明顯;對于舊學與新知、中學與西學之間關系的認知判斷,大體上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相近。另值得注意的是,《嚴復譯赫胥黎〈天演論〉讀后》一文,與蔡元培之前幾篇閱讀記明顯不同的是,該文僅述嚴譯《天演論》一書之大意精要,未作任何比對評述。而在之后幾篇文章譬如《〈紹郡中西學堂借書略例〉序》《〈東西學書錄〉敘》《紹興府學堂學友約》之中,蔡元培通過對地方興辦新式學堂、翻譯新書等具有“維新”色彩事務的關注、介紹及支持,表明了自己對于西學、新知立場及主張的某種并不引人注目的輕微調整。《〈東西學書錄〉敘》一文中,不僅稱呼晚清來華西方傳教士為西儒,另對傅蘭雅所作《譯書事略》予以充分肯定,且未沿襲之前將此類西學之說納入到本土古書古制之中考察論述的“正統”方式。[1](P.244)而在《題贈日人中畑榮以冊征詩》(五言三律)中,顯示“天演之說”的自然進化思想,似乎正在擠兌原本由天道循環、周而復始之說所掌控的話語權力。[1](P.249)
上述著述言論,反映出蔡元培的知識與思想,在1890年代尤其是在“戊戌變法”之后,開始出現有跡可循的調整改變,對于西學與新知的閱讀、關注及闡發應用,逐漸多了起來,這也說明,蔡元培的“變革”思想,并沒有因為“維新變法”的失敗而偃旗息鼓、改弦更張,反而變得更加明確而堅定。《紹興推廣學堂議》開篇即毫不避諱地引述西人對于中國的論述,“痛乎哉,西人之論中國也……”,這種句式與議論方式,顯然已經不再是西學“暗合中國古制”“以西法比附古書”那種思維范式與價值取向,而是借西人之說來對本土顢頇者進振聾發聵之語。而此類句式與文法,亦恰恰是“維新變法”前后維新派人士在文章言說方面漸興漸廣者。
對于自己蒙學以來的讀書經歷以及學識思想之進步,蔡元培在1900年2月27日的《剡山二戴兩書院學約》一文中有專門敘述,其中特別提到了《天演論》以及日本明治時代的維新思想對于自己的影響:
又四五年,而得閱嚴幼陵氏之說及所譯西儒《天演論》,始知煉心之要, 進化之義……近之推之于日本哲學家言,揆之于時局之糾紛,人情之變幻,而推尋其故,益以深信篤好,尋味而無窮,未嘗不痛恨于前二十年之迷惑而聞道之晚。[1](P.257)
盡管上文中依然有將《天演論》一派之學說,“反之于《春秋》《孟子》及黃梨洲氏、龔定庵諸家之言”的類比,且仍能有“怡然理順,渙然冰釋,豁然撥云霧而睹青天”之中西會通[1](P.257),不過與最初拿西學西說來“暗合”“比附”本土古書古制的立場及觀點相比,此文中所表達之方法與思想,已經明顯不同,其中“更法”“改圖”一類的意念與訴求,顯然已經成為蔡元培此間學術—政治思想之基本立場與目標。
如果說上述詩文著述,所反映者尚且為蔡元培知識、思想及學術、政治諸方面所發生的調整改變,基本上還沒有滲透并影響到他對思想言論的表達方式,尤其是語言文體方式的思考及實踐的話,這一現狀在1900年3月的《上皇帝書》及之后,則發生了第二個層面的改變,即從思想觀點立場的改變,延伸到表達方式即語文方式的改變,這也就是蔡元培所謂的“文變”。
二
1900年3月,蔡元培撰寫了《上皇帝書》《夫婦公約》《佛教護國論》三文,這三篇文章在寫作動機上,很難看出彼此之間存在確切的內在關聯,不過在文章寫作實踐層面,卻較為一致地反映出當時蔡元培在君國、君臣、夫婦以及民教諸方面相對獨立、更為自由之思想立場與言論主張,同時亦反映出蔡元培在傳統語文的書寫實踐方面所開啟的具有一定連續性的探索嘗試。而且,在義理、考據與詞章諸方面,相較于正統古文章法,已判然有別,其中尤為明顯之處,就是所隱含或顯示出來的“世界意識”,即《夫婦公約》中所謂“全球之例”。此種視野與意識,并不僅限于考據一途,實際上對于文章之詞章甚至義理,亦有關聯影響,而此文中利用西學中的物理學尤其是電學中的電學原理,來解釋中國傳統思想中的陰陽男女之說,由此推及保國保種之一代之事,其中邏輯推演與起承轉合,可見蔡元培“文變”思想在實踐層面體現之一斑:
凡體者,皆合眾質點而成者也。一體有一體之性質,雖析之極微,而一 點之性質與一體同,此人與物之公例也。是故其體有強弱之差者,其所發電力有多寡久暫之差;其神志有智愚之差者,其所發電以成器之性,亦有靈蠢之差。此理之必不可易者也。[1](《夫婦公約》,P.268)
此外,該文之中尚有涉及君國之論者,其言論立場亦較為激進,從中亦可見此間蔡元培政治思想之一斑:“持戟之士失伍,則去之;士師不能治士,則已之,為其不能稱職也。君有大過,反復之而不聽,則去,為其不能稱職也。” [1](《夫婦公約》,P.270)而此類思想,一方面可以放在“維新變法”運動這一時代語境之中考察,亦可以放在“庚子事變”這一語境之中考察,同時還可以放在蔡元培從1890年代以降所開啟的“思變”及“文變”的個人語境之中來考察。誠如其在《佛教救國論》一文中所言:“觀嚴幼陵所譯斯賓塞氏之說可知也。他日進化之極,至于人純以靈魂相接,無借乎肉體,成不生不滅之質,則無取乎男女之交,而取妻之風自絕矣。”[1](P.275)推導議論雖然或顯簡單甚至極端,但其中知識思想及立場觀點,顯然已非舊學一途。而《嚴復譯赫胥黎〈天演論〉讀后》一文中不曾公開表達的立場與觀點,至此則近乎成為文章立論的知識與思想基礎。
如果說上述三文,尚且為思想主張層面之議論,緊隨其后的《悼夫人王昭文》,則顯示出蔡元培在日常生活層面尤其是夫婦關系方面已經發生的明顯轉變:
近一兩年,余深繹平權之義,自由之界,乃使君一切申其意,而余惟時時以解足纏、去華飾、不惑鬼怪為言,君頗以為然,而將次第實行之,余亦不之強,而俟其深悟而決去也。[1](P.278)
文中不僅寫了夫人王昭的“超俗之識”以及“勁直之氣”,同時也清楚明了地宣示了1898-1900年之間蔡元培思想的基本面貌,包括他對“維新黨人”的立場態度。這一點,在《挽夫人王昭聯》之一中更是毫不掩飾地公開說明:
維新黨人,吾所默許,乃不及于難,鹿車南返,鷦巢暫棲,尚有青氈,博得工資同一飽;
自由主義,君始與聞,而未能免俗,天足將完,鬼車漸破,俄焉屬纊,不堪遺恨竟終身。[1](P.279)
所寫雖伉儷之情,但亦言及此間歷史、政治及個人立場主張。如果說上述諸文及聯語,多為自我申張,那么1900年9月4日的《〈四語匯編〉讀后》中所云“嗚呼!我朝全盛時,大臣家法固已如是,宜乎養成今日之風氣也夫”[1](P.281),則顯示出蔡元培此時對于讀書、士風、家教以及自私自利的時代風氣的憂思與批判。這也是蔡元培1900年前后的著述文章中,較為明確、清晰且堅定的時代社會之批評。
而此種憂思與批判,并沒有僅停留于言論,在此間蔡元培的行動實踐中亦不時可見。“鄙人蒿目時艱,推尋原始,非有開智之事,必釀亡種之憂。一手一足,命在何時,隨地隨時,嚶求同志。”[1](《告嵊縣剡山書院諸生書》,P.283)這種但開風氣的“開智”“新民”之舉,在剡山書院的藏書構成中亦顯現出來,“院中藏書,經史大部已具,所必須增加者,惟新學書而已”[1](《告嵊縣剡山書院諸生書》,P.284)。對于“新學”的推重,且將其視作與傳統“經史”對等之存在,足可見蔡元培此間無論是對于自己抑或是對于官僚士紳階層尤其是新興知識階層的知識期待,顯然已經發生改變。盡管實際上的思想及行為,時間上顯然要比見諸于文章者更早,但文章中的自我宣示,無疑更能夠證實1898年至1900年之間,蔡元培的思想與實踐兩方面所發生改變之深刻:
戊戌之變,元培在京師,歷見其始終。而推暨其故,以為天演所趨,蓋有不得不變通者,而當事諸君為之而不成,蓋亦有操之過蹙者與。國大器也,人質點也。集腐脆之質點以為器,則立壞;集腐脆之人以為國,則必傾。居今日而欲自強,其必自人心風俗始矣。[1](《書姚子〈移居留別詩〉后》,P.287)
這是蔡元培參照“天演論”之學說,并結合“戊戌變法”之失敗教訓,所確認的變通自強以救國救種之新路徑。這一政治思想方面的新立場及新追求,自始至終與蔡元培此間在道學、文章及學術方面的新進步或新變化密不可分。在《〈化學定性分析〉序》一文中,借用西方歸納法、演繹法,來比附“格物致知”之說,看上去與之前拿西學來暗合本土古書古制的立場觀點相近,實際上已經開始用歸納法、演繹法這兩種“科學大法”,來作為學者“按圖以索,舉隅而反,發爻通情,旁薄萬匯”的現代治學良方。[1](P.299)這種方法論意義上的借鑒與超越,并不比“天演論”之學說在思想領域所造成的震動與激發遜色。由此而激發出來并逐漸生成的改造精神與新思想,則與此間蔡元培在文章著述方面的書寫實踐相互滲透結合。
三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蔡元培選編《文變》三卷,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出版。這也是蔡元培自1898年以來,4年之間經歷思想之變、方法之變后,政治立場以及文學或文章立場亦發生明確改變的一個標志。同年,蔡元培與章太炎等人在滬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借辦教育之名鼓吹革命。如果說之前在地方呼吁并參與興辦新式學堂,至中國教育會之創立算是一個歸結,那么,此前在文章方面的種種議論、呼吁及倡導,至《文變》選編,亦可算是另一個歸結。
《文變》選編分上中下三卷,其中中卷又有上、下兩卷。
上卷收《培根論》《無名之英雄》(飲冰室自由書)、《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任公)、《過渡時代論》、《養士論》(日本 深山虎太郎)、《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任公)、《風俗篇》(觀云)、《辟韓》(嚴復)、《原君》(黃宗羲)、《原臣》(黃宗羲)文10篇。
卷中收《中國士流改進策》(亞泉)、《論支那人國家思想之弱點》(闕名)、《支那人之特質》(任公)、《砭新論》(闕名)、《維新圖說》(闕名)、《義和團與新舊兩黨之關系》(冰語)、《論黨會》(蘆中人)、《支那近日黨派說略》(四明 劉謙)、《變易國民腦質論》(錢塘 李世基)、《論中國文章首宜變革》(闕名)、《論宜盛翻譯翻印西書》(闕名)、《論空言無補于時局》(日本 山根虎侯)、《論跪拜之禮不可行于今日》(高鳳謙)、《論世變之亟》(闕名)、《清朝興衰之關鍵》(闕名)、《去奴》(唐甄)、《十九世紀之歐洲與二十世紀之中國》(闕名)、《兩世紀之大觀》(闕名)文18篇。
卷下收《論種界之競爭》(日本 石川半山)、《日人日心保華論》《文明國人之野蠻行為》(闕名)、《中國人種侵略世界》(日本 竹越與三郎)、《論吉甫林》(錄《日本人》月報)、《黃種之存亡》(闕名)、《俄國學者訴本國中暴虐于世界》《俄人之自由思想》《男女婚姻自由論》《女子亟宜自立論》《論女權之漸盛》《妒非女人惡德論》(俞正燮)、《節婦說》(俞正燮)、《廣孝》(唐甄)、《記江西女士》(梁啟超)文15篇。[2]
上述《文變》三卷,收文凡43篇,其中闕名、無名作者之文18篇,大體上反映出當時激進言論與革命文章所面臨的時代環境,以及著作者因應周圍環境的無奈之舉。
從所選編文章內容來看,上卷諸文涉及時代英雄論、時代性質論、思想論、風俗論以及君臣關系論等;中卷諸文涉及中國問題論、國民性及士流改造論、維新論、會社黨派論、文章變革論、翻譯西書論、世變與思想改造論等;下卷涉及種族及國際關系論、男女關系及女性自立論、女權及女德論等。這些文章,大體上反映出1902年之前中國思想界、言論界以及著述界對于時局以及中國所處世界之地位的分析判斷,對于士紳、國民性、平權及女權等關切時局及未來之重要命題之思考看法。而從這些文章作者來看,基本上以當時當世作者為主,尤其是梁啟超、嚴復、杜亞泉等一時風云人物之文章,尤為選編者所青睞,而日本思想者的言論文章,顯然亦受到蔡元培的關注,這也符合蔡元培對于自己當時改造思想之來源的基本闡述。
至于選編上述文章的原由,或如《〈文變〉序》所言:“讀者尋其義而知世界風會之所趨,玩其文而知有曲折如意應變無方之效用,以無為三家村夫子之頭巾氣所范圍。”[3]但這所反映的,顯然僅只是《文變》選編初衷之一端而非全部。事實上,對于《文變》選編之立意與出發,蔡元培所寄寓希望者,并非只讀者一方,對于著述者以及文章兩方面,在《文變》序中亦有清楚明了之闡述說明,從中亦可見蔡元培的文章改造思想的基本脈絡:
自唐以來,有所謂古文專集,繁矣。拔其尤而為纂錄,評選之本,亦不鮮。自今日觀之,其所謂體格,所謂義法,糾纏束縛,徒便摹擬,而不適于發揮新思想之用。其所載之道,亦不免有迂謬窒塞,貽讀者以麻木腦筋、風痹手足之效者焉。先入為主,流弊何已!
方今科舉,易八股為策論,鄉曲士流,皆將抱古文選本為簡練揣摩之計。前者之弊,復何異八股乎?[3]
這段文字,不僅是對晚清改八股為策論以救時局之權宜之計的批評,更是對千百年來中國讀書人在文章體格、義法方面所遭受到的重重束縛以致于思想壓抑扭曲、個性得不到舒張、新思想得不到發揮現象的冷靜反思與深刻揭示。更關鍵亦更重要的是,序文中還對此類文章所載之“道”對于作者以及讀者的雙重戕害,進行了毫不隱晦含糊的批評。也正是與這一文章史的認知判斷有關,對于作為千古文章之最基本之義法的“文以載道”之說,蔡元培亦結合時勢之變,而進行了重新詮釋:
先儒有言,“文以載道”。道不變也,而見道之識,隨世界之進化而屢變,則載道之言,與夫載道之言之法,皆不得不隨之而變。[3]
這一觀點最重要的地方,當然是對“變”的突出強調,以及“應變”之策的跟進隨行。《文變》所依托的原則,也就是這一因時而變、因世而變以及因勢而變的“變化”,也就是所謂“見道之識”“載道之言”以及“載道之言之法”“皆不得不隨之而變”的“變”。
不過,與上述突出強調“變化”幾乎同樣重要的是,蔡元培這里也強調了“道不變”,也就是說,在突出強調“變化”的同時,蔡元培也同樣強調了“不變”。怎樣理解這里“不變”的“道”,與“變”的“識”“言”與“法”之間關系的論述?是否可以由此而得出蔡元培文章改造思想的不徹底性或時代性的結論?又或者,蔡元培這種極為突出“變化”的文章思想中,依然保留了一定的與傳統思想之間的關聯性及延續性?或者說維持了一種“變”與“不變”之間在抽象的哲學與邏輯意義上的辯證平衡?弄清楚這一點,不僅對于認識蔡元培1902年前后的文章改造思想很重要,對于認識此間蔡元培的改造與革命的思想同樣重要。1902年的蔡元培,似乎通過《文變》的選編,揭示出了自己的思想在走向徹底革命之前,在改造與革命之間最后的一段歷程。盡管其中并沒有顯出自我思想上的糾結掙扎,或對于所謂“道”的眷念與不舍,而是更突出、更明晰同時亦更堅定地昭示出對于變化、改造乃至革命的積極證明及深沉呼吁。不過,恰恰是在對于“道”與“識”“言”“法”之間關系的揭示上,《文變》或者蔡元培又為“道”在現代留下了一個抽象而模糊的存在空間或可能性。
四
關于“文變”之論述或思想,在中國古代文論中并不罕見,不過,進入近代尤其是現代之后,“文變”一類的言論主張顯然更多耳聞,“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一類的主張,亦很快為“文學革命”一類的主張所取代。蔡元培的《文變》選編及其所呈現闡發的“文變”思想,應該也正處于這樣一個文論思想的過渡階段或者歷史語境之中,并由此確立了它在思想史以及文論史上的歷史定位以及思想與學術貢獻。
就中國文論史或批評史而言,對“文變”思想尤其是文章之繼承與創新關系闡述得尤為清楚明白者,大概是劉勰的《文心雕龍》。其中在《附會》《時序》《通變》諸篇中,反復提及并闡述了“文變”之思想。而蔡元培的“文變”思想及主張,除了在近現代之交的時代語境中得以考察解讀外,在中國文論史以及《文心雕龍》一類的學術思想譜系中亦可得以彰顯。
“夫文變無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為事賊。”[4](《附會》,P.844)這是從微觀角度對一篇文章的具體書寫評價,見仁見智。但“文變無方”一說,顯然是強調文章需要根據具體語境來形成自己的文體及語言修辭風格。這種“變”,是語言修辭與文體風格意義上的變。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4](《時序》,P.874)此處所言“質文代變”,顯然是從宏觀角度,尤其是從大時間乃至時代角度,對于不同時代的文章風格、情理表達、審美取向之間所出現的差異及其原由予以闡釋,而明白了這一點,亦就不難理解“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4](《時序》,P.874)。
“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4](《時序》,P.890)這一概括判斷,從“世情”與“時序”兩個維度,對于文章之變以及文章興廢的外部世界之原由——即在創作主體之外——予以解釋說明。而這一外部世界之原由,基本上與社會環境以及政治生活相關,亦就是說文學或文章的發展變化,是會受制于前者的。而作家—環境—文章之間的關聯互動,既是文章生成的內在機制,亦是文章之變乃至興廢的主客觀條件。
“贊曰: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沿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曖焉如面。”[4](《時序》,P.895)從上述論述可見,文章或文學的變化是常態,盡管一時代之文學已經確立,亦具有一定獨立性或穩定性。在這里,《文心雕龍》在世情與時序之外,亦突出強調了朝代政治尤其是某些主導性力量及因素對于文學變遷所產生的決定性影響。在上述討論影響“變遷”的力量要素之中,因外而起或內外互動而引發導致的變動乃至興廢關注討論較多,較少涉及到作者主動改變或者個體性的改變對于一個時代文學的變遷所產生的影響。
如果說上述討論的文章之變,集中在文章的外部因素與文章之變之間的影響關系上,那么,《文心雕龍·通變》中所謂“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4](P.573)這一論述,則是從文體有常,而“變文之數無方”的角度,揭示了文章之體與形之間的辯證關系。
而結合上述種種,可見中國古代文論中對于文章的“不變”與“變”,或者從文章史的角度來揭示文學本身“因革”“通變”的發展變化規律,早已有過長期觀察、深入思考和精辟闡述,并肯定性地推斷出文章“變則堪久,通則不乏” [4](《通變》,P.580)這一關乎文章發展變化的重要規律。
而從1898年至1902年之際《文變》的著述及思想言論來看,蔡元培在這4年之間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語言表達以及價值信仰等,都經歷了較為明顯而激烈的起伏變化,并有了一個相對清晰和穩定的思想與立場歸結,即從一個正統文化、主流體制中的士大夫,較為快速地轉變成為一個知識、思想以及價值信仰方面的自我改良者乃至自我革命者。而且,這種改良與革命,不僅體現在政治、思想、價值及信仰方面,同時亦體現在文章或文學方面。而作為上述改良乃至革命之最為集中之體現者,莫過于《文變》。它既是蔡元培此間政治、社會、文化之思想立場變化之體現,亦是此間蔡元培在文章乃至文學方面的觀念、理論乃至實踐諸方面所發生變化之體現。
而與《文心雕龍》中的基本立場及其具體所論不同的是,蔡元培此間所經歷并主張的“文變”,與他的思想、價值及方法之變是相互關聯并彼此成就的。如果說最初對于“文以載道”中的“道”的認知,或許尚有傳統性的一面或者更多體現傳統的因襲傳承,那么在《文變》前后尤其是之后,蔡元培對于“文以載道”中的“道”的認識及主張,顯然已經更多具備并體現了其非傳統甚至反傳統的現代面向及構成。換言之,此間無論是蔡元培所呼吁并倡導的“文變”,還是“文變”之后所承載之“道”,皆已發生深刻改變,應該已經不只是傳統之道結構系統內的所謂“質文”與“雅俗”之爭或之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