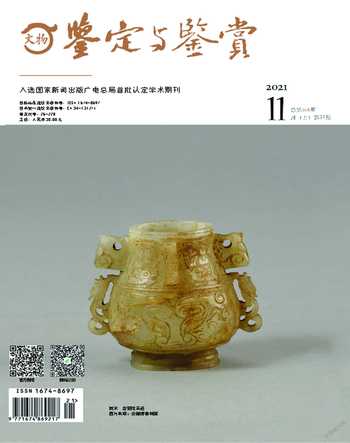從晚明書畫收藏著錄看世風之變
姚東一
摘 要:與前代相比,明代中晚期書畫著錄的編著有明顯的變化,主要體現在:書畫著錄體例完整,更多地記錄書畫鑒藏的信息;書畫著錄演變成私人藏畫錄或過眼書畫錄,對書畫交易流轉和藏家信息的記錄增多。反映出晚明社會書畫收藏的流行和藝術消費風氣的盛行,以及文人對閑適雅致生活追求的世俗面向。
關鍵詞:書畫著錄;私人;世風;變化
書畫著錄是前人記錄法書、名畫的目錄性著述,一般比較詳細地記錄流傳作品的信息,對作品的時代、材質、題跋、藏家有相對全面的記錄,正如金維諾先生所言,書畫著錄往往記載了有關繪畫發展狀況的資料,能為我們研究繪畫發展提供豐富的材料①。某種程度上,書畫著錄也是我們全面了解特定歷史時期書畫發展狀況和時代風氣的一扇窗口。本文通過對晚明書畫著錄的編著情況和其中的變化、特點與具有代表性的著錄的分析,探討晚明私人藏家著錄編著的新趨勢,其中所反映出的當時書畫收藏的流行和藝術消費風氣的盛行,以及文人對閑適雅致生活追求的世俗面向。
1 明之前與明初中期的私家書畫著錄
個人私家的書畫著錄出現在元代,書畫的品評鑒藏開始逐漸廣泛起來,此時也出現了第一部記錄私人書畫收藏的《云煙過眼錄》。作者周密,字公謹,祖籍山東濟南,流寓吳興(浙江省湖州市),曾官義烏縣令,周密亦是精鑒賞的藏家。《云煙過眼錄》記錄其所經眼書畫,是書分上下二卷,開了私家收藏著錄的開始,書中記錄當時私人藏家所藏書畫,錄有趙孟頫、喬簣成、焦敏中、鮮于樞、張受益、王子慶、王介石、張斯立、郭天錫、尤氏、趙仁榮、劉伯益、松江鎮守張萬戶、王英孫、張萇、董六千、游氏、莊肅、廉希貢、徐容齋、道士禇雪巘、郝清臣、高克恭、胡詠、楊伯嵓、李倜等40多位藏家所藏書畫,對藏品的記錄以名錄為主,沒有太多記述,但有趣的是,其中的記錄詳略大異,有的極其省略,有的也相對詳細。如記張受益藏品李成《看碑圖》:“乃李成畫樹石,王崇畫人物,今止有一幅,其人物一幅則不可見矣,余平生觀李丘營筆當以此軸為最,舊藏王子慶,今歸張受益。”②略加自己的心得和作品流傳,此記錄算是記述較多。對一些作品記錄甚簡,如對范寬《雪景三幅》記錄則甚簡,僅記一句:“闊景甚偉,原王子慶物。”②有的甚至只錄其名,不加說明。雖然此著錄沒有像之后出現的書畫著錄詳細記錄作品的內容、題跋、印記、流傳,但作為首次記錄私人藏家藏品的書畫錄,已經有很大的貢獻和史料價值。周密是宋朝遺民,所錄藏家為元初私人藏家,可見此時已開始醞釀書畫民間私家收藏的風氣。而到元末,江南的藏家愈加多起來,無錫倪瓚、松江曹云西皆是一時聞名的書畫收藏大家,昆山顧阿瑛的玉山草堂的雅集成為一時文人集散中心。
至明代,書畫著錄的編著越來越多,有明一代的書畫著錄與當時的書畫鑒藏相得益彰,在沒有圖像記錄的情況下,當時的鑒藏活動助長書畫錄的編著,書畫錄轉而成為鑒藏者可依賴的資料工具,這一改變從明中期開始出現,此后逐漸演變成具有私家藏畫錄性質的各種書畫錄形式。
這一轉變中出現的比較重要的開一時新風的書畫錄形式,是從朱存理所著《珊瑚木難》和《鐵珊瑚網》開始的,朱存理(1444—1513),明代藏書家、學者、鑒賞家,字性甫,又字性之,號野航,長洲(今江蘇蘇州)人,雖為布衣,仍然“未嘗一日忘學問,人有異書,必從訪求”。因此,《珊瑚木難》為朱存理抄錄書畫題跋文字結集而成,書有八卷,所錄以元末明初人的題跋為主,所錄書畫作品年代從石鼓文到元代書畫家,從此書的體例看,似乎不像最后成稿。此書與之前書畫錄如《云煙過眼錄》最大的不同在于,此書主要關注對書畫作品題跋的搜集和記載,缺少對書畫本身的描述和記錄,但開創了以題跋文字形式著錄書畫作品的先河,不僅在書畫品論史上有重要的意義,在此時出現此種形式的書畫著錄也有很大的當下意義。
對書畫作品中題跋的記錄其實也變相地說明對書畫賞評的重視,從關注書畫本身更進一步發展至關注不同人的賞評題跋,很明顯,說明此時書畫賞評之風已經成形。同時,記錄不同觀者留下的題跋的同時也等于直接記錄著作品的流傳更替狀況,由賞至藏的活動過程已開始明確地以文字形式呈現。另外,題跋文字的記錄更如同為作品貼上了具體的標簽,此件作品曾有誰題跋,也直接為作品的真偽之辯提供可供參考的印證。不妨看《珊瑚木難》中的一例,如趙孟頫《水村圖》,其中記錄后人詩文詞題跋甚多,如錄顏天祥詩:“疏柳平蕪落雁飛,斷橋斜日釣船歸。江天萬頃秋如畫,一笑人間罪墨非。”①湯彌昌詞:“染秋云,圖澤國,野趣人游戲。能事何須,五日畫一水,重重楊柳,陂塘茅茨,籬落鱸鄉外,西風漁市,晚煙霽,恰有客乘扁舟,延緣度疏葦,欲訪幽居,宛在碧溪尾,浩然目送飛鴻,醉歌欸乃,溪光裹,亂山橫翠。”②通而算之,共計詩48,文8,詞5,另有賦1,可謂認真嚴謹。在記錄題跋的同時,作品的流傳也見記錄,如《米元暉大姚村圖目》中后跋:“此卷為吳城沈煦氏所藏,其先公舊物也,嘗一出示予,前年朝廷購求江南書畫,郡守劉瑀承時豪奪而得之,惜乎,徐仲山為錄一過,留沈氏,予就其錄本而又錄之,丙午四月十一日。”③
清晰記錄了作品的流傳,為后人提供可靠信息,對于《珊瑚木難》,人言其“凡所題品,具有根據”。《珊瑚木難》不僅在當時為書畫鑒賞者提供指導,今天來看仍具有相當的文獻資料價值。此外朱存理另著有《鐵珊瑚網》,比起《珊瑚木難》,此書更完整和清晰,是書有十六卷,分書品十卷,從石鼓文至元代書家,畫品六卷,從唐代閻立本至元倪瓚,依舊是對書畫題跋的記錄。此外,明中期亦有都穆的《寓意編》,楊慎的(1488-1559)《名畫神品錄》《法帖神品錄》記錄法書名畫,開啟書畫錄私人編著的趨勢。
2 晚明書畫著錄的變化與特點
明代書畫著錄從中期吳門畫派代表畫家的編著中可見明顯改變,如吳門文氏父子所編《文待詔題跋》《鈐山堂書畫錄》中記錄了更多的藏家和過眼信息,書畫著錄與書畫收藏流通產生了直接的聯系。如果說《文待詔題跋》還只是記錄文徵明題跋過的書畫及跋文,那么文嘉(1501—1583)的《鈐山堂書畫錄》則對書畫真跡做標記,是書為嘉靖四十四年(1565)奉旨查抄嚴嵩宅第時所做的書畫登記冊,作者對所收作品均加標注,標明收藏經過及真偽。因此此書更多記錄了作品流傳,文嘉的過眼經歷并審定真偽,更加具有鑒藏的價值,如記《顏真卿書朱巨川誥》:“一真一偽,真本乃陸氏舊物,黃絹縝密,真佳本也,但筆覺差弱,諸法皆備,亦不易得,別本云,黃紙上所書略無毫發動。”④再如懷素《自述貼》:“舊藏宜興徐氏,后歸吾鄉陸全卿氏,其家以刻石行世,以余觀之,似覺跋勝。”④整體來看,此錄更像是文嘉的鑒藏筆記,文嘉也在卷末言:“今日偶理重錄一過,稍微區分,隨筆箋一二傳諸好事,明窗凈幾一時一展閱,恍然神游于金題玉躞間也。”⑤
在文嘉時代,書畫的鑒藏流傳方興未艾,吳門書畫趣味正在流行,項元汴的書畫收藏正在積累期。就在同時,一時文壇領袖王世貞也同樣熱衷書畫,并收藏頗豐,其所錄《弇州山人題跋》與《文待詔題跋》屬于同類書畫題跋,在品論書畫之余,也兼記錄自己的所見經歷和流通情況,如跋《右軍三貼》:“余前得先右軍《大熱》《此月》二帖于昆山顧氏,乃黃琳美家物,轉入陸太宰全卿,顧氏其外孫也……”⑥這類題跋更具有私人記錄性質。
此外豐坊(1492—1563)編《書訣》,豐坊亦是書家、篆刻家,藏書家,鄞縣(今浙江寧波)人。《書訣》雖名“書訣”,其中亦列舉前朝書家畫家及書畫目錄。
徽人詹景鳳(1532—1602)著《東圖玄覽編》,該書四卷,明萬歷十九年(1591)成書,記錄平生所見書畫作品600多件,沒有目錄,書畫作品亦一起記錄,并不分類,所記作品從鐘繇書至宋元,其中也多記錄書畫的流向,如記王維《山陰圖》卷一:“后又米元章與宋元諸賢題跋,舊在吾歙臨河程氏,今聞鬻與河南,吾郡汪司馬曾見語余,余考摩詰無山陰圖,圖者顧閎中,周公瑾云煙過眼圖載,李伯時為米元章寫山陰圖,時有米及諸名人跋,今聞此卷歸云間董翰林思白。”①不僅記錄作品的藏家流向。《東圖玄覽編》最大的特點則是如啟功所言,“不斤斤于款識印章,而詳于筆墨法度”,使“鑒賞之道始不墮于空談”②,這對后來者大有裨益。
另有孫鳳編《孫氏書畫鈔》亦是記錄所見書畫,錄其題跋并個人賞鑒意見。孫鳳,字鳴歧,江蘇長洲人,書畫裝裱工人。居節(字士貞,號商谷,江蘇吳縣人)萬歷庚辰(1580)寫的跋語稱:孫氏雅善裝潢,頗喜讀書,有以古書畫求裝潢者,則錄其詩文跋語,積久成巨帙,名之曰《孫氏法書名畫鈔》。這也是唯一一本由書畫裝裱工人編撰的書畫著錄書,書畫裝裱人亦對書畫做錄,也可見此時的書畫流通之盛。
從這些書畫錄中,可見此時著錄的幾個特點:①幾乎看不到對以前書畫中的神逸能妙做出劃分。②在記述中自然會連帶記錄作品的流傳和藏家信息。這些書畫錄基本是記錄其所過眼書畫,或者偏向對作品的詳細解讀辨別,或者記錄作品題跋文字。③書畫著錄愈發具有私人書畫鑒藏記錄性質,體現在多為藏家自己編著自己的藏品錄或者是過眼書畫錄。
3 藏家著錄編著的代表
晚明私家書畫著錄的編著者多是藏家本人,具有較高鑒賞水準,比較能代表此類著錄和相對全面的有汪珂玉編的《珊瑚網》和張丑編的《清河書畫舫》《真跡日錄》。
汪珂玉,字玉水,號樂卿,自號樂閑外史,秀水(今浙江嘉興)人。其父愛荊,與項元汴交好,筑“凝霞閣”以貯書、畫,收藏富甲一時,又廣為搜羅,別置“蓮登草堂”“韻石閣”等,并就其所藏及聞見所及編成《珊瑚網》,崇禎間成書。汪珂玉在《珊瑚網》跋敘中言:“余也自幼趨庭,見先荊翁所藏書畫,心窮儀之,狀而于知交間,得掌錄名跡,以至老,積有廿余帙矣……此皆前賢遺墨,多未經壽梓。”③
《珊瑚網》所編也仍是記錄過眼書畫作品,間做品論。《珊瑚網》分法書題跋和名畫題跋兩部分,法書題跋24卷,其中包括藏家藏品和各家論書,名畫題跋亦24卷,也包括藏家藏品記錄和名家論畫部分,所錄法書名畫按時代更替,從魏晉至宋元。珊瑚網所錄題跋不少為同時期人的題跋,如項元汴、王世貞、文徵明、董其昌等人的跋文多見于此,更有汪珂玉自己對作品的個人記錄或記事,如記錄自己和同道如李日華、程季白等的交集,其中也有與董其昌的交集記錄,但汪珂玉似乎更關注作品和藏家,對書畫鑒賞的意見觀點并不多,更著重于記錄名跡。相比起來,張丑(1577—1643)著《清河書畫舫》則更能見藏者觀點,張丑的書畫鑒藏可謂早有淵源,其家族為書香之家,祖父和叔父皆進士,其父親張應文更是善文能畫,曾與王世貞書畫相交,家族中的長輩皆有書畫鑒藏的愛好,良好的文化氛圍使其在少年時代就顯現出與眾不同的書畫鑒藏觀念,成年后更全身心投入其中,與一時藏家韓是能、王穉登、文從簡、董其昌交。因此,張丑對書畫鑒藏可謂深入其中,頗多心得和經驗之談,其在《清河書畫舫》中對書畫鑒賞提出不少真知妙論,如論鑒定書畫:“鑒定書畫,須是細辨真跡改造,以定差等。多見俗子將無名古畫,亂題款識求售,或見名位輕微之筆,一律剜去題識,添入重名偽款,所以法書名畫,以無破損為上,間遇破損處,尤當潛心考察,毋使俗子得行其伎倆,方是真賞。”④
其他如論鑒賞書畫要訣,對不同畫家作品的觀點等皆能不從俗流,發一家之見,《清河書畫舫》可說是張丑不斷的書畫鑒賞實踐的成果集成,所收錄書畫自三國至明代書畫名家81人,成書于萬歷四十四年,其中也不乏提及董其昌及其書畫藏品和鑒定觀點。張丑雖不如董其昌的盛名,但其書畫鑒賞觀點更平實客觀,代表了一時書畫鑒賞藏家的水平。
大體而論,從這兩人的代表書畫著錄中,更加明顯可見此時的書畫著錄不僅對具體書畫作品翔實記錄和整理,對書畫作品的內容、題跋進行記錄,也會在其中加入個人的賞鑒評定意見,而這種記錄和意見的背后呈現出不斷的書畫交流和鑒藏活動的場景和情節,其中涉及的人物有的也可見史料,不少已經無從查起,可見此時的書畫在這些嗜好者之間的流傳具體而微的情景,這種記錄也源源不斷地呈現出各種信息。
到明末清初,吳其貞著《書畫記》更是一部記錄書畫交易活動的實錄,吳其貞(約1607—1681),安徽休寧人,出身書畫鑒藏世家,其父善鑒藏。《書畫記》所記錄為吳其貞從明崇禎八年(1635)起至清康熙十六年間所見所收書畫的事實狀況,所記錄作品范圍涉晉、唐、宋、元,其體例按時間順序,對作品的記錄依次為質地、保存狀況、藝術特色、款識、題跋、收藏印記及鑒定意見,最后記錄在何時何地與何人見此作品,間及對收藏者和交易者的簡單介紹。記錄多簡單扼要,如一則記錄,《趙松雪前后赤壁圖卷絹畫一卷》:“氣色尚佳,畫法不見其妙,全失松雪筆性,乃勝過無名氏所作,后人擬為松雪也,卷首程云南篆書題赤壁圖,后隸書書前赤壁賦。又翰林編修董璘等四人題跋,以上四幅觀于居安黃黃山家,黃山則黃石之兄,為士夫中賞鑒名家。”①
此書錄入了不少鮮為人知的鑒定者、書畫商人、書畫裝裱者的情況,為其他著錄所沒有。由于所錄作品皆注明時間,四庫編者在書畫錄提要中稱所錄書畫歷四十年之久,今日看,《書畫記》也可以看作當時書畫商的一部閱畫手稿。此外,文人筆記小品陳繼儒《妮古錄》也記錄所見的書畫、碑帖、古玩等,間以點評,屬于藝術類賞鑒隨筆。另外在晚明不少文人的文集中,也多有談論到書畫的鑒賞,如何良俊的《四友齋叢說》和焦竑的《焦氏澹園續集》中皆有對書畫的賞鑒。
4 結語
綜上,通過梳理明代中期到晚期書畫著錄編著,可見私人藏家或書畫愛好者編著的書畫著錄,已經成為一種新的趨勢,換言之,即晚明書畫著錄的編者人群主要是畫家、收藏家和熱衷者等個體人群。對書畫記述的詳盡、對作品流轉的記錄以及賞鑒觀點皆在記錄中有所呈現,從中不難看出,當時社會中書畫收藏的流行和藝術消費風氣的盛行,以及文人對閑適雅致生活追求的世俗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