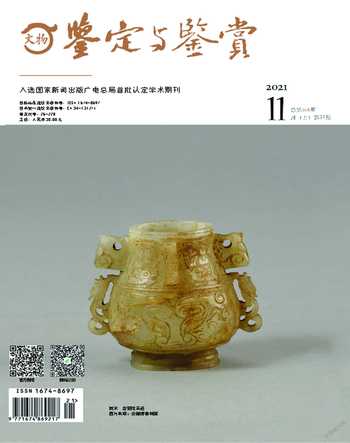從傳播學的角度淺析后疫情時代博物館的直播現象
李霞
摘 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來襲讓全國各大博物館在防疫狀態下相繼處于關閉狀態,閉館期間各大博物館在線上尋求傳播渠道,云傳播成為博物館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的一種新方式,博物館的直播現象層出不窮。2021年,新型冠狀肺炎正在悄然退出歷史舞臺,后疫情時代到來,這意味著博物館的傳播方式出現大變革。
關鍵詞:博物館;云傳播;直播現象;傳播模式
博物館自古希臘及公元2世紀的埃及,到14~16世紀的文藝復興時期,一直都作為珍藏、展示和研究藝術、知識與人類文明的殿堂,直到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打開盧浮宮大門,博物館才從僅供富人與貴族觀賞的珍藏室轉變為向公眾開放的文化機構,真正地做到社會化。①當今社會,博物館作為文物的收藏、保護、研究與展示的公共文化服務機構,以常態化的陳列展覽與臨時展覽向廣大受眾傳播歷史文化知識,使其感知傳統文化的獨特魅力。但是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與社交媒體時代的到來,博物館傳統線下的展覽模式已然不能滿足廣大受眾積極探索歷史文化知識的訴求,線上快捷方便的傳播模式深受青睞。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的來襲倒逼全國各大博物館提升技術服務,尋求線上傳播文化資源的渠道。近年來,抖音、快手等直播平臺的出現與迅猛發展,為博物館的線上宣傳展示提供了新的途徑與發展方向。
1 云傳播——博物館一種全新的傳播模式
據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2020年4月調查顯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全世界8.5萬座博物館閉館,占世界博物館總數的90%,其中近13%的博物館可能面臨永久性關閉。新冠肺炎疫情客觀上讓線上資源和虛擬技術與博物館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緊密聯系,數字技術在本次博物館抗疫中的作用得到了充分驗證,社會對博物館線上資源的認可度大幅提升。事實證明,疫情期間博物館的云傳播等線上傳播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1 云傳播的概念及定義
現如今,社會進入人工智能高速發展的新階段,大數據、云計算的出現,使傳統的傳播模式發生了質的變化,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渾然一體,實時性、交互性顯著增強。云傳播是基于云計算的傳播,是互聯網技術不斷發展的產物,沉浸式的VR體驗、AI智能實時傳輸、移動云直播等都是云傳播的基本傳播形式。②云傳播最重要的特征是實時性、交互性、平臺化和智慧化。直播作為云傳播一種基本傳播模式,已經被社會各界廣泛運用,方便快捷的短視頻平臺為云傳播的高速發展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
1.2 博物館對云傳播模式的運用
2021年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為“博物館的未來:恢復與重塑”。后疫情時代的到來,為博物館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等方面帶來了全新的變革,全球大多數博物館開始在線上尋求文化資源傳播路徑,以恢復到往常的工作狀態,但這種“恢復”是一種全新的文化傳播模式,數字技術將全面賦能博物館的自身發展,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物聯網、云服務、游戲化、沉浸式體驗、圖形數據庫、保存數字化藏品(如軟件)和數字設備(硬件+軟件)等都將應用到博物館的建設中。在疫情防控常態化下,全國各大博物館紛紛在“兩微一端”推出“云展覽”“360全景”“網上展廳”等,將線下展覽搬到線上,為廣大觀眾帶來全新的視覺饕餮盛宴,并取得了較好的傳播效果。除此之外,廣大博物館還與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合作,開通官方賬號,發布與博物館相關的小視頻,增強與網友的互動性,擴大傳播范圍。博物館對云傳播模式的應用已然成為日常宣傳的重點。
在博物館的云傳播中,我們應該注意到,博物館線上傳播不應局限于博物館的宣傳推廣策略,更應是博物館藏品和文化藝術資源的有效延伸,要真正具有教育意義,要更加關注博物館的包容性和對人們健康福祉的貢獻。
2 直播成為博物館線上宣傳傳播的常態化手段
文物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系民族精神,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財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博物館作為歷史的見證者與記錄者,更是傳承歷史文化知識的殿堂。博物館里的文物要想真正地“活”起來,不但要靠常規的陳列展覽、相關教育活動的舉辦以及文創產品的研發,而且移動數字直播技術的應用將為博物館提供全新的云傳播途徑。直播具有快速、便捷、互動性強等多種優勢,博物館利用先進的直播技術將線下的展覽在線上展出,還可以將館藏無法展出的文物展現在廣大受眾面前,讓受眾能夠獲取更多的歷史文化知識。博物館以展覽為依托,借助微博等社交媒體平臺,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的技術優勢,打造直播活動。2020年2月20日,為了豐富抗疫期間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發揮文物資源積極作用,國家文物局指導并聯合抖音平臺推出“在家云游博物館”直播活動。中國國家博物館、敦煌研究院、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館、山西博物院、廣東省博物館等九家博物館參與其中,各館派出強大講解員陣容,并邀請跨界嘉賓參與,直播講解本館重要線上展覽,讓觀眾足不出戶欣賞珍貴文物。這次直播活動一經推出,便受到了廣大公眾的關注與熱捧。“云游博物館”的直播活動微博話題閱讀量高達6億,討論量15.7萬。①本次直播活動成功地推動了博物館線上傳播手段的多元化發展,在此之后各大博物館的直播活動層出不窮,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得以廣泛傳播(圖1)。
博物館的直播活動受到廣大公眾關注與認可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2.1 直播打破了時間與空間維度的界限
在互聯網傳播時代,博物館傳統的線下展覽模式已不能滿足廣大受眾獲取文物知識以及主動探求文物背后歷史故事的訴求,有限的展館空間、規定的時間局限、灌輸性的講解讓許多來博物館參觀的觀眾無法對文物獲得全面的認識,大部分觀眾都是云里霧里、一知半解地離開。如今國內多家視頻平臺的快速發展為博物館的直播活動帶來了無限的可能。珍貴文物不再只是展館內的擺件,它們突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走進線上平臺,現場感極強,加上直播活動中講解員幽默風趣的風格,內容豐富,形式多樣,使廣大受眾能夠深入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與深厚的文化內涵。
2.2 直播受眾群體的擴大
將傳統歷史文化知識傳播推廣出去,是博物館義不容辭的職責。傳統意義上博物館的受眾群體大部分局限于博物館或文物知識的研究者、愛好者等,是一種“窄傳播”。而博物館的直播活動在移動手機端便可觀看,方便快捷的傳播模式讓更多的人能夠參與進來,尤其是吸引了當代年輕人的觀看,擴大了傳播范圍,增強了傳播效果。從某種意義上,它改變了博物館傳統的“窄傳播”模式,成了大眾文化傳播,人人都可以點進直播界面觀看,人人都可以參與互動,人人都可以發聲。
2.3 直播活動中交互性的增強
廣大受眾在博物館線下觀展只能通過參觀文物本身、文物的說明牌等方式被動地接受文物信息,講解員的講解也是一種灌輸性的知識傳播行為,受眾的信息接受方式被動且接收到的文物信息受限,無法深層次地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與文化內涵。直播活動在博物館信息傳播中的應用改變了這種被動的信息接受模式,它不是將線下的實體展覽原封不動地搬到線上,更多的是受眾可以通過直播界面的點贊、評論等功能發表自己對展覽的觀點與看法,與他人進行互動交流。有時直播中還設置有獎競答環節,主播與網友的互動讓文物知識的傳播更有效。此外,直播中講解員風趣多變的講解風格也平添了展覽的趣味性,一些專家學者的加入也讓廣大受眾更加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3 從傳播學的角度看,“博物館+直播”是全新的信息傳播模式
隨著后疫情時代的到來,博物館的傳播模式也在發生巨大變化。新冠肺炎疫情的到來給博物館帶來的既是機遇又是挑戰,全球大部分博物館在疫情期間都處于閉館狀態,如何能在關閉的狀態下將文化資源傳播出去,是博物館應該思考的問題。“博物館+直播”的傳播模式為廣大博物館所利用,開啟了博物館全新的傳播時代。從傳播學的角度看,博物館的傳播就是一個完整的信息傳輸系統。傳統意義上博物館的傳播是博物館(傳播者)以陳列展覽為媒介向廣大受眾傳輸歷史文化知識的過程。而博物館直播現象的出現改變了這種單一的信息傳播模式,我們可以從傳播過程構成的基本要素出發去探究博物館的直播現象。
3.1 博物館在傳播信息系統中擔負著“編碼者”與“解碼者”雙重身份
文物作為博物館中最重要的介質,考古發掘出來之后如果不經過考古人員的科學研究,從物質本身來說沒有任何意義。考古人員從文物出土的時代、質地、歷史價值等方面對文物進行信息的“編碼”,這些經過“編碼”后的文物陳列在博物館里,博物館工作人員在對其所蘊含的信息對觀眾進行“解碼”,這是在線下傳播過程中博物館充當了“解碼者”的角色。但是在線上的直播活動中,博物館既要充當“解碼者”,又要對文物信息進行適合觀眾線上接受信息的再一次“編碼”,完成對展覽的二次傳播。直播活動中的博物館的編碼過程是對觀眾進行科普文物信息,以達到公眾化、通俗化的效果。
3.2 直播平臺成為傳播系統中的媒介
直播平臺為博物館線上傳播建立優質的信息通道,傳播范圍廣,具有極強的互動性與現場感。直播還可以通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轉發形成裂變傳播,從而起到增強宣傳效果的作用。2020年值“5·18國家博物館日”之際,山西博物院在抖音直播平臺推出“壁上有乾坤、一眼越千年”北朝壁畫直播活動,本次直播觀看量有150余萬次,粉絲互動熱烈。①本次直播活動還通過山西博物院官方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擴大直播宣傳效果,是一次較為成功的直播典型。
3.3 展覽不再承擔傳統意義上媒介的角色,而是傳播過程中的訊息
在博物館的主流傳播模式中,廣大受眾通過陳列展覽來了解文物信息,展覽肩負更多的是闡釋與敘述的媒介使命,通過展覽將文物信息符號以空間視覺的形式表達出來。而在“博物館+直播”的傳播模式中,展覽成了直播過程中訊息的存在,是直播平臺的二次傳播。這種全新的傳播模式,不是將線下的展覽照搬到線上,而是通過講解員或者專家深入細致的講解,讓廣大受眾感知線下展覽中無法獲得的文物故事。
3.4 受眾從信息的受傳者轉變為知識的生產者與傳播者
在博物館的傳統傳播模式中,廣大受眾通過展館中藏品信息名牌、講解員的灌輸性講解來獲取文物信息,受眾是被動的、機械的。而在“博物館+直播”的傳播過程中,廣大網友是主動的、有主見的,能夠自己設置議程。他們通過點贊、評論等信息反饋渠道及時地表達自己的觀點與見解,在與講解員及其他網友的互動過程中重塑自我的認知模式,在某種程度上也引導著他人議程形成。
4 結語
博物館作為城市的文化性地標建筑,承擔著重要的文化傳播使命。后疫情時代的到來,給博物館事業的發展帶來的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數字技術的高度發展為博物館提供了多種文化傳播渠道,數字技術賦能博物館發展的理念已經被廣泛應用。值得注意的是,數字技術為博物館的文化發展只是提供了多種傳播平臺與渠道,博物館還是要堅持“內容為王”,以文物本身的歷史價值、優質的展覽內容為根基,給觀眾帶來高品質的優秀文化內容。“博物館+直播”的全新傳播模式需要博物館工作者從傳統的學術性論文思維轉變為以敘事為主的傳播性思維。此外,博物館還可以借助大眾媒體成熟的直播技術與設備為自身的文化傳播服務,進行跨界融合,從而擴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影響力。
參考文獻
[1]王宏鈞.中國博物館學基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1.
[2]潘東輝,龍禹濛.戰略布局 技術賦能 融合驅動—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云傳播創新實踐[J].新聞戰線,2020(12):60-63.
[3][佚名].山西博物院推出整月線上活動 慶祝“5·18”國際博物館日[EB/OL].[2021-10-21].http://www.shanximuseum.com/sx/archive/detail.html?id=7470.
[4]黃洋.博物館“云展覽”的傳播模式與構建路徑[J].中國博物館,2020(3):27-31.
[5]李紅.“直播+博物館”發展模式文化價值研究—以故宮博物院2020年清明小長假首次網絡直播為例[J].媒體觀察,2020,6(14):7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