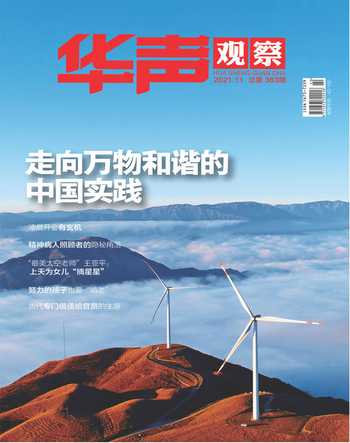監督拖延癥的生意人
鞏持平
監督員們明白,無論他們怎樣嚴厲,監督只是一種外力,是個幫手,要想真正自律,還得有內生動力。
“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既然這么多,不妨再拖拖。”這個段子,是對拖延癥的真實寫照。最近,在電商平臺上,提供“監督服務”的店鋪越來越多,考研考證、減肥吃飯、起床干活、遛狗接娃……生活中一系列需要定時定點防拖延的事,都可以到店鋪下單,找監督員搭把手,強力防溜號兒。
監督服務
記者到電商平臺,搜索關鍵詞“監督服務”,類似的商品還真不少。記者進入一家排名靠前的店鋪,打算體驗一下。
店鋪上架的主要商品只有一個——監督服務,分為“普通監督”和“強力監督”兩種:前者每天只能有3次提醒,售價每天6.66元;后者則是無限次的,售價每天15元。若想要持續監督,還能下單連續一周、一月的服務。普通監督一個月定價133元,強力監督是前者的3倍,一個月收費400元。記者下單了一天的“強力監督”。
很快,監督員呂宜波來加好友了。在呂宜波引導下,記者制定了從起床到睡覺的計劃,精準到每個小時要做什么事情。第二天,到了計劃所列的起床時間,呂宜波按約打來了叫早電話:“快點動起來!”“馬上去洗漱!”他接連發來幾個消息,語氣非常急切。他要求記者,到了計劃的時間,打卡拍照給他,按時匯報行程動態。若一不小心晚了幾分鐘,“連環奪命催”馬上就來。
監督的效果如何?服務是互動式的。呂宜波最擔心遇上冷漠的客戶。他們往往帶著獵奇心理,買一天體驗。監督員發一連串消息后,只收到“嗯”或“好”的回復。因為客戶積極性不高,他們只能做到最基本的按時催促,到點檢查任務完成指標,想要有進一步溝通很難。呂宜波曾經叫一位顧客起床,從早上9點45分開始打電話,一直打到中午11點30分,打了將近150個電話,才讓他起床成功。
花錢買來的監督員很難實行真正的懲罰。監督員們也明白,無論他們怎樣嚴厲,監督只是一種外力,是個幫手,要想真正自律,還得有內生動力。
生意門道
呂宜波的老板叫余本欽。23歲的余本欽剛上大四,在電商平臺開店,提供監督服務已經3年了。
最初,被監督的需求來自他自己。剛上大學,余本欽每天打游戲到凌晨三四點,導致上課遲到。他十分苦惱,試過很多方法,卻陷入“經常制定計劃,經常完不成”的怪圈。他買來研究自控力的書,得出結論,改變拖延癥,還得靠別人。搜索過程中,他發現了提供監督服務的店鋪,能花錢找人按照自己列下的計劃監督,他覺得是破局之路。不過當時,電商平臺上店鋪沒幾家,銷量最高的每月也就八九十單。
余本欽嗅到商機,2018年3月,他也開了家店,把監督服務的商品上架了。等了一兩個禮拜,有訪客,卻沒人下單。等了1個月,余本欽接到第一單,連續一周的叫早服務,因為“特別想把單子拿下來”,他只收了20多元。那年6月8日,早上6點多,店鋪有了第一個差評,客戶要求5點多鐘叫早,他沒起來,錯過了時間。
生意一直不溫不火,余本欽直接把店交出去,給別人打理。半年前,他才開始真正對這家小店上心——轉機發生在5月,突然有媒體聯系他進行采訪,“有一家媒體采訪了,就會有源源不斷的媒體上門,大家都在宣傳,說明市場前景不錯。”
余本欽從自己的傳媒公司選了5個人出來,都是男生,年紀比余本欽還小,有兩個是“00后”,組成新的小團隊。經營慢慢走上正軌,店鋪規模擴張得很快,店鋪后備的監督員數量,現在達到了近2000名,最多時,同時給400名監督員發工資。團隊核心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分工。余本欽是老板,掌舵的;陳穎瑞算是余本欽的副手,負責管理店鋪客服;金富軒負責派單環節,如果有客戶對現在的監督員不滿意,找他重新分配監督員;莊宇運營短視頻平臺,推廣店鋪產品;呂浩每天看各種數字,做數據分析;呂宜波是第一個全職監督員。
火爆之后
7月10日,莊宇在短視頻平臺發布了他們的第一個視頻。視頻中借用了“唐僧”的嘮叨人設,以“貧僧”的語氣,連續幾十條信息轟炸,勸誡“施主”不要拖延,抓緊時間學習。視頻發出幾天,反響不大。過了半個月,另一個號模仿他們的創意又做了條視頻,“一下就火了”。莊宇說,模仿者的視頻點贊量兩天達到60萬。這波流量到了電商平臺,他們的店鋪爆單。
呂浩觀察了那幾天的數據:“關鍵詞‘監督’的搜索次數是往常的3倍,將近2萬次。”監督員也獲得了大豐收,店鋪半個月發一次工資,接“唐僧單子”最多的監督員,5天一口氣接了200多單,最多手上同時有8個單子,還能個個秒回,工資達到了驚人的數字。
最近生意的確好做了不少。2018年和2019年,店鋪每個月只能接100多單;2020年上半年,店鋪月銷量漲到500多單;今年5月,店鋪每天都能接50單左右;到了7月份,銷量繼續上漲,日營業額過萬元。火爆的狀態持續到8月中旬。
問題隨之而來。銷量經歷了一波暴漲,店鋪擴張太快,管理上很多漏洞來不及填補。監督員的招募是最直接的。店鋪要求,應聘監督員的首先要買一天普通監督進行體驗,然后才有資格進群搶單。僧多粥少,2000名監督員,大多數時候,店鋪接的單量滿足不了監督員需求。有的監督員心有不滿,反而給店鋪寫差評,說這是一種刷單騙局。
監督拖延癥的商機也不再是秘密。不過在電商平臺上,這個行業不討喜。因為是虛擬商品,沒有實體產品,說不清楚賣的是什么,這樣的店鋪容易被懷疑打色情擦邊球。2020年以前,在電商平臺不定期的檢查中,余本欽的店鋪經常被下架。
新開的店鋪卻有很多。尤其5月以來,越來越多同類店鋪冒了出來。即使是7月中旬新鮮出爐的“唐僧”創意,也已經被模仿得遍地開花了。“這個行業沒有門檻,只要是想試試的,都能做。”余本欽一共開了3個店,上架的商品大同小異,服務缺乏核心競爭力,沒有技術壁壘,如果想拿到更多的單子,占據更大的市場份額,只能多開店,這樣客戶到電商平臺進行關鍵詞搜索,店鋪露出的概率更大。
“隨著行業逐漸被公眾熟知,不做改變,很難活下去。”余本欽認為,監督拖延癥的生意,營銷渠道和售賣渠道已經變了,他們要找到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不過,他還是看好這門生意,臨近畢業,他和團隊都打算在這個行業里做下去。“最大的希望是,我們的客戶購買一段時間的服務后,不再需要我們了。”
摘編自《解放日報》2021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