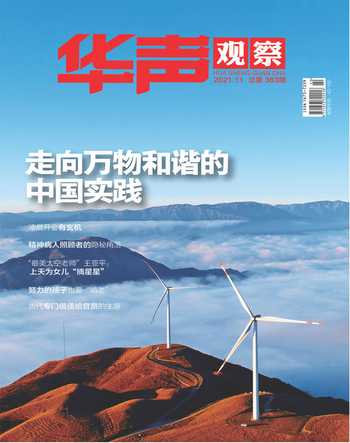避暑山莊:康熙帝的親民樂園
德霖
康熙帝有意通過避暑山莊的活動場景,拉近臣屬與帝王的關系。
相比于頤和園、蘇州園林這樣地處黃金地段的景點,同為中國古典園林精華的承德避暑山莊,算是《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里“熟悉的陌生人”。然而,在18世紀,它是整個大清帝國的重要權力中心,清朝宮廷每年約有半年時間移居此處。
美國學者魏瑞明的《龍脈:康熙帝與避暑山莊》一書,通過闡述避暑山莊的選址、營造及其象征意義,對康熙時代的政治愿望及其相應的藝術表現(xiàn)提出了新的見解。
四方的“拴馬樁”
避暑山莊又稱“熱河行宮”,始建于1703年,建成于1792年。它的面積相當于兩個頤和園,是世界上現(xiàn)存最大的皇家園林。1994年,避暑山莊及其周圍寺廟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
避暑山莊的營建,主要集中于清康熙、乾隆兩朝。如今,里面有樓、堂、殿、閣等各類建筑120多組。著名的有康熙帝于康熙五十年,以四字題名的36處景點,稱“康熙三十六景”;還有乾隆皇帝以三字題名的36處景點,稱“乾隆三十六景”。“一座山莊,半部清史。”避暑山莊見證過許多清朝歷史大事件。
今天我們在探討避暑山莊的過程中,除了造園藝術之外,另外一個不可忽略的地方在于:它的選址所代表的清代統(tǒng)治者的地理觀及其對中國歷史的意義。
所謂“龍脈”是我國古代堪輿學的重要術語,傳統(tǒng)堪輿學認為中華大地有三條龍脈,皆發(fā)源于昆侖,而泰山的龍脈是“中龍”之脈。為了從堪輿學角度論證清朝政權的合法性,康熙帝專門寫了一篇名叫《泰山山脈自長白山來》的文章,將滿族興起的長白山定性為泰山輸送風水能量的根源。
康熙帝在文中指出,沿著大興安嶺的走勢,從東北偏北,蜿蜒向南,穿過熱河,一直延伸到華山;同樣,阿爾泰山也經(jīng)由熱河,成為以長白山為終點的一道大弧線的西端。據(jù)此,魏瑞明認為,避暑山莊的位置可被解讀為四方的“拴馬樁”、清朝地理的軸心,它將關內(nèi)和關外聯(lián)結為一個整體。“龍脈”的背后,是康熙帝對安邦定國、四方和諧的種種考量。
私人化的社交平臺
早在1681年,清廷就在熱河地區(qū)建立了季節(jié)性狩獵營地,到了1702年8月,又開始在熱河流域開發(fā)一個永久性的皇家建筑群。
那年夏天,康熙帝在熱河停留了18天,接待了一批上層人士,走訪了周邊的鄉(xiāng)村,并進行了狩獵。8月下旬離開熱河后,皇帝立即向工部發(fā)布命令,指示測量師勘測并標示一塊可建造大型建筑群的土地。官員們也開始了招募工人和準備材料的工作,包括從山東和直隸招募勞工,從木蘭圍場采伐木材,考察工地周圍的山脈和巖石,以及建造窯爐等。
從1703年初開始,工部和內(nèi)務府承擔了以上各項任務。那年夏末,康熙帝花了三天時間前往位于熱河下營稍北一點的洪泛平原,也許是為了視察規(guī)劃工作的進展情況。宮廷文書將這處建筑稱之為“熱河上營”,這個名稱沿用到了1708年。
1711年,康熙帝親筆書寫的“避暑山莊”銅匾掛上了大門。兩年后,山莊外墻和附近的兩座寺廟也完工了。
有意思的是,幾乎與康熙帝同時代的印度奧朗則布、法國路易十四和俄羅斯彼得大帝,都把宮殿和園林景觀用作顯示自己權威的中心舞臺,突出強調(diào)等級制度,而避暑山莊則定位于皇帝與臣民親近和交流的場所,反其道而行之,刻意消除君臣之間的社會差異。
從1711年至1717年,康熙帝經(jīng)常會到熱河。夏天關外的活動季開啟后,康熙帝要在避暑山莊停留約三個月。隨后前往木蘭圍場,狩獵一個多月,又在熱河停留一段時間,再返回北京。到了農(nóng)歷十一月和十二月,康熙帝通常會進行一次額外的北巡,在此期間也要到熱河停留兩天。
康熙帝北巡時,避暑山莊是主要的統(tǒng)治中心,他每天要會見官員,處理國家事務或賞賜大臣。在木蘭圍場之旅中,會見基本停止,更多的是蒙古各旗的首領前來朝覲皇帝。這類活動的核心是賜費,即由皇帝單方面賞賜臣民。
在熱河,賞賜物品范圍很廣,包括馬匹等牲畜、肉類、水果、毛皮、紡織品、貴重金屬和其他精制物品。朝廷官員偶爾還會收到皇帝的墨寶、畫作、圖書或其他雅賞物品。在魏瑞明看來,就像皇帝把自己打到的獵物賞給臣下是變相展示其武功一樣,上述賞賜品既是物品的交換,又構成了其文才的公開表演。
康熙帝有意通過避暑山莊的活動場景,拉近臣屬與帝王的關系。1708年夏天,作為康熙隨行官員中的一員,張玉書前往熱河,參加了皇帝一年一度的夏季巡游,張玉書對此有過詳細描述:
康熙帝親自帶領客人從正門進入,翻過一座小山,來到位于行宮中心的湖區(qū)。人們走過一座小橋,來到了“芝徑云堤”,皇帝登上一座小亭子,向聚集在一起的客人介紹他新建的園林。
眾人繼續(xù)前往中心的島嶼,參觀了康熙帝的私人住所,然后在宮苑中游覽。他們從如意洲乘船渡湖,在樹木遮陰的岸邊徘徊,走訪了熱河山谷的溫泉。宮苑游覽中還有戲曲表演和宴會款待,臣子們獲準在那里享用御膳。
9天后,官員們再次前往游覽,這次是徒步穿越園林西邊的山麓。在康熙帝的帶領下,這群人體驗了宮苑的許多景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張玉書的原始敘述里,主客之間的親密感更加生動,可見,他非常享受這段備受優(yōu)待的游程。在紫禁城里,大臣們活動的區(qū)域主要是在外廷,且總是小心翼翼,而在避暑山莊,皇帝甚至允許他們一睹自己的起居住所,著實是前所未有的體驗。
從本質(zhì)上說,在張玉書對游覽行宮的體驗和描寫中,這個政治威嚴的象征性景觀被歸入了精英社交的場所,皇帝可以和志同道合的人士逗留于此,一起穿行于園林之中。避暑山莊拉近了君臣關系,起到了紫禁城所不具備的作用。
“無限次的邀請”
在中國古代,對皇家園林的描繪和描述相當罕見,避暑山莊卻是例外。
1711年,康熙皇帝正式啟動了一個項目:編纂《御制避暑山莊詩》。
康熙帝一生勤勉好學,博學多才,能詩善文。他親自從避暑山莊中選出36景,每景作詩一首,并命大臣為其詩逐句注釋。此外,每詩附一圖,可謂詩情畫意,相得益彰。
清朝顯然對皇家園林的管理更加嚴格。康熙年間,不直接為皇帝服務或不參與避暑山莊維護的人,想進入?yún)⒂^的可能性不大。《御制避暑山莊詩》的印制,使得更多人有機會了解這座皇家園林,相當于皇帝給了他們“無限次的邀請”。
《御制避暑山莊詩》并不是單純描繪這座宮苑,也不是單純再現(xiàn)在帝王引導下游覽熱河的體驗。“它本身就是一個獨特的景觀,通過它,宮廷構建了皇帝身份的綜合視覺呈現(xiàn),并試圖將其傳達給讀者。御制詩畫冊頁集一般慣例和創(chuàng)新形式于一身,從皇帝的角度傳達每一景的視覺、感官、情感、行為、知識和文化元素,創(chuàng)造一種親密感。”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2021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