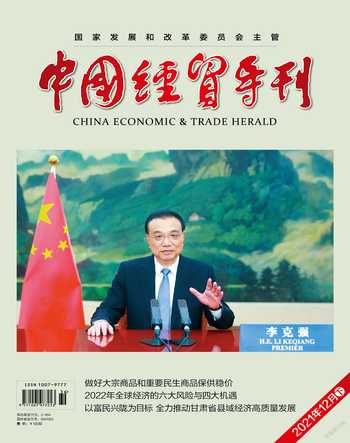金磚國家收入分化的教訓及對我國促進共同富裕的幾點啟示
張艦 賈若祥
一、印俄巴居民收入差距變化過程
(一)俄羅斯:20世紀兩次政體劇變使收入差距經歷了先變小后變大的U型模式
20世紀20年代至80年代末:低工資高就業的平均主義就業體制使貧富差距明顯縮小。蘇聯時期采用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相對單一的所有制結構決定了居民收入與來源以職工工資和集體農莊莊員勞動報酬為主,極大改變了沙俄時期的收入分布形態。1905—1929年,最富裕的10%群體收入總額占比從47%降至22%,最富裕的1%群體收入份額從20%下降到4%—5%,收入最低的50%群體和中等偏高的40%群體的收入份額分別從17%、40%提升到30%、48%。斯大林去世后,蘇共高層在經濟上逐步采取相對自由的“去斯大林”政策,在不涉及國家產權變更條件下適當允許非國有經濟成分存在。1956—1968年間,勞動報酬增速略有提升,且收入最低的50%群體收入份額從24%進一步升至32%。
20世紀90年代后:經濟轉軌提升了居民絕對收入水平,但造成群體收入分化程度驟然上升。蘇聯解體后,俄羅斯認為傳統國有制不能與市場機制相結合,向市場經濟過度必須解決所有制問題。隨后私有化進程的快速推進、私營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居民貨幣收入結構中勞動報酬占比下降、資本等其他要素收入占比上升。1989—2016年間,全體居民人均收入增長了41%(年均增速為1.3%),但分群體看,收入最低的50%群體經歷了長達27年的收入負增長,收入降幅達20%、年均降低0.8%。中等偏高的40%群體雖然保持正增長,但27年間增幅僅15%、年增速0.5%。相比下,最富裕的1150萬人(10%)人均收入年增速為3.8%,增幅高達171%。這一時期俄羅斯宏觀經濟增長中99%的份額被最富裕的10%群體拿走,僅留下1%給剩余的90%人口(1.03億人)。
(二)印度: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政策轉向使居民收入差距從逐步縮小轉為逐步擴大
20世紀40至80年代:土地制度改革、推進國有化、支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等使收入分配格局得到顯著優化。1947年印度主權獨立后,廢除了土地的柴明達爾制,削弱大地主對土地的高度壟斷,以帶動農村經濟發展。通過在50年代初將鐵路和機場國有化、70年代中期將石油部門國有化,使公共部門獲得了大量私營部門轉移來的財富,富裕階層隱性資本收益受到制約。推行個人所得稅高累進稅率,1965—1973年間最高累進稅率從27%升至98%。通過稅收減讓、信貸支持、利率補貼等措施鼓勵私營部門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吸納勞動力就業。系列措施影響下,印度最富裕的1%群體的收入份額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21%降至50至60年代的10%—12%,而后進一步降至1983年的6%,達到自1922年有稅收記錄以來的最低點。同期最富裕的10%群體收入占比為30%,收入最低的50%群體和中等偏高的40%群體的收入份額分別為24%和46%。
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以自由化為導向的經濟改革使居民收入差距由降轉升。這一時期市場開放和貿易自由開始成為決策者關注的議題,《第七個五年計劃(1985—1990)》推動快速放寬市場管制、加大外債舉借、提升進口規模,同期個人所得稅最高累進稅率從70年代的97.5%降至80年代中期的50%。至1990年,收入最高的10%群體的收入占比提高至34%,較1983年提升4個百分點;中等偏高的40%群體和最低的50%群體的份額則下降2個百分點,分別為44%和22%。
20世紀90年代以來持續“去國有化”進一步加劇了收入不平等。1991年后,印度將私有經濟發展擺在核心位置,通過不再保留或注銷部分國有企業、收回公共部門投資、放松市場管制(石油、糖、化肥)等推動私營部門更深程度介入經濟重要領域,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進而提升,同期金融、保險、房地產、IT等受資本追捧產業快速發展,增速在1997年超過制造業部門,農業發展被嚴重忽視。受此影響,1990—2014年間,最富裕的10%群體收入份額由34%攀升至56%,中等偏高的40%群體收入份額由44%降至32%,最低的50%群體收入份額由22%降至16%左右。
(三)巴西:二戰以來居民貧富分化長期存在并持續擴大
1945年至20世紀80年代,外資依賴和“進口替代”引起的生產資料集中使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二戰后的20年里,巴西高度依賴外國資本來解決國內資本短缺,政府則通過大量增加公共債務和通貨貶值來抵償,1957—1964年間通膨率從7%上升至92%,嚴重影響社會財富分配。1965年軍政府上臺后,又將巨大的資源投入到發展“進口替代”所需的產業,社會財富被大量的集中到少數人的手里。1960—1983年間,10%最富裕的群體的收入份額從39.6%上升至46.2%,收入最低的50%群體的份額則從約18%下滑至不足12%。
1985年以來,經濟自由化改革方案的推行進一步加劇了貧富分化。軍政府倒臺后,開啟“再民主化”的巴西在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義思想浪潮中,通過了涉及金融自由化、投資自由化、貿易自由化、國有企業私有化、壓縮公共福利、減少政府開支的雷亞爾計劃。一系列措施尤其是金融自由化加劇了巴西宏觀經濟調節的脆弱性,為維持較高外匯儲備,巴西必須吸收更多外資,這進一步造成外貿赤字增加,壓縮了中小企業生存空間,失業率從1995年的4.6%快速升至2000年的9%,社會向下流動趨勢凸顯。至2015年,巴西最富裕的10%群體的收入份額達到55%,40%中等偏高的份額為32%,收入最低的50%群體僅占有12%的份額,尚不足最富裕的0.1%群體(僅14萬人)14%的收入份額。并且全國范圍內沒有成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2015年全體居民人均收入為37100雷亞爾,但收入最低的50%和中等偏上的40%群體的人均收入分別僅有為9200雷亞爾、30500雷亞爾,反映出90%的居民人均收入達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相比下,最富裕的10%群體人均收入達207600雷亞爾,為全國平均水平的5倍。
二、印俄巴西居民收入分化的主要教訓
(一)快速推進自由化改革造成財富分配失衡
三國在20世紀80、90年代在經濟、產業、城鎮等體系尚不健全的情況下,均將國有經濟私有化、貿易投資自由化、金融資本市場開放、匯率制度改革等置于主導位置并迅速推行,在部分提升了經濟效率、收入增速的同時,由于忽視了社會公平,造成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俄羅斯在經濟轉軌中快速推進私有化、放開資本市場,給一些原國有部門“內部人”同國內外大資本、少數權貴里應外合吞并國有資產的機會,體制的不健全也使得二元市場結構下國家壟斷部門更易獲取壟斷租金,社會財富日趨集中。印度在80年代后將大量公有學校推向市場造成私立學校規模快速擴張,聚集優質教育資源,競相提高教育費用。巴西過快推行金融、貿易、投資自由化致使國內許多中小企業經營失利破產,沖擊就業。匯率管制放松削弱了本就脆弱的金融調控能力,造成的物價波動又進一步作用在貧富分化上。
(二)側重資本優先積累造成經濟增長與結構改善脫節
俄羅斯在發展中存在明顯的資本積累優先問題,長期將資源配置向能源、重工業傾斜問題,其產值比重異常高,但輕工業等遭受嚴重忽視、比重仍處于典型低收入國家水平,經濟發展找不到新增長動力,行業間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巴西由于在發展中面臨資本積累低的阻礙,各屆政府均將擴大大型重工業企業資本積累作為重要著力點,造成社會財富更多向企業家和少數權貴集中,依靠勞動報酬為主要收入構成的普通勞動者從經濟發展中分享的利益被大大壓縮。2001—2015年間,盡管巴西居民勞動報酬差距有所收斂,最富裕的10%群體勞動報酬占比從47%降至44%,但收入占比卻從54%升至55%;最富裕的1%群體在2015年所獲勞動報酬份額為14%,總收入份額卻高達28%。同期全體居民收入增長額中57.8%被最富裕的10%群體獲得,收入最低的50%群體只分享到了16%的增長額。
(三)土地占有長期不均和農業政策失調
巴西在現代化進程中一直未對大地產制進行徹底改革,且由于政府為利用農業出口來積累資本發展民族工業,國內小農業長期受到忽視。1964—1979年間軍政府向大莊園主提供了大量的、廉價的農業信貸使其從事大規模的出口作物經營,客觀上鼓勵了大莊園主進一步集聚土地。過程中大量失地農民被迫移居城市,造成城市人口急劇膨脹,20世紀50至80年代,圣保羅人口由250萬激增至1350萬、里約熱內盧由290萬增至1070萬。然而政府對勞動密集型產業重視的不足使得城市無力創造充足就業崗位,致使大量進城農民淪為城市貧民、失業群體和流浪人口,許多大城市貧困人口比例高達30%—35%,反過來又加劇政府財政負擔、引發社會治安問題。印度在進行經濟自由化改革后,農業發展和農民利益也長期受到忽視,農業總資本占全部經濟總資本從70年代的超15%降至90年代末的不足6%,農民從金融機構可獲貸款越來越少,但同時農業投入品價格上漲迅速,造成占總人口近2/3的農村人口的收入提升受到嚴重抑制。
三、對我國促進共同富裕的啟示
(一)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夯實共同富裕財富基礎
面對大變局疊加大疫情下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是邁向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礎,必須將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與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二者有機統一起來。持續推動國有經濟布局結構調整優化步伐,推進戰略性重組。加快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探索各種所有制經濟深度合作的途徑和辦法。建立覆蓋全部國有企業、分級管理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國有資本收益。持續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破除各種“玻璃門”“旋轉門”“彈簧門”。把握民營經濟體制靈活優勢,推廣員工持股制度,完善股份制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的分紅制度。
(二)堅持人民至上,強化政府社會職能
突出經濟增長與人民對美好生活需求之間內在聯系,努力建設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把政府社會職能、公共責任納入國家經濟發展總體框架,堅持政府的適時干預,消除經營壟斷、整頓分配秩序、強化稅收調節,大幅增加民眾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機會。重視資產價格波動和教育、醫療不合理收費對中低收入家庭生活的影響,糾正住房、教育、醫療改革中過度市場化的傾向。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進一步完善養老、醫療、住房保障體系,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三)堅持城鄉融合,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真正把農村發展和城市發展擺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強化“一盤棋”格局,加快改革城鄉分割的制度設計,突破制約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的體制機制障礙,保障農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加大要素配置、資源條件、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支持。充分認識鄉村振興中農村與農民關系不僅局限于農業生產,突出農民在鄉村建設中的主體地位,改變地方政府“大包大攬”做法,鼓勵農民積極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和民生領域事業,從鄉村振興的“大蛋糕”分配中獲得更多收益。
(四)堅持勤勞致富,促進更高質量更加充分就業
共同富裕的實現要鼓勵勤勞致富、合法致富,暢通向上通道。要瞄準技能人才、科研人員、小微創業者、高素質農民等重點群體,完善有針對性的就業支持制度,建立促進創業帶動就業、多渠道靈活就業機制。健全就業公共服務體系,著力緩解經濟轉型進程中出現的結構性就業矛盾,提高重點群體的收入水平,使其盡快進入中等收入群體行列。完善教育、科技、醫療、文化、設計等領域退休后返聘機制,讓有繼續工作意愿的資深專家和高級人才發揮余熱。
(作者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地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