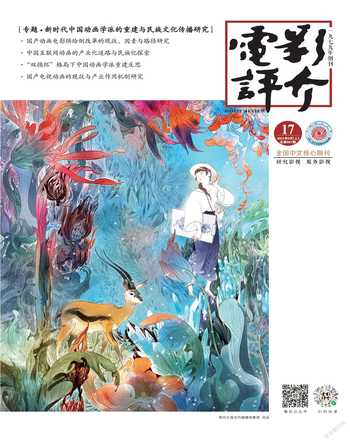自反與修復:好萊塢歌舞片中的懷舊書寫
張蘋秋 黃洪珍
當早期電影人探索合適的拍攝對象時,運動著的舞蹈身體自然地進入了動態捕捉的視線。盧米埃爾兄弟1896年短片《蛇舞》(Danse Serpentine)以單鏡頭固定的方式記錄了現代舞先驅洛伊·富勒(Lo?e Fuller)的曼妙身影。由此可看出,被納入早期電影創作的舞蹈,不僅僅是彰顯影像動態美學策略般的存在,更因其趣味性成為創作者邀請觀眾參與感受電影媒介表現力的暗語。而現場配樂則是具有節奏韻律感的音樂藝術樣式對視覺表現與共情經驗的一種補充。直到20世紀20年代后期有聲技術的出現,歌舞表演才從分散的吸引力元素逐漸演變為相對固定的表達范式,開啟了歌舞類型的生命周期①。
好萊塢歌舞類型歷經了較為漫長的“演化”,自20世紀20年代末建立起形式慣例;三四十年代在藝術與文化表達上日趨達到成熟;50年代從坦率的透明敘事發展至自覺的形式主義;60年代大片廠制落幕,出現內核與形式上頗具創新的反歌舞片(anti-musical),歌舞類型進入中興;進入21世紀,平靜中偶有佳作的后經典時代。
近年來,少數原創作品與大量改編、翻拍作品組成了好萊塢歌舞片市場。本文針對歌舞片創作中的懷舊現象展開研究,延續簡·福伊爾關于歌舞類型中的自我意識與娛樂神話的關系討論,對當今懷舊歌舞片的功能進行定義。在追尋“永恒回憶”的單向度懷舊中,解神秘化與再建神話間的不可分離性是否被消解?如果答案是否定,娛樂神話在何種程度以哪種方式延續?
一、銀幕上的懷舊
懷舊(nostalgia)起初作為思鄉癥出現在十七世紀的醫學手記中,它源于一種時間和空間位移變化所帶來的親近感喪失的主觀體驗。隨著現代社會不斷加速發展,人們逐漸打破線性發展的迷思,對時空的理解也變得更為深刻與多元。從外太空到網絡虛擬世界,人類認知的邊界被不斷打開,集體記憶不再附著于“實在的土地”,那些深深影響“我們是誰”的元素被選擇性地以碎片形式在擬像中被重新建構。如詹明信所言:后現代文化中以空間而非時間為感知基礎的文化邏輯盛行,導致深度感的消失與主體的死亡,改變了人們對于傳統歷史時間的經驗。[1]
變調的時間在歌舞類型生產創作中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形式肌理上,通過技術的返祖,采用黑白默片、膠片攝影、寬銀幕電影(CinemaScope)、特藝彩色(Technicolor)等手段,重現經典好萊塢時期影片的視覺體驗,如文森特·明奈利寬幕電影中瑰麗的場景,《紅菱艷》中獨特的色彩韻味。這些自發光屏幕無法比擬的視聽體驗,某種程度上修復了影院觀影的感官記憶,用以對抗流媒體的沖擊。結合20世紀50年代制片廠加大技術開發以面對來自電視業的挑戰,經驗層面上的懷舊便擁有了更豐富的意指內涵。
其二,融入復古的內容元素,使影片充斥遠離現時代特征的符號能指,電影《巴斯特·斯克魯格斯的歌謠》(2018)重新將牛仔歌舞片(Singing Cowboy Film)帶入人們視野,《愛樂之城》(2017)展現爵士樂、踢踏舞等一系列好萊塢黃金時代的遺留物。
其三,經典文本的再生產,一方面是經典美國青少年歌舞片的翻拍(Teen Musical),例如《油脂》(2016,福克斯)、《渾身是勁》(2011,派拉蒙)、《辣身舞》(2017,獅門),以及斯皮爾伯格導演的《西區故事》(2021,二十世紀福克斯)。另一方面,以迪士尼為主掀起的動畫真人化改編熱潮,《美女與野獸》(2017)、《阿拉丁》(2019)、《獅子王》(2019)等作品雖口碑參半,但都進入當年全球票房前十①。對源文本的轉譯,體現出懷舊不僅僅是一種“歷史的心緒”,更是基于投資成本與風險等要素考量的市場行為。
這些見諸于歌舞片生產創作的特點,成為懷舊情緒可見的顯影,銀幕皮膚背后,消隱的未來形態也對把握懷舊起著關鍵的作用。“懷舊耦合浪漫情感,回蕩著離鄉與思鄉的傷春悲秋,復古則用濃重的憤世與不羈去調和著懷舊的那些愁緒。”[2]如果說復古有著復蘇古典形式(revival)的積極意涵,懷舊本質上是一個缺失現在與將來時態的回望、倒帶之旅。例如以四季展開線性敘事的《愛樂之城》,一段未果的感情為主角的懷舊旅程提供動力,結合弗萊在《批判的剖析》中所認為的人類的生命運動同自然界的規律具有同構性,“冬”“春”“夏”“秋”四個部分暗示著主人公的事業與愛情。“冬”兩人處在人生低谷,沒有擦出火花的初遇,承接著好萊塢精神喜劇般的歡喜冤家開始;“春”愛意萌動,關于萬物復蘇的神話,狂熱的贊美詩和狂想詩的原型;“夏”熾熱的愛戀,喜劇的原型;“秋”的分歧之傷,也是理想愛情枯萎凋謝的時刻,悲劇和挽歌的原型。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心靈軌跡關聯懷舊敘事中常見的“伊甸園”式存在狀態,敘事最初平衡的原始狀態類似于懷舊的對象,當失去或改變時,兩者都會激發人們尋找并試圖重新奪回比現在優越的時間和地點的機會。[3]若敘事結構是從一類結構到另一類結構的運動的過程,《愛樂之城》的四季循環敘事結構中,冬春是上升的運動方向;春秋季代表則是一個下降的過程,最終呈現便是一個向內的下沉漩渦,這也從本質上說明影片的懷舊取向。
二、延續的娛樂神話
歌舞電影以因果邏輯鏈條為主導,它先向人們展現普遍的感知—運動影像,劇中的人物通過歌唱舞蹈作出反應,當純描述懸置了敘事,個人的運動轉變為世界運動,從而超越了運動情境,進入“夢中夢”。該敘事的代表性結構便是后臺歌舞片,其滿足邏輯真實性要求的同時,歌舞表演者的職業屬性直接指涉電影本身所代表的娛樂造夢文化。因此,“就寬泛的意義而言,一切藝術歌舞片都是自我指涉的,但是亦有一些情況,即某些歌舞片比其他歌舞片表現出更大程度的自我意識”。[4]
不同于一般人們所認為的在美學或政治上有所想法的自反性影片,通過對構成影片自身表意符碼的展露產生間離,從而解構傳統電影敘事的封閉虛幻空間,引起觀眾反思。歌舞片中的自反性,不是一面映照出觀眾觀看事實的鏡子,而更像是棱鏡,折射出幻想的多彩電影世界。“各方面看自體反思型歌舞片都是保守性本文”。[5]簡·福伊爾將自體反思型歌舞片與娛樂神話聯系起來,認為主體暴露的非神秘化處理是建構娛樂神話的重要力量,并將娛樂神話細分為三個范疇:自發性的神話、融合的神話和觀眾的神話。
反觀當今歌舞片,在單向度的懷舊中,主體不再依賴于在二元對立框架中確認自我,而是在自反式回溯與放大進行媒介自身與社會意義上的彌合。當主體從過去的生活之流中看到他的統一的整個生活的時候,內心和外部世界的二重性才能得到消除。[6]因此,娛樂的神話并未終結,解神秘化與再建神話間并未分離,只是發生的機制有了新變化,指向物也從歌舞類型,拓展至好萊塢本身。
(一)類型歷史的自我指涉
早期好萊塢歌舞片,熱衷于創造豐富、多樣和驚奇的觀看感受,強調多元的聚合而非整合一體,這與美國大眾娛樂傳統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百老匯、齊格菲歌舞團、夜總會、馬戲團等場景,成為早期歌舞片的主要靈感來源與敘事空間。即使是通常被認為本質上的電影風格的古典好萊塢時期歌舞巨匠巴斯比.伯克利作品,其中對美國民間藝術美學的繼承也是顯而易見的,主要是19世紀的大眾娛樂傳統:P.T.巴納姆的美國博物館、吟游劇、雜耍、滑稽戲等,“它們提供了一種從根本上不同于那些面向統一、連續和一致的現代形式的娛樂方式”[7]。電影《馬戲之王》(2017)講述的就是“馬戲團之王”P.T.巴納姆的傳奇故事(P.T Barnums American Museum),“奇觀傳統”的鼻祖,某種程度上也是歌舞片風格的“祖師爺”。影片混合雜技、歌舞等充滿戲劇吸引力的表現元素,再現了好萊塢歌舞片中“過剩”的美學傳統。
電影《滑稽戲》(Burlesque,2010)講述能歌善舞的小鎮女孩在洛杉磯一家名為“滑稽戲”舞廳的追夢故事,片名暗含了對歌舞類型美學傳統來源的回顧與“致敬”。影片中女主角在舞廳的歌舞表演從最初的對口型到真正的聲音演出,該細節處理也隱喻了歌舞片類型所從無聲到有聲所經歷的發展歷史。
關于電影制作過程,展現自身類型發展歷史,揭露電影工業機制的影片并不鮮見,《雨中曲》《篷車隊》等都是很好的例子,但它們卻不是懷舊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自體反思型歌舞片以一種“自嘲”的態度展現自身歷史,儀式性地闡明其在觀眾精神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篷車隊》(1953)開頭所拍賣的禮帽與拐杖,指涉主演阿斯泰爾演出的歌舞電影《禮帽》(1935),而結尾段落,眾人齊聲向主角歌唱,并發表一番情深意重的言論,簡·福伊爾評論道:這是該(歌舞)類型對自己的(以及好萊塢的)經濟上的死亡和禮儀上的再生的慶祝。[8]該類影片通過設置大量的價值對立(包括新舊),辯證地肯定了歌舞類型合理性,但對于過去冷漠的態度,讓該展現面向未來。而近期歌舞電影中的類型歷史自我指涉則成為影片對本身連貫系統的自證。
(二)影像創作機制的暴露
早期歌舞片為突破舞臺這一限制表演場域,將敘事的情感引導功能最大化,借助同周遭事物的聯系,形成有機、自發的表演。這種對自身夢幻屬性耿耿于懷,強調沉溺,將幻想與現實進行縫合的想法,在近年的歌舞片中似乎被淡化,內化成特定的拍攝規則技巧,而不是理念宗旨。電影《畢業舞會》(Prom,2020)中,借一名歌舞劇愛好者之口,直白地唱出歌舞片弱敘事邏輯、強情感體驗的特點,以及帶人們逃離沉悶乏味的日常生活、遠行并治愈的本質,“當電影里開始舞蹈時,并沒有人想知道為什么”。舞蹈不再是勾勒世界的夢幻運動,它成為走近另一個世界,也就是說走近另一個人的夢幻或過去的唯一方式。[9]
經典后臺歌舞平行敘事,在浪漫的個人生活與殘酷舞臺現實之間找到一種平衡。成功的歌舞展演往往促進情感的發生,伴隨著矛盾的解決,觀眾也隨之進行情感認同。近年來,融合的神話出現了新的變奏:問題在音樂結束后也并未消失,通過影像機制的自我暴露,呈現一虛一實的兩重情境。從現實來看,歌舞片的融合神話似乎失效,因為電影中反映了相愛的兩人最終分離,或是無法改變宿命般的結局。然而在電影機制暴露后所提供的替代性結局中,歌舞依舊發揮著修復現實裂痕、治愈人心的功能。
影片《愛樂之城》在主人公面部特寫鏡頭后戛然而止,現實與烏托邦的張力是對前一幕幻想情節所蘊含情感的無限增殖。流淌的主題音樂在偶發性時刻將人們帶入一個超現實、心理的夢中夢世界,鏡頭緩緩向前推移,正反打中燈光逐漸暗淡與聚焦,模擬精神回憶過程從而實現戲劇空間的過渡。鏡頭拉遠,男女主人公攜手穿過正在進行拍攝的攝影棚、好萊塢片場,落座在黑暗的劇院中,銀幕上閃動著的膠片顯影,伴隨早期默片時代的倒計時。人們在模糊卻又異常動人的影像中,看見了另一種只存在在光影中的皆大歡喜。這種自反的姿態,清晰地展現出電影作為造夢藝術的特征,將觀眾對娛樂業內部的好奇轉換為對電影藝術魅力的加持;亦虛亦實的處理也一反傳統類型模式的平鋪直敘,為敘事空間注入余味,使影像意義之維呈現更豐富的樣態。
(三)文本鏈的生成
懷舊熟練運用文化詞匯,讓意義關系在文本鏈中滑動。歌舞電影的文本間性體現在對好萊塢“遺產”的繼承之上,游走在各式各樣的類型文本中,重申“永恒的記憶”,其表征為:1.重復使用熟悉的音樂、舞蹈動作、場景,例如科恩兄弟在《凱撒萬歲》(2016)還原了埃斯特·威廉斯在《出水芙蓉》中的水上歌舞,以及吉恩·凱利在影片《起錨》(1945)中的水手舞蹈。《愛樂之城》兩人星空共舞的創意出自《紅磨坊》,而拍攝場景的天文臺正是電影《無因的反叛》中結尾段落的發生地點。2.對電影文化地理空間符號的著重描繪,《滑稽戲》中對對日落大道的強調,以及歌舞片中常出現的片場、藝術影院,印證了懷舊與人造精神家園千絲萬縷的聯系。如《愛樂之城》開篇,高架上交通堵塞中的集體歌舞,昭示活力四射的音樂喜劇回歸的同時,暗示電影所體現出濃厚的城市文化,但這并不是現實空間維度上的“應許之地”,而是以好萊塢為代名詞的虛幻光影世界。
電影百年的歷史形同生命的輪回:不由人意地出生,持續獲得各種榮譽,在過去十年中開始顏面盡失、出現不可逆轉的頹勢。[10]在數字與多屏時代剛剛開始時,蘇珊·桑塔格已尖銳地表達了對電影藝術未來的憂慮。在這一維度上,當今的懷舊對于電影來說,不僅僅是重現沉沒的“泰坦尼克”或紙醉金迷的爵士時代那么簡單,它攜帶著修復影像生成裝置的信念,試圖重喚傳統的感官體驗,強調電影作為可能性的藝術,并在不同時期好萊塢遺產碎塊基礎上,建立起一座電影的神廟,以此實行“自救”。“后現代主義”的自反書寫路徑,讓源文本在不斷交織中煥發新生命,但懷舊的傾向讓原本通過補充、肯定或反駁所進行的文本對話,成為摹仿邏輯的犧牲品。
三、想象性的修復
曾經,懷舊被視為一種歐洲的疾病,晚近成熟的國家依就某種反懷舊的前提發展自己的身份,以此躲避歷史的負擔,19世紀早期的美國人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的民族”,只生活在現在,不需要過去[11]。也因此,電影最初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臨時的身份建構工具,一種面向未來的媒介,試圖代行傳統和宗教在描繪理想社會前景、整合價值觀中所起的作用。“電影不但向這些人展現他們曾所是的樣子,而且讓他們必須回憶這就是他們所曾是的樣子。”[12]福柯曾討論權力在此過程中所留下的痕跡,并表示電影對于“大眾記憶”至關重要:“應該占有這個記憶,規訓它,支配它。”
歌舞片中常見的有關個體奮斗、社群融入、精英藝術與流行文化融合的主題,其精神內核源于講述外來移民在平等新大陸上融合與奮斗的美國夢。一個人只要有抱負、奮斗和美德,那么他終歸會獲得成功。這樣一來,成功是衡量好品質和努力工作的標準,然而“如果成功意味著美德,那么失敗就意味著罪行”。[13]歌舞片高假定性、閉合的特質“合法化”了新自由主義敘事中無法言說的隱秘因子。
實用主義傾向隱于娛樂生產背后,類似懷舊電影的出現,對現實進行“再編碼”,以實現結構性裂痕的修復。然而該修復因其浪漫化的傾向,在社會意義上往往是虛幻、斷裂的,粗暴地提取某些符號以完成敘事,缺乏對系統整體準確性的描繪。如《愛樂之城》中固執地持有“爵士樂原教旨主義”的主人公,拒絕與流行音樂合流,向往回歸最初的純粹爵士樂。如果稍微了解一些爵士音樂史,便知道爵士樂與黑人血淚史的深厚淵源,當黑奴被販賣至美洲,他們用歌聲抒發苦悶,爵士樂即興的音樂特點在某種程度上便是對黑人經驗的變形和模擬,“麻煩是布魯斯的起源,如果你是一個奴隸,那么語言、食物和生命中的一切都是一種‘異在,如果你不能隨機應變,你就可能會深陷麻煩”。[14]因此,真空化地表達爵士樂的復興,無法消除歷史的傷疤,更無法解決社會種族歧視的問題,對歷史“田園牧歌般”的處理與挪用,讓人們產生關于過去的在政治上是完全合理正確的錯覺。這種沉湎于修復破碎、空缺的“小寫懷舊”具有媚俗、美化罪惡的傾向。[15]影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后種族主義的隱秘與日常性,扁平的白人男性救世主形象,也讓電影所能涉及的反思停留在一廂情愿的想象之中。
懷舊歌舞片以其極強的娛樂屬性,輕而易舉地調動起觀眾的情緒,以供消費的懷舊電影大大削弱了觀者批判思考的能力,而創作者的懷柔政策也讓修復之路走向未知。看似多元,實則是遵照著一定程式拼貼,無限復制的單質結構,某種程度也成為時代的表征,懷舊淪為一種政治修辭。鮑曼在其生前最后一本書中也談到逆托邦(retrotopia)可能帶來的危險,“逆托邦鼓吹秩序具有地方性、非終極性,并拋棄了‘達致完美的思想,也拋棄了無休止地不斷變革的觀念,并先驗地使不斷變革去合法化。”[16]
從懷舊電影談開,我們看到的是一種趨向收縮、保守的思潮。過去的魅力源于人們永遠無法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懷舊影像所希冀的社會修復功能,因浪漫化表達與娛樂屬性,難以轉換為積極的行動主義,而流于一種自我安慰式想象,對過去有立場的重新書寫則攜帶著排外的主體至上基因,值得人們警惕。
結語
近年來歌舞電影中所體現的自反性,并不意味著其是20世紀70年代布萊希特式反歌舞片的精神之子。反之,通過影像機制祛魅、文化語匯的回聲與話語的再造,電影“參與式吸引力”復歸,娛樂神話得以延續。作為修復手段的歌舞類型在懷舊的語境中趨向保守,但也透露出,無論影像的肌質如何流變,電影仍然并且一直會是一門關于愛與可能性的藝術。
參考文獻:
[1]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M].張旭東,編.陳清僑,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433.
[2][德]托比亞斯·貝克,馬妮.“懷舊”意義的系譜學考察及其批評[ J ].江海學刊,2021(02):58-66.
[3]Sprengler, Christine. Screening Nostalgia:Populuxe Props and Technicolor Aesthetic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lm 2009:74.
[4][5][8][美]簡·福伊爾,徐建生.自體反思型歌舞片和娛樂的神話[ J ].世界電影,1990(03):4-21.
[6][德]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講故事的人[M]//本雅明文選.陳永國,馬海良,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291.
[7]Rubin,Martin."Busby Berkeley and the backstage musical."Hollywood Musicals:The Film Reader.New York: Routledge(1993):53-61.
[9][法]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時間-影像電影2[M].謝強,等譯.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98.
[10][美]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沉默的美學[M]//蘇珊·桑塔格論文選.黃梅,等譯.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174.
[11][15][美]斯維特蘭娜·博伊姆.懷舊的未來[M].楊德友,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19.
[12][法]米歇爾·福柯.新迷影叢書 寬忍的灰色黎明[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7:288.
[13]周文姬.當代美國電影中的美國夢與后種族主義[ J ].電影藝 術,2020(02):3-12.
[14][美]威廉·迪安.美國的精神文化 爵士樂、橄欖球和電影的發明[M].袁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177.
[16][英]齊格蒙特·鮑曼.懷舊的烏托邦[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14.
【作者簡介】? 張蘋秋,女,湖南長沙人,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戲劇與影視學碩士生;
黃洪珍,男,湖南郴州人,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媒介經濟、
影像傳播、新媒體傳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