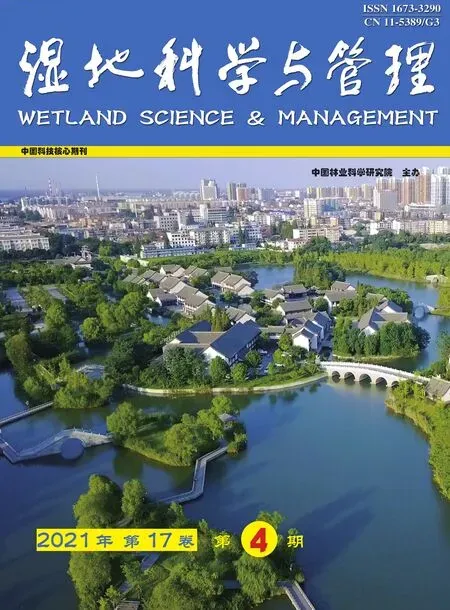上海市濕地保護的戰略思考
王春林 朱凱群 曾 琪 張可凡 安樹青,2 姚雅沁 趙 暉*
(1 南京大學常熟生態研究院,南大(常熟)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蘇蘇州215501;2 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江蘇南京 210046)
濕地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維護國家生態安全、保護生物多樣性、維護城市健康發展等方面意義重大(中國濕地保護行動計劃, 2002)。隨著對濕地保護的重視,國際組織、各國政府、國際重要都市均分別從濕地修復、濕地保護科普宣傳等方面展開了深入的探索和實踐。目前,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濕地保護研究深度、民眾參與意識、濕地保護與社會和諧發展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
上海市地處長江三角洲沖積平原,上海的發展史就是一部濕地形成、利用、保護與發展的歷史(仇傳銀等, 2019)。據《上海濕地資源遙感監測2018年度報告》可知,上海市濕地(不含水稻田)總面積為46.86萬hm2,占上海市國土面積的45.91%(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 2018)。濕地不僅占據上海市的主要國土空間,同時也為上海市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物質產品和文化產品,是上海市重要的生物棲息地和應對自然災害的天然生態屏障(馬濤等, 2008)。因此,總結分析國外濕地保護成效、共享濕地保護經驗,對我國探索濕地保護與城市和諧發展路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濕地保護戰略的重要性
濕地保護戰略是全球多項重大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促進城市和諧發展至關重要。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戰略提出要建立可持續的綠色、生態濕地農業體系(聯合國大會, 2015),積極開展濕地自然自查評估及審計核算(段赟婷, 2020)。《濕地公約》十二屆締約方大會決議提出要制定濕地管理計劃,實施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措施,加強濕地科研監測水平和能力建設,構建濕地生態系統服務的快速評估體系,促進濱海濕地生態系統及生態棲息地的保護、恢復、管理和合理利用,將濕地保護戰略納入城市總體規劃,強化國際間交流合作(馬梓文等, 2015)。根據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屆、第十四屆會議精神,要求將濕地生物多樣性保護納入城市規劃和統計系統;加強濕地可持續農業發展,減少濕地資源過度開發,采取措施減緩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2010)。
2 國外濕地保護戰略
2.1 國家層面
美國、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對環境保護的認知度普遍較高,尤其在濕地保護方面取得了豐富經驗和良好成效。如英國強調自然保護區網絡的構建,充分考慮不同利益主體的訴求,盡可能購置優質濕地資源,交由專業的社會組織統一管理。同時,通過《污染控制法》《水資源法》《水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設立,明確濕地保護和利用邊界,實現濕地資源保護的專業化、標準化和法治化管理(趙峰等, 2009)。美國在濕地保護戰略中,基于立法保護濕地,重點突出經濟鼓勵和市場機制在濕地保護方面的應用,其主要表現在:一是通過頒布《清潔水法案》等,劃定受保護濕地邊界,杜絕濕地資源的隨意開發或農業開墾;二是健全濕地資源補償機制,鼓勵濕地資源所有者進行濕地保護和合理利用,發揮自然濕地系統的功能價值;三是通過對濕地資源進行量化和資源化管理,創新成立“濕地銀行”市場機制,確保“零損失”政策的有效實施,濕地保護成效顯著(侯方淼等, 2021)。在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其他發達國家的濕地保護中,日本突出強調公眾參與和公眾協商,通過聽證會、公眾監督、補償機制等制度,發揮公眾在濕地保護中的重要作用。澳大利亞積極發揮政府引導作用,通過籌集自然遺產保護基金等,保障濕地保護資金投入;同時,推行《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濕地保護政策》,指導地方各州進行濕地保護;構建“澳大利亞濕地聯盟”,鼓勵公眾參與,共商、共享濕地保護經驗(趙峰等, 2009)。
2.2 城市層面
濕地資源歷來是城市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為城市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質條件,探索城市濕地保護策略與可持續發展戰略將有效促進城市的和諧發展。紐約市的濕地保護戰略:(1)采取由聯邦(《清潔水法案》)、州(《潮汐濕地法》和《淡水濕地法》)、地區(地方濕地保護條例)的三級立法,形成完整的法律體系;(2)建立濕地數據庫,明確受保護濕地邊界,了解濕地動態變化趨勢。通過濕地權屬轉移明確保護權責,將絕大部分受保護濕地的管理權和資源所有權轉移到國家和地方保護部門,具有完整的管理權;(3)嚴格補償制度,保證濕地總量凈增長,紐約市規定對0.405 hm2的濕地遷移補償量至少為0.81 hm2,依托市場機制(濕地銀行和預付費制度)為濕地保護提供動力與資金(沈哲等, 2012)。倫敦在城市濕地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取得的成就使其成為國際公認的濕地保護戰略領先者,具體體現在:(1)保留大量的自保留地,占總土地面積近20%,并進行分級管理;(2)將一些廢棄的鐵路、水庫、垃圾堆場、老工業區等改建為半自然保留地;(3)自然保留地和社區相連接,留出生物通道,形成開放空間的網絡結構,保持自然過程的整體性和連續性(韓紅霞等, 2004)。東京在生態環境保護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建立區域環境保護協作機制(即九都縣市首腦會議環境問題對策委員會),通過制度化機制在低碳、大氣污染、水質改善和綠化等領域展開區域合作;(2)突出公眾參與在環境保護戰略中的作用,日本《環境基本法》將公眾參與作為基本原則和長期目標,保障了公民環境權益,將環境教育課程納入中小學課程體系,從小培養環境保護意識(劉召峰等, 2017)。
3 國內濕地保護戰略
近年來,我國為濕地保護和恢復工作作出了巨大努力,公眾對濕地的關注度和保護意識不斷提升,成效顯著,具體體現在:(1)通過立法保護濕地。2000年以來,我國先后出臺了《中國濕地保護行動計劃》《濕地保護管理規定》《濕地保護修復制度方案》、各省級濕地保護條例等濕地保護政策法規,為濕地保護提供了良好的管理依據;(2)初步建立以國家公園、濕地自然保護區、濕地公園為主體的濕地保護體系。據統計,截止2018年,我國共有國際重要濕地57個、濕地自然保護區602個、國家濕地公園899個,濕地保護率達到49.03%(王志高, 2018);(3)實施濕地保護考核機制,“濕地保護率”已納入了中央對地方年度評價的《綠色發展指標體系》(王志高, 2018)。全國各省明確將濕地面積、濕地保護率、濕地生態狀況等納入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體系;(4)確保濕地總量穩步上升。確定了濕地保護戰略目標,即到2020年,全國濕地面積不低于53.333萬km2(8億畝);到2035年,全國濕地面積達55.333萬km2(8.3億畝)(張建龍, 2018)。
4 上海市濕地保護戰略目標
遵循《上海市2035城市總體規劃》提出的建設“生態之城”的戰略目標,針對上海市濕地保護在城市發展定位不夠清晰、濕地長效保護機制尚未健全、濕地自然資源評估機制仍未建立、區域協同管理難度大等問題。基于國內外濕地保護戰略成效的經驗分析總結,制定適合上海市的濕地保護戰略目標和策略措施,其總體目標包括:(1)大力實施濕地重大修復工程項目,加強全市濕地資源的保護恢復與合理利用,實現上海市濕地資源總量的動態平衡;(2)創新完善濕地保護法規政策機制,建立上海市濕地長效保護管理體制;(3)加速推進長三角一體化戰略,構建長三角濕地協同保護體系;(4)強化提升濕地科研及科普宣教水平,打造世界濕地科技創新中心與具有國際水準的科普宣教基地;(5)深化實施生態入城、濕地融城策略,全面建成國際濕地城市。
5 上海市濕地保護戰略措施
5.1 確保濕地總量動態平衡
全面實施重大灘涂濕地治理工程、崇明國際生態島建設工程等典型濕地修復工程,實現全市濕地資源的總量動態平衡乃至穩定增長,為上海提供戰略儲備和預留空間,打造成為全球范圍內濕地資源保護與可持續利用的典型示范。
5.2 建立濕地長效保護機制
通過政策創新,積極推動《上海市濕地保護條例》《上海市濕地保護專項規劃》等全市層面的政策規劃的出臺。深入開展全市濕地資源的功能及服務價值評估,逐步開展全市濕地資源的產權登記工作,建立上海市濕地資源資本賬戶體系,為上海市濕地長效保護提供支撐。創新成立“濕地銀行”,由政府主導監管,逐步建立并完善“濕地交易”的相關市場交易機制,實現上海市濕地資源“無凈損失”的目標。
5.3 加速推進長三角濕地保護一體化
以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的先行啟動區作為“長三角濕地一體化示范區”的先行試點范圍,探索建立跨流域、跨區域的濕地生態補償制度、跨區域濕地投入共擔和利益共享財政制度,共同制定濕地保護統一標準。加大跨界濕地環境綜合治理力度,統籌策劃示范區內的濕地農業、濕地旅游等濕地產業布局,形成區域差異化發展模式,提升示范區濕地綜合利用水平。
5.4 打造全球濕地保護技術創新高地
制定完善相關企業研究支持獎勵政策,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濕地科技創新體系,為上海市的濕地保護和產業發展提供堅實的科技支撐。整合利用現有濕地宣傳教育資源,整合全市濕地宣教資源,搭建上海市的“濕地宣教網絡平臺體系”,大力發展線上濕地教育,全面開展濕地教育培訓,進一步提升全民濕地保護意識。
5.5 全面建設國際濕地城市
應長期堅持“濕地之城”的城市發展策略,將其作為全市所有政策、規劃制定時的前提考慮基礎,確保發展策略的長期性、持久性。基于濕地生態、濕地生產、濕地生活相融合的濕地保護理念,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生態、循環濕地農業體系,完善濕地產業鏈條,凸顯濕地保護與利用在城市發展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