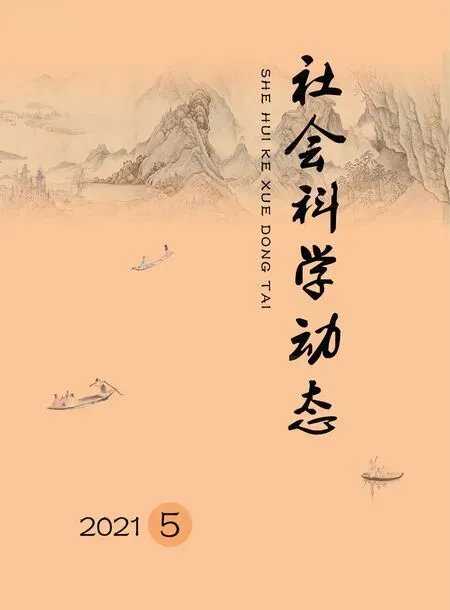百年中國文論對當代西方文論評價觀的吸收與本土化建構
陳新儒
以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為起點,中國現代文論至今已誕生逾百年。而與“五四”幾乎同時興起、以俄國形式主義與英美新批評為代表的西方文論也進入了科學化批評的現代新時期。時至今日,在近一個世紀間,西方文論“不但如同電擊雷鳴,作為外界物沖擊著中國現代文論的版圖結構,而且還如同水墨畫中泅散開的筆墨,與中國現代文論界限模糊,形影相隨,構成它的色澤和質感”①,甚至“文學理論”這一概念本身也是西方的舶來品,幾乎所有當代主流西方文論都在不同時期對中國現代文論帶來不同程度與不同方面的影響②。這些理論一旦進入中國語境,受到國內理論框架的過濾和改造,又在全新的文藝實踐過程中加以變形與發(fā)展,已成為中國化的全新理論。而對于作為理論“他者”的當代西方文論中的評價觀③是如何被中國現代文論吸收并運用于本土化建構的,則依然有待學界進一步的關注。
筆者此前曾將當代西方文論中的文學評價觀大致分為客觀形式論、讀者導向論、外部評價論、“后”理論語境下的新文學評價觀這四個有所不同但又在內部各自聯系的類別④,通過認真梳理后發(fā)現,當代西方文論本身包含了多元的評價觀,從批評流派的角度來看則更加紛繁蕪雜,但它們的共同特征是不同程度地存在將包括評價觀在內的一系列批評話語科學化的傾向,其中也交織著人文主義傳統與新的評價標準激烈交鋒,這些評價觀顯然深刻影響了中國現代文論建設的進程。面對建設我國文藝評論價值體系這一新的目標,我們有必要重新回到現代中國對西方文論的接受與吸收史這一命題,以文學評價觀這一新的回顧角度總結得與失。根據當代西方文論評價觀在現代中國文論中所扮演角色的變化,本文將分為五個不同時期進行分別考察,力圖考慮到主流西方文論評價觀在中國語境下的吸收與本土化過程,以期展現出一個較為清晰的理論接受史的框架。
一、 1919 年至 1942 年: 誕生與萌芽
本時期的中國文論界首次吸收了幾乎同一時期崛起的西方文論中的諸多評價觀,并演變?yōu)閮煞N對立的文學評價觀,且在這一階段保持了勢均力敵的交鋒態(tài)勢。伴隨五四運動所到來的、以“民主”與“科學”為綱的新文化運動,使得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首次出現科學化的傾向,文學則在其中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從文學評價標準方面而言,“藝術標準”與“現實標準”這一組二元對立始終作為主流的兩股對立力量在現代中國文論界進行著激烈的初步交鋒。程金城認為,正是從“五四”開始,文學介入社會價值體系重建,出現了兩股旗幟鮮明的文學評價觀:以文學研究會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思潮,偏重文學介入社會和“為人生”的價值目標,文學的價值屬性定位于對社會現實的反映與批判;以創(chuàng)造社為代表的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偏重于文學對主體的內心世界和生命意識的表現,文學的價值屬性被理解為對內心情感的抒發(fā)和意志的張揚⑤。這一時期的文學評價觀主要體現在對于評價標準的不同認定之上,“藝術的”與“現實的”評價標準之爭,實際上反映的是“美”與“真”這兩大價值維度在具體的文學評價過程中互不相容、對立大于統一的觀念預設。
何以如此?這需要從當代西方文論對早期中國現代文論的影響中去尋找答案。在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前的十幾年間,西學東漸乃至“全盤西化”正是社會主流思潮,國內學術氛圍相對寬松,與外界交流頻繁,文學批評與研究明顯受到來自西方的同步影響。來自19 世紀俄國文論中的現實主義文學評價觀,經過馬克思主義文論的重新闡釋,率先為中國現代文論樹立了一種“文學真理觀”。它將文學是否準確反映了現實作為衡量文學作品價值的主要標準,即“真”大于“美”。其實早在“五四”之前,已經有包括王國維在內的一些理論家借助德國古典主義美學,試圖將“美”與“真”的問題在評價標準的維度上進行分離,主張“美”大于“真”的文學評價標準。但限于當時國內的政治形勢,并未對當時中國主流的文學評價觀帶來根本性的影響,尤其是1925 年“五卅慘案”之后,國內的知識分子階層對待現實的態(tài)度開始發(fā)生根本性的轉變:由關注自我轉向關注社會,由關注精神層面的個人情感轉移向關注現實世界的社會情感,由思考文學的自由獨立價值轉向關注文學的社會文化內涵,由關注文學的審美價值的塑造轉向關注文學所傳達的社會意義⑥。于是,關注文學的革命性、社會性與批判性的左翼文論成為相當長一段時期國內理論界兩支主導話語中的一支。
而另一方面,對于“美”在形式上的價值探討,進而提倡“美”大于“真”的具體文學評價標準,則借助英美新批評(同時也包括方興未艾的象征主義文論)在國內的初步傳播開始形成一定的氣候。1929 年,新批評派的先驅瑞恰慈首次來華執(zhí)教,這吸引了一大批當時最頂尖的青年學者的關注。隨著瑞恰慈的代表作《科學與詩》 的翻譯出版,新批評主力們的著作與文章陸續(xù)在1930 年代被譯介到國內,其中包括艾略特與瑞恰慈的多篇重要論文⑦。1937 年,瑞恰慈第二次來華執(zhí)教,同時也是他的學生燕卜遜首次來華執(zhí)教,形式論批評在國內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國內學界出現了一批從內部視角進行文學評價的論著,作者主要為卞之琳、錢鐘書、吳世昌、曹葆華、袁可嘉等新批評著作的譯者,尤其是袁可嘉所提出的“新詩現代化”主張,即是借助新批評對國內詩歌批評的具體理論建構,其中的“純詩”理論明顯將對詩歌的評價標準落到語言形式本身。這種美學主導的文學評價觀盡管當時還沒有如日后那般受到西方文論的系統化影響,但其在相對自由的思想環(huán)境下,也得到了較為充分的發(fā)展空間。
此外,還有一批以朱光潛、李健吾為代表的留洋文論家,在自己的論著中也不同程度地批判吸收了包括形式論和心理學批評在內的西方文論中的文學評價觀,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高覺敷對精神分析理論的引介與評論、魯迅在《苦悶的象征》的譯介中對西方文論的間接引用,等等。朱光潛出版于1936 年的《文藝心理學》可以說是這一階段的集大成者,盡管本書主要以論述比較西方流行的文藝理論為主,并未建立起自己的理論系統,但在很多方面已經有了初步的批判與反思。作者不僅在書中細致地考察了當時流行的各個西方批評思潮的優(yōu)缺點,更是站在審美心理距離的角度辨析了“寫實派”和“理想派” (實際上即前文所說的“現實的”和“藝術的”)兩種對立評價觀各自的合理性和片面性,并最終得出結論,認為不同類型的文藝作品所依據的評價標準也應該不同,不應局限于寫實或理想、主觀與客觀的任何一種⑧。
綜上,從“五四”直到1940 年代前期的中國文論界對當時西方文論評價觀的吸收與本土化建構正處于萌芽與起步階段,中國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已經開始自覺地接受其中的新觀點所帶來的沖擊,并在文學評價標準的問題論爭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勢。另一方面,評價主體與評價對象的問題在本階段仍未借助西方文論的資源得到充分討論。
二、 1942 年至 1979 年: 沉寂與蟄伏
由于受到現實政治的影響,西方文論在本時期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被打入“冷宮”,關于文學評價標準的論爭被迫中斷。隨著抗戰(zhàn)救亡運動的全面展開,“救亡壓倒啟蒙”作為政治口號被提出,以新批評為首的客觀形式論批評所帶來的評價觀難以適應國內具體形勢的變化,除了錢鐘書的《談藝錄》等涉及中西文論之間比較闡發(fā)的極少數著作吸收并自覺運用了部分西方文論中的文學評價觀,左翼文論所提倡的革命文學評價觀基本主導了當時的文論話語,其他話語很快便被視為邊緣排除在主流文論話語之外。1942 年,毛澤東發(fā)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其中明確提到了文藝批評的兩大標準——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同時規(guī)定了政治標準應大于藝術標準。新中國成立以后,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相統一、政治標準主導藝術標準更是成為當時文論中唯一正確的評價標準。這樣一來,之前在中國現代文論中所提倡的“現實標準”逐步被“政治標準”所取代,國家意識形態(tài)對文學創(chuàng)作與文學批評帶來了空前巨大的影響。在這種大環(huán)境中,盡管在文論界關于兩種評價標準的論爭一直延續(xù)到了40 年代末,但由于官方的早早定性,許多對當時西方文論的進一步引介與研究工作被迫中止,上述論爭也很快陷入沉寂。
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在50 年代后期以來,隨著政治工作對于文藝工作的進一步影響,蘇聯馬列主義文論一家獨大,所有其他當代西方文論都逐漸被視為與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對立面加以全面批判,學界對當代西方文論進行正面的學習與評價愈發(fā)成為一種奢求。1962 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是此時期唯一一本論及當代西方文論的著作,該著囊括了一戰(zhàn)后至1960 年間主要的文藝理論,其中包括艾略特、瑞恰慈、布魯克斯、蘭瑟姆、伯克等幾乎所有新批評主力,并對當時的批評家按照階級理論進行了劃分:對于一些積極關心政治、表現出“左”傾傾向,“認真走向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學者,該書認為他們“基本上已經”超出了資產階級的范疇,不予選擇;而對于那些“一時投機”,“搬弄馬克思主義詞句的文藝論著的文章”,就性質說,“形成了資產階級文藝理論的一個變種”,因此編為一輯,并將其直接定性為“反動”⑨。換言之,只要是出自“西方資產階級陣營”的文論家,無論他們的文學評價觀本身如何千差萬別,都被當時中國文論界公開視作社會主義陣營的敵人,認為其觀點背后所隱藏的價值觀念一定是消極的、錯誤的、反動的。盡管存在政治干預的問題,但《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客觀上還是讓當時許多年輕的知識分子首次接觸到了西方20 世紀前半葉主流文論的許多重要觀點,日后此書的多次再版也證明了其學術翻譯的價值。
綜上,當年文學批評標準問題的提出,主要來自于政治定論,而非學術爭鳴,缺乏相應的學理邏輯。隨著政治影響的增大,包括文學評價觀在內的當代西方文論中一系列思想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的中國文論界均已失去了吸收與本土化建構的基本條件。
三、 1979 年至 1985 年: 回歸與探索
改革開放以來,政治形勢的變化直接影響到西方文論中國化的整體進程,而直接涉及價值判斷的文學評價觀首當其沖,終于迎來了全新的發(fā)展契機。1979 年12 月,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召開,鄧小平倡導尊重藝術規(guī)律,捍衛(wèi)批評自由,不再提“文學為政治服務”等口號,這是國家權力有限度地退出文藝領域的標志,同時也意味著文藝界的全面“解凍”,為西方文論的大量傳入提供了亟需的健康學術環(huán)境。
首先出現的是“翻譯熱”。這主要基于當時國內學界的一個共識:中國社會各領域百廢待興,通過譯書來了解西方、認識西方成為第一要務⑩。文論界首先出版了一批解放前已經出版過的古典譯著,并很快發(fā)展為對當代西方文論著作的全面翻譯,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俄國形式主義文論、結構主義/符號學在內的一大批經典西方文論都首次被引介到中國學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韋勒克、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在1984 年的翻譯與出版。該書從評價標準的差異上區(qū)分了文學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這在“表面上不偏不倚,承認外部研究的重要性……在美國語境下,可能是從新批評立場后退一步,承認外部研究的重要性;在中國幾十年只有外部研究的環(huán)境下,內部研究的提出,就是一個振聾發(fā)聵的提醒,就是在提出一個重大的補缺”?。這不僅標志著以新批評為代表的當代西方文論重新回到主流學界的視野,也預示著兩種文學評價標準論爭的回歸。此外,還有許多西方文論家的重要論文也被譯介刊發(fā)在一些學術期刊上。通過這一時期的大量翻譯成果,當代西方文論首次對中國現代文論的本土化建設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我們不難發(fā)現,這些著作所傳達的內容無一例外,都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被統統冠之以“形式主義”的文藝自律論,所涉及到的評價觀也基本限定在內部美學范疇,這無疑是對于此前多年官方強調現實的乃至政治的文學評價標準的一種強力反撥。
與“翻譯熱”相映成趣的是“引介熱”。學界主要通過發(fā)表期刊論文和出版學術專著的方式,將當代西方各種文論流派在短短幾年間大量介紹給了國內讀者?。這種“學術再發(fā)現”盡管依然停留在介紹階段,較少涉及具體的闡釋與批判,但它們無疑都為日后中國現代文論的自主建設進行了必要的知識性儲備。值得一提的是,1985 年,后現代主義理論大師、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代表人物詹姆遜來華講學,開設“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專題課,這是新時期西方重要文論家首次直接與國內學界展開交流,其中對于后現代主義特征的描繪與評價,在國內學界產生深遠影響。隨著這些思想與理論對中國現代文論中評價觀的不斷影響與滲透,文學評價中的現實性被進一步削弱,而藝術性標準則不斷被強調。
最后是這一時期的“美學熱”。美學在中國重新回到了康德的審美自律語境,受到了大眾的普遍重視,美學在此時的中國學界本身成為超越其他學術話語的“先鋒理論”,這也賦予了美學研究者非凡的社會地位。美學家成為最炙手可熱的學術明星,美學著作成為最為暢銷的書籍類型,美學研究生的入學考試更是“千軍萬馬來擠獨木橋”?。這一時期對于美學的重新重視可以說是一種必然,其根本原因在于對過去數十年文藝評價觀極端路線的“急剎車”和“強轉彎”。“美學熱”來到文論領域,便發(fā)展為對于“純文學”價值的強調,以與之前強調外部研究的“雜文學”價值觀相對立。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似乎又回到“五四”年代:翻譯傳播、借鑒移植、拿來主義,卻很少有自己的東西。至少在當代消費社會的條件下,審美話語以及抽象的藝術形式已經成為金融資本的文化觸角?。
綜上,在政治環(huán)境得到極大改善的新時期,中國現代文論對于當代西方文論中評價觀(主要仍是評價標準)實際上并未很快得出清晰客觀的認識,而是首先秉承“拿來主義”,在已經有了“孰高孰低”的文學評價觀的基礎上,再去西方文論資源中尋找和揀選符合自身預設立場的理論話語作為權威。但在本階段,國內文論界對于眾多在西方已成為主流話語的西方文論依然停留在介紹與探索的程度,更多時候只是為了扭轉“藝術標準大于政治標準”這一文學評價觀而服務的。
四、 1985 年至 1995 年: 吸收與拓展
20 世紀80 年代后期,國內文論界開始自覺將西方文論中的文學評價觀運用到各自具體的研究對象中,并試圖發(fā)展出具有中國經驗的本土化理論范式。
首先是文學主體性理論對于文學評價主體的重新認識。建立在哲學主體性理論基礎上的文學主體性理論,以劉再復發(fā)表的一系列論文為標志。劉再復提出,要“賦予作家以創(chuàng)造主體的地位,賦予文學形象以對象主體的地位,賦予讀者以接受主體的地位,作家的大腦不是生活的簡單容器,文學形象不是任憑作家擺布的玩偶,讀者不是只能呆板地接受作家的教育”?。至此,中國現代文論中的文學評價觀走出了以往在西方文論影響下僅僅討論文學評價標準的局限。這種部分借鑒了接受美學與讀者反應批評的思想,不僅批判了以往的文藝理論對評價主體與評價對象存在的定位模糊的問題,而且傳統文學評價觀中的機械反映論(即認為最有價值的文學作品是最能真實反映現實的)所暴露出的局限性進行了及時的糾正。此外,文學主體性理論也對當代形式主義文論中的文本中心主義提出質疑,認為有必要從具體的作者、讀者與接受語境出發(fā)來重新認識文學的多元價值。正是基于此,相當一批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的文學價值得以重新發(fā)現,并提出“重寫文學史”的口號。接受美學與讀者反應批評也由前一時期的純粹引介變?yōu)檫@一時期國內學者的理論武器。80 年代末,大量以“文學主體性”為價值坐標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論著得以紛紛涌現。然而,這種對于文學主體超越時代與歷史的無限拔高,使得文學主體性理論又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盡管確認了文學評價主體是作為獨立個體的讀者,而非虛無縹緲的“人民群眾”,但是卻有將文學評價標準歸于虛無的危險。
另一方面,當代西方文論的譯介工作仍在繼續(xù)深化,俄蘇形式主義、結構主義/敘事學、接受美學與讀者反應批評、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批判理論等經典西方文論,都在此時不同程度地加深了譯介的力度。1987 年,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代表學者伊格爾頓的《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是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譯介成果,這也是國內學界首次譯介對當代西方文論思潮進行系統梳理與反思的著作,其中伊格爾頓對于各家文論的批判性解讀和自身旗幟鮮明的以政治批評為評價立場的觀點,給此時依然熱衷于“內部研究”的國內學界帶來強大的觀念沖擊。與此同時,對于上述當代西方經典文論的本土化吸收已不再局限于引介,而是進入到方法論甚至本體論層面,用以具體分析和解決國內文學研究所面對的對象。這種方法論的運用,具有很大的積極意義。中國現代文論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所使用的文學批評方法依舊來自俄國社會主義文論以及之后的蘇聯馬列主義文論,結果造成評價單一、形式陳舊的“模式化”評價陷阱,這顯然無法適應新時期對文學研究的要求。于是,一批批國內學者將目光投向當代西方文論,試圖借助方法論的移植來解釋自身所面對的文學現象。以敘事學為例,從80年代末到90 年代初,一系列運用西方經典敘事學理論來分析中國古典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論文和專著得以問世,并間或討論了中國文化背景下所孕育的獨特敘事特征及敘事模式。但是這樣一來,許多學者就陷入了當年新批評與結構主義所陷入的同一個誤區(qū):將批評方法直接用來當作對文學作品的評價標準,乃至于只做意義分析,回避正面的評價,具體的作品批評到最后變成了“文學公式”的總結。“充滿熱情的存在主義讓位于高舉科學大旗的結構主義”?——其深層原因乃是對此前漫長歷史中過分強調評價立場的一種修正,但是這種修正同樣難免矯枉過正之嫌。
1986 年,“中外文藝理論信息交流會”在天津召開,會議確定了對于當代西方文論的方針,即先用來吸收與借鑒,而不是先貼標簽與定性。在此方針指導下,西方文論的引介工作進入到一個更為深入的階段。一大批活躍于當代的西方文論大家如洛特曼、福柯、拉康、德里達、德曼等人作為“學術明星”被首次引介到國內并受到熱烈追捧,包括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敘事學、后殖民理論、文化研究等在西方理論話語中占據主導地位的一批“顯學”也首次被大量介紹給了國內學界,甚至還有相當數量的西方自然科學方法論也進入到了國內文學研究者的視野當中。一時間,各種理論 “百花齊放”,令人眼花繚亂,最終呈現為井噴的態(tài)勢。然而,表面上的文論繁榮掩蓋了潛在的弊端:在中國現代文論、中國傳統文論與當代西方文論眾聲喧嘩、各抒己見的話語競爭與比較參照之下,結合中國發(fā)展的特殊語境,往往會出現令人尷尬的“誤讀”與“錯位”。例如,當代西方文論中涉及評價方面的“陌生化”、“含混”、“結構”等術語,無論如何也難以同“沖淡”、“比興”、“風骨”等中國古代文論中的詞匯一一對應,“以西方文學觀念為基準來梳理古代文論話語顯然就不得不舍棄那些與之相左的或者不搭界的內容,這樣的研究無疑是遮蔽了中國古代文論話語資源的豐富性與獨特性”?。此外,在評價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的眾多著述中,普遍存在將法蘭克福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的描述——評價框架機械運用到中國的大眾文化批評的傾向,而沒有對這個框架在中國的適用性與有效性進行認真的質疑和反省。
綜上,由于認識到中國與英美文論的發(fā)展存在一個時代的“視差”,學界終于徹底拋棄了前一階段依然存在的對西方文論的保守態(tài)度,轉而開始對各種新思想保持高漲的吸收熱情。這種“運用”當代西方文論解決“中國問題”的思路,激發(fā)了文論界的學術熱情,學者們也正是通過這種方法論的“運用”達成了“主體性”的建立與發(fā)揮。但方法本身并非完全“中性”的,方法背后所隱藏的評價觀也在深刻地影響學者運用方法所得出的“結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最后還是回到了“全盤西化”與否的舊命題上,“不貼標簽、不定性”的“拿來主義”所暴露的問題其實是對方法本身的理解還不夠深入,而當我們一一試用過武器的趁手與否后,就到了對方法本身及其效果進行總結和反思的階段,此時浮現出的種種問題也引發(fā)了人們對于方法論的檢討和質疑。
五、 1995 年至今: 對話與反思
從20 世紀90 年代后期開始,學界對當代西方文論中評價觀進行更深刻的反思,其中包括評價主體、評價對象和評價標準在內的各種文學評價觀都在這一時期得到更加深入的檢驗。
1995 年,由曹順慶所提出的“中國文論失語癥”這一論題引發(fā)了學界的普遍關注與熱烈討論。所謂“失語”,就是放棄自身文論話語的固有立場,轉而照搬或借用西方文論中的一套話語,這樣才能證明自己觀點的合理性。而具體到文學評價觀中,就意味著只能通過引用西方文論所涉及到的關于評價主體、評價對象和評價標準等一系列方面,來建立對某個具體的文學現象或作家作品的合理評價體系。在一些學者看來,“中國文論失語癥”的實質在于“把對中國古典文學理論和中國古典文藝理論的研究權和闡釋權出賣給西方,這是在理論意識形態(tài)上對西方后殖民主義文化的一種更深刻、更徹底和更自覺的膜拜”?。長此下去,這種典型的“后殖民癥候”不僅會使我們無法對于當前正在發(fā)生的文學進行合理的評價,甚至無法對中國古代文學史有清晰的認識。圍繞著“失語癥”所出現的學術爭鳴表明,中國現代文論對于西方文論中評價觀的吸收與本土化建構已進入了新的階段,這突出地體現在對于來自西方的諸多“后”理論的誤讀與闡釋之中。盡管杰姆遜早在80 年代中期就已經來華傳播后現代主義的基本思想,但直到90 年代中后期,后現代主義才隨著后結構主義、后殖民主義、后經典敘事學等“后學”真正進入到中國現代文論話語體系中。這些“后學”盡管各有側重,但都具備同一種十分強烈的評價觀:反本質主義——而這也是國內學界最早拿來化用的理論武器。面對“失語癥”的焦慮,反本質主義可以很好地消解一切邊緣與中心的二元對立,在文論的語境下,則便于建立新的文學評價主體與文學評價標準。具體而言,反本質主義將“現實”與“藝術”都視為可評價的對象,而不是凝固的“真理”。此時的國內文論界關注的重點不再是如何反映現實(因為不存在確定無疑的唯一的現實),也不再是封閉于文學作品內部的“藝術形式”或主觀的“文學性”,而是作品生產、傳播、接受并被判斷為“文學”的過程,這就出現了評價主體(精英與大眾)、評價對象(文學與非文學)與評價標準(精英認可的與大眾認可的)的這三組新的二元對立。
幾乎同一時期,當代西方文學批評界的領軍人物布魯姆出版了專著《西方正典》,書中關于文學經典價值問題的討論很快就為國內學界所關注,并引發(fā)了關于中國文學經典價值重估的新一輪思考。不久后,圍繞金庸是否應該入選《百年中國文學經典》這一問題,學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有學者認為,金庸對于文學史的意義,在于他的作品以通俗手法表現了身后的文化與美學意義,體現了雅俗共賞的中國文學發(fā)展方向,但也有許多學者堅持認為,武俠小說只是一種低檔次的暢銷書,不足以進入經典行列?。這一論爭很快上升到對于文學評價觀的基本界定問題,同時將大眾文化與消費文化在文學評價中所起到的作用也納入到了討論中。隨著國內大眾文化研究的進一步發(fā)展,一些原本處于文學邊緣地帶的大眾文化的研究價值開始受到注意,源自于西方大眾文化研究的“消費社會”與“日常生活審美化”成為此時學界的兩大熱門關鍵詞。這一方面是對于“雜文學”觀念的一種復歸,開闊了文學研究的視野,文學的邊界即文學評價的對象被一再擴大。但另一方面,也存在著忽視文藝內部規(guī)律、誤將經濟標準作為終極評價標準的危險。有學者不無擔憂地指出,在今天,雖然沒有人提出“文藝從屬于經濟”的極端口號,但實際上“文藝從屬于市場”似乎已作為一種強大的現實而被普遍默認——在大眾文化、消費社會、文化研究及所謂的“日常生活審美化”等討論中就存在著這種傾向?。
此時來華訪問的西方文論家也不同于20 世紀30 年代的瑞恰慈或者80 年代的詹姆遜(他們主要帶來的是新知識與新方法),他們更多是抱著平等對話的心態(tài)與中國學者進行交流的。當文學從“經典”跌落入與電視節(jié)目、電子游戲同等場域的大眾消費品中,關于今日文學地位和文學作品價值的討論隨著2001 年希利斯·米勒在北京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提出“文學終結論”得以迅速升溫,國內學者紛紛對此著文做出回應,其中經歷了從一開始的誤讀與批評到后來的理解與共識,這場論爭日后被認為是“是中國文藝理論界透過他者之鏡對自身境遇的反思和審視,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文藝學學科發(fā)展中的一場極具象征意義的事件”?。通過圍繞“文學終結論”的討論可以看到,中國文論工作者已經逐步開始在同西方文論的對話交流中形成批判性的文學評價觀:西方的“后學”固然是有力的消解手段與批判武器、懷疑一切原則與中心,但同時也可能滑向一種嬉皮士式的游戲一切的“瀟灑”,在“人人都是批評家”、“一切皆可成為藝術品”這類無限度的批評自由的背后是真正自由的喪失?。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現代文論對于西方文論中的評價觀不再是一味地吸收或排斥,而是在面對自身獨特的問題時靈活運用、取其精華,并反思是否有不適用的成分,特別是在西方“后”理論的語境下,開始擺脫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維模式,走出泛本質主義的理論范式,從不同的評價主體與評價對象中尋求多元化的評價標準。
近年來,學界圍繞“強制闡釋論”、“本體闡釋論”以及“公共闡釋論”所進行的新一輪爭鳴,同樣是緊密圍繞著當代西方文論中的評價觀所進行的理論反思。在這場爭鳴中,學界已經深刻認識到,上世紀中葉之前盛行的舊文學評價觀在新的歷史時期已不符合當代文學與文論的發(fā)展潮流,21 世紀中國文藝學應立足于當代哲學人文學術的研究成果,尋找符合當代需要的理論范式,回應今天的文學文論現實,推動文藝學開拓出新的發(fā)展道路?。在程金城所提出的“21 世紀中國文學價值重建”這一論題中,便談到了“后”學中的評價觀所帶給我們的啟示:“文學價值沖突、失范與多元化的相互糾纏,無法建立較為穩(wěn)定、相對合理而又具有主導傾向的價值觀念體系。文學現象越來越豐富多彩和多樣化,但同時也愈發(fā)難以進行價值定位。在認識論和價值理念上,對新形勢下如何融通和建構主流價值體系缺乏認識,也存在疑慮,并且往往把價值多樣混同于價值相對主義,把文學自由與無價值目標、無是非觀混淆起來”。?曾軍同樣指出,中國學者運用西方文論闡釋中國經驗,經歷了從“以中國經驗印證西方理論”的學習階段到“以中國經驗來修正西方理論”的反思階段,后者正是中國學者在積極與西方文論對話的過程中中國經驗進而推進理論創(chuàng)新的一種努力?。
綜上,國內學界對于在西方文論本土化語境下對文學評價觀的反思力度,較以往已有了長足的進步。但不可否認的是,目前學界針對文學評價觀的重構與中國經驗修正西方文論依然處于起步階段,其中許多理論設想依然有待實現或正在實現,其中依然存在巨大的深耕空間。
結語
中國現代文論對當代西方文論評價觀的吸收與本土化建構,表面上看以采納西方理論話語體系為主,但是隱藏在背后的始終是一種“中國中心”的問題意識與價值取向,這其中包含著這樣幾個關鍵性環(huán)節(jié):選擇中的“文化過濾”、理解中的“文化誤讀”與接受中的“文化改寫”?。通過對當代西方文論中的文學評價觀在百年現代中國的理論旅行進行細致梳理,可以發(fā)現其大致經歷了從單向引介到沉寂以及之后的回歸,再到近年的雙向對話與反思的過程,這實際上也是百年中國文論借助西方文論資源,從認識論到方法論再向本體論漸進發(fā)展的歷史進程,這種借鑒吸收,并不是單方面的亦步亦趨或照抄照搬,而是根據不斷變化的中國現實語境,有選擇、有批判、有目的地學習借鑒和創(chuàng)造性地吸收轉化,是中西互鑒、“西化”與“化西”既博弈又融合的辯證過程?,其中能夠總結出許多成功的經驗,同樣也有不少值得繼續(xù)反思的教訓。正如陶東風所指出的,此前文藝學的一些文藝學研究喪失了對于自主性的歷史反思能力,以為自主性所確立的所有評價標準便是一種本質化、普遍化、無條件的“真理”,可以運用于一切文藝現象,包括與精英藝術存在巨大差別的泛藝術化現象?。如今面對西方文論評價觀的持續(xù)滲透,中國文論話語在評價維度中存在著滑入三種誤區(qū)的風險:其一,是拒絕“本質”、懸置“價值”,理論的復雜化日趨成為評價觀缺席的理由,這種允許多元共存的寬容,在實際操作中很容易滑向無評價尺度的技法展覽;其二,是將“真、善、美”這三種評價標準互相割裂,使具體的文學批評在意識形態(tài)具有中性含義的掩護下,對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理解也程度不一地呈現出將藝術技巧與倫理道德、形式與內容、意識形態(tài)與審美屬性冠之以簡單對應的二元對立理解;其三,是將“理論的全球化”等同于“理論的西化”,即把一些西方文論中的評價觀直接套用于解決中國獨有的問題,將中國傳統文論中不少同樣具有極高參考價值的評價觀視為傳統糟粕加以拋棄。
劉俐俐認為,當今學界圍繞文學評價標準的爭論可以概括為“真善美究竟哪個為統帥問題的反復,以及隨之在功利、審美和認知三個方面功能上的反復,緣于對于三者之間關系究竟應落實在哪里的問題沒有解決。深層次問題是文學性質的把握,或者說審美性質的把握問題沒有解決。筆者有傾向的看法就是,落實到審美上的基本原理尚未獲得更深刻的把握,這個問題需要一個更大的視野去解決”?,而這也正是百年中國文論中的評價觀對于西方文論相關資源的吸收與借鑒后總結出的歷史經驗與教訓,文藝評論價值體系的缺失問題依然亟待解決。如今我們面對在當代重建這一體系的新目標,無論是對具體文學作品的評價還是關于文學本體價值的思考中,應同時擯棄當代西方文論所普遍存在并對中國文論施加影響的“價值無涉”立場與二元對立思維,更應避免全盤西化或全盤否定西方視角的理論偏見,為當代文論提供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價值坐標。
注釋:
①⑥?? 王一川等:《西方文論中國化與中國文論建設》,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 年版,第169、137、186、284 頁。
②“當代西方主流文論”是一個外延相對固定的說法,指的是沒有對中國現代文論帶來過決定性影響的歐美主流文論,一般而言包括俄蘇形式主義文論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但是不包括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論與蘇聯現實主義文論,因為后者借助主流政治話語對中國現代文論帶來過決定性影響。
③ 文學研究中的“評價”這一概念,其內涵包括三個不同的層次:其一,文學作品中所反映出的作家對于一些事情與問題的評價;其二,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中對于具體文學現象、作家和作品的評價;其三,文學理論中對于具體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的評價。本文主要考察的對象乃是第二種。
④ 陳新儒: 《20 世紀西方文論中的文學評價觀述論》,《社會科學動態(tài)》2017 年第2 期。
⑤ 程金城:《20 世紀中國文學價值系統與傳統文學價值觀》,《科學·經濟·社會》2006 年第2 期。
⑦ 其中包括瑞恰慈的《文學批評原理》 《批評理論的分歧》以及艾略特的《批評底功能》 《傳統與個人才能》 等。詳見張惠: 《“新批評”在中國的早期譯介研究》,《吉首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5 期。
⑧ 朱光潛:《文藝心理學》,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0—36 頁。
⑨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組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作家出版社1962 年版,第7頁。
⑩?? 高建平編:《當代中國文藝理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469、447、299 頁。
?? 周小儀、張冰主編:《新中國60 年外國文學研究》 (第四卷: 《外國文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第 16、100 頁。
? 其中重要的包括:以1980 年楊周翰的《新批評派的啟示》與1981 年趙毅衡的《新批評——一種獨特的形式主義》為標志,新批評的形式論研究重新被學界所認識;1981 年夏仲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藝術創(chuàng)作散論》首次介紹了巴赫金學派;1981 年江天驥的《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的社會理論》 最早對法蘭克福學派做了介紹;1981 年張裕禾的《新批評——法國文學批評中的結構主義流派》 最早介紹了結構主義文論;1982 年袁可嘉的《關于“后現代主義”思潮》是當時最早關于后現代主義的介紹;1983 年李輝凡的《早期蘇聯文藝界的形式主義文論》首次從正面介紹了俄蘇形式主義文論;1983 年張隆溪的《關于“接受美學”的筆記》首次向國內介紹了闡釋學與接受美學文論;1985 年安和居的《“符號學”與文藝創(chuàng)作》首次向國內介紹了符號學批評。
?? 代迅:《西方文論在中國的命運》,中華書局2008 年版,第 151、306 頁。
???? 陶東風、和磊:《當代中國文藝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494、468、578、557頁。
? 朱立元:《“文學終結論”的中國之旅》,《中國文學批評》2006 年第1 期。
? 單小曦:《從“反本質主義”到“強制闡釋論”——中國當代文藝學的“本質論”迷失及其理論突圍》,《山東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5 期。
? 程金城、冒建華:《關于21 世紀中國文學價值重建的思考》,《甘肅社會科學》2006 年第6 期。
? 曾軍:《西方文論對中國經驗的闡釋及其相關問題》,《中國文學批評》2006 年第3 期。
? 朱立元: 《當代中國文藝理論的演進與思考》,《中國社會科學》2018 年第11 期。
? 劉俐俐:《文藝評論價值體系與文學批評標準問題研究》,《南京社會科學》2016 年第1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