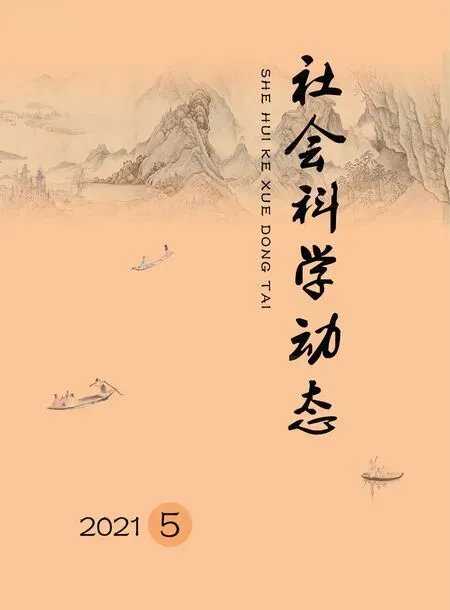鑄國家之魂,講好中國故事
——以《湖北日報·東湖》副刊和《生命之證》的抗疫書寫為樣本
彭 宏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的第十一個專題為“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編選了十九大以來習近平的六篇講話(要點或部分)。這些講話,圍繞“堅持文化自信”這一核心,從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的高度,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文化事業進行了一系列深刻的闡述,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為新形勢下的宣傳思想工作、文化文藝工作、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青年工作、網信事業發展、媒體融合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
一
一個國家的強盛,一個民族的復興,離不開正確思想的指引,離不開強大靈魂的支撐,離不開先進文化的滋養。《自覺承擔起新形勢下宣傳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務》,是2018 年8 月21 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要點,其中提出:“堅持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堅持思想工作‘兩個鞏固’的根本任務,堅持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堅持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堅持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堅持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堅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①講話總攬全局,旗幟鮮明,對宣傳思想工作的指導意義重大。
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文化對國家、民族來說,具備凝神鑄魂、正本清源的深廣價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魂》是2019 年3月4 日習近平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聯組會時發表的重要講話。這一講話立足全局,高瞻遠矚,對文化文藝工作和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即“一個靈魂”和“兩個十分重要”。習近平指出:“作為精神事業,文化文藝、哲學社會科學當然就是一個靈魂的創作,一是不能沒有,一是不能混亂”。②這兩項工作,“在黨和國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基于這樣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總書記希望廣大文化文藝工作者、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堅持與時代同步伐”“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以精品奉獻人民”“堅持用明德引領風尚”③。這些要求與希望,寄望殷殷,寄語切切,為做好新形勢下文化文藝工作、哲學社會科學工作進一步指明了方向,是文化文藝工作者、哲學社會科學者創作和研究的基本遵循。
當今世界,新興媒體飛速發展,既對傳統媒體形成巨大沖擊,也讓宣傳思想工作、文化文藝工作面臨新的挑戰。在《加快推動媒體融合發展》一篇中,習近平要求:“宣傳思想工作要把握大勢,做到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強調“推動媒體融合發展,使主流媒體具有強大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凝聚起全體人民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的“同心圓”,“讓正能量更強勁、主旋律更高昂”。習近平要求:“擴大主流價值影響力版圖,讓黨的聲音傳得更開、傳得更廣、傳得更深入。”他強調,“主流媒體要敢于引導、善于疏導,原則問題要旗幟鮮明、立場堅定,一點都不能含糊。”④這些講話中蘊含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從強化突出主流輿論,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精神力量和輿論支持的高度,給文化文藝工作者和媒體工作者提出了更高、更明確的任務和要求。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舉國同心、舍生忘死,以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大無畏氣概,與瘟疫進行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殊死較量,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重大戰略成果。在這場偉大斗爭中,各行各業都涌現出英雄的“最美逆行者”,文學界也不例外。除擔任志愿者、下沉社區、組織捐助、守望相助,親身參與抗疫斗爭外,不管是成名的作家、詩人,還是文壇新秀,紛紛通過傳統紙媒或自媒體,用詩歌、散文、書簡、非虛構作品、報告文學等各種樣式,記錄抗疫斗爭,抒寫心路歷程,寄托生命悲憫,贊美抗疫英雄。作家們與時代同步,為人民立言,鑄國家之魂,講好了中國故事。
疫情期間,《湖北日報》 文學副刊《東湖》,迅速用一系列詩篇和短章,落筆抗疫帶來的情感心理,擷取疫情期間的生活截面,速寫投身抗疫的各色平民英雄,呈現了主流媒體傳播主流價值影響力的責任擔當。抗疫斗爭全面勝利后不久,劉詩偉、蔡家園推出長篇報告文學《生命之證——武漢“封城”抗疫76 天全景報告》,則以“見證歷史的在場姿態”,全景式地再現了武漢抗疫的宏大畫卷,踐行了習近平對文學工作者“描繪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圖譜,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⑤的希望,是當下抗疫報告文學的扛鼎之作。選取《東湖》副刊和《生命之證》為樣本,以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偉大斗爭為背景,思考從抗疫之中到后抗疫時代,文學工作者的使命任務,是本文學習、研究、闡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第三卷的重要視角。
二
2020 年1 月29 日,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武漢“封城”后近一周,作為湖北權威主流媒體的《湖北日報》,其文學副刊《東湖》出版首期抗疫文學專版《陽光與生活不會隔離——湖北作家抗疫題材作品選》,共發表5 首詩歌,2 篇紀實性散文。其中一首題為《詩人》的詩歌自問:“新冠病毒穿著黑色大氅,襲擊我們的時候,詩人,我們該做什么?我們能夠做什么?”作者進而自答:“我們給被襲擊的人們祝福祈禱,愿他們頑強抵抗,早日站起來,和我們一起享受春風陽光。我們給不畏危險與犧牲,日夜戰斗在疫區的白衣戰士,寫一首深情的歌,獻上我們心中的問候與敬意。我們給奔馳千里來援的軍人,我們給告別家人放棄休假的各地醫療隊,給各行各業捐物捐錢的人們,寫一首長詩。”最后卒章顯志:“我們就是與中國在一起!”⑥本詩是急就章,淺顯直白,但真情流淌,也許代表了大多數湖北文學人面對災難的情懷和立場。這樣的情懷、立場,一直延續到湖北“解封”、武漢“開城”,以至后疫情時代,奠定了《東湖》副刊以及《湖北日報》抗疫專版《眾志成城,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 《毫不放松,堅決打贏湖北保衛戰武漢保衛戰》中抗疫文學書寫的主要基調,踐行了習近平對主流媒體的要求,正能量的旗幟始終高舉,主旋律的節奏始終昂揚。
初略統計,從 2020 年1 月 29 日到 2020 年5 月23 日,《東湖》副刊和《湖北日報》其他兩個抗疫文學專版,共發行14 期。其中發表抗疫題材的作品45 篇,包括現代詩17 首,現代散文20 篇,古詩詞5 首,古體辭賦2 篇,書評1 篇。白居易曾言:“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這些作品,形式不一,視角各異,但都在對抗疫斗爭的即時記錄中,履行了習近平強調的“堅持與時代同步伐”,“為時”“為事”,“發時代之先聲”的使命,在新時代的重大事件中體現了湖北文學人的積極作為。
詩歌是時代的號角,當為時代鼓與呼。特別是時代風云激蕩、國家民族面臨危難之際,詩人們抒情、言志,為時代吶喊、謳歌,發出時代的最強音,這是中國詩歌源遠流長的傳統。古詩詞工整凝練,情思蘊藉,詞約義豐;現代詩不拘格套,自由奔放,直抒胸臆。它們在回應時代需要時噴薄而出,最為迅捷。《東湖》副刊和其他專版發表的抗疫詩歌,大多篇幅短小、語言質樸,但以國家、人民為書寫對象,以展現生死之間艱苦卓絕的抗疫斗爭、謳歌崇高悲壯的抗疫精神為主要內容,所以整體依然風格豪邁、大氣磅礴。詩詞的主題之一,是歌頌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責任擔當,歌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歌頌黨和國家領袖生命至上、運籌偉力的卓越領導。如詞作《聲聲慢》下闋所詠:“縱有驚濤駭浪,憑燈塔、中流擊楫馳情。直面風狂雨急,力挽危情。凝眸華表高聳,成城志、抖擻豪情。送瘟神、春雷滾滾,蔥綠關情。”⑦主題之二,是激情洋溢地歌頌白衣天使、人民軍隊、人民警察、志愿者——這些勇敢逆行的戰士、英雄。這些詩歌,常常展現以鐘南山為代表的各行各業抗疫英雄的群像,對他們的勇敢、奉獻、擔當、犧牲充滿感激和敬意。如《請記住那些護住武漢傷口的人》中所寫:“記下那位84 歲的老人”,記住“一襲白衣,一身橄欖綠、警察藍”⑧。其他如《堅守》 《致親愛的勇士》 《一個超負荷的群體》 《戰士》 《天使的身影》等詩作大多都是這樣對英雄群體的贊美。《是不是》則聚焦個體,勾勒身患漸凍癥仍堅守一線的張定宇醫生的形象,向這位勇士寄寓美好期許,“漸凍癥,是不是在寒冷的冬天,一塊土地暫時凍住了。等到春暖花開,一雙腿就會蘇醒過來,這條漢子就能重新大步流星”⑨。主題之三,則是以普通人的立場,表達與國同心、共抗疫情、共度時艱的意志。如《隔離》,鋪展生活圖景和心靈體驗,誓言“珞珈山的櫻花夢沒有隔離;900 多萬守城者的燈火與漫漫長夜沒有隔離;龜蛇相望,與黃鶴樓興衰廢替沒有隔離;陽光與生活不會隔離;俞伯牙與鐘子期的琴聲,不會隔離;高樓與高樓的喊話,不會隔離;我與你,流沙一樣的光陰,不會隔離;這千年的城郭,與安寧祥和,不會隔離”⑩。表達了普通人身處疫情的堅定、沉著,其他如《守望的貢獻》 《這座生我養我的城市》皆與之類似。
《東湖》副刊等文學專版表達抗疫主題時,散文的篇章最多。但這些文字,如習近平對文藝工作者所希望的,跳出了“身邊的小小的悲歡”,不再是傷春悲秋、吟風弄月、考據辭章,而是對抗疫斗爭的現實場景和心路歷程進行了真實、深刻、精微的記錄,大半都是非虛構文學。這些文字主題與詩歌類似,但內容則更為豐富,情感則更為充盈,哲思則更為深蘊。《新“英雄兒女”的故事》 《護士李倩》 《攜手逆行》 《背影》 《“媽媽,你什么時候回來”》等,都以紀實的筆觸、細節的再現、真誠的情感,描繪了一線醫務工作者、下沉干部、志愿者的工作和生活。作者似乎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不動聲色,文章多以平淡舒緩的語調,將城鄉基層的逆行者還原為普通人,將他們勇敢的抗疫行為,置于與父母、孩子、親人之間凡俗感情,置于受到沖擊但依然繼續的日常生活中,娓娓道來。這樣的筆法書寫平民英雄群體,樸素真切,感人至深。疫情洶洶,這些平民英雄,卻格外體現出自在樂觀的精神、堅韌沉著的意志,及對生活的熱愛和戰勝瘟疫的勇氣。也許,這也是中國大多數普通百姓的氣質和秉性,就是習近平希望文藝創作要闡釋好的“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
在《自覺承擔起新形勢下宣傳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務》中,習近平強調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是堅持文化自信的重要前提。《東湖》 副刊發表的2 篇抗疫古體辭賦,一為《疫說》,一為《武漢壯歌》,前者是運用唐宋散文的寫法,后者則類似于漢賦。《疫說》溯古追今,落筆中外,點評人類歷史上遭遇的各種瘟疫,提出“今日科技如是發達,衛星上天潛器入海,患小蟲何?”“今日之疫,何以倏兒全球焉?”“人類向有疫災,防范自不可怠,何至嚴重如是”等系列拷問,并作出回答,最后以“人類同類,疫情面前全球之人宜為一體也”?作結。全篇別有思考,頗有警世之言的意味。《武漢壯歌》以“庚子開元,武漢戰疫,華夏一盤棋,萬眾齊奮起,蕩滌瘟神,護民安康,山河無恙,苦戰疫遁春歸”開篇,以“阻擊疫情,宅居衛家國”“挽救生命,白衣天使建奇功”“共克時艱,武漢攻堅鑄豐碑”為線索,在鋪排句式、駢偶對應間,展現了武漢——這座英雄城市抗疫的全景畫卷,歌頌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抗疫精神。該文以梳理武漢的歷史變遷終章,發出“庚子抗疫,封萬千居民于一城,令百業俱損所不惜,亙古壯舉,增輝華夏”?的感慨。《武漢壯歌》縱論古今,既總結了武漢抗疫現實圖景,也對家國天下的未來進行了展望,宏闊縱深,寄寓深遠。這兩篇抗疫古體文,讓人看到當代中國文學工作者堅持文化自信,繼承和發展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讓其成為新時代建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可貴資源的努力。
三
劉詩偉、蔡家園的《生命之證——武漢“封城”抗疫76 天全景報告》 (以下簡稱《生命之證》)發表于《中國作家》 (紀實版)2020 年第10期。這部作品,被推薦人譽為“國內第一部全景式書寫武漢‘封城’抗疫的長篇報告文學……凸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信念……闡揚了中國作家為社會留檔、為歷史存真、為民族鑄魂、為人類問道的擔當精神及寫作初心”?。這部作品,與時代同步,為人民立言,鑄國家之魂,呈現出較強的“腳力、眼力、腦力、筆力”。作品選材鮮活翔實,格局縱深廣廓,視域多維交錯,氣度雄渾悲壯,思緒深蘊沉郁,是后抗疫時代全面還原驚心動魄的抗疫斗爭、弘揚偉大的抗疫精神、講好全民抗疫的中國故事的佳作,是作家不辜負習近平對文化文藝工作者殷切冀望而努力耕耘的成果。
習近平要求,文藝創作要“立足中國現實,植根中國大地”,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生命之證》以切身的在場視角,深入一線,呼應了總書記的要求;貴在真實,秉持了報告文學的要義。兩位作者都是湖北武漢作家,疫情爆發、武漢“封城”之際,他們正在圍城之中,親身經歷了疫情期間,從生命流逝、恐慌痛苦、封城禁足,到舉國馳援、疫情緩解、開城解封、最終勝利的全過程,有著至為真切的身心體驗。難能可貴的是,疫情尚未緩解之際,他們就下沉社區主動申請并獲許可后,就冒著生命危險,奔赴抗疫一線,“逆行”采訪,至4 月8 日武漢“開城”,長達42 天。他們四處奔走,足跡遍及醫院、社區、工地、科研單位;他們廣稽博采,采訪對象從院士、醫生護士、志愿者、援鄂醫療隊、火神山雷神山的建設者,到警察、患者、市民、社區工作者,獲得了鮮活、豐富的一手材料。作者“走進實踐深處”,立足翔實證據,忠實全面紀錄,對重大歷史事件進行在場性、親歷性的書寫,真正做到了“把握時代脈搏,聆聽時代聲音”,如作品的命題“生命之證”,是對時代的“立此存證”。
習近平強調,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方向:“文學藝術創造、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為誰創作、為誰立言的問題,這是一個根本問題。人民是創作的源頭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創作才能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他勉勵文化文藝工作者,要“觀照人民生活,表達人民心聲,用心用情用功抒寫人民、描繪人民、歌唱人民”?。《生命之證》精心選擇,對火神山、雷神山、方艙醫院等“生命島”或“生命方舟”,進行了散點聚焦的全景書寫——堅定果敢的決策者,與時間賽跑的建設者,仁心大愛的醫護人員,從恐懼到安心的患者……特殊時期、特定空間中的眾生態躍然紙上,萬眾一心、生命至上、勇敢樂觀的精神力量也是呼之欲出。《生命之證》還匠心巧思,用寓意深遠的比喻,為抗疫斗爭中居功至偉的“逆行者”畫像。他們是:“生命擺渡人”——重癥醫療隊醫生;“與死神跳貼面舞”——插管切管隊員;“上醫治未病”——中醫專家和醫生;“黑色提燈人”——護理工作者;“封城第一堡壘”——社區工作者;“滿城螢火蟲”——志愿者;“人類的福音”——科研工作者。對這七個群體的刻畫,面目生動,速寫整體概貌與工筆描摹個體穿插,第一人稱直言實錄與多人稱側面渲染并用,謳歌偉大精神與記錄凡人情懷兼備。通過多場景、多視角、多語境的寫法,《生命之證》“以人民為中心”,樹立起新時代的人民英雄群像,對于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意志力、堅韌頑強的生命力、深厚強大的凝聚力,表達了真誠熱切的贊美與謳歌。
《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結的偉大抗疫精神,第一就是“生命至上”,強調我們黨不惜一切代價,保護人民生命安全的宗旨和意志。《生命之證》的命題,就突出了這一宗旨。在“引子”中,作者開宗明義地指出:“瘟疫之于人類,根本上是一種避開種族、階層、國家和意識形態的進犯,人類必須盡快建構并學習與瘟疫相遇、相處、相爭的文明,而這個文明的根基與指引只能是生命至上。”并認為,生命是“生發和確認真理的邏輯起點”。?將“生命至上”視為文明的根基、真理的起點,讓《生命之證》對重大疫情的書寫,沒有流于控訴生命逝去的“賣慘”,而是從哲理高度,譜就了一曲交響樂般波瀾壯闊、激越跌宕的生命悲歌。交響樂的首章是“悲傷”:它記錄了開始封城的一段時間,不斷新增的確診病例、死亡病例,各種生離死別消息的蔓延,猝不及防的恐慌、憤激和憂傷,曲調低沉而空茫。交響樂的主章是“悲壯”交織“沉思”:高層果斷決策全面部署,醫護爭分奪秒與死神拉鋸,百業齊心同抗瘟疫,全民參與英雄輩出,捷報頻傳轉危為安,疫霾散去城市復蘇,放眼世界向天問道……多聲部的旋律交織回旋,高低起伏,曲調悲愴、壯闊而昂揚。交響樂的終章是“希望”:伴隨林徽因的詩歌《你是人間的四月天》、周華健的歌曲《親親我的寶貝》,疫情期間新生兒和患兒的故事奏響,讓最后的曲調清新而明朗!這是一曲磅礴悠長的生命悲歌,貫穿著生命的“死亡——救贖——新生”的脈絡,寄寓著“悲天憫人”的情懷。就如習近平指出的:“生命至上,集中體現了中國人民深厚的仁愛傳統和中國共產黨人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追求。”?《生命之證》是對生命的關注和思考,某種程度上,也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神內涵,進行了傳承和闡釋。
習近平希望文藝創作,要“把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闡釋好”,要“樹立高遠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國情懷,把個人的藝術追求、學術理想同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緊緊結合在一起”?,要“不斷推出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書寫中華民族的新史詩”?。《生命之證》的敘事,以國家敘事為主視角,其中個體視角、人性視角、文化視角錯雜,既形成敘事的張力,也達致敘事的復調。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人類遭遇的一場災難,《生命之證》 也可被視為災難文學。書寫災難,作家會思考、探究、反抗一切造就災難的因由,包括虛偽的政治、僵化的體制、顢頇的官僚,強化“荒誕”“異化”等主題,如加繆的《鼠疫》。《生命之證》沒有回避類似的反思,卻未走向對國家政治的指責、批評和對抗。從第三章《我們有國家》、第四章《戰役進行時》開始,直至終章,作者梳理了“封城”抗疫的頂層決策、國家層面的雷霆行動、扭轉戰局的關鍵舉措、舉國動員的制度優勢、令人安心的經濟實力、和衷共濟的文化力量……記敘客觀,數據詳實,體現了國家敘事的基本立場,再現了災難面前,國家始終都在,國、家、人,整體抗疫的中國故事。這讓人想到詩人杜甫。在國家遭遇巨大動蕩,人民身處深重災難,自身也顛沛流離、窮困潦倒之際,杜甫不忘將個人命運、個體視角和國家命運、國家政治緊密相連,始終與國家共命運、與人民同呼吸。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及“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等詩句,飽含感時憂世、仁民愛物、心懷社稷、與國同心的思想情懷。《生命之證》很大程度繼承了這種“家國同構”的文化傳統。作者以深沉的家國情懷,通過宏觀的國家敘事,再現了驚心動魄、艱苦卓絕的抗疫斗爭,贊美了“舉國同心”“舍生忘死”的偉大抗疫精神,闡釋了新時代的中國精神、中國價值和中國力量,作品也在這種意義上,具備了中華民族新史詩的氣魄。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的其他專題在論及建設生態文明和國際關系時,多次強調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各國各民族之間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生命之證》也將書寫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斗爭,放諸世界抗疫的大勢中,切入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體現了較為鮮明的共同體意識。在“引子”中,作者指出,瘟疫引發對人類生命的真理的重新敘述,“不是觀念的超越而是自然的終結,是人類好日子的前提。當然,它不可能通過寫作來實現——必須經由人類共同契約踐行”?。在第十三章結尾,記錄下對科研工作者石正麗的采訪,她說:“這個病毒(SARS)不是因為我們人類而來的,是為了自己的生存不斷繁衍下來的……人類的安全,是與野生動物和大自然和諧共處。”?作者恍然悟到:病毒對我們人類并沒有進犯的主觀故意,人類的福音,是與病毒簽個和平協議或各走各的陽關道。第十四章《武漢告訴世界》,既不諱言某些國家惡意指責中國抗疫,其背后潛藏的叢林法則及邪性的“優越”“傲慢”與掠奪性;同時坦率地指出對待疾病與瘟疫的經驗、觀念及文化的差異,也是國家間出現抗疫分歧的原因。在本章,作者講述了兩類故事:武漢醫生與外國同行交流抗疫經驗的故事;三位在漢參與抗疫的外國友人的故事。這種對共同體意識的思考,讓《生命之證》的視野更為廣闊和深刻。
新冠肺炎疫情,是進入新時代的中國遭遇的“一場艱苦卓絕的歷史大考”。這場大考面前,一些有信仰、有情懷、有擔當的文化文藝工作者,積極投身抗疫斗爭,以筆為旗,留下了作為時代記錄的文字。這些文字,散見于報刊等傳統媒體,以及公共號、微信群、微博等新媒體,有些已結集出版。《東湖》副刊和《生命之證》在抗疫之中和后抗疫時代,圍繞抗疫斗爭的主題,是主流媒體、文化文藝界貫徹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的兩個樣本,顯現出可貴的成績。令人遺憾的是,還有相當多的抗疫文學呈現出急就章、同質化、缺錘煉的傾向;有些作品在浮泛的抒情、虛造的故事、空洞的議論、瑣碎的細節、淺陋的語言中,消解了崇高感、使命感和英雄主義,悲憫性、反思性和深刻性也有不足。因此,關于抗擊新冠疫情的文學書寫,富有影響力的優秀作品尚未大量涌現。
當下,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完全結束,中國社會已進入后抗疫時代,但對抗疫斗爭的文學書寫不會結束。畢竟,剛剛過去的這場斗爭,交織著生與死,血與淚,勇敢與怯懦,偉大與卑瑣,逆行與退縮,責任與推諉……可供書寫的太多太多。后抗疫時代,對抗疫的回顧、反思、沉潛,抗疫帶來對現實和未來的憂患、期待、展望,疫情引發對人類之間、人與自然等命題的探尋,對抗疫斗爭激發出的民族精神的挖掘,將會成為文化、文藝創作長期傾注心力的方向。后抗疫時代,從詩人、作家到劇作家,從報紙、電視到網站、公眾號,更多的文化文藝工作者和媒體從業者的任務:第一,是深入學習、研究、闡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全面領會其中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第二,要以更加全面的視野,更加深入的了解,更加細致的書寫,更加深刻的思考,濃墨重彩地敘寫和贊美抗疫斗爭中的英雄人物、英雄事跡;第三,要高揚抗疫斗爭鑄就的“生命至上、舉國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學、命運與共”的偉大抗疫精神,繼續闡釋新時代的中國精神、中國價值和中國力量;第四,要堅持“四個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繼續用文學的力量,繼承并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講好后抗疫時代的中國故事,建設好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家園,筑牢民族團結奮進、一往無前的思想文化基礎。
注釋:
①? 習近平:《自覺承擔起新形勢下宣傳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務》,《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 卷,外文出版社2020 年版,第311、313 頁。
②③⑤??? 習近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魂》,《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 卷,外文出版社2020 年版,第 322、323—325、323、324、323—324、325 頁。
④ 習近平:《加快推動媒體融合發展》,《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 卷,外文出版社2020 年版,第317—319頁。
⑥ 謝克強:《詩人》,《湖北日報》2020 年1 月29日。
⑦ 羅輝:《聲聲慢》,《湖北日報》2020 年2 月21日。
⑧ 侯國龍:《請記住那些護住武漢傷口的人》,《湖北日報》 2020 年 2 月 15 日。
⑨ 李昌海:《是不是》,《湖北日報》2020 年4 月20 日。
⑩ 謝春枝:《隔離》,《湖北日報》2020 年1 月29日。
? 葛昌永:《疫說》,《湖北日報》2020 年5 月20日。
? 劉友凡: 《武漢壯歌》,《湖北日報》 2020 年4月 20 日。
? 葉梅: 《生命之證·推薦人語》,《中國作家》(紀實版)2020 年第 10 期。
?? 劉詩偉、蔡家園:《生命之證》,《中國作家》(紀實版)2020 年第 10 期。
? 習近平:《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0 年9 月9 日,第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