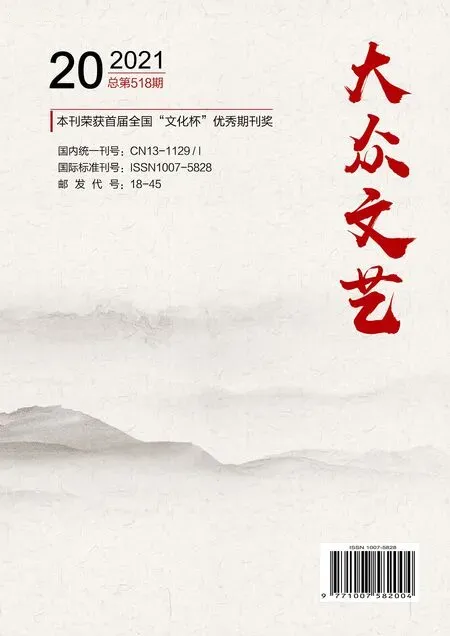從“氣韻”看中國古典美學的詩性思維特點
(四川文理學院,四川達州 635000)
氣韻的美學范疇是中國文化領域最具代表性的范疇之一,在南北朝畫論之后普范化于美學的各個領域,占據著核心地位,表達了先人們對宇宙、人生和藝術的看法觀念,通過直觀感悟,刻畫著事物外象之外的東西,呈現出了一種充滿詩性韻味的言說,達到了天人相合的境界,透露出了無垠的生命光芒,受眾在此種美感的浸淫,觸動了更多人生領悟。
一、詩性思維
縱觀中國古典美學的發展,一直以感悟的、形象化的方式談論美學問題,從早期《尚書》的“詩言志”,到劉勰的“神思”說,再到近代王國維《人間詞話》的“境界”說,[1]一直沿襲著這種極具詩性化特征的表達方式。這也使得我國的古典美學發展始終沉浸在濃郁的人本主義關懷當中,有著相當厚實的倫理基礎,并非強調對客觀事物的屬性認知,而是更加偏向于道德、精神和情感的熏染,力求心靈心境的升華,與西方理性思維有著明顯差別,類似于維柯的“詩性智慧”。思維模式是人的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有歷史社會文化的元素,也有現實社會意識形態的元素,既是文化深層次結構的,也是人的行為的顯性呈現,具有相當大的普遍性。“詩性思維”可以說是維柯對原始人類思維認知方式的統稱,他將“詩性”思維看作一種非理性、非邏輯推理性的感性思維方式,主張通過人類豐富的想象與聯想來達到“詩性”思維。認為“最初的詩人們給事物命名,就必須要用最具體的感性意象”。同時,臺灣學者林雪鈴基于對維柯《新科學》的研究,對“詩性思維”進行了更為詳盡的表達,認為“詩性”思維是人類思維方式的一種返璞歸真,是以孩童的視角來重新審視周圍事物,通過想象、聯想的運用將主觀情緒過渡到客觀事物上,由此達到一種心、物交融的精神境界。 詩性思維最顯著的特點在于“以己度物”,即以自我為中心、以自我為衡量的尺度來想象事物,并以這樣的方式認知世界。縱觀中國古典美學中的詩性思維呈現,創造了情景交融的境界,心物合一是對其最本質內涵的有力表達,更容易牽引出受眾的共鳴感受。以林永的《雨霖鈴》為例,他用寒蟬、長亭、驟雨、蘭舟、煙波、楊柳、殘月等深度刻畫了別離的傷情,滿眼盡是無邊的秋景,一幅凄婉而恢宏的場景瑩然腦海之中,可以說是對詩性思維最為典型的運用。同時,詩性思維還長于用奇特的想象來創造心的意象和境界,并通過比喻、擬人、夸張等手法來完成思維的過程,在中國傳統文學創作中尤其多見。當然,中國古典美學中的詩性思維,絕非原始思維,其只是更多保留和積淀了原始思維的某些特質,并在此基礎上加以創新,形成了一種全新的美學范式,有著極為重要的啟示意義。
二、“氣韻”視角下的中國古典美學詩性思維特點辨析
中國古典美學中的詩性思維尤其明顯,塑造了差異化的美感,在繼承了部分人類原始思維方式的同時,又強調必須遵循思維發展規律,充分迎合集體無意識共同文化心理,從“氣韻”的古典美學范疇進行解讀,可進一步窺探其特點特色,具體相關表述如下:
(一)耦合哲學
中西方的思維生態演化有著極其深遠的歷史,與之生成背景有著莫大的關聯。在西方世界,理性思維伴隨著否定之否定的演化道路更新迭代,并寓于其中的真理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發展,繼而推動著獨特社會形態的顯化。反觀中國傳統文化歷史,在清末國門被打開以前,幾千年的輪回發展中似乎只有一種“生產”范式,縱然不斷改朝換代,但社會形態的本質卻尤其簡單,從氣論上講,我國先人的世界圖式似乎已經圓融無缺,在包含了所有否定與重復的永恒中,締造成了一個合題,即“善”,用直覺和感悟表達著對客觀世界的認知,突出了“人本”的思想追求。而“向善”思維所追求的并非直達心靈彼岸的安寧,而是要突顯這種文化精神對現世人生心靈的渲染,促進其內在品質的升華。區別于西方以知識為中心建立的嚴謹邏輯思想體系,中國先人更加強調以人為出發點,在“象”與“意”的直接關聯中,塑造了獨特的審美氣韻,附帶有明顯的泛神論意義,是可以通過實踐和直覺求得的,頌揚了人之本身存在的本質。從氣韻上來看,中國古典美學可以說是直覺感悟與理性思維相互融合的產物,無論是對主體心靈還是對客觀事物都發揮著重要的掌控作用,從而生成了一個思維與情感相融的整體,將之置于現代哲學體系中,則呈現出了對事物整體式地把握,其詩性思維特點在于具體事物的抽象表達,達到了知情意合一的美學境界。某種維度上講,正是基于中國古典美學“氣韻”范疇和,通過詩與哲學渾然一體的思維,折射出了文化本身就具有的詩性特質,并非刻意而為之,顯示出了中國古典文化以和為美的心理定式。在中國傳統文化歷史上,雖然不乏覺醒者,著力主張生命力的“氣”,如管子說:“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和,知乃止矣。… …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由此可見,管子將精、氣、道看做了世界萬物生命的本源[2],但受儒道思想的影響,其中蘊含的陽剛色彩逐漸被淡化,最終落于自我精神的玩味。中國傳統文化中以生命為美,對平安、祥和、圓滿的追求,尤其突出了氣韻中的崇高意味,象征著觸及生命與無限宇宙合一時主體生成的精神狀態,是哲學中獲得美感與體驗的升華。
(二)同情萬物
氣韻釋義為文學或藝術上獨特的風格。單從“韻”字上講,很容易聯想到音響律動,而魏晉南北朝時期則又將“韻”當作一個形容詞對待,突顯人物的卓越風姿。這種內涵意義的變化,正是基于審美對象所呈現給感官的情感形式或“格式塔”。在中國古典文學領域,以氤氳浩渺的“氣”為中介,達成了音韻和諧與生命感悟的同奏,促進了實體精神附著,增強了萬物的生命之光,“天人合一、物我相忘”的詩性思維特點由此生成,展現了一派祥和的“氣韻”。劉勰就曾經指出詩人“為情而造文”“述志為本”。作品美感成就的高低,決定于它的“情志”有無和高低。在“情志”中,是“心與物”皆在其中的。心物交融,即情與志豐厚、深沉地互相滲透狀態,這是物—我即主觀與客觀水乳交融的一種審美情境。[3]我們可以將此處的“心物交融”視為一種“詩性智慧”,源于“擬人化”的情態,造成了原始思維中物我混沌的狀態,在未有西方科學精神的規范下,其所迸發出的情感更為強烈,有著極為明顯的象征韻味,如腐草生螢、精衛化鳥、螟蛉為子等。中國古典美學的這一詩性思維特點,建構起了“氣韻”的心理基礎,打通了萬物情態與道德精神的聯接,促進了生命感悟的升華。某種意義維度上講,中國古典美學所塑造的“氣韻”,不單單是事物風度儀態的客觀呈現,同時又形象刻畫著生命音響的流動,這本身就是詩性思維最具典型性的成果,達成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寓于中國古典美學中的“氣韻”,締造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希望在藝術的創造與鑒賞中關照對天地萬物的體悟,并在跳脫當中大徹大悟,這既是對大自然磅礴氣勢的回應,更是對無垠生命的感懷,主體情感的植入,使得中國古典美學的氣韻更顯靈動,某種維度上亦是對“本善”的回歸,這與先人們以和為美的思想觀念高度契合。從“韻”的角度對中國古典美學的詩性思維特點進行解讀,讓人們對自然之美的把握更加深刻,并觸及了更加深層次的人生感悟,并因此尊重生命、熱愛生命。
(三)跳脫理性
單純地對中國古典美學的詩性思維特點進行解讀顯得了籠統,可對照西方美學理性思維,從而使得“氣韻”范疇的美觀呈現更加鮮明。自亞里士多德將“有機整體”概念引入到藝術理論之后,就孕育出了西方美學中的“生氣灌注”思維。對此,知名藝術大家歌德亦指出藝術要以一種神圣而極具飽滿的精神作為敘述的語言。在歌德時期的西方美學范疇中,唯有富有生命力的藝術創作才是崇高的,要求塑造出能夠顯示特征的整體,可以在思想上達到理性與感性、主客觀的高度統一,其中蘊含著各部分能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內在規律,從而呈現出事物的有機性和完整性。同時,在黑格爾看來美與藝術應當是絕對理念的派生物,他從“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這一維度層次出發,窺探到了藝術美的基本特征-感性觀照,強調理性與感性的融合升華,尤其突出了心靈的觸感。正如黑格爾所述說的那樣,“藝術美是由心靈產生和再生的美”。藝術之于人類社會發展的價值,在于用感性的形式去顯現真實,并由此傳遞某些深邃的思想理念,促進人世間的美好。對此,黑格爾就曾在其著述中強調藝術家不僅要具備理性思維,更需要在深厚情感的刺激下顯示出一種極具靈魂、生氣、風骨、情感的精神,從而進行藝術作品的創作。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美學中的“生氣灌注”與我國古典美學中的“氣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均是追尋著對事物本體外觀的感悟,強調了藝術創作中的情感、精神表達。但是,中國古典美學中的詩性思維亦有著自身獨屬的一面,區別于西方美學中的“生氣灌注”,在尊重自然之美的同時,將其中的自然氣韻轉化為藝術氣韻,一山、一木、一草、一樹等顯露出了天地之大美,相比與西方理性思維,更加接近詩性思維的審美心理原貌,所呈現出的藝術效果更容易觸及受眾的心靈和共鳴感受。
三、結語
綜上所述,中國古典美學中的詩性思維特點尤其突出,對“氣韻”的營造,綻放出了無垠的生命之光,其本身源于客觀事物,而又升華于其外象,力求自然之美與道德精神的締結,達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其中布滿了哲學的韻味,游離于理性思維之外,而又暗合著對人生的思考,是最具代表性的美學范疇之一,在現代文學創作中的運用值得借鑒和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