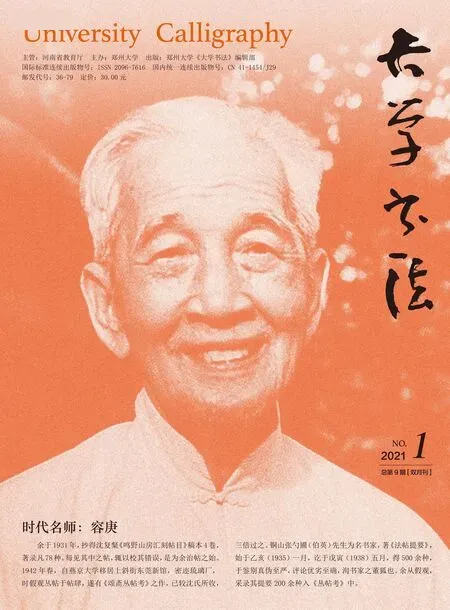屏幃精良與書藝輝映
——宋代書藝與屏風的互動關系及其傳播
⊙ 張文強
引言
魏晉以降,書法成為一門以觀賞性為主的獨立藝術。書家們嘗試著各種表現書法藝術的形式,在探索過程中,題寫屏風成為書家表現書法藝術的方式之一。史書記載,東晉王羲之有書扇題屏的雅好,南朝人庾元威在《論書》中講道:“書十牒屏風,作百體,間以采墨。”[1]唐代時不僅有唐太宗書《屏風帖》傳世,而且張旭、懷素題寫的粉壁醉屏也一時傳為佳話。屏風這一形式在魏晉以來各個時期都有所運用,到了宋代,隨著高型家具的普及,屏風形制的日益完善,宋人書法藝術的繁榮,題寫屏風成為表現書法的重要形式之一。
宋代是中國書法發展的繁榮期。寬松的社會環境、尚文的社會政策、造紙術的進步與昌盛使書法藝術在民間空前的繁榮。說到宋代最好的書法陳列和展覽形制,后人根據流傳下來的手卷作品、掛軸和題壁資料,就認為卷、軸和題壁是宋時書法藝術的主要表現形式。然而,這種認識過于簡單化了,書法藝術在發展過程中是紛繁復雜的。事實上,在當時有一種常見且適于展現書法的形式被后人忽視,即屏風書法。
一、宋代屏風書法之表現意義
關于宋代屏風書法,歷史文獻中有許多記載。如董嗣杲《新橋遇秋巖》:“鳥巾漉酒菊花店,醉揀陶詩書紙屏。”將陶淵明的詩作為題材揮灑到紙質屏風上。陸游《暖閣》:“紙屏山字樣,布被隸書銘。”[2]用古老的隸書抄寫銘文。“乘閑欲擬歸來作,小草斜行滿曲屏”[3],閑來無事題小草于折疊屏風之上。咸淳士人有詩云:“深院無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尚輝煌。”[4]林用中亦有詩句:“行客悠悠心目快,漫題新句在空屏。”行人有感而發,將創作的詩句題寫于屏風之上。這些詩句都反映了宋時期屏風書法作為一種常見的表現形式活躍于文人墨客之間。
屏風書法在宋代能夠風靡一時,其本身較于其他形制具備不可替代的優勢。
首先,屏風隨著宋時人們生活起居和室內結構的擴展而增高增大,且在宋時得以普及。屏風大量存在于酒樓、客廳、臥室等公共和私人場所,宋時卷軸畫和壁畫中有描繪當時擺設屏風書法的場景。例如,夏圭所繪《雪堂客話圖》中有屏風書法陳設,李成的《晴巒蕭寺圖》中蕭寺塔下酒樓裝飾有屏風書法,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報關辦事處官員身后則是行書屏風書法,陜西韓城宋墓墓主行醫圖背后也有草書屏風。從這些繪畫作品中,我們能夠看出無論是酒肆樓閣,還是私人場所,書法屏風陳設都使觀者一目了然。屏風內字的大小相對于卷軸來講能夠更加靈活,章法排列具有可塑性。橫卷和掛軸則不然,卷的常態是放在盒內收藏,只有在人們欣賞時才打開,且宋時卷的縱高往往是30cm左右,例如蘇東坡的《黃州寒食帖》是縱34.2cm,橫199.5cm(含黃跋);米芾的《蜀素帖》是縱29.7cm,橫284.3cm;黃庭堅的《李白憶舊游》是縱37cm,橫392.5cm;《諸上座》是縱33cm,橫729.5cm。長度和寬度決定手卷適用于攤在桌上把玩,是宋時書齋式的觀賞方式,而軸受裝裱和懸掛的影響往往以三到五行為主。宋代題壁書法的規模雖然沒有如唐代那樣粉壁長廊數十間,但宋人題壁依舊盛行。遺憾的是,題壁書法一般存在于高樓和寺廟墻壁,且不易保存。

李成 晴巒蕭寺圖(局部) 納爾遜 · 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
其次,各式各樣的屏風充斥在宋人生活中,玉堂瓊榭、茶房酒肆內陳列著直立板屏、折疊屏風,臥室與床榻相結合的枕屏,書房中的硯屏,庭院里的石屏,皆可與書法藝術相結合。因而,宋代文人將書法與屏風這一器物相結合,形成一種集休閑、娛樂、觀賞于一體的互動關系。
題壁和手卷,早在魏晉時期早已出現,到宋代仍是主流形式。宋時造紙術的興盛又推動了掛軸出現,因此這三種書法形式對宋代書風的面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除此之外,屏風的存在也成為宋代書法的一條獨特的風景線。宋時文人士大夫對屏風充滿著別樣的意趣,通過對屏風的書寫體現出最佳的呈現方式和高雅的審美情趣,筆者認為這也是宋時期掛軸盛行而屏風卻未被掛軸完全取代的原因。
總之,宋時期存在著多元的書法形式,在多種書法形制的交相輝映下,其書法生態呈現出豐富多彩的樣貌。而在多種表現形式之中,屏風作為最佳的展覽方式之一則顯得尤為突出。
二、唐宋屏風書法之轉型
唐宋時期,屏風在文人的觀照下,成為表現書法藝術的重要載體。然而,唐宋兩代的屏風書法有著明顯的差異。
藝術風格的形成、轉變與社會環境息息相關。唐朝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國力最強盛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內,唐統治者采取積極包容的政策與周邊民族和周邊國家交往,無不彰顯著強大的文化自信。因而唐朝的藝術風格大氣磅礴、雍容華貴,無不彰顯著大國風范。顏真卿雄健渾厚的楷書與行書,張旭、懷素龍蛇飛動般的狂草,皆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代表。書法風格反映在屏風上,就像韓偓所說的那樣:“若教臨池畔,字字恐成龍。”[5]
屏風書法的磅礴氣勢在這一時期表現得淋漓盡致。這一時期唐太宗、張旭、懷素、徐浩、李陽冰、白居易、劉禹錫等皆喜好題屏。其中,唐太宗李世民作真草屏障以示群臣,其筆力遒勁;徐浩以草隸入屏,被時人描述為“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任華《懷素上人草書歌》曰:“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已后始顛狂。一顛一狂多意氣,大叫一聲起攘臂。揮毫倏忽千萬字,有時一字兩字長丈二。”可見其氣勢奪人。梅堯臣曾作詩云:“往在河南佐王宰,王收書畫盈數車。我于是時多所閱,如今過目無遁差。石君屏上懷素筆,盤屈瘦梗相交加。蒼虬入云不收尾,卷起海水秋魚蝦。毫干絹竭力未盡,山鬼突須垂髿髿。牽纏回環斷不斷,秋風枯蔓連蒂瓜。縱橫得意自奔放,體法豈計直與斜。客有臨書在屏側,豪強奪騎白鼻?。超塵絕跡莫見影,競愛此家忘彼家。賞新匿舊世情好,射殺逢蒙亦可嗟。”[6]詩中記載的草書區區盤旋,纏繞回環、美妙絕倫,這些詩句正是以懷素為代表的屏風書法的狂放不羈的最佳寫照與真實證據。
反觀宋代,則是另一番景象了。宋時學人注重內心的修養與追求質樸無華,士大夫往往重內涵而輕形式,這一時期的屏風樣式簡潔雋秀、裝飾簡雅。宋代書法尚意,以行書見長,書法風格追求文人書卷氣,屏風書法在宋代成為表現詩文內容的藝術形式,宣情達意的功能退居其次。例如,《古今詞話》中云:“潘逍遙狂逸不羈,往往有出塵之語,自制《憶余杭》詞三首,一時盛傳。東坡愛之,書于玉堂屏風。石曼卿使畫工繪之作圖。”蘇東坡由于喜愛潘閬詩詞,將詩詞寫于屏風之上,而非以表現書法為主旨。
米元章曾有題屏詩云:“目炫九光開,云蒸步起雷。不知天近遠,親見玉皇來。”[7]元湯垕《古今畫鑒》也記載:“米芾元章,天資高邁,書畫入神,宣和立書畫學,擢為博士,初見徽宗,進所畫《楚山清曉圖》,大稱旨,復命書《周官》篇于御屏,書畢,擲筆于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體,照耀皇宋千古’。徽宗潛立于屏風后,聞之不覺步出,縱觀稱賞。”[8]從米芾題屏我們可以看出關于宋代屏風書法的相關情況。
宋徽宗命米芾書《周官》篇。《周官》作為一篇倫理綱常的典籍,強調君王在處理朝政時應符合禮儀規范,而宋徽宗從屏風后聞之不覺步出,對米芾的書法大為稱贊,此時《周官》在宋徽宗眼里不僅是書寫的內容,而他真正感興趣的則是屏風中的書法,特別是書學博士米芾的墨跡。然而米芾書畢后大言:“一掃二王惡體,照耀皇宋千古。”有宋一代,“二王”帖學在廣大文人層面得以傳播,文人以“二王”書風作為學書楷模,蘇軾曾說:“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9]黃庭堅也贊曰:“右軍筆法如孟子道性善,莊周談自然,縱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拘之。”[10]這些宋代一流書家崇尚“二王”書風,由此可見學習“二王”書風在整個書壇的興盛,主張創新的米芾對當時師法“二王”泥古不化的風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提倡創新書法風格,創造出照耀皇宋千古的宋代書風。宋徽宗可能關注的是米芾書法,而米芾自身關注的則是由題寫屏風來表達自己的書學主張。
黃庭堅被貶戎州時,在屏風上題詩一首:“蝴蝶雙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群蟻爭收墜翼,策勛歸去南柯。”這屏風又被帶入京城變賣,當朝太師蔡京的門人看到立馬買去討好蔡京。蔡京一看詩的內容大怒,以為黃庭堅不服朝廷的處理,寫詩發泄,有怒氣,便下令再重貶,時流落宜州的黃庭堅已在困頓折磨中離開了人間,那道貶謫令自然也無效了。[11]
故宮博物院所藏《西園雅集圖》有描繪米芾題石屏的場景,然而詩人之間的唱和成為主角,而非書法藝術。這些例子無一不在說明,宋時期注重的是觀賞屏風的書寫內容。
總言之,重內容而輕形式的表現形式導致宋代的屏風書法呈現出尚意、簡雅的獨特風格,不過,從另一層面來看,宋人注重詩書畫于一體的屏風書畫使屏風書法多了一層文化底蘊,少了幾分狂躁。
三、宋屏雅韻對金的影響
自宋太祖趙匡胤建宋以來,女真與契丹憑借著強悍的武力在北方地區建立政權,與宋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
作為馬背上興起的國家,金在政治、經濟上是無法與宋相提并論的,然而,金的統治者深知,宋朝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對于金國建設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因此,在國內大行改革,結合自身民族特性與地域性,進行漢化,金與宋王朝進行頻繁的交往。

張擇端 清明上河圖(局部) 選自《宋畫全集:第1卷》
金王朝在重塑文化自尊的同時,漢民族優秀傳統全方位滲透到女真族當中。
在制度方面,金王朝的官制與宋王朝無異;生活習俗方面,金人對漢族服飾開始接受,喪葬習俗也有所改變等;在文化方面,章宗臨朝大力推行文治,尊孔讀經,廣建寺廟。宋人詩詞也廣受金朝文人的仰慕與追捧。
往來過程中,金文化與中原文化交融,文化和習俗差異日益減少,形成了“說一種話,寫一種字,據同一的文化,行同一倫理”[12]的局面。
在學習中原文化的同時,金代的書法藝術也隨之走向繁榮。金天德三年(1151年)置翰林學士院,承擔文字學習、書畫鑒賞的功能,金宮廷秘書監下設書畫局、筆硯局,書畫管理的官職制度隨之建立。
金章宗崇尚漢文化,善書法、知音律、工詩詞。《癸辛雜識》載:“章宗凡嗜好書札,悉效宣和,字畫尤為逼真。金國之典章文物惟明昌為盛。”[13]金章宗建立與書畫相關的“掌圖畫縷金匠”的圖畫署和繪制屏風等器物的裁造署,從而推動了金代美術的發展。金章宗還仿效宋徽宗的收藏印章“宣和七璽”,從而制作“明昌七璽”。其書法像極了宋徽宗的瘦金體。
金代一流書家也無一不對宋代尚意趣書風表示出激賞之意,如蔡松年父子取法蘇軾,趙秉文體取顏、蘇,王庭筠學米芾等。
宋王朝對金的影響,除經濟、政治、文化外,對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影響也頗多。其中與書畫藝術密切相關的便是高型家具在金王朝的普及。隨著高型家具在金國的普及,女真族席地而坐的生活習慣也隨之改變。
在高型家具中,以屏風為代表在金代中流傳甚廣。
屏風在金代的盛行,一方面來自戰爭的掠奪。金人北撤時,除擄去徽宗、欽宗二帝外,還有大量金、銀器物、工匠等,汴京城二百多年所積蓄的財物被洗劫一空,宋室南遷后,也無力與金抗衡,一味求和,每年向金進貢大量財物,這其中就包括屏風在內的家具。
另一方面,金朝對內積極改革,學習中原地區先進的手工業,屏風等高型家具由于易于制作,屏風便進入到尋常百姓家中。
書法藝術的繁榮,屏風器物的普及,由此在屏風上題寫書畫的風氣也在金王朝流行起來。
《金史》中記載多處皇宮與王宮貴族家中常常擺放屏風書法,金哀宗褒獎在戰爭中陣亡的將士,將陀滿胡土門子孫的名字題寫在御屏之上。元好問有詞云:“幾處銀屏珠箔。”蔡松年有詩云:“喜銀屏、小語私分,麝月春心一點。”
在大量金代墓室壁畫中也能看到陳列書畫屏風的情景,例如山東高唐金代虞寅墓里的屏風、山西長子縣小關村金墓東壁與北壁墓屏風。從壁畫中我們可以看出,金代的屏風樣式、形制與陳列方式與宋朝屏風別無二致。其書法風格也正是宋時期的尚意書風的特征。

山西長子小關村金墓屏風圖(局部) 長治市博物館藏
這些正是金受漢文化影響的真實寫照,屏風書法在金代的流行也正是金朝文人對漢文化的追慕,從而印證了宋代屏風書法繁榮的狀況。
小結
徐無聞先生曾說:“宋代書法的研究,不論深度還是廣度,在整個書法史研究中,都顯得薄弱。目前一般的書法論著,對蘇、黃、米、蔡講得較多,此外就注意得少,或者根本不管,這與宋代書法發展實際是不符合的。”[14]
在以往書法史研究中,研究者關注點往往在卷、軸、碑刻,對題壁書法、屏風書法這一類書法表現形式則關注較少,一方面因為其文獻材料太少,另外一方面沒有實物作為支撐。而屏風書法是隨著文學藝術的興盛,建筑、家具、社會生活的變遷而興起的,在今天它的實用功能已經大大減弱,在生活中已經很少看到這種家具。但是它作為一種文化產物曾經在古代輝煌過,且在文人士大夫的觀照下成為一種表現書法藝術的形式。正如前文所說,中國書法的發展過程是紛繁復雜和異彩紛呈的,強調屏風書法在當時的興盛,就是盡可能還原當時書法發展的真實面貌。
注釋:
[1]庾元威.論書[G]//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5:21.
[2]張春林.陸游全集:上[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627.
[3]褚人獲,輯撰.李夢生,校點.堅瓠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72.
[4]陸游.陸游集:第2冊[M].北京:中華書局,1976:752.
[5]周振甫.唐詩宋詞元曲全集[M].合肥:黃山書社,1999:5057.
[6]張毅,于廣杰.宋元論書詩全編[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7:16.
[7]何薳.春渚紀聞[M].北京:中華書局,1983:108.
[8]湯垕,著.馬采,注譯.畫鑒[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59:48.
[9]蘇軾.論書[G]//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書畫出版社.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314.
[10]黃庭堅.山谷論書[G]//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61.
[11]《美術大觀》編輯部編.中國美術教育學術論叢:造型藝術卷[M].沈陽:遼寧美術出版社,2016:468.
[12]傅斯年.現實政治[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12:169.
[13]周密,撰.王根林,點校.癸辛雜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1.
[14]徐無聞.關于宋代書法史的研究[G]//中國書法家協會.當代中國書法論文選:書史卷.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10: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