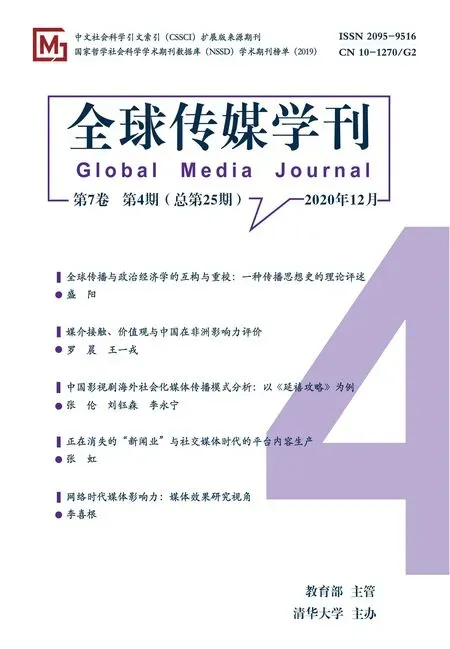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媒體效果研究視角
李喜根
導言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有關疫情進展以及重大社會事件和問題的信息通過網絡時代的各種渠道廣為傳播,其中包含相當數量的虛假信息,使得民眾真假難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信息泛濫導致民眾對于事態發展感到迷茫和焦慮,這一現象凸顯了主流媒體作為重大社會事件期間信息主導的必要性,以及主流媒體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的重要性。多年來,提高新聞輿論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一直是國內新聞傳播業界和各級宣傳部門共同致力的重要任務和工作目標,也是新聞傳播學界和業界經常研討的話題 (沈正賦,2016;丁柏銓,2018),但是這類討論多數停留于對相關問題重要性的認識,或是從新聞業務角度展開的對策分析,鮮有學者依據傳播效果理論和媒體效果研究成果來探索其原理和實現途徑。媒體信息的影響力是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的來源,如何提高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是新聞傳播學界和業界面臨的首要問題。媒體影響力機制不僅需要用傳播效果理論和媒體效果研究成果進行深入闡釋,而且需要通過理論指導下的實證研究去檢測和評估。網絡時代讓一個社會有大量可以自由發聲的信息傳播渠道,當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要求有資質、有權威的媒體成為社會信息主導,深入闡釋、恰當評估和有效提升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就成為新聞傳播學界和業界的一項緊迫任務。本文從媒體效果研究視角解析對媒體影響力有重要決定作用的社會、媒體與受眾因素,考察網絡時代作為媒體影響力本源的信息傳播要素、媒體影響力特性,并闡釋傳播效果理論和媒體效果研究成果對于深刻理解、有效提升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的重要作用與意義。
一、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社會基礎:媒體生態、信息主導與受眾依存
媒體影響力指的是大眾媒介通過信息傳播帶來的社會、文化與心理影響 (impact) (Bryant &Oliver,2009);媒體影響力體現為媒體發布的新聞使受眾有所觸動、感染,產生共鳴,并由此產生觀念、態度和行為的變化。西方新聞傳播學者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開始探索媒體影響力,至今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理論與實證研究文獻。西方學者把研究媒體信息對于受眾觀念、態度和行為的影響稱為“媒體效果” (media effects) 研究 (Neuman &Guggenheim,2011),并通過不斷驗證創建了一系列有關媒體效果的理論用以說明媒體信息對于受眾的影響力 (Bryant &Oliver,2009;Sparks,2016)。本文闡釋的媒體影響力即西方新聞傳播學者長期致力研究的“媒體效果”。區別在于,媒體影響力是有關媒體信息帶來的觀念、態度和行為變化的一般說法,而“媒體效果”是基于實證研究、有對第一手數據分析后獲得的證據支持的媒體信息所導致變化的具體呈現。
要理解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首先要認識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要素。本文討論的媒體是指在國內有發布新聞資質的主流媒體,主要是報紙、電視、廣播以及主流媒體延伸至網絡與移動媒體的信息發布渠道和平臺。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要素包括社會因素、媒體因素和受眾因素。
(1) 主導媒體方向的社會因素,包括媒體制度、媒體生存環境、社會意識形態以及其他社會規范,它們構成媒體社會生態。其中媒體制度決定了媒體的社會地位、媒體與公眾的關系以及媒體運作方向,這些因素又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媒體的公信力。媒體環境主要指媒體采訪、發表信息的空間與自由度以及信息發布的社會接納程度,是媒體生存的前提和媒體信息產生影響力的場域。網絡時代的媒體環境與傳統時代最大的不同是,主流媒體不再是僅有的新聞信息發布渠道,網絡和社交媒體的發展使得主流媒體在新聞信息傳播領域失去壟斷地位。主流媒體雖然在新聞資質方面仍有優勢,但是在由無數網絡和社交媒體組成的新聞叢林中依然要靠競爭生存。網絡時代的社會生態迫使媒體放下有政府背書的身份,成為和所有其他媒體共同發聲、爭取受眾關注并運用各種手段增強其影響力的社會機構。媒體所處的社會生態對于媒體影響力起著決定作用。
(2) 奠定信息主導地位的媒體因素,包括媒體資質、媒體公信力、媒體用于新聞采訪與報道的資源等因素。媒體資質是指由主管部門授予的媒體參與采訪報道新聞的資格、媒體聲譽、社會服務表現以及社會信任程度,是媒體報道重要社會問題、致力推動社會發展而形成的社會地位和服務社會綜合表現的集合。媒體資質是網絡時代媒體的最重要資源,是媒體發揮影響力的前提。信息技術的發展催生無數基于網絡和移動平臺的媒體,主流媒體因為其資質和公信力占有信息發布的主導地位。但是網絡時代主流媒體在傳播方式和傳播渠道特性方面與其他媒體趨同,在有些方面可能還落后于其他網絡與社交媒體。主流媒體要保持其主導地位,就要不斷擴展其媒體資質方面的優勢,依靠充分的新聞報道資源來聯系社會、吸引受眾。網絡時代的媒體資質、媒體公信力以及媒體獨有的新聞報道資源是媒體影響力的重要基礎。
(3) 與媒體互為依存的受眾因素,受眾作為整體,其社會觀念、媒介素養、媒體使用習慣、媒體依賴程度等決定媒體信息對受眾的影響程度。媒體素養,即受眾對于媒體性質、特點的了解,獲取、分析、評價和傳輸各種信息的能力 (Silverblatt,2001),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受眾對于媒體及其內容的選擇和使用方式。網絡時代受眾可以從眾多渠道中選擇信息渠道,逐步形成自己的媒體使用習慣。能夠最大程度滿足受眾對于信息需求的媒體,成為他們經常使用的媒體。媒體使用習慣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媒體信息對于受眾的影響力 (Althaus &Tewksbury,2000)。受眾因為個人生活、工作和社交目的需要依靠媒體獲取信息。個人對媒體的依賴程度越高,媒體信息對于個人來說就越重要,其影響力也就越大 (Ball-Rokeach,1998;Riffe et al.,2008)。此外,受眾的個性特征會影響人對信息內容的認知與理解,并進而影響對新聞報道所涉及問題的態度和行為。受眾對所選擇的特定媒體的接觸時間越多,該媒體對受眾的影響力相對就越大。
二、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本源:公共利益、傳播效能與權威信息
媒體影響力靠信息的生產和傳播來實現。媒體信息傳播要素包括反映公共利益的信息來源、高效信息傳播渠道、有社會擔當的權威內容。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由社會、媒體、受眾等因素決定,而媒體信息傳播要素則是媒體影響力的本源。網絡時代由于信息傳播環境、傳播手段和傳播效能都與傳統媒體時代截然不同,雖然媒體信息傳播要素并未改變,但是其內涵與傳統媒體時代卻有著顯著差別 (Bolter &Grusin,1999)。下面以媒體報道重大社會事件和問題的傳播實踐來考察網絡時代媒體信息傳播要素。
首先是反映公共利益的信息來源。網絡時代,媒體信息來源比傳統媒體時代有所擴展,主要來源依然是政府部門、社會團體、商業機構、專家學者以及其他人士。這些信息來源從不同方面向媒體提供信息,體現各自的社會角色,同時代表不同機構和群體的立場和利益 (Manning,2001)。網絡時代不僅有資質和公信力的機構與個人成為媒體的信息來源,各類網絡信息發布者也成為信息來源。網絡時代信息來源擴大和多樣化造成利益訴求多樣化。媒體在采訪不同信息來源時,除了依靠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提供權威信息外,需要對信息來源提供的信息進行篩選以提高媒體影響力。面對各類有不同利益訴求的信息來源,需要淡化信息來源所代表的機構和部門利益,使媒體發布的信息盡量符合社會公眾的信息需要和共同利益。例如在報道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媒體最大的影響力來自于那些與公眾共同利益相關機構所提供的信息,即有關疫情防控重大決策、疫情中社會民生保障的信息。從信息來源看,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來自于信息來源所提供信息的公共利益最大化。
其次是高效信息傳播渠道。網絡時代主流媒體發布新聞信息除了通過原有渠道,還可以利用網絡與社交媒體。與傳統媒體時代相比,網絡時代信息傳播渠道的最大差異在于傳播效能 (Wendel &Dellaert,2005)。由于網絡與移動媒體的快速發展,主流媒體受眾規模與網絡和移動媒體相比已經不再有明顯優勢。當信息傳播渠道延伸至網絡和移動媒體領域,網絡時代傳播渠道優勢主要表現在信息傳播速度、規模和效率 (Jeffres et al.,2004)。速度體現為信息的即時發布,規模體現為接受信息的受眾數量,效率體現為以受眾最樂于接受的方式將信息準確無誤地傳播至目標受眾。主流媒體在網絡和移動媒體領域已有一定程度的延伸,融合媒體和智能媒體的發展為主流媒體提升信息傳播速度、規模和效率提供了新的技術手段。網絡時代媒體應用新一代傳播技術手段的門檻越來越低,主流媒體和其他網絡媒體面對新的傳播技術經常處于同一起點。主流媒體需要更加主動地掌握和運用高效傳播手段以取得領先地位。在報道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主流媒體充分利用網絡和移動媒體平臺高效及時發布有關疫情發展和民生保障的重要信息,傳播渠道效能的提升使主流媒體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疫情期間民眾依賴的最可靠信息來源。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期間媒體信息傳播的實踐顯示,在保持信息權威準確的前提下,網絡時代主流媒體的影響力來自于由優勢技術手段支持的高效信息傳播渠道。
再次是有社會擔當的權威內容。傳播內容無論在傳統媒體還是網絡媒體時代都是媒體影響力的本源。媒體發布的不同主題、新聞價值各異、表現形式多樣的信息內容是媒體吸引受眾、發揮新聞的公告作用進而產生社會影響的主要產品。但是作為影響力要素,網絡時代主流媒體傳播內容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內容的權威性。傳統媒體時代,能發布信息的媒體有限,媒體刊載的信息,由于媒體的社會信息主導地位而自然顯示其權威性。網絡時代各種媒體并存。雖然主流媒體因為其新聞資質在信息發布方面有主動權,在信息內容方面有一定獨家優勢,但是面對網絡和移動媒體每天發布的海量信息,主流媒體要靠其發布信息所具有的受眾認可的權威特性在媒體叢林中獨樹一幟,才能發揮其影響力。媒體傳播內容的權威性主要體現在內容是否承載了時代的擔當,是否把握了社會在特定時期的重要社會脈絡,提供社會公眾最需要、最值得信賴的權威信息,使得媒體所傳播信息能在受眾中形成共鳴 (Perse &Lambe,2017)。例如面臨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民眾可以從不同渠道獲得有關疫情的信息。主流媒體應該當仁不讓地傳播最權威、最及時、與民眾利益息息相關的信息,使得媒體傳播的信息成為民眾不可或缺的生活依存 (Holland et al.,2012)。因此,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來自于作為社會信息主導媒體發布的承載時代擔當、表達公眾利益、具有不可替代權威性的信息。
三、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特性:影響力正負、即緩、隱現、遠近與強弱
媒體本身及其傳遞的信息具有一定影響力是媒體的生存基礎,是媒體產生經濟與社會效益的前提 (Bryant &Oliver,2009;Perse &Lambe,2017)。在國內現有媒體制度下,更是主流媒體完成其政治與社會使命的前提。媒體影響力可以從不同方面考察。有學者根據我國傳播學界對于媒體影響力的研究總結出了效果說、方式說和綜合說 (強月新、夏忠敏,2016)。“效果說”從媒體傳播效果來定義媒體的影響力,強調媒體影響力體現為媒體信息對受眾在認知、態度、行為等方面產生的顯著影響 (鄭保衛、李曉喻,2013);“方式說”從媒體如何影響受眾的角度來定義影響力,即信息傳播方式對于媒體影響力有決定作用(陸小華,2005);“綜合說”則涵蓋傳播過程和傳播效果,有學者認為,媒體影響力的本質特征是媒體作為信息傳播渠道對其受眾的社會認知、社會判斷、社會決策和社會行為打上特定的 “渠道烙印” (喻國明,2003)。但是上述定義以及相關討論只說明了媒體影響力的一般特征,并沒有深入闡釋媒體信息產生什么樣的效果才算有影響力,而媒體影響力又是通過何種方式實現的。有關媒體影響力的討論缺少基于實證研究的理論闡釋,其主要原因是,國內傳播學界對于媒體影響力的實證研究匱乏,因而無法進行基于實證研究發現的理論闡釋。雖然有學者對于媒體影響力的定義作了充分細致的解讀,卻很少有系統綜合的基于實證研究的理論論述。
媒體信息帶來的變化涉及認知、觀念、態度、行為等不同方面。人們對于事物的認知需要經過信息接觸、理解和價值評估等步驟,人的觀念、態度、行為的變化也要經歷對信息的解讀、評判和接納的過程。這種變化有時是從無到有,即從媒體信息中獲得后,經過思考與判斷逐步接受新的觀念;有時是強化或者改變已有觀念與行為;有些改變是內在的,例如情感、心理變化;有些改變是外在的,例如針對某件事物的態度以及采取的相應行動。媒體信息對個人、群體產生的影響,經過累積可能擴展為對社會的影響,例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通過媒體傳播給受眾,對受眾個人的影響匯集成為具有一定規模的公眾行為,進而對社會產生顯著影響。下文依據傳播效果理論和媒體效果研究成果來討論媒體影響力的特性。
(1) 媒體影響力可以是正面的或者負面的。媒體信息如果能產生影響力,其結果并不總與信息發布者的愿望相一致,有些信息的影響力是正面的,可能推動某項活動或者事業朝積極方向發展,例如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經過媒體的廣泛傳播,就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力,對于端正全社會對于住房商品屬性的認知,抑制炒房行為有明顯效果;有些信息的影響力是負面的,信息發布帶來的結果與信息發布者的愿望相反,例如2011年 “7·23”溫州動車追尾事故發生后,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在解釋事故處理方式時所作的評述“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經過媒體傳播后,放大了其作為危機處理責任人無所作為、缺少擔當的態度,帶來明顯的負面影響。
(2) 媒體影響力可以是即時的或者緩釋的。媒體信息的即時影響力來自于重大突發事件和出乎公眾意料的信息;與公眾有密切關系的信息發布后也會帶來即時影響,例如有關高考的新規定和國家放開二胎生育政策的信息發布可能立即引發廣泛的社會討論,產生即時影響,引發連鎖反應。然而,媒體信息產生的影響力多數是平緩釋放的,即媒體信息會使受眾對所報道的問題有一定程度的關注和認知,逐步改變人對某些事物的態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的行為,但是一般不會立刻引起公眾的強烈反應。這種平緩釋放的影響力在一定時期內緩慢積累效應,例如媒體關于轉基因食品的報道對人們有關轉基因食品安全看法的影響就是緩慢積累的,需要通過長期跟蹤研究才能具體明確地了解有關報道對公眾的影響力。
(3) 媒體影響力可以是隱形的或者顯見的。媒體信息給受眾帶來的觀念、態度和行為的變化有的是隱形的,不會立刻有所反應并通過傳播渠道明確表達。傳統媒體時代受眾意見表達渠道缺失,媒體發布信息后,除了媒體主動搜集受眾反應作為后續報道外,媒體影響力很少直接顯現。網絡時代民眾表達渠道多樣,但是多數人可能依然選擇不作公開表達。這類由媒體信息給受眾帶來的內在反應和變化需要通過系統調查來了解。媒體信息的影響力也可以是外在可見的,人們明確表現出接觸特定信息后在觀念、態度或行為上的變化,例如網絡平臺發布的新聞后面的跟帖與評論、網絡論壇中就各類新聞開展的討論、社交媒體傳播的因各種信息帶來的個人與社會行為變化。這類公開表達的意見與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媒體信息顯見的影響力。
(4) 媒體影響力有短期或者長期效應。媒體的影響力一般是短期的,在新聞信息發布近期,受眾的反應會相對強烈 (Yanovitzky,2002)。例如有關近期空氣污染的報道,會在短期內引發社會公眾的思慮、風險感知和應對行為,短期的追蹤調查會發現媒體信息的顯著效果。媒體對重要問題的報道是有周期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媒體信息帶來的影響力會慢慢淡化。但是媒體對有些問題的長期連續報道,會使這些問題在受眾頭腦中逐步積累,逐漸形成較為深刻的認識,有關問題的重要性和相應觀念會在頭腦中長期留存。例如媒體有關全球變暖報道的影響力,就是在長期報道中逐步積累形成的。遇有氣候變化帶來后果的重大事件,相關報道會產生短期即時反應。多年有關氣候變化和發展趨勢的持續報道,則對受眾有關全球變暖的認知與態度帶來持續時間較長的影響 (Li,2015)。
(5) 媒體影響力可能體現為觀念、態度或者行為的改變,也可能只是對原有觀念態度的強化。媒體影響力帶來的改變是指因為受眾接受媒體信息,受到感染或說服,原來持有的觀念或態度發生了變化。在商品廣告領域,商品廣告包含的說服信息使消費者在觀念或態度上有所改變的情況經常發生。有關公眾利益的重大問題的報道,例如2020年初全球蔓延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期間是否應該戴口罩的問題,媒體基于嚴峻現實的報道,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西方社會民眾對于疫情期間戴口罩的看法。有關媒體效果研究的成果顯示,要改變人們已經持有的觀念很難,多數情況下媒體信息的影響力體現為對已有觀念的強化,即在原來的基礎上更加確信已有觀念。這種觀念的強化是通過受眾自覺地、有選擇地接觸與自己原有觀念相似的信息而實現的 (Garrett,2009)。
媒體影響力特征有時并不那么清晰可辨,而是經常表現出混合特征,例如媒體信息同時具有正面與負面影響力。上述媒體影響力特征在網絡時代還會受到媒體信息傳播渠道、方式以及受眾接受媒體信息方式與媒體使用習慣的調節。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除了上述一般特征外,還顯現出具有網絡信息傳播的新趨勢。首先,傳統媒體時代媒體影響力偏于隱形影響,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則更多表現為顯性影響。網絡時代受眾表達意見和態度、展示行為的渠道多樣,媒體信息發布后受眾有較多機會通過網絡和社交媒體發表意見,對媒體信息的反應通過網絡傳播渠道顯現,形成有跡可循的媒體影響力反應。其次,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更多表現為即時影響,即信息一經發布,受眾的反應立刻顯現。主要是因為網絡媒體的傳播效率,無論是媒體信息發布還是受眾信息接受都不再有時間延遲。網絡也為意見表達提供了充分條件。一條攪動社會脈絡的信息,經由網絡傳播,信息受眾動輒數千萬,經常是信息發布還在進行,網上評議就已經展開,形成有相當規模的即時受眾回應。再次是媒體影響力強化原有觀念態度的效應倍增。網絡本來是一個半匿名場域,網絡成員對媒體發布的信息可以相對自由地表達意見。但是經過多年孕育,網絡逐漸成為表達同質意見的場所,難以容納不同意見。有些信息發布后,意見表達呈現一呼百應狀態。同質意見的表達在很大程度上強化某一群體原有觀念。網絡時代媒體信息更容易引發相同多數意見的表達,媒體影響力更多體現為網絡場域同質意見的強化 (Shen et al.,2009)。
四、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研究脈絡:對媒體傳播效果的認知演進
傳播學者對媒體影響力的認識與探索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傳統媒體時代,傳播學者對媒體影響力的最初認知是媒體具有強大影響力。這一認知被推翻后,相當一段時間里,傳播學者認為,媒體信息只會對人的某些想法、態度和行為產生有限影響或者強化原有觀念。但是隨著信息傳播環境、傳播內容以及傳播手段的變化,尤其是在網絡時代,有了比傳統媒體時代更具技術優勢的信息傳播渠道,有學者質疑媒體有限影響力的說法。隨著對媒體影響力研究的不斷深入,學者對媒體影響力的理解也不斷深化。傳播效果理論和媒體效果研究成果給我們提供了深入解讀媒體影響力的系統知識。基于實證研究的傳播效果理論從不同方面對媒體影響力作出新的說明和預測。
有關媒體信息對人的觀念態度的影響作用,尤其是網絡時代媒體信息的效果研究,近年來取得新進展。選擇性接觸理論以及相關研究告訴我們,由于人們傾向于接觸與自己的觀念和態度一致的信息,媒體接觸難以改變人們已有的觀念,只能導致原有觀念的強化(Zillmann &Bryant,1985)。不過傳播學者近期的研究對于選擇性接觸理論又有新的闡釋。在網絡和社交媒體條件下,由于信息數量巨大,紛繁復雜,選擇性接觸變得相對難以實現。人們在信息接觸過程中會有意或無意接觸各類與自己原有觀念不一致的信息,因此與已有觀念不一致的信息可能帶來或多或少的影響 (Li &Liu,2012)。近年發展起來的網絡信息平臺基于大數據分析的信息推送,給選擇性接觸信息提供了新的途徑。在國內,由頭條新聞之類信息平臺推送的新聞使得媒體使用者能夠選擇性接受自己感興趣的信息,實現了一定程度的選擇性接觸。但是這類信息平臺推送的多數是軟新聞,較少涉及政治觀念和重要社會問題的時事新聞,還不是原本意義上與政治觀念有關新聞的選擇性接觸,不涉及對于重要政治與社會問題觀念與態度的變化。而國外社交媒體依靠大數據算法推送,在選擇性接觸方面有顯著推進。社交媒體可以基于由數據分析獲得的讀者政治觀念和態度的信息,只推送與讀者觀念和態度一致的信息。這類信息推送使得選擇性接觸的原本含義重新得到實現,即人們只接觸與原有觀念和態度一致的信息,進而強化人們已有觀念與態度。例如超過5000萬Facebook用戶信息數據被一家名為“劍橋分析” (Cambridge Analytica) 的公司利用,用于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針對目標受眾推送廣告,從而影響大選結果。基于大數據算法推送、以技術手段推動媒體使用者的選擇性接觸,能夠達到何種傳播效果,為媒體效果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網絡時代媒體信息對人的觀念和態度在不同場域下的影響力以及相關的選擇性接觸理論需要通過深入的實證研究獲得新的理解與更新。
有關媒體影響力的理論在長期的有關媒體效果的研究中,不斷獲得檢測從而得到證實并獲得充實與豐富,給我們認識與探索媒體影響力提供更為深入的分析與評估手段。例如議程設置理論闡釋媒體如何通過不斷重復突出的報道,在受眾頭腦中構建對于重要問題的認知。議程設置理論可以用來檢測媒體影響力,考察網絡時代主流媒體對有關問題的長期突出報道是否在受眾頭腦中形成相關重要性的認識。例如,國內媒體關于“中國夢”的報道已經持續多年,媒體有關“中國夢”的報道是否有成效可以用議程設置理論指導下的實證研究來檢測,以考察媒體信息對受眾在有關問題重要性認識方面的影響力。議程設置理論在過去幾十年有關媒體效果的研究中發展出了新的分支理論,其中之一是二級議程設置理論。該理論提出,媒體對事物的突出報道不僅使受眾對當前的重要議題有顯著認知,還會使受眾對于所認知事物的相關特性 (attributes) 有一定了解。二級議程設置理論可以用來進一步檢測媒體有關“中國夢”報道的效果,即媒體有關“中國夢”的報道是否使受眾不僅了解“中國夢”這一重要理念,而且也了解其相關特性與具體內涵。如果媒體使用者對 “中國夢”的內涵與特性有所了解,就說明媒體報道在二級議程設置上也有明顯作用。如果有關媒體報道影響受眾對“中國夢”內涵與特性了解的假設沒有得到證實,則說明媒體報道影響受眾對重要議題內涵與特性的認知比起對重要議題本身的認知更為困難,有關“中國夢”報道的影響力還需要通過長期深入的報道才能逐步實現。
五、國內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研究:對策分析與指標構建
國內新聞傳播學界與業界近年來對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研究常有涉及,主要有兩類研究成果,一類是發表于新聞業務期刊的網絡時代新聞媒體業務討論和提高媒體影響力對策分析,另一類是發表于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研究類論文。這兩類論文各有偏重,總體而言,對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都還處于探討層面,對于深刻理解、系統闡釋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尚缺少理論與知識性貢獻。
從發表于新聞業務期刊的論文看,有關媒體影響力的探索主要集中于解釋媒體影響力內涵、探討如何提高媒體影響力的手段和途徑。探討的主題包括:媒體影響力內涵、價值與提升(藍燕玲,2013);媒體影響力構建與實踐路徑(曲升剛,2018);新媒體環境下如何重塑主流媒體影響力 (張廣星,2018);融合背景下如何提高主流媒體影響力(陸華,2019)。這類論文的主旨是業務探討,通過對媒體業務,包括網絡時代主流媒體面臨的傳播重要信息、引導社會輿論等業務實踐的分析,提出提升媒體影響力的建議與對策,基本停留于如何通過新聞業務提升媒體影響力的分析和探討,缺少基于實地調查和實證研究得出的有關媒體影響力動因的研究發現。
發表于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有關媒體影響力的論文較少。其中強月新和夏忠敏(2016)在對我國主流媒體影響力的調研與分析方面作了有益嘗試。該項研究在構建媒體影響力測量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對1000多名媒體使用者作了調查,運用相對客觀的媒體影響力測量指標體系對國內媒體影響力作了一個基本評估,是國內有關媒體影響力研究的探索性工作。該項研究的缺陷在于只對媒體影響力現狀做了基本描述,并未深入探索媒體影響力機制,例如哪些因素對于媒體影響力有重要影響作用。該研究本身也缺乏理論指導,研究發現對于理解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機制尚無重要理論貢獻。馮銳和李聞(2017)運用文獻分析、灰色統計、層次分析等方法構建了社交媒體影響力評價指標體系,為社交媒體影響力提供了比較客觀的測量手段。研究者對40位社交媒體領域的專家作了調查,匯總專家意見,最后形成有一定表面效度 (face validity) 和內容效度 (content validity) 的可用于社交媒體影響力檢測的評價指標體系。上述兩項研究在媒體影響力研究方面都做了有益的基礎性工作,它們構建的測量指標體系都還有待于在更多研究中使用以確認其測量效度 (measurement validity)。
媒體影響力主要通過傳播效果顯現。國內學界和業界對于傳播效果研究也較為關注。發表于新聞業務期刊的有關傳播效果的論文偏重于討論如何提升與實現傳播效果,而不是具體研究媒體信息的傳播效果。這類論文探討的主要問題包括:主流媒體傳播效果的提升路徑與評估體系(胡正榮、李荃,2019);傳統媒體在新媒體平臺的傳播效果(楊毅,2017);新媒體環境下傳媒業視聽傳播效果(馬宇航,2019);全媒體視野下新型主流媒體傳播效果評價(朱春陽,2019);新媒體環境下各類媒體信息傳播效果評價(鄧君洋、鄭敏,2011;閆坤、李寧,2011;齊志,2019;沈悅,2019)。其中胡正榮和李荃(2019)對于主流媒體傳播效果提升路徑與評估體系的研究主要從行業規范標準考慮效果評估,未從理論層面深入探索如何實施智慧全媒體傳播效果研究。朱春陽(2019)對于新型主流媒體傳播效果評價狀況進行了反思,提出了全媒體視野下新型主流媒體傳播效果評價的創新路徑,對于優化網絡時代主流媒體傳播效果評價體系,提高評價體系的效度有一定啟發意義。其研究的局限在于對主流媒體傳播效果評價缺乏明確的理論主導,停留于評價體系的構建。其他發表于各類新聞業務期刊的論文多數對于什么是媒體傳播效果以及如何檢測傳播效果不甚了了,基本都是從新聞業務出發,套用傳播效果評價或研究的說法,對于媒體如何在網絡時代提升傳播效果提出建議和對策,少有依據第一手觀察獲得的研究結論。
發表于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媒體傳播效果相關論文中,采用規范研究方法和適用理論的研究也并不多見。趙彤(2018)有關媒體融合傳播效果評估路徑、模型與驗證的研究建立了傳統媒體融合傳播效果評價指標體系和理論模型,并運用大數據手段采集報紙和電視媒體數據對評價模型進行驗證,得出不同媒體傳播效果的結論。該研究的意義在于構建了融合傳播效果評價模型,比較不同媒體的傳播效果優勢,但是理論依據不足,并未闡釋研究結果的理論意義,缺乏理論與知識貢獻。王天嬌(2020)從媒體使用和媒體效果考察網絡信息渠道異質性,對“新媒體使用”概念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從媒體使用和媒體效果兩方面對新媒體和傳統媒體的傳播效果開展了辨析。該項研究運用二手數據檢測“網絡新媒體”作為一個集合概念的內在一致性,發現同屬新媒體的門戶網站和以微信為代表的社交媒體的媒體效果差異,在厘清“新媒體使用”概念和辨析基于新媒體使用的媒體效果方面都有一定貢獻。
各類于新聞傳播期刊發表的關于媒體信息傳播效果的論文數量并不少,例如重大突發事件信息的傳播、謠言傳播以及冠以各類傳播學理論的傳播效果分析文章。但是這類論文多數都是基于對某類現象的分析,很少有通過采集第一手數據對具體傳播現象和傳播效果的考察。這類文章不少都帶有“議程設置”“沉默的螺旋”等理論名稱,但是所涉及的理論一般只起到標簽作用,很少有在相應理論指導下,依據對現象和問題的系統觀察,通過對采集的第一手數據的分析致力于理論檢測和知識貢獻的研究。就像祝建華和漢考克兩位學者在討論智能時代傳播學受眾與效果研究時提到的,中國學者在精確化層面已經取得很大進步,但在理論化層面仍顯不足。中國學者的文章大部分都是描述性的,在概念和解釋層面上的理論水平還需提升(李曉靜、付思琪,2020)。本文對于國內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和傳播效果研究文獻的梳理證實了兩位學者的看法。國內新聞業務類期刊和新聞傳播學術期刊都不乏對媒體影響力和傳播效果的分析和探討類文章,但是考察和探索媒體影響力和傳播效果的研究很少有理論導引和第一手數據,對于關乎媒體影響力的、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鮮有回應。有關媒體影響力和傳播效果的研究側重于對策分析和評價指標體系構建,而忽略對于媒體傳播現象的實際考察。偶爾有通過數據采集來研究媒體影響力和傳播效果的項目,一般也停留于對傳播現象的描述,缺少對媒體影響力的決定因素以及媒體影響力形成機制的探索,更缺乏理論思考和在對傳播現象的研究中運用理論并通過研究發現對相關理論的補充和創新。
六、理解與把握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理論與實證探索
網絡時代的信息傳播與傳統媒體時代的不同之處在于:首先是信息發布權不再被主流媒體壟斷,人人都可以通過網絡與社交媒體發布信息;其次是信息發布渠道多樣,各類網絡與社交媒體與主流媒體分流受眾,主流媒體的主導地位受到挑戰;再次是信息內容多元,信息導向與基調各異,社會各方利用網絡平臺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主流媒體信息的影響力受到相當程度的銷蝕。受眾方面,接收信息由傳統媒體時代的被動接收變為網絡時代運用各種手段、從不同信息渠道主動選擇。這種主動選擇可以過濾掉許多有重大社會意義問題的信息,一方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強化接收某些方面的信息,另一方面又會進一步削弱主流媒體信息的接觸機會。此外,媒體自身的發展、信息傳播渠道和傳播內容的變化也會不斷調節媒體信息對于受眾的影響力,會給有關媒體影響力的問題帶來全然不同于傳統媒體時代的答案。
因此在網絡時代,關于媒體影響力的很多問題有待回答。例如,網絡時代信息傳播特性的變化給媒體影響力帶來什么變化?主流媒體在多大程度上是受眾對重要社會問題認知的權威信息來源?是主流媒體引導網民的討論議程?還是網絡討論影響主流媒體的報道重點?網絡與社交媒體和主流媒體的議程怎樣相互影響?當有重大社會事件時,人們是相信主流媒體報道,還是自己去設法尋求信息并做出判斷?當網絡信息和主流媒體信息出現沖突時,公眾對不同信息源提供信息的取舍由哪些因素決定?這些有關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的問題沒有顯而易見的正確答案。要回答這些問題,不能依靠拍腦袋想出來的測量手段,不能只靠思辨和討論得出結論,不能依據對于個別現象或者不同點面的觀察獲得的印象得出“引起極大反響”之類的粗略說法。而需要通過對受眾的媒體使用、信息接觸、媒體依賴以及相關的觀念、態度和行為等方面情況采集第一手資料的實證研究來逐步回答。不運用科學方法進行細致考察與系統分析,就無法回答這些需要從實證研究中尋覓答案的問題。
傳播效果理論和媒體效果研究成果對于如何提高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例如在有關輿論引導的問題上,宣傳部門一般強調要突出新聞宣傳的輿論導向,力圖以新聞導向引領社會輿論,期待輿論導向指導下的媒體報道形成一定的主流基調,進而對社會公眾產生預期的影響。而媒體效果研究結果顯示,人從媒體獲得信息有認知和解讀過程,這種認知受到媒體使用習慣、信息接觸頻度、對媒體內容的感知和理解以及受眾原有觀念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對重要問題的認知還不等于媒體信息對人的觀念、態度和行為產生了影響。帶有輿論引導功能的信息,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受眾接受,受眾對于信息的解讀和理解會帶來何種結果,并不以輿論導向設置者的意志為轉移,而是受到社會、媒體與受眾等因素的影響。不考慮受眾媒體接觸過程和認知過程,忽略社會、媒體與受眾因素之間的互動及其對人的觀念、態度和行為的影響,就難以產生方向明確的輿論引導效果。
有關媒體報道的框架理論分析,從另一角度幫助我們理解受眾接觸媒體信息并形成對事物認知的過程。新聞框架指的是記者在采編新聞時,選取所報道現實的某些方面,并在新聞內容中突出和強調這些方面,而忽略或削弱事物的其他方面 (Entman,1993)。由此產生的新聞報道對于受眾感知和理解相關問題產生不同影響。由于媒體的報道重點不同,記者的認知能力差異,對同一新聞事件的報道往往有不同視角。例如關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新聞報道,可以從科學角度報道新冠病毒感染的發病機制,也可以從經濟角度報道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發展和民眾生活的影響,還可以從全球視角報道不同社會制度和文化對于疫情管控的影響。因此,新聞信息的消息來源和新聞素材相同,由于報道視角不同,其所傳遞的信息內涵會有明顯差異,從而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受眾對有關問題的認知。新聞框架經常成為主流媒體與其他網絡媒體爭奪和影響受眾的手段。媒體怎樣利用新聞框架傳達事實與理念并影響受眾的認知和態度成為網絡時代需要深入探索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因此推行輿論導向不能忽略傳播效果理論和媒體效果研究揭示的信息傳播規律,把信息傳播過程簡單化。輿論導向是一種期待,媒體報道在與社會意見的互動中逐漸形成某種導向。傳播效果理論和媒體效果研究的發現表明,新聞報道不論是否有明確導向,其對公眾產生影響的結果是多元的。媒體對有關問題的報道是否會帶來所期待的結果受到社會環境、媒體屬性、報道方式以及受眾特性等諸多因素的調節。把握輿論導向首先需要了解信息是怎樣經過媒體的處理而傳播至受眾的,網絡時代受眾是如何有選擇地接收并處理信息,形成自己對有關問題的認知和評估,并進一步影響其觀念、態度和行為。只有通過基于實證研究的細致考察與系統分析才可能了解輿論導向對社會公眾認識與理解相關問題會有多大效用,逐步發現信息在特定社會環境下的傳播規律,進而提高信息傳播效果。
七、結語
有關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的實證研究不是一次能完成的,而是一項長期、系統的科學探索。傳播效果理論與媒體效果研究給我們提供了解讀媒體影響力的系統知識,從不同方面對媒體影響力作出說明和預測。此外,心理學、社會學和政治學領域的一些理論也從不同方面說明媒體信息對人的觀念、態度和行為以及對社會輿論與其他社會活動的影響。理論的作用是導引,探索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和傳播效果需要著眼于對傳播現象的細致考察,要通過實證研究探索媒體傳播信息過程中重要事物間的聯系,以揭示媒體傳播規律,進而對主流媒體提高影響力提供有理論依據的導引。國外媒體效果研究成果被用來揭示受眾的信息認知和信息處理過程,幫助媒體實現傳播效果,有關媒體效果理論和實證研究發現還被用來提高各類競選活動成效和廣告發布效益,有些和公眾行為相關的研究發現還成為制定公共政策的依據,發揮了推動改善媒體內容的社會效益。國內有關媒體影響力的研究還剛剛起步。研究者還只習慣于通過對個別事物的觀察,或者相關傳播現象的討論思辨來獲得提高媒體影響力的對策。即使有學者開展媒體影響力的實證研究,多數也偏重對媒體信息傳播現象的描述,有關社會、媒體、受眾因素如何對媒體影響力起主要作用的關系性研究還很少涉及,在傳播效果理論指導下旨在測試與發展傳播學理論的實證研究更是罕見。因此用社會科學方法來考察與檢測媒體影響力,探索媒體影響力的主要決定因素,進而尋求改善媒體影響力的途徑,是新聞傳播學界面臨的艱巨任務。有關網絡時代媒體影響力的研究,需要采用社會科學方法,包括定量與定性實證研究方法,系統探索信息傳播和媒體效果機制。不僅要考察媒體信息發布和傳播過程、受眾媒體使用與信息處理方式,還要探索社會環境對媒體新聞報道活動的影響,考察不同時期的重大政治、社會活動與新聞報道的互動,探究受眾的心理認知與反應對輿論形成的影響等。這些有關媒體影響力的重要課題已經遠遠超出現有大眾傳播理論和傳播學研究的范圍,涉及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甚至計算機科學,需要不同學科的學者開展協同研究,以揭示國內目前網絡與社交媒體環境下新聞輿論、媒體影響力的機制及其帶動的社會變化與發展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