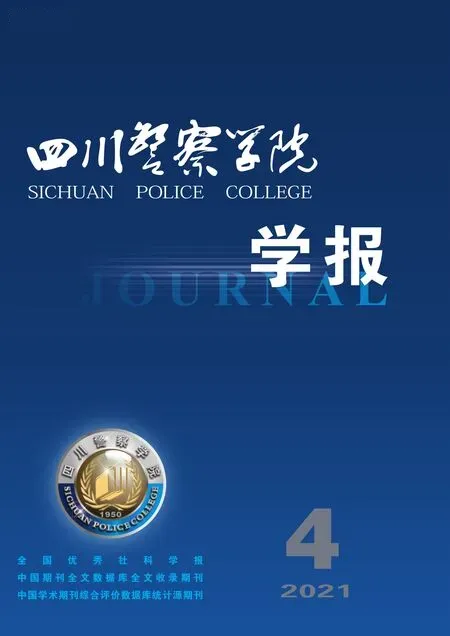我國秦代邊疆地區人口跨境流動的歷史考察
劉建昌,劉景云,俞保華
(1.廣西警察學院 廣西南寧 530029;2.廣西民族大學 廣西南寧 530029)
秦代,從史學角度,是指公元前221 年秦朝建立,至公元前202 年2 月,劉邦建立漢朝前的這段時期。秦代是極具典型性的歷史朝代,它統一中國,使中國成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建立了第一個封建制度國家,使中國歷史由奴隸制社會轉入封建社會。它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各方面都有其開創性、時代性、獨特性、全面性等特征,選擇秦代考察我國邊疆地區人口跨境流動的歷史,具有典型性、代表性。本文的人口跨境流動是指人員跨越國境或從內地到邊疆、從邊疆到內地的遷移活動。
人口的跨境流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現象,也是統治者治理邊疆的一種策略。秦代統治者重視通過人口管理維護邊疆的穩定。秦代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國家,研究其人口跨境流動的歷史對我們學習借鑒歷史經驗,推動現代邊疆治理有現實意義。目前,研究秦代人口跨境流動的成果不多,在中國知網上尚未找到一篇相關論文,只在宋昌斌所著《中國戶籍制度史》中有涉及人口跨境流動的內容,主要是介紹秦代人口遷徙流動的歷史情況,對我們分析秦代的人口跨境流動有參考作用,但其對人口跨境流動的原因、特征、影響與作用沒有作系統深入分析。本文在歸納分析秦代人口跨境流動的類型的基礎上,剖析了秦代人口跨境流動的特征、影響因素及積極意義,進一步拓展了秦代人口跨境流動研究范圍,進一步豐富了秦代人口管理的研究內容。
一、我國秦代邊疆地區人口跨境流動的類型
秦代不允許人口自由流動。秦代實行“禁民二業”的基本國策,即社會各業勞動者如士、農、工、商,只能各干一行,恒作一業,不能改業,不能兼業,如:官吏不允許經營其他行業,不能“與下民爭利”;商人不允許為宦做官、經營土地;農民不允許經商打獵、外騖他業。實行“禁民二業”,目的是促民歸農。由此,使用各種手段“使民無得擅遷”,嚴格限制人口自由遷徙、流動。一是不允許離開秦國本土,如《秦簡·法律答問》記載:“臣邦人不安其主長而欲去夏者,勿許。”[1]226二是協助他人遷出秦國的,實施處罰:“有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為鬼薪,公士以下刑為城旦。”[1]130
但是,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全國人口的控制,維護封建國家的長治久安,秦王朝政府實行大規模的移民政策。秦代的移民主要分兩種情況,一是遷富豪、強族于關中,二是徙平民、罪吏與邊疆地區[2]258。秦始皇在統一中國后的十余年內,前后進行了八次大規模的移民。因此秦代邊疆地區的人口跨境流動是比較頻繁的。秦代的人口跨境流動主要有兩大類型:一是官方主導的人口跨境流動,即從遷徙流動的動議到具體組織實施都是由官方主導;二是民間的人口跨境流動,即不完全由官方主導或官方管控不了的遷徙流動。
(一)由官方主導的人口跨境流動
1.由內地流向到邊疆地區。即由官方主導將內地的人口遷徙到邊疆地區,包括三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將犯罪的人口強制流動到邊疆地區。也就是適用流刑,將犯罪的人流放到邊疆地區服刑。流刑,也稱“流放刑”,就是將犯罪的人(包括其家屬)流放到邊疆地區從事苦役的一種刑罰。流刑作為一種刑事處罰,早在奴隸社會的商代就已經出現。商代就有將犯罪的人流放到邊遠地區的歷史。如伊尹放太甲事件,據《史記·殷本紀》記載:“帝甲即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太甲于桐宮”。西周時期,將犯罪的人口遷徙到“海外”或“千里之外”或“不同國”,《周禮·地官·調人》載:“凡和難,父之仇,辟諸海外;兄弟之仇,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仇,不同國……”,即凡殺害父親的仇人,須徙于海外;凡傷害兄弟的仇人,須徒于千里之外;凡傷害從兄弟的仇人,不得同居一國之中,毫無疑問,將之遷徙到別國。《禮記·王制》中也載有:不聽命令、不服從管教的人,先由鄉的長官向司徒匯報、及時誡諭,如果不聽勸告,則由左鄉遷徙到右鄉,或由右鄉遷徙到左鄉,以示懲罰,如果再不聽勸告,則由“國”中遷徙到郊區,由郊區遷徙到野外,直至“屏之遠方”①。實際上,這是后來各朝代的流刑的起端,而且是開了將內地人口遷徙到邊疆地區的先例,因為西周時所謂的“野”“千里之外”“遠方”“海外”等在當時來說,就是邊疆地區了。秦代承襲商周以來的流放制度,將犯罪的人流放到邊疆地區,以示懲罰。
流放刑是秦代八大類刑罰之一②。早在商鞅變法時期,秦就推行徙民政策,曾經把那些議論新法的罪人即“亂化之民”,“盡遷之于邊城”,如,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司馬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③。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8 年),長信候毐叛亂,叛亂平定后,“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余家,家房陵。”[3]227公元前222 年,秦滅趙,將趙王遷于漢中防陵;秦破楚后,遷徙嚴王之族于嚴道。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繼續沿用流放刑。
秦代的流放刑有遷刑與謫刑兩種情況:“遷刑”對官吏與平民百姓均可適用;“謫刑”僅對犯罪的官吏適用,適用“遷刑與謫刑”時,家屬必須隨遷[4]43。秦代廣泛適用流放刑,如,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第,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戌。”④三十七年(前210年),“又徒天下有罪吏民置海南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⑤
第二種情況,是將富豪、叛亂分子以及六國舊貴族遷往邊疆地區。豪強因為具有較強的實力,容易形成對中央的威脅,并破壞地方治安穩定,所以是秦統治者的打擊對象。使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將一部分富豪、六國舊貴族強制調離本土,放到邊疆地區,如:公元前238年,平定長信候毐叛亂后,“及奪爵遷蜀四千余家,家房陵。”[3]227秦滅趙(公元前222年)后,將趙王遷于漢中防陵;秦破楚后,遷徙嚴王之族于嚴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將全國12萬戶富豪遷至咸陽;公元前212年,又“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云陽。”[3]256還有將這些人遷徙到臨邛、瑯琊、野王、上谷、南陽、余杭、臨洮等地。
第三種情況,是有組織將內地人口集體遷徙到邊疆地區。隨著疆域的不斷擴大,為加強邊疆防衛與開發,秦始皇實施大規模移民實邊政策。公元前219 年,“徙黔首三萬戶瑯琊臺下,復十二歲”⑥,開秦代徙民實邊之端。公元前214年,派大將蒙恬率領30萬大軍北擊匈奴,收復河套南北的廣大地區之后,“徙謫實之”。公元前211年,又遷3萬戶到北河、榆中墾殖,公元前210年,徙大越民置余杭、烏程等地,以充實邊防。在南部和東南部,即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及兩廣一帶,秦始皇征服“百越”后,先后設立了會稽郡、閩中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遷徙了50萬人戌守五嶺,與越族雜居[4]112。
2.從邊疆地區流向內地。即強制性將邊疆地區的人口遷徙到內地。將邊疆地區人口遷徙到內地的做法,早在西周時期就已經出現。西周時將被征服的異族人口遷徙于“野”中,以便于控制、役使。這里的“野”是指與“國”相對應的地方即王畿附近。西周時將周天子直接統治的王畿,稱為“國”,王畿四周則稱為“野”,西周時將一些人口從邊疆外遷移到“王都”附近的做法,實際上,這是后來各朝代的流刑的起端,而且是開了將邊疆地區人口遷徙到內地的先例。秦代也效仿西周的做法,為保證中央王朝周圍有足夠的力量控制關外,同時也以此監控被遷入關內的不軌人口。秦代時,實行“徒民實都”,即將關外之民遷徙到關內和首都[5]328。秦始皇為了防止六國貴族組織反抗,“徙天下豪富于咸陽十二萬戶”,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公元前212年,又“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云陽”[3]256。這些人離開故土,移居他鄉,處于一個陌生的環境中,其實力自然被削弱,這樣,就地集中控制,有利于國家安定和社會穩定。
(二)民間的人口跨境流動
雖然秦代嚴禁擅自遷徙流動,但是仍存在民間的人口遷徙流動。這體現在當時的人口遷徙流動政策和制度的設計上。秦代的人口遷徙流動的政策上設計有正常的遷徙、流動程序。首先,遷徙者提出遷徙流動申請,由通過鄉、亭薔夫報縣司決定,縣司如同意遷徙,則發給“符傳”。其次,遷徙申請者憑“符傳”流動出行、居留,過界經關,要接受盤查,若無官府的符傳,不準隨意流動。否則要受處罰⑦。秦代對于邊境地區的人員的出入境設計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其一,在邊境,設有關,并設“關市”官職。“關市”亦即西周時的“司關”和“司市”“合為一官”⑧。還設有“亭”其遍設于驛道、關津。《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6]742“亭”起初只在邊境上設置,負責監視敵情,屬于帶有軍事性質的機構。其二,實行憑證出入境制度,要求出入境商人須持“符傳”,否則,處以刑罰。這些人口遷徙流動政策與制度的設計,不僅表明秦代政府允許民間正常的遷徙流動,而且說明當時的社會現實中存在民間的人口正常的遷徙流動包括人口跨境流動現象。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如《秦律》中的《法律問答》中就有關于來自他國的商人的記載,把各國來秦國貿易的商人稱為“客”“邦客”。這些“客”和“邦客”都是一些來自他國的商人。
在秦代,民間的人口遷徙流動,除了普通老百姓的正常遷徙流動外,主要是兩類人的遷徙流動:
一是商人的遷徙流動。秦代雖然重農抑商,但是仍然允許商業的存在。《史記·秦始皇本紀》就記載有戰國時期秦國的商業活動。如:秦獻公七年(公元前387 年),有“初行為市”;秦孝公時,商鞅“立三丈木于國都市南門”。秦始皇統一中國,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以及道路交通設施等,有利于各地區交流,為商業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條件,因此秦代不僅允許商業的存在,而且商業有更大的發展,當時遍布各郡的城市既是該地的政治中心,也是該地的商業中心,如:蜀郡成都,“市張列肆,與咸陽同制”⑨,市區內有繁華的商業區;自戰國以來就較為發達的城市,如薊(北京市)、邯鄲、陶(定陶)、溫(河南溫縣)、軹(濟源)、臨淄、吳(蘇州)、壽春(安徽壽縣)、宛(南陽)、番禺、雍(陜西鳳翔)、櫟陽、烏氏(甘肅平涼市西北),以及新發展起來的城市如麗邑、云陽、臨邛等,都有商業市場;秦代的法律《秦律》中還有專門針對市場的規定即《關市律》,記載了關于管理關卡及市場交易等的法律規定。有商業,必然有專門從事商業貿易的人(秦代的商業分官營商業和民營商業,專門從事商業貿易的人分經官營商人和民營商人),毫無疑問也必然有商人的流動,包括商人邊疆地區的跨境流動,如前述《秦律》體系中的《法律問答》關于來自他國的民營商人的記載和邊境實行憑證出入境制度的設計便是佐證。
另外一種是流民的流動。早在先秦時代和春秋戰國時期,不少百姓就因政局動蕩和戰爭等原因而自發遷徙流動。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沒有取得政府的許可,百姓不能隨意遷徙流動,但秦代仍存在流民問題,如六國中仍不愿意與秦合作的一部分世家貴族,為了躲避秦朝的征召,他們踏上的逃亡的路途。躲避“連坐法”的途徑包括:有犯罪的人的同一宗族的族人要逃亡;有的不堪忍受“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的殘暴統治而逃亡;還有的因為土地被兼并后,失去土地而逃亡。這些流民,主要流向邊遠的地區,如山區,甚至邊疆地區。如秦始皇征發刑徒修長城時,便有不少刑徒逃亡塞北,成為匈奴的子民,或者嘯聚山林,成為大盜。
二、秦代邊疆地區人口跨境流動的特征
秦代邊疆地區人口跨境流動總體上以官方主導為主、民間人口流動為輔,呈現出人口跨境流動集體性、強制性以及政策的相對穩定性等具體特點。
(一)一定規模的集體性
秦代,個體單獨的遷徙流動很少,大部分是規模性的集體遷徙流動。如前述,公元前238年,平定長信候毐叛亂后,“奪爵遷蜀四千余家”[3]227。公元前222 年秦滅趙后,將趙王遷于漢中防陵。秦破楚后,遷徙嚴王之族于嚴道。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將全國12 萬戶富豪遷至咸陽。公元前219年,“徙黔首三萬戶瑯琊臺下”(《史記·秦始皇本紀》)。公元前214年,擊敗匈奴,收復河套南北廣大地區,在陽山、陰山、榆中(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區)沿黃河一帶,設置九原郡,并設44縣后,“徙謫實之”。公元前212年,又“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云陽”。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又遷三萬戶到北河、榆中墾殖。公元前210 年,徙大越民置余杭、烏程等地,以充實邊防。征服“百越”后,遷徙了55萬人戌守五嶺,與越族雜居。
(二)鮮明的政府強制性
因為不允許自由遷徙流動,但是形勢和現實卻需要通過遷徙人口,達到統治階級所期盼、所需要的目的,又必須有人口的流動。為此,只能由官府來組織實施統一的人口遷徙流動。秦代邊疆地區的人口跨境流動,以強制性手段為主,輔之以經濟手段。對犯罪的人流放到邊疆地區,以及將六國舊勢力、豪強從內地遷徙到邊疆地區,或從邊疆地區遷移到關內和首都,都是使用刑罰或行政命令,甚至暴力等強制性手段來推行,以確保統治者階級意圖的實現。但是也采用經濟手段等柔性手段來推動人口跨境流動。秦代在推動邊疆地區人口跨境流動上重視運用經濟手段。早在尚未統一中國的秦國時期(即春秋戰國時期),秦國就用經濟手段開展了我國有歷史記錄的第一次有組織、有計劃的人口遷移。秦國頒布《徠民法》,對移民工作做得好的官員,進行獎勵,對新移民墾荒者五年免賦稅,其子女享受秦民同樣的待遇[7]25。秦代統一中國后,政府采取定期“復”(即免除徭役)和賜爵的辦法,獎勵農業生產,鼓勵內地人口到邊疆地區開墾種田,發展農業經濟,如公元前219 年,遷黔首3 萬戶到瑯琊臺(今山東膠南),“復十二歲”。公元前212 年,又遷5 萬戶到云陽(今陜西淳化),“復不事十歲”。公元前211 年,遷3 萬戶到北河、榆中(今內蒙古河套與陜西交界處),皆拜爵一級,使河套地區成為新墾的農業區[4]110。
(三)移民政策的相對穩定性
移民邊疆地區是秦代的一貫政策。秦代的徙民實邊政策具有持續性、穩定性。早在戰國時期的秦國,就有遷徙人口到邊疆的做法。如在商鞅變法時,有過將內地人口遷往邊疆地區的做法,即把那些妄議新法的“亂化之民”,“盡遷之于邊城”。同時,秦國每攻克一個地方,就采取移民的方式以鞏固占領區。《華陽國·蜀國》載秦滅蜀后,秦惠文王于后元十一年(前314年)“移秦民萬家實之”。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80年),秦國擊敗楚國,“赦罪人遷之南陽”⑩。秦王嬴政即位后,延續了將不軌之民遷之巴蜀、南陽等邊地的做法。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根據形勢的需要,持續實施了大規模的移民。在其執政的十余年內,前后進行了八次大規模的移民,共遷徙居民約106 萬戶,達500 多萬人口[2]257-258。
三、影響秦代邊疆地區人口跨境流動的因素分析
人口跨境流動狀況受一個國家的治理理念、政治形勢等多種因素影響。秦代的邊疆地區人口跨境流動狀況就與秦王朝統治者的治理思想以及政治形勢、邊境形勢、政策法令、交通條件等因素密切相關。
(一)與統治者的思想認識有關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秦王朝所實施的邊疆地區人口跨境流動政策、措施、手段源于統治者的治國理政、治理邊疆的思想。秦王朝的統治者采納丞相李斯的“中央集權”思想,指導治國理政與邊疆的治理。秦始皇統一全國后,實行什么樣的政治體制,朝廷中曾有不同的主張,有的認為應該“師古”實行分封制。而當時的重臣、丞相李斯反對分封制,認為分封制會削弱王朝中央的權力,主張實行郡縣制,“認為郡縣制能夠保證天下沒有可以和中央權力相抗衡的政治勢力,從而使中央政權穩定,社會秩序井然”[8]73。秦始皇采納李斯建議,加強中央集權,在包括邊疆地區在內的全國范圍,推行郡縣制,建立中央集權的管理體制。一方面,在邊疆地區設置政府機構,任命官吏,加強對邊疆地區的政治管控,如:在北方邊疆,派蒙恬率三十萬大軍收復河套南北的廣大地區后,設置九原郡;在南部和東南部邊疆地區(即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及兩廣一帶),秦滅楚,統一了浙江和福建一帶后,設立了會稽郡和閩中郡;統一嶺南地區,設置南海、桂林、象郡。在西南邊疆地區(當時的“西南夷”即今云南、貴州和四川西南部)修筑了“五尺道”,并委派官吏去治理[4]112。“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3]236另一方面,為了加強對邊疆地區的控制,秦始皇從內地遷徙大量人口到邊疆地區戌邊,鞏固邊疆,開發邊疆。
(二)與秦代國內面臨的政治形勢有關
秦王朝是在消滅韓國、趙國、燕國、魏國、楚國、齊國等六國的基礎上而建立起來的。六國的主要軍事力量被摧毀之后,仍存在較大的舊貴族殘余勢力,蓄謀反抗。他們不甘心在秦的統治下茍且偷生,總想恢復昔日的權勢,伺機東山再起,比如,史書記載,張良原是韓國貴族后代,秦滅韓后,張良的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殺秦王,為韓報仇[3]2033-2034。六國舊貴族勢力的存在是對新生的秦代政權的潛在威脅。為了防止六國舊貴族勢力的復辟與動亂,秦代政權對六國舊勢力和豪強采取強制性遷移,或從內地遷移到邊疆地區或從全國各地遷移到首都附近集中管控,以消除動亂的隱患,維護中央對地方的政治的控制。
(三)與秦代周邊面臨的形勢有關
秦代疆域“東到大海,西到隴西,北到長城,南到象郡。”[4]112秦代的版圖面積大約為354.69平方公里,比西周的統治區(南至長江以南,西至今之甘肅,東北至今遼寧,東至今山東)范圍要大。但限于當時自然地理環境以及經濟、交通等條件,秦代居民的活動范圍主要集中在中原一帶的陸地區域。同樣,王朝政府的管理活動也在這一帶的陸地區域。面臨的威脅主要來自于北部邊疆地區,秦代時,匈奴是居住在中國北方蒙古高原一帶的游牧民族,其利用騎兵行動迅速的優點,經常襲擾中原,并乘秦、趙、燕各國互相戰爭之機,占領河套以及河套以南地區,對秦朝構成很大威脅。秦統一后,匈奴對秦王朝的威脅仍然很大。而邊疆地區,人口少,防衛力量明顯不足以防范和抵抗匈奴的騷擾。為了解除這一威脅,秦王朝首先運用軍事手段主動進攻,抗擊匈奴的侵擾,秦始皇于公元前215年,派蒙恬率領30萬大軍北伐匈奴,收復了河套南北的廣大地區。同時,采取移民實邊措施,維護邊疆地區的穩定,于公元前211年,又遷3萬戶到北河、榆中一帶墾殖,以充實邊防[4]112。
(四)與秦代的刑事政策即流放刑的設置有關
在我國古代,西周政權就設置了流放刑,此后為各朝代承襲沿用。流放刑是秦代時期八大類刑罰中的一個重要種類,包括遷刑與謫刑:“遷刑”適用于官吏與平民百姓;“謫刑”適用于犯罪的官吏,適用“遷刑與謫刑”時,家屬必須隨遷[5]43。秦代時期常適用流放刑,如公元前214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第,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戌。”?公元前210年,“又徒天下有罪吏民置海南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
(五)與秦代的交通條件有關
人口的流動與交通條件有密切聯系。交通條件落后、交通不便,會制約人口的流動。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為了加強對全國各地的控制,建立了以首都咸陽為中心的水陸交通網。陸路交通方面,通過修建“馳道”“直道”“新道”“五尺道”,形成了以咸陽為中心的交通系統,使中原地區與邊疆地區聯成一體:一是修建以兩條干線為主的“馳道”,一條由咸陽往東通向齊、燕海濱,一條由咸陽往南通向吳、楚之地;二是修建由咸陽向北穿過陜西北部,經內蒙古草原,至九原郡(今內蒙古包頭西南),全長1800里(約今700公里);三是修建湖南、江西、兩廣地區的“新道”,使新道與馳道相連接,從而貫通中原與嶺南的聯系;四是在今宜賓與云南曲靖的崇山峻嶺之間開鑿一條“五尺道”,溝通西南邊境與關中地區。水路交通方面,疏浚雍塞的川防,暢通江河水道,船只可通航黃河、長江、岷江、湘江、錢塘、漓江等河道,同時通過海上航道溝通南北水系。還在甘肅開鑿秦渠,在咸陽至南山開鑿漆渠,在廣西興安修建靈渠,通過連接湘江和漓江,聯通了長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迅速改變了古代交通落后的狀態。全國水陸交通網的形成,為人口的跨境流動提供了條件。正是因為有了發達的全國水陸交通網,秦始皇得以部署實施八次大規模的移民計劃,民間的跨境流動也才得以實現。
四、我國秦代邊疆地區人口跨境流動的積極影響
秦代的人口跨境流動,主要的是內地往邊疆地區的流動和邊疆地區往內地流動。無論是內地往邊疆地區的流動或邊疆地區往內地流動,都對秦代的經濟社會帶來積極的影響與作用。
(一)有利于鞏固政權,維護邊疆地區安全與穩定
秦代,疆土拓展到哪里,政權組織就建設到那里。在邊疆地區設置政權機構,任命官員,將邊疆地區納入中央政府管轄范圍。在南部邊疆的“百越”?地區,統一浙江和福建一帶的越族后,設立了會稽郡和閩中郡。統一了嶺南地區后,分別設置了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在西南邊疆地區(當時的“西南夷”即今云南、貴州和四川西南部)修筑了“五尺道”,并委派官吏去治理[4]112。在北方邊疆地區,收復河套南北廣大地區,設置郡縣,加強對這一地區的統治。
在邊疆地區設立政權機構,任命地方官員,表明政治上統治關系的確立,這為人口的跨境流動提供了保障。人口的跨境流動又促進國家政權的鞏固和邊疆地區的社會穩定。將邊疆地區的豪強遷徙到內地,“徙天下富豪于咸陽十二萬戶”將邊疆豪強置于國家的直接控制之下,不僅有利于消除動亂隱患,維護政治上的穩定,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國家對經濟的控制,有利于國家政治經濟的穩定。而從內地向邊疆地區移民意義有三。一是有利于實行有效的政治統治。移民邊疆地區,擴大了邊疆地區政權的群眾基礎,有利于秦王朝地方政權,推行統一的政制(郡縣制),統一的法律制度,實行有效的政治統治。秦代,在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地區設置的道,由道薔夫主管,執行中央統一的法律、田令。《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書》載,南郡守騰向縣、道薔夫分布命令,要求不論縣或道都要執行中央統一的法律、田令等,不得奸私。二是充實了邊疆地區的軍事防衛力量。移民按照軍隊組織編制,平時開墾種田,戰時就作為士兵,可以防范和抵抗外敵的騷擾或侵略。三是壯大了邊疆地區的經濟實力。移民在邊疆地區開墾種地,發展邊疆地區的農業,帶動其他經濟如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壯大邊疆地區的經濟實力。
(二)推動邊疆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
一方面,均衡全國人口分布,為邊疆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人力支持。黃河流域、長江流域是發祥地,人口比較集中,耕地面積比較少,文化,農業比較發達。而邊疆地區如百越、嶺南一帶還是處女地,有的還處于刀耕火種的時代,而且剛剛被征服,人口稀少,荒地多。從中原地區遷移50萬人到嶺南,一方面減少了中原地區的人口壓力,另一方面增加了嶺南地區的人口,邊疆地區人口密度明顯上升,人口分布由河谷盆地向山地、由海拔較低地區向較高地區延伸,為邊疆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人力支持。
另一方面,移民邊疆地區,將中原地區的農耕經濟向邊疆地區擴展,助推以農業為主體的國民經濟體系的初步形成。秦代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制度國家,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作為經濟基礎,把發展農業當作“立國之本”,推行重農抑商政策,優先發展農業生產,限制其他經濟部門的增長。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即宣揚“上農除末”政策,陸續向北部、西北游牧區南方山區移民,將中原地區的農耕經濟向四周擴展,形成了包括黃河流域,涇、渭、汾河流域,長江流域等北起長城,南到嶺南的統一農業經濟區,初步形成了封建社會以農業為主體的國民經濟體系[2]247。
人口跨境流動直接促進邊疆地區農業的發展。在秦代,中原地區農業生產相當發達,而邊疆地區交通閉塞、開發較晚、人丁稀疏、經濟落后。如在嶺南等南方有些地區還處在火耕水耨的落后階段,甚至還有“食肉衣皮,不見鹽谷”的原始部落?。移民遷入后,邊疆地區勞動人口數量增加,為耕地開墾提供了人力基礎,加上隨之而來的較為先進的耕作技術和生產工具,推動了邊疆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變遷。移民進入邊疆地區后,辛勤耕作,開墾荒地,使邊疆地區的耕地面積大幅增加;耕地面積的增加促使糧食作物的發展。如前211年,遷3萬戶到北河、榆中(今內蒙古河套與陜西交界處),使河套地區成為新墾的農業區。秦代通過移民邊疆地區開墾,種田,使耕地面積隨著疆域的擴大而不斷擴大,糧食產量也有很大提高,以致中央至地方乃至邊疆地區的糧倉盈滿,如巴蜀地區,經過不斷移民開墾,成為秦代的一個重要產糧區,甚至直到秦漢相爭時,這里糧食仍然充足,“漢祖自漢中出三秦伐楚,蕭何發蜀,漢米萬船,而給軍糧”?。《史記·高祖本紀》也記載,因漢初饑荒嚴重,高祖遂令民就食蜀漢[2]259。
人口跨境流動,改變了流入地的勞動人口結構、耕作方式和種植結構,帶動了邊疆地區手工業的發展,加速了邊疆地區的綜合開發。移民們依托邊疆地區豐富的礦產、野生動植物資源等自然資源,有的因地制宜,種植桑麻等經濟作物,有的從事畜牧業、冶鐵業、青銅業、制陶業、漆器業、紡織業、制革業、煮鹽業等。《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秦代把一批六國的冶鐵富豪遷至巴蜀、南陽等地后,這些人利用自己的資金和技術,募民冶鐵,“大鼓鑄,規陂地,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商業也開始活躍起來。在邊疆地區,出現了一批兼具政治功能和商業功能的城市。如蜀郡成都,“市張列肆,與咸陽同制”,西北的烏氏(今甘肅平涼市西北)、嶺南的番禺(今廣東廣州),商業市場相當發達[2]260。
(三)推動民族融合,促進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形成
民族融合通常通過人口遷徙、經濟文化友好交往、實行行政管轄和民族政策,甚至聯合斗爭等形式來實現。秦代政府與邊疆地區建立并保持政治、經濟、文化的聯系,有利于民族融合。如前所述,秦代,疆土拓展到哪里,政權組織就建設到那里,秦代王朝政府與邊疆地區建立的統治關系為人口的跨境流動提供了保障,也為內地與邊疆地區的經濟文化交往創造了條件。
秦代,內地與邊疆地區建立并保持經濟文化往來。政府在中原地區與邊疆地區推行統一的土地政策,“使黔首自實田”,統一貨幣與度量衡,保持經濟措施的一致性。民間的商人跨境流動,加強中原地區與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交往,也推動民族間的融合。
而向邊疆地區移民,各民族遷徙雜居,有利于民族融合。秦代持續8次規模性的移民以及流民跨境流動,將中原華夏族的人民遷徙到北方游牧民族地區和嶺南地區,與當地土著居民如越族人雜居,為華夏民族與邊疆少數民族的融合創造了條件,加速了華夏族于少數民族的融合。同時,向邊疆地區移民也有利于密切邊疆與內地的聯系。遷徙人口受中原文化影響“根”的意識很強,無論遷徙到哪里,始終與祖籍地緊密相連。這種心理認同,也有利于國家統一、民族融合發展。
[注釋]:
①《禮記·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②秦律設有笞刑、勞役刑、流放刑、肉刑、死刑、恥辱刑、經濟刑、株連刑等八類刑罰。
③出自《史記·秦本紀》,轉引自:https://www.gswen.cn/bookview/15320.html,查閱日期:2021-03-20。
④出自《史記·秦始皇本紀》,轉引自https://www.gswen.cn/bookview/15321.html,查閱時間:2021-03-20。
⑤出自《越絕書》卷八,轉引自https://so.gushiwen.org/guwen/bookv_46653FD803893E4F8F41AEC5EC64F551.aspx,查閱時間:2021-03-11。
⑥出自《史記·秦始皇本紀》,轉引自https://www.gswen.cn/bookview/15321.html,查閱時間:2021-04-20。
⑦出自《秦簡·游士律》:“游士在,亡符,居縣貲一甲;卒歲,責之。”,轉引自孫繼蘭的《古時“游學”:一旦遠游學,如舟涉江湖》,載于http://k.sina.com.cn/article_2011075080_77de920802000i9em.html,查閱時間:2021-04-22。
⑧出自《資治通鑒·周紀四》,轉引自https://www.gswen.cn/bookview/15449.html,查閱時間:2021-05-20。
⑨出自《華陽國志·蜀志》,轉引自:https://so.gushiwen.org/guwen/bookv_46653FD803893E4FB3CBF084E0810116.aspx,查閱時間:2021-04-25。
⑩出自《史記·秦本紀》,轉引自:https://www.gswen.cn/bookview/15320.html,查閱時間:2021-04-25]。
?出自《史記·秦始皇本紀》,轉引自:https://www.gswen.cn/bookview/15321.html,查閱時間:2021-05-20。
?出自《越絕書》卷八,轉引自https://so.gushiwen.org/guwen/bookv_46653FD803893E4F8F41AEC5EC64F551.aspx,查閱時間:2021-05-21。
?“百越”是生活在我國東南沿海地區以及南部的古老民族,包括:居住在今浙江境內和江西東部的東甌;居住在今福建境內的閩越;居住在今廣東和廣西東部、湖南南部的南越;居住在今廣西西部、南部和云南東南部的雒越。
?出自《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轉引自https://so.gushiwen.cn/guwen/bookv_46653FD803893E4FCE8E499977BE4212.aspx,查閱時間:2021-05-21。
?出自《華陽國志·蜀志》,轉引自https://so.gushiwen.org/guwen/bookv_46653FD803893E4FB3CBF084E0810116.aspx,查閱時間:2021-05-21。
?出自《史記·貨殖列傳》,轉引自https://www.gswen.cn/bookview/15444.html,查閱時間:2021-05-23。